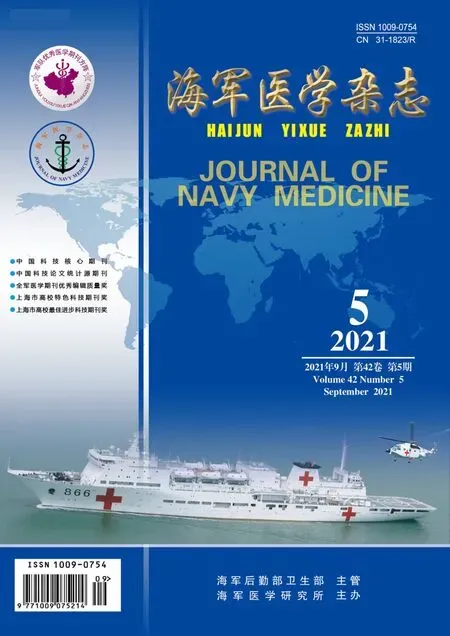阿帕替尼聯(lián)合PD-1抑制劑治療非小細胞肺癌一例
蔣麗媛,盧晶,崔志華,趙磬,溫省初
隨著環(huán)境及生活方式的改變,肺癌患者越來越多,其發(fā)病率和死亡率均居惡性腫瘤第1位。多數肺癌患者發(fā)現(xiàn)時已為晚期,已經沒有手術的必要,內科治療成為主要治療手段。驅動基因陰性的晚期非小細胞肺癌(NSCLC)以化療、免疫治療、抗血管生成治療為主要治療手段。無論是一線治療還是維持治療,臨床試驗均證實在化療、抗血管生成治療的基礎上聯(lián)合免疫治療均可使患者受益。現(xiàn)將保定市第一醫(yī)院腫瘤科收治的1例一線應用阿帕替尼聯(lián)合程序性死亡蛋白-1(PD-1)抑制劑(卡瑞利珠單抗)治療患者報道如下。
1 病案摘要
患者男性,80歲。主因右肺癌3個月,于2020年7月1日入院。診斷:右肺上葉腺鱗癌IV期 右手環(huán)指轉移。患者緣于2020年2月發(fā)現(xiàn)右手環(huán)指腫物,進行性增大。活檢病理提示惡性,建議進一步查肺。免疫組化:CK(+++),CK7(+++),CK20(-),TTF1(-),PSA(-),Vim(-),S-100(-),HMB45(-),Ki67(+,40%),見圖1。行肺CT提示右肺上葉尖段可見團塊狀異常密度影,大小約為40.8 mm×46.5 mm×42.5 mm(前后×上下×左右),可見分葉、毛刺及胸膜牽拉,邊界不清。患者自行口服吉非替尼4個月,療效評價為病變進展(PD)。腫瘤增大為70.0 mm×68.0 mm×52.2 mm。患者就診于中國醫(yī)學科學院腫瘤醫(yī)院行進一步治療,會診病理切片提示(右手環(huán)指):纖維結組織中見分化差的惡性腫瘤浸潤,結合免疫組化染色及分子病理檢測結果,形態(tài)支持分化差的癌,不能完全排除腺鱗癌可能。免疫組化結果顯示: AEI/AE3(+++),CK19(+++),P63(灶+),P40(+),CD9(+),TF-1(-),Napsina(-),PAX8(-),CDX-2(-),TG(-),GATA3(-),CD34(-),Calponin(-),Desmin(-),Bcl-2(-)。之后患者就診于保定市第一醫(yī)院腫瘤科,于金域醫(yī)學檢測公司行基因檢測結果提示未見敏感基因突變,而PD-L1表達TC 60%,見圖2,TMB 6.4 mutations/MB(參考值5.4 mutations/MB),MSI-L、MMR基因未檢出變異。于2020年7月7日開始給予阿帕替尼250 mg,1次/d,聯(lián)合卡瑞利珠單抗200 mg/次,1次/2周治療,6周期后復查腫瘤縮小至14 mm×13 mm×21 mm,腫塊內空洞形成。療效評價部分緩解(PR),見圖3。繼續(xù)目前治療。期間患者出現(xiàn)因高血壓170/99 mmHg、蛋白尿(++)。給予纈沙坦膠囊(80 mg/d)、硝苯地平緩釋片(20 mg,2次/d)降壓治療,同時給予金水寶膠囊(3粒/次,3次/d)治療,后患者血壓、蛋白尿大致維持正常。此患者繼續(xù)上述方案治療中,將繼續(xù)隨訪。

圖1 右手環(huán)指腫物病理切片(HE 10×10)

圖2 右手環(huán)指腫物DD-LI表達(IHC 4×10)

圖3 治療前后患者胸部CT對比
2 討論
腫瘤的發(fā)生發(fā)展離不開新生血管及血液供應,其中一個重要機制就是血管內皮生長因子(VEGF)的參與。在低氧狀態(tài)下,VEGF由腫瘤細胞廣泛分泌并與內皮細胞上的VEGF受體(VEGFR) 結合,促進新血管生成[1]。抑制VEGF與VEGFR的結合,可以使現(xiàn)有的腫瘤血管體系正常化、抑制新的病理血管生成及抵抗血管的通透性,從而抑制腫瘤生長轉移[2]。目前的抗血管生成藥物包括貝伐珠單抗、重組人血管內皮抑制素、雷莫蘆單抗及阿帕替尼等。此患者應用的抗血管生成藥物阿帕替尼作為國產原研的口服小分子抗血管生成靶向藥物,通過高度選擇性競爭細胞VEGFR-2的ATP結合位點,阻斷下游信號轉導,從而抑制腫瘤組織血管生成發(fā)揮抗腫瘤作用[3]。劉雨桃等[4]研究阿帕替尼單藥用于二線及二線以上治療晚期非小細胞肺癌(NSCLC)的療效和安全性,結果顯示疾病控制率(DCR)為88.0%。無進展生存期(PFS)為6.0個月,阿帕替尼治療時機是晚期NSCLC患者PFS的獨立影響因素。其療效確切,安全性較好。盡早應用阿帕替尼可延長患者的PFS,改善患者的生活質量。為阿帕替尼在非小細胞肺癌中的應用提供臨床及理論依據。
免疫逃逸是導致腫瘤發(fā)生發(fā)展的重要因素,在多種腫瘤中發(fā)現(xiàn)PD-1/PD-L1信號通路的高表達[5]。活化T細胞上的PD-1與腫瘤細胞上的程序性死亡受體配體1(PD-L1)結合后可以抑制T細胞活化,導致腫瘤細胞免疫逃逸促進腫瘤發(fā)生發(fā)展。基于理論基礎,此患者腫瘤組織中PD-L1高表達(60%),PD-1抑制劑卡瑞利珠單抗作用于T細胞表面的PD-1分子,通過阻斷PD-1與PD-L1相結合,阻斷負向調控信號,使T細胞重新活性,恢復T細胞對腫瘤的免疫應答效應,識別腫瘤細胞并達到抗腫瘤作用[6]。KEYNOTE-024[7]研究中納入標準為PD-L1表達比例≥50%晚期驅動基因陰性NSCLC患者,pembrolizumab組與化療組相比,PFS分別為10.3個月和6.0個月,中位總生存期(mOS)分別為30個月和16.5個月,死亡風險較化療組降低40%。基于上述研究結果,F(xiàn)DA批準pembrolizumab用于PD-L1表達比例≥50%的局部晚期或轉移性NSCLC的一線治療。
晚期肺癌的治療以綜合治療為主,2種甚至3種治療方法的聯(lián)合可使患者從中受益。越來越多的研究證明,抗血管生成治療聯(lián)合免疫檢查點抑制成為晚期肺癌新的治療方案。
腫瘤微環(huán)境在抗血管生成及免疫治療抗腫瘤的效果起著重要作用。抗血管生成藥物可以抑制病理性血管生成,使異常的血管系統(tǒng)正常化,此種效果不僅可以改善組織的乏氧狀態(tài),還有可能逆轉腫瘤微環(huán)境的免疫抑制狀態(tài)。在胰腺癌和乳腺癌小鼠模型中發(fā)現(xiàn),抗 VEGFR2治療耐藥的腫瘤組織中PD-L1表達異常增高。另外有研究表明當EGFR2表達增加時PD-L1降低,這表明血管生成可能受到VEGF以外的細胞因子調節(jié),而這些細胞因子可能參與抗血管生成藥物的耐藥機制。上述研究從理論上為 ICI 和抗血管生成藥物聯(lián)用提供了可能性,存在2者協(xié)同作用及逆轉耐藥的可能。此類研究在肺癌、腎癌中研究較多[8]結合上述實驗研究及相關理論,此患者給予阿帕替尼抗血管生成治療聯(lián)合免疫治療,2者協(xié)同作用,使得腫瘤實性成分明顯減少,空洞形成,療效評價PR。出現(xiàn)3級不良反應,經對癥治療后好轉,無疾病進展時間持續(xù)延長。Rizvi等[9]選取一線鉑類化療4周期后6周內腫瘤無進展的NSCLC患者,研究納武利尤單抗聯(lián)合貝伐珠單抗對比納武利尤單抗維持治療的臨床效果。患者被隨機分入聯(lián)合治療組和單用納武利尤單抗治療組,直至疾病進展或發(fā)生不可耐受的毒副反應,結果顯示聯(lián)合治療組中位PFS 37.1周,鱗癌16.0周,非鱗癌21.4周。毒副反應增高30%,但未發(fā)生4級及以上毒副反應,且經對癥治療后好轉。驅動基因陰性的晚期NSCLC的一線標準治療為含鉑兩藥方案,在PD-L1表達水平≥50%的NSCLC患者中一線使用PD-1單藥治療,或是聯(lián)合化療,其療效性及安全性均有研究報道。IMpower150研究中[10]的亞組分析,聯(lián)合PD-1藥物治療中,PD-L1表達越高,患者獲益越明顯,PFS數值差距越明顯,使用一線化療+貝伐珠單抗+阿特珠單抗治療,后續(xù)使用貝伐珠單抗+阿特珠單抗雙藥維持治療,降低患者死亡風險,為此類患者提供了新的選擇。
綜上所述,對于老年、不能耐受化療、驅動基因陰性的晚期NSCLC的患者,抗血管生成藥物治療聯(lián)合免疫治療具有很好的增強協(xié)同作用,療效較好、毒副反應小、安全性良好,可能成為使此類患者具有生存優(yōu)勢的治療方案。但對其相關機制的了解尚不成熟,藥物種類、用藥時機、最佳藥物劑量及受益人群如何選擇,需要更多深入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