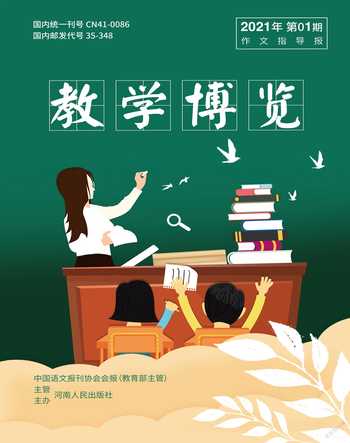高職院校“計算機應用基礎”課程教學改革研究
王晶
【摘要】隨著我國互聯網、大數據的不斷發展,信息時代已經到來,這就意味著對于我國大學生來說有了新要求。在學習計算機課程的過程中,學生不僅要深刻了解計算機理論知識,也要有熟練的上機操作技能。本文主要針對高職院校計算機課程的教學現狀,深入分析其中的問題,并結合現如今社會發展的趨勢,改變落后的教學觀念,提出新觀點、新觀念,深入探討分析其改革措施。
關鍵詞:計算機應用基礎;教學改革;高職院校
近年來,隨著大數據技術的不斷發展進步,其對社會發展的推動作用越來越重要。在高職院校的計算機基礎應用教學中引入大數據及其相關技術,不僅是未來計算機教學的趨勢,更是符合當今計算機應用實踐所需的重要改變。應用大數據能有效促進高職院校的計算機教學改革、探明高職院校計算機教學發展方向。計算機應用基礎課程計算機的教學中是一門入門課程,只有對計算機應用的基礎知識有了深刻的了解,才能加深對計算機知識和技能的掌握。因此,開設高水平的計算機應用基礎課程十分重要。然而,大數據的時代對計算機應用基礎課程提出了新的要求,需要改進和更新,以保證教育質量。尤其是在教學領域,大數據技術不僅可以給教師帶來極大的便利,同時還可以為學生的教學提供新的思路。文章深刻分析了大數據在高職院校計算機應用基礎教學改革中的重要性,從傳統的教育形式仍舊盛行、大數據的積極作用尚未被充分認識、所支持的人才難以滿足時代變化的要求等方面入手,探究了大數據背景下高職院校計算機應用基礎教學改革路徑。
1“計算機應用基礎”課程教學現狀及存在的問題
1.1課程標準與專業學科特點匹配度低
“計算機應用基礎”課程作為高職院校所有專業學生學習計算機應用的一門必修課程,旨在培養學生的自學能力和獲取計算機新知識、新技術的能力,使學生具有使用計算機工具進行文字處理、數據處理、信息獲取的能力,培養和提高學生的計算機文化素質,同時利用信息技術輔助本專業的學習。但是,大多數高職院校對所有專業采取統一課程標準開展教學工作,沒有在教學內容和教學要求上進行專業區分,完全忽視了專業學科的特點,導致很多學生學習吃力進而厭學情緒高漲,特別是非計算機專業的學生。
1.2傳統教學模式減弱學生自主學習能力
“計算機應用基礎”是一門知識、技能和應用相結合的課程,注重培養學生的實踐能力,使學生在操作過程中學習知識,在學習知識過程中體驗知識。但在實際教學過程中,該課程往往采用以計算機知識結構為主線、教師為中心的傳統教學模式,導致學生只停留在能聽懂教師授課內容、完成習題和作業的層面,不能良好地將所學知識結合實際需要,解決日常生活中遇到的一些問題。這違背了課程的教學標準和教學要求,無法幫助學生真正學習到計算機技能、解決實際問題,無法培養和提高學生的計算機文化素質,不利于學生畢業后快速適應崗位。此外,教育的地域性差異使得新生的計算機應用水平參差不齊,這勢必會導致學生對計算機基礎知識的掌握差異變大,給課程的教學組織和實施帶來困難。再者,課程面臨有限課時的挑戰,從大多數院校課程設置的實際情況來看,“計算機應用基礎”課程一般會在大一第一學期設置,由于新生入學報到時間較晚,再加上入學軍訓,課時嚴重不足,課程教學質量無法保證。
1.3課程內容與崗位需求存在一定斷層
當前,企事業單位對高校畢業生的計算機水平要求越來越高,實際就業的崗位需求往往高于學校教學內容。按照當前職業教育“服務為宗旨,就業為導向”的教育方針,“計算機應用基礎”課程的內容應貫徹教育必須服務于社會發展和經濟建設的方針,滿足用人單位的實際技能需求。因此,應從崗位實際需求出發,結合崗位能力要求,以提高學生計算機操作能力和專業辦公能力為培養目標,不斷調整、完善和優化課程的教學內容和覆蓋范圍。但在實際教學中,往往存在課程內容偏舊、實操項目應用度不高以及綜合操作占比偏少等問題,這樣無法更好地培養學生的實操能力和綜合運用能力。
1.4單一的考核方式缺乏合理性和科學性
課程考核是檢測學生對知識掌握以及應用情況的一種重要手段,同時也是教學過程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環節。“計算機應用基礎”課程一般由理論知識和實踐操作兩部分構成,因此,大多數院校的課程考核方式也采取理論考試和上機操作組合模式。但這種“一刀切”的考核方式忽略了學生的個體差異,對于有計算機基礎的學生而言過于簡單,對于進校前未接受計算機方面知識學習的學生而言會比較吃力,不利于課程的教學。同時這種“終結性”考核的期末試卷往往源自歷年題庫系統,一份試卷內含的考試要點、題型及題量等是有限的,不可能包羅萬象,因此,“終結性”考核只能考察學生對部分知識點及其應用的情況。再者,這樣“固定”的考試模式還會導致學生不注重平時學習和練習,常常采取“臨陣磨槍”的方式應付期末考試,長此以往,學生會逐步失去對課程學習的積極性,只會一門心思地應付考試,助長學生不良習慣的形成。
2計算機課程教學中的問題
2.1計算機課程內容設計不科學
部分高職院校針對計算機課程認識不深刻,在講課過程中仍然比較注重理論性的知識。計算機老師采用以往灌輸式的教學方法,將課本中的知識面面俱到講授給學生,卻只停留在問題和知識的表面,每個問題都會涉及,但都缺乏深層意義。這就會導致學生每個知識都有了解,但都沒有深刻理解。結束課程后,許多同學不但沒有記住學過的知識,反而不知道學了什么。這不僅會降低學生的積極性,更不利于培養學生的實踐能力。
2.2計算機課程安排不合理
計算機應用基礎課程主要特點就是實踐性強,需要同學們有大量的上機時間來練習,才會使學過的理論知識得到鞏固。而目前許多高職院校在理論課程與實踐課程的安排上出現問題,安排大量需要老師講解的理論課程,實踐課程卻很少,讓同學們利用課余時間來自主練習,這樣非常不利于同學們對課計算機課程的學習。(1)同學們學到的許多理論知識得不到及時的練習,容易導致學生理解不透徹和出現遺忘的現象。(2)高職院校的學生一般主動性較差,對于老師提出課下練習的主張,也很難積極順從。因此,同學們的積極性和課堂氛圍都會隨之下降。
河南大學 466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