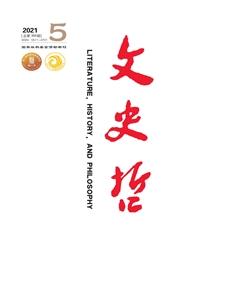西周學校的等級體系、升汰機制與學員出路

摘要:學校教育是人們實現向上流動的重要途徑,西周時期也不例外。當時的國家是由周王國和諸侯國構成的,二者的學校體系近似,都有國學和地方學校兩大系統。其中,國學里有大學和小學,地方學校包括鄉學和遂學。西周各類學校系統內部有級別不等的諸多學校,而且系統內部從下到上、系統之間從外到內都有流通的渠道。西周時期最低級別學校的入學條件并不苛刻,一般人員均可以入學學習。當時的每一級學校都有一定的考核機制,其中優秀者可以升入更高級別的學校學習,拙劣者則會被淘汰。學校教育為西周時期的貴族和平民入仕提供了門徑,也為不能入仕的學員帶來了境遇改善和生活便利。
關鍵詞:西周時期;學校;等級體系;升汰機制;學員出路
DOI:10.16346/j.cnki.371101/c.2021.05.04
無論處在怎樣的民族國家或歷史時期,才能和智慧都是人們實現向上流動的重要資本①,正如漢代學者何休所說“士以才能進取”②,而學校教育無疑是人們獲得才能和智慧,并最終實現向上流動的重要途徑③。中國歷史上的西周時期當然也不例外。因而研究西周時期的社會流動,不可避免地要考察當時的學校。
從社會流動的角度來研究西周時期的學校,關注的方面必然會與之前的同類研究有所不同。就筆者思考所及,它需要考察以下一些問題:(一)西周時期學校分屬哪些系統;(二)每個系統內部有哪些學校,各類學校的級別如何;(三)不同學校系統之間有無流通的渠道;(四)最低級別學校的入學條件如何;(五)學校怎樣考核學員,又如何選拔出優秀者;(六)低等級學校的學員怎樣升入高等級的學校;(七)學校怎樣淘汰和處理不合格的學員;(八)學校教育能否為學員的向上流動——如仕進——提供便利;(九)學校教育能為沒有仕進的學員帶來哪些境遇改善和生活便利。
在翻覽學術史的過程中,我們發現之前的學者對(一)(二)研究得較多。在這兩個問題上,學者們都注意到當時存在國學和鄉學,而國學又包括大學和小學。其中,有的學者對西周時期的國學、鄉學進行了總體式的介紹④;劉志云、王問學對西周國學和鄉學的狀況、學校教育的內容和特征進行了探討⑤;方愛龍對學校的名稱進行了考辨⑥;楊寬研究了西周時期的大學和小學,特別是大學的特
作者簡介:王進鋒,華東師范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上海 200241)。
基金項目:本文為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西周時期的社會流動研究》(批準號:18CZS007)的階段性成果。
①格爾哈特·倫斯基:《權力與特權:社會分層的理論》,關信平、陳宗顯、謝晉宇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8年,第360361頁。
②《春秋公羊傳注疏》卷一六,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第2287頁。
③李強:《社會分層十講》(第二版),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年,第6頁。
④毛禮銳、沈灌群主編:《中國教育通史》第一卷,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1985年,第7177頁。
⑤劉志云、王問學:《西周學校教育管見》,《貴州文史叢刊》1990年第4期。
⑥方愛龍:《先秦時代學校名稱辨考》,《杭州師范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1998年第1期。征楊寬:《西周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706722頁。;王暉對大學(辟雍)的形狀王暉:《西周“大學”“辟雍”考辨》,《寶雞文理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14年第5期。、大學小學所學內容的差別王暉:《庠序:商周武學堂考辨——兼論周代小學大學所學內容之別》,《中國史研究》2015年第3期。進行了探討。但是,這些學者都沒有討論遂學的問題;對國學和鄉學各自內部的等級、鄉學與國學之間的流動也沒有考察。另外,學者們對(三)(四)(五)(六)(七)(八)(九)探討得都比較少。
有鑒于此,筆者將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對這些問題做進一步探討。不妥之處,敬請方家教正。
一、西周時期周王國的國學及其等級
西周時期的國家由周王國和諸侯國構成,當時的學校就分別位于在周王國和諸侯國境內。西周時期周王國和諸侯國的學校位于各自的都城和都城以外的地區。位于都城地區的、由政府設置的學校被稱為“國學”。位于都城以外地區、由政府設置的學校,過去一般被稱為“鄉學”;然而,從下文可知,都城以外除了鄉地區以外,遂地區也設立了學校,這些學校就不好用“鄉學”來稱呼。所以,在此筆者將用“地方學校”來指稱西周時期都城以外的學校。同時,筆者在本文中還使用了“鄉學”和“遂學”的概念,“鄉學”是專門指代都城以外、鄉地區設立的學校;“遂學”指都城以外、遂地區設立的學校。
我們先來考察西周時期周王國國學的情況。西周時期周王國的國學分為大學和小學,如《尚書大傳·周傳》所言“古之帝王必立大學、小學”皮錫瑞:《尚書大傳疏證》卷六,北京:中華書局,2015年,第282頁。。大學又稱辟雍,如《禮記·王制》所謂“天子命之教,然后為學。……大學在郊,天子曰辟雍”《禮記正義》卷一二,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第1332頁。。《詩經·大雅·文王有聲》“鎬京辟雍”、《詩經·大雅·靈臺》“于樂辟雍”、《詩經·周頌·振鷺》“于彼西雍”《毛詩正義》卷一六、卷一九,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第527、524、594頁。,都說明西周時期已經建立了大學。西周青銅器銘文中也已經有了關于辟雍的記載,麥方尊銘文(《集成》6015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殷周金文集成》(修訂增補本),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第3704頁。下文簡稱《集成》,不另出注。,西周早期)中的“璧雍”即“辟雍”,也即大學。根據麥方尊銘文,它是位于都城宗周的。因為辟雍的形狀類似玉璧之狀,外圍是一個修建的圓形大池,中間是圓形的高臺王暉:《西周“大學”“辟雍”考辨》,《寶雞文理學院學報》2014年第5期。,所以,它有時又稱為“大池”(遹簋銘文,《集成》4207,西周中期)、“辟”(伯唐父鼎銘文,《近出》356劉雨、盧巖:《近出殷周金文集錄》,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第220頁。下文簡稱《近出》,不另出注。,西周中期)。
除了大學、辟雍,西周時期周王國的大學還有其他的種類和名稱。具體來說,有以下一些:
(一)成均。《周禮·春官·大司樂》記載:“大司樂掌成均之法。”鄭玄注:“董仲舒云:‘成均,五帝之學。成均之法者,其遺禮可法者。”《大戴禮記·保傅》王聘珍解詁:“太學,謂成周當代之學,曰辟雍,亦曰成均者也。”《周禮注疏》卷二二,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第787頁;王聘珍:《大戴禮記解詁》卷三,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第52頁。則大學可叫成均。
(二)東膠。《禮記·王制》:“周人養國老于東膠。”孫希旦謂“周之東膠,大學也”孫希旦:《禮記集解》卷一四,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第385頁。,大學可稱東膠。
(三)瞽宗,又稱西學。《周禮·春官·大司樂》:“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為樂祖,祭于瞽宗。”鄭玄注引鄭司農曰:“《明堂位》‘瞽宗,殷學也;泮宮,周學也,以此觀之,祭于學宮中。”《周禮注疏》卷二二,第787頁。可見大學又可稱瞽宗。《禮記·祭義》:“食三老、五更于大學,所以教諸侯之弟也。祀先賢于西學,所以教諸侯之德也。”孫希旦注:“大學,成均也。……西學,瞽宗也。”孫希旦:《禮記集解》卷四六,第1231頁。則瞽宗又稱西學。
(四)東序。《禮記·文王世子》:“凡學世子及學士,必時: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皆于東序。”孫希旦謂:“學,教也。學士,胄子及鄉所升之俊士也。……東序,夏后氏之學也。”孫希旦:《禮記集解》卷二○,第555頁。則當時有一類大學叫東序。
(五)上庠。《禮記·文王世子》:“春誦夏弦,大師詔之;瞽宗秋學《禮》,執《禮》者詔之;冬讀《書》,典《書》者詔之。《禮》在瞽宗,《書》在上庠。”孫希旦注:“瞽宗,殷學也。……上庠,有虞氏之學也。”孫希旦:《禮記集解》卷二○,第557頁。則有一類大學稱上庠。
(六)宣射、射廬、學宮。西周金文中的“宣射”(簋銘文,《集成》42964297,西周晚期;虢季子白盤銘文,《集成》10173,西周晚期)、“射廬”(匡卣銘文,《集成》5423,西周中期)、“學宮”(靜簋銘文,《集成》4273,西周中期)也是大學的別稱參見王暉:《西周“大學”“辟雍”考辨》,《寶雞文理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14年第5期。王暉:《庠序:商周武學堂考辨——兼論周代小學大學所學內容之別》,《中國史研究》2015年第3期。。
正因為西周時期設立不同種類和名稱的大學,所以《禮記·祭義》謂:“天子設四學,當入學而大子齒。”孔穎達疏:“‘天子設四學者,謂設四代之學。周學也,殷學也,夏學也,虞學也。”孫希旦注:“天子立四學,周制也。周立四代之學:虞庠在北,瞽宗在西,東序在東,而當代之學居中,南面,謂之成均。”見孫希旦:《禮記集解》卷四六,第1232頁。《易傳·太初》也謂:“天子旦入東學,晝入南學,暮入西學。”見《后漢書·祭祀志中》注引蔡邕《明堂論》,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第3179頁。
西周大學的不同種類和名稱,應當是根據各自的教育功能來區分的。《大戴禮記·保傅》記載:
及太子少長,知妃色,則入于小學,小者,所學之宮也。《學禮》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則親疏有序,如恩相及矣。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則長幼有差,如民不誣矣。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則圣智在位,而功不匱矣。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則貴賤有等,而下不逾矣。帝入太學,承師問道,退習而端于太傅,太傅罰其不則而達其不及,則德智長而理道得矣”。王聘珍:《大戴禮記解詁》卷三,第5152頁。
則在東學、南學、西學、北學、太學里學習之后,受教育者所達到的教育效果是不同的。
學員在西周大學的學習有一定的期限,而且學習期間可能是住在大學里的。西周中期的靜簋銘文記載:
唯六月初吉,王在京。丁卯,王令靜司射,學宮小子、眔服、眔小臣、眔夷仆學射。雩八月初吉庚寅,王以(與)吳、呂(剛),(佮)(豳)、師、邦君射于大池。靜學(教)無(尤)。王賜靜鞞(璲)。靜敢拜稽首,對揚天子丕顯休,用作文母外姞尊簋,子子孫孫其萬年永用。(《集成》4273)
“司射”是管理射箭的一切教學等事務;“學宮”即辟雍;小子,為貴族子弟在學者,不是《周禮》中的“小子”官;服,從事政事的人唐蘭:《西周青銅器銘文分代史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369頁。;小臣即在周王的朝廷任職的官員王進鋒:《臣、小臣與商周社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222226頁。;夷仆,官名馬承源主編:《商周青銅器銘文選》(三),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年,第111頁。;吳、呂剛即班簋銘文中的吳伯、呂伯;“豳、師”即指豳師和師,分別為豳、兩地軍隊的長官唐蘭:《西周青銅器銘文分代史征》,第369370頁。。邦君,畿內封君任偉:《西周金文與文獻中的“邦君”及相關問題》,《中原文物》1999年第4期。。丁卯與庚寅之間相差23日;根據靜簋銘文,丁卯在六月的初吉,那么即使按照加一個甲子的83日,按照八月有庚寅日算,也不可能在初吉。所以,銘文中的八月庚寅應該是次年的庚寅日馬承源主編:《商周青銅器銘文選》(三),第111頁。,如此說來兩個時間相隔了380多天。從銘文“靜教無尤”來看,吳、呂剛、豳師、師、邦君都是射學宮中的學員,而且屬于“小子、眔服、眔小臣、眔夷仆”。從這篇銘文可以看出,學宮中的學員吳、呂剛、豳師、師、邦君,從頭年的六月丁卯開始到次年的八月庚寅,大約380多天,一直都在學宮里由靜教射。依此來看,當時的學員在大學學習期間可能是住在大學里的。
西周大學學員的學習主要是通過教員的教學,同時觀摩和參與大學中舉行的各類禮儀活動也是他們學習的重要方式。在靜簋銘文中,大學學員是通過靜的教授來學習的。除此之外,大學里還會舉行各類禮儀活動,如“大禮”(麥方尊銘文,《集成》6015,西周早期)、冊命儀式(簋銘文,《集成》42964297,西周晚期)、獻俘禮(虢季子白盤銘文,《集成》10173,西周晚期)、禮(伯唐父鼎銘文,《近出》356,西周中期),學員可以通過觀摩這些禮儀活動來學習。學員也可以通過參與大學中的禮儀活動來學習,西周中期的遹簋銘文記載:
唯六月既生霸,穆穆王在京,呼漁于大池。王郷(饗)酒,遹御亡(無)遣。穆穆王親賜遹(爵)。遹拜首(手)稽首,敢對揚穆穆王休,用作文考父乙尊彝,其孫孫子子永寶。(《集成》4207)
大池,指辟雍的環水;“遹御亡(無)遣”,意為遹侍王漁而無災譴之咎馬承源主編:《商周青銅器銘文選》(三),第104105頁。。遹可能是大學里的學員。在遹簋銘文中,周王在大學里命令相關人員舉行捕魚的活動。在饗酒的環節,遹參與進來。因為表現無差(“無遣”),周王賞賜他爵位。遹是通過參與大學中的禮儀活動來學習的。
大學里的學員絕大多數都是沒有官職的,但是也有一些學員已經有了官職。如上文提及的靜簋銘文中的小子、服、小臣、夷仆,包括吳、呂剛、豳師、師、邦君,都是有了職位之后才在大學學習的。
除了大學,西周時期周王國也已經設立了小學,如《禮記·王制》記載“天子命之教,然后為學。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又如鄭玄注《禮記·王制》“六十養于國”所謂“國,國中小學”《禮記正義》卷一二、卷一三,第1332、1345頁。。西周金文中也有小學的記載,請看以下內容:
唯九月,王在宗周,令盂,王若曰:“盂……汝昧辰有大服,余唯即朕小學,汝勿蔽余乃辟一人”。(大盂鼎銘文,《集成》2837,西周早期)
唯十又一月,九月初吉丁亥,王在周,格于大室,即位。宰琱甥入佑師,王呼尹氏冊命師,王曰:“師,在昔先王小學,汝敏可使,既命汝更乃祖考司小輔。”(師簋銘文,《集成》4324,西周晚期)
可見,西周時期已經建立了小學。
西周大學的級別要高于小學。通常情況下,小學學習結束后優秀者才能進入大學學習,如以下史料所呈現的:
公卿之太子,大夫、元士嫡子,年十三,始入小學,見小節踐小義。年二十,入大學,見大節而踐大義。(《尚書大傳·周傳》皮錫瑞:《尚書大傳疏證》卷六,第282頁。)
古者年八歲而出就外舍,學小藝焉,履小節焉;束發而就大學,學大藝焉,履大節焉。(《大戴禮記·保傅》王聘珍:《大戴禮記解詁》卷三,第60頁。)
八歲毀齒,始有識知,入學學書計。七八十五,陰陽備,故十五成童志明,入大學,學經籍。(《白虎通義·辟雍》陳立:《白虎通疏證》卷六,北京:中華書局,1994年,第253頁。)
可見大學學習是在小學之后的,那么大學的級別應當高于小學。
二、西周時期周王國的地方學校及其等級體系
一般認為,西周時期周王國的統治區域,從內到外以“郊”為分界線,分為“國”和“野”兩大區域。其中“國”區域最中心的位置是王城,王城以內的地區稱“國中”;王城以外的區域稱“郊”或“四郊”。西周時期在王城以外、郊以內設立了“六鄉”;在郊以外、野以內設立了“六遂”楊寬:《西周史》,第421422頁。。“國中”就是都城地區,“六鄉”和“六遂”都屬于都城以外的地區。
西周時期地方學校的設置與當時的國野劃分密切相關,在鄉、遂內不同級別的基層居民組織都建立了學校。當時在郊地設立了六鄉,在野地設置了六遂《周禮·地官·敘官》“鄉老”鄭玄注:“王置六鄉……。六鄉地在遠郊之內,則居四同。鄭司農云:‘百里內為六鄉,外為六遂。”(《周禮注疏》卷九,第697頁)。每個鄉、每個遂內部又設有從小到大不同級別的基層居民組織,《周禮》記載:
五家為比,使之相保。五比為閭,使之相救。四閭為族,使之相葬。五族為黨,使之相教。五黨為州,使之相赒。五州為鄉,使之相賓。(《周禮·地官·司徒》)
遂人掌邦之野。以土地之圖經田野,造縣鄙形體之法。五家為鄰,五鄰為里,四里為酂,五酂為鄙,五鄙為縣,五縣為遂。(《周禮·地官·遂人》)《周禮注疏》卷一○、卷一五,第707、740頁。
可見,每個鄉內有比(5家)、閭(25家)、族(100家)、黨(500家)、州(2500家)、鄉(12500家)六級基層居民組織,每個遂內有鄰(5家)、里(25家)、酂(100家)、鄙(500家)、縣(2500家)、遂(12500家)六級基層居民組織。
西周時期在鄉內的有些級別的基層居民組織里建立了學校,這些級別組織所對應的學校情況如下:
(一)閭內建立了塾。《禮記·學記》謂“家有塾”,鄭玄注:“古者仕焉而已者,歸教于閭里,朝夕坐于門,門側之堂謂之塾。”孔穎達疏:“此明立學之所在。《周禮》百里之內,二十五家為閭,同共一巷,巷首有門,門邊有塾。謂民在家之時,朝夕出入,恒受教于塾,故云‘家有塾。”《禮記正義》卷三六,第1521頁。可見塾實際是設立在閭內的。
(二)黨內設立了學校,名稱不一,有時叫庠,有時叫序。《禮記·學記》謂“黨有庠”《禮記正義》卷三六,第1521頁。,可見黨內的學校叫庠。《周禮·地官·黨正》謂“黨正各掌其黨之政、令、教、治。……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周禮注疏》卷一二,第718頁。,此時黨內的學校又稱為序。
(三)州內建立了序。《周禮·地官·州長》謂“州長各掌其州之教、治、政、令之法。……春、秋以禮會民,而射于州序”,鄭玄注:“序,州、黨之學也。”《周禮注疏》卷一二,第717頁。
(四)鄉內的學校叫庠。《禮記·鄉飲酒義》謂“主人拜迎賓于庠門之外”,鄭玄注:“庠,鄉學也。州、黨曰序。”《禮記正義》卷六一,第1682頁。
可見,西周時期在鄉內的閭、黨、州、鄉這些級別的基層居民組織里都建立了學校,這些學校的名稱依次為:閭為塾;黨為庠或序;州為序;鄉為庠。西周時期在都城以外、鄉地區設立的這些學校被稱為“鄉學”。
既然鄉內設立了學校,那么西周時期在遂地區有沒有建立學校?有些學者認為沒有,如楊寬,他認為六遂的居民沒有受教育的權利楊寬:《西周史》,第431頁。;又如毛禮銳、沈灌群,他們認為西周時期的六遂“是不可能設學立教的,遂之學在歷史上恐屬烏有”毛禮銳、沈灌群主編:《中國教育通史》第一卷,第74頁。;再如喬衛平,他認為“遂民的身份其實就是賤于牛馬的奴隸,絕無受教育的權利”喬衛平:《略論西周的選士制度》,《人文雜志》1984年第3期。。然而,西周時期位于六遂之地的農民具備文化知識的事實可以輕易推翻這種判斷。《詩經·小雅》之《大田》《信南山》的作者應當都是西周時期的農民《詩序》謂《大田》“刺幽王也。言矜寡不能自存焉”,鄭玄箋:“幽王之時,政煩賦重,而不務農事,蟲災害谷,風雨不時,萬民饑饉,矜寡無所取活,故臣工思古以刺之。”(見《毛詩正義》卷一四,第476頁)《詩序》謂《信南山》“刺幽王也。不能修成王之業,疆理天下,以奉禹功,故君子思古焉”(見《毛詩正義》卷一三,第470頁),臣工、大臣應當選取了古時農民們吟唱的詩歌來諫刺幽王。所以,《大田》《信南山》的作者應當是西周時期的農民。,根據鄉、遂地區居民分布的差異鄉內居住的是“國人”,具有國家公民的性質,屬于當時的統治者;遂內居住的是“甿”“氓”或“野民”“野人”,是勞動者、被統治者,是農業生產的主要承擔著。見楊寬:《西周史》,第421431頁。,他們應當居住在遂地。然而他們能吟唱出如《大田》《信南山》般對稱押韻、語言優美的詩歌,可見這些農民作者都有一定的文化素養。他們的這種文化素養應當就來自遂地的學校教育。更重要的是,傳世文獻中有遂地設立學校的明確證據。《禮記·學記》記載:
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陳澔以為“術,當為州”(陳澔:《禮記集說》,南京:鳳凰出版社,2010年,第284頁)。按:術、州二字聲部較遠,不能通假,陳硬把“術”說成是“州”,有改字解經之嫌,不可信。
鄭玄注:“術,當為遂聲之誤也。……《周禮》五百家為黨,萬兩千五百家為遂。黨屬于鄉,遂在遠郊之外。”《禮記正義》卷三六,第1521頁。可見遂內建立了學校,而且它的名稱為序。
不僅如此,《禮記·學記》這段文字所蘊含的遂內學校的信息,還可以進一步地挖掘。這段文字比較奇怪,它前段所記的閭、黨都是鄉內的居民組織,但是后段并沒有相應地記鄉,而是直接跳到了遂;然而對于遂,它并沒有描述其他基層居民組織內的學校情況,理解起來非常困難。對于這種現象,清人孫希旦的解釋會讓我們豁然開朗,他說:
此于鄉但言“黨”,于遂但言“術”,略舉而互見之也。孫希旦:《禮記集解》卷三六,第958959頁。
即認為這段文字是一種互文的手法,《學記》為了行文的方便而做了相應的省略;實際情況應該是:鄉內與遂相對級別的居民組織有學校的設置,遂內與閭、黨、州相對的居民組織有學校的設置。他從而認為六鄉系統里的鄉和六遂系統里的里、鄙、縣都設置了學校。孫希旦的分析非常有道理,可以信從。如此看來,鄉里的閭、黨、州、鄉,遂內的里、鄙、縣、遂都設置了學校。遂內的這些學校可以被稱為“遂學”。
既然相對應級別的基層居民組織都設置了學校,那么鄉學和遂學里相對應級別上的學校的級別是否完全一致?在這個問題上,學者們有不同看法。北宋學者陳祥道認為“遂之學亦降鄉一等矣。降鄉一等,而謂之州長,其爵與遂大夫同,則遂之學其名與州序同可也”見孫希旦:《禮記集解》卷三六,第958頁。,即遂內各級基層居民組織里的學校,要比鄉內相對級別的學校低一等。孫希旦提出“六鄉之中,閭側有塾,州、黨有序,鄉有庠;則六遂之中,里側有塾,縣、鄙有序,遂有庠”孫希旦:《禮記集解》卷三六,第958頁。,則認為遂內各類學校與鄉內名稱、級別完全相同。在判斷他們的對錯之前,我們可以先看一下鄉內和遂內官員級別的情況:
鄉老,二鄉則公一人;鄉大夫,每鄉卿一人;州長,每州中大夫一人;黨正,每黨下大夫一人;族師,每族上士一人;閭胥,每閭中士一人;比長,五家下士一人。(《周禮·地官·司徒》)
遂大夫,每遂中大夫一人;縣正,每縣下大夫一人;鄙師,每鄙上士一人;酂長,每酂中士一人;里宰,每里下士一人;鄰長,五家則一人。《周禮注疏》卷九,第697、699頁。(《周禮·地官·司徒》)
可見,遂內的職官要低于同級的鄉內職官一級。與之相應,遂學應當也低于鄉學一級。以此來看,還是陳祥道的看法正確,即遂中的里、鄙、縣設立的學校級別分別低于閭、黨、州學校一級。
如此我們可以考察遂學里各級學校的名稱。因為鄉學里閭、黨、州、鄉級學校的名稱是清楚的,分別為塾、庠/序、序、庠,而遂中的里、鄙、縣設立的學校級別低于閭、黨、州學校一級,那么遂內鄙、縣、遂的學校名稱分別為塾、庠/序、序。這樣,遂內唯一不清楚名稱的是里一級的學校,其他文獻的記載為我們的認識提供了線索。何休在解詁《春秋公羊傳》宣公十五年“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什一行而頌聲作矣”時,解釋道“中里為校室,選其耆老有高德者名曰父老。……十月,事訖,父老教于校室”《春秋公羊傳注疏》卷一六,第2287頁。,可見里內的學校叫校室。
關于西周時期鄉學、遂學內部各種學校的級別,我們可以看《禮記·學記》“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一句孔穎達的疏證,其內容為:
于黨中立學,教閭中所升者也。……于遂中立學,教黨學所升者也。《禮記正義》卷三六,第1521頁。
我們在了解《禮記·學記》這段經文本身是互文之后,對于孔疏不能再死板地按照字面意思來理解,而應將孔疏也視為一種互文。實際的情況應該是:在鄉學層面,黨學招收閭學所升者,州學招收黨學所升者,鄉學招收州學所升者;在遂學層面,鄙學招收里學所升者,縣學招收鄙學所升者,遂學招收縣學所升者。以此看來,鄉、遂內不同級別的基層組織都設立了學校,它們的等級是逐級提高的。孫希旦說“庶民之子以家之塾,州、黨之序為小學,以鄉之庠為大學。……庶民之子,其小學有三,則其遞升于大學也遲”見孫希旦:《禮記集解》卷二八,第770頁。,也認為這些學校的等級是逐級提高的。
至此,我們可以將西周地方學校的體系、等級和名稱,表格圖示如下:
三、西周時期諸侯國的學校狀況及其體系
雖然關于西周時期其他諸侯國學校的材料不多,但仍然有一些零星的史料。我們在此考察其他諸侯國的學校狀況,從而更全面地認識西周時期的學校。
在學校體系方面,西周時期的諸侯國與周王國相仿,仍是存在國學和地方學校兩大體系,其中國學包括大學和小學;地方學校包括鄉學和遂學。如《禮記·王制》所謂:“五十養于鄉,六十養于國,七十養于學,達于諸侯。”鄭玄注:“天子、諸侯養老同也。國,國中小學。……學,大學也。”《禮記正義》卷一三,第1345頁。可見諸侯國模仿周王國的學校系統,建立了大學、小學和鄉學。
西周時期的諸侯國建立了大學,但是它們的名稱與周王國有差別,如《禮記·王制》所言“大學在郊,天子曰辟雍,諸侯曰頖宮”《禮記正義》卷一二,第1332頁。。
西周時期的魯國建立了大學。《禮記·學記》“國有學”,孔穎達疏:“《周禮》天子立四代學……尊魯,亦立四代學。”《禮記·明堂位》“米廩,有虞氏之庠也。序,夏后氏之序也。瞽宗,殷學也。頖宮,周學也”,孔穎達疏:“明魯得立四代之學。”《禮記正義》卷三六、卷三一,第1521、1491頁。可見,西周時期的魯國建立了大學,而且有米廩、序、瞽宗、頖宮四種。
當時的滕國也建立了大學。1989年1月,山東省滕州市姜屯鎮莊里西村磚瓦廠在莊里西遺址西側取土時,發現了一批青銅器,隨即被現場的民工哄搶一空。消息傳開后,滕州市博物館在公安部門的協助下收繳了被哄搶走的銅器,但沒有全部收回。經查,這批銅器皆出土于一座后來被命名為M7的墓葬。考古人員隨即對其進行了清理杜傳敏、張東峰、魏慎玉、潘曉慶:《1989年山東滕州莊里西西周墓發掘報告》,《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2012年第1期。。2008年,胡盈瑩、范季融刊布了他們收藏的一批青銅器,其中有三件器首陽齋、上海博物館、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首陽吉金——胡盈瑩、范季融藏中國古代青銅器》,上海: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72、74、83頁。下文簡稱《首陽吉金》,不另出注。。這三件器物的器主和祭祀對象與莊里西M7出土的器物完全相同。有理由相信,這三件器物最初就是從這座墓葬出土并流出的。經綜合統計,M7出土的銅器,目前已經確知的有141件,其中禮器12件,兵器11件,車馬器118件。其中多件銅器有銘文。另外,從出土器物比對來看,M7的時代應該是西周早期杜傳敏、張東峰、魏慎玉、潘曉慶:《1989年山東滕州莊里西西周墓發掘報告》,《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2012年第1期。。這是一批西周時期滕國的銅器。其中的簋銘文記載:
唯九月,者(諸)子具(俱)服,公廼令,在(辟),曰:“凡朕臣興、畮(賄)”。敢對公休,用作父癸寶尊彝。(《首陽吉金》26,西周早期)
銘文中的“辟”,即辟雍。《說文》謂“,墻也。從廣辟聲”,徐鍇《說文解字韻譜》“,廱”,《說文解字系傳》“()所謂廱”,《說文解字義證》謂“()通作辟”徐鍇:《說文解字系傳》,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第187頁;桂馥:《說文解字義證》,濟南:齊魯書社,1987年,第797頁。都可作為證據。這篇銘文說明西周時期滕國也建立了大學,它的名稱與周王國相同,叫辟雍。
齊國也建立了大學。齊國在戰國時期非常著名的大學——稷下學宮,根據學者的研究,在西周時期可能就已經建立了張富祥:《齊國的官學》,《山東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1999年第2期。。劉向《別錄》謂:“齊有稷門,城門也。談說之士期會于稷下也。”《史記》卷四六注引,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第1895頁。談說之士匯聚于此,應是齊人于稷門建立了學舍。
在國學方面,西周時期的諸侯國還建立了小學。《漢書·食貨志》記載西周時期的“諸侯歲貢少(小)學之異者于天子,學于大學”,《春秋公羊傳》宣公十五年何休解詁也謂“諸侯歲貢小學之秀者于天子,學于大學”《漢書》卷二四,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第1122頁;《春秋公羊傳注疏》卷一六,第2287頁。。諸侯能把優秀的學員進獻給周王,并學習于周王國的大學,前提應該是諸侯國里建立了小學。
西周時期的諸侯國也已經建立了地方學校,鄭國的“鄉學”可以作為例證。《左傳》襄公三十一年記載:
鄭人游于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謂子產曰:“毀鄉校,何如?”子產曰:“何為?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我聞忠善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豈不遽止?然猶防川,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不如吾聞而藥之也。”《春秋左傳正義》卷四○,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第20152016頁。
杜預注:“(鄉校)鄉之學校。”春秋時期鄭國“鄉校”應當是建立在鄭國鄉地區的學校。它們在春秋時期應該不是忽然出現的,可能最初在西周時期就已經設立了。
四、西周學校的入學條件、學業考核與升汰機制
西周時期最低級別學校的入學條件并不是很苛刻,一般的民眾都可以入學學習。根據上文的論述,西周學校體系里最低級別的學校,應該是鄉地區“閭”和遂地區“里”內設立的學校。根據《周禮》的記載,當時的一閭和一里都為25家,規模并不大,每家居民距離內部設置的學校應當都不遠。同時,鄭玄在注《禮記·學記》“家有塾”時,說道“古者仕焉而已者,歸教于閭里,朝夕坐于門,門側之堂謂之塾”《禮記正義》卷三六,第1521頁。,可見閭內學校的教員主要是當地出去的又退休回來的官員。何休在解詁《春秋公羊傳》宣公十五年“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什一行而頌聲作矣”時,解釋道“中里為校室,選其耆老有高德者名曰父老。……十月,事訖,父老教于校室”《春秋公羊傳注疏》卷一六,第2287頁。,則里內學校的教員是當地老而有德之人。閭、里內學校的教員都比較容易接納附近的鄰里學員。如此說來,閭、里內的居民進入學校學習都不困難,正因為此,程子才會說“古者家有塾,黨有庠,遂有序。故未嘗有不入學者”見孫希旦:《禮記集解》卷二八,第770771頁。。
西周時期不同級別的學校都會對學員進行考核。
西周國學體系中的大學對學員進行考核的方式是讓學員參與在大學中不定期舉行的禮儀活動。在靜簋銘文(《集成》4273,西周中期)中,周王讓大學里的學員吳、呂剛、豳師、師、邦君,參加射禮活動,目的就是為了檢驗他們的學習效果。在遹簋銘文(《集成》4207,西周中期)中,周王讓遹侍奉他的“饗酒”禮儀,目的也是檢驗他的學習效果。
西周鄉學也會對學員進行考核,《禮記·學記》記載:“比年入學,中年考校。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群,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強力而不反,謂之大成。”鄭玄注:“學者每歲來入也。中,猶間也。鄉遂大夫間歲則考學者之德行、道藝。……離經,斷句絕也。辨志,謂別其心意所趣鄉也。知類,知事義之比也。強立,臨事不惑也。不反,不違失師道。”《禮記正義》卷三六,第1521頁。當時的鄉學就是通過這樣一些項目來考核內部的學員。
西周鄉學一項重要的學習內容是射。在射這個項目中也有諸多的考核,如《周禮·地官·鄉大夫》所謂:
(鄉老、鄉大夫)退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眾庶: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興舞。此謂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周禮注疏》卷一二,第716717頁。
根據《禮記》記載,天子在射宮之中,考驗推薦上來的人,選出“容體比于禮,其節比于樂,而中多”的人參與祭祀,“數與于祭而君有慶;數不與于祭而君有讓。數有慶而益地;數有讓而削地”《禮記正義》卷六二,第1687頁。。
西周時期鄉學、遂學所在的不同級別的基層居民組織,都設立了相應的官員。他們有權考核內部的居民。那么各級學校里的學員作為其內部居民,無疑也會受到考核。如閭胥會對閭內的民眾“掌其比、觥、撻罰之事”,“比”即“較比之法”《周禮注疏》卷一二,第719頁。。遂大夫會對遂內的民眾“辨其可任者……。三歲大比,則帥其吏而興氓”,“興氓,舉民賢者、能者”《周禮注疏》卷一五,第742頁。。西周時期鄉學和遂學里學員受到考核之后,優秀者就會升入更高一級的學校或者任官,拙劣者則會被淘汰。
西周學校里也有升學機制。
周王國小學里的學員在學制結束后,優秀者可以升入大學,《春秋公羊傳》宣公十五年何休解詁“八歲者學小學,十五者學大學”《春秋公羊傳注疏》卷一六,第2287頁。,就是對這種歷程的很好說明。
西周地方學校里的學員,優秀者可以升入高一級的學校。《禮記·學記》“家有塾,黨有序,遂有庠”,孔穎達疏:“于黨中立學,教閭中所升者也。……于遂中立學,教黨學所升者也。”《禮記正義》卷三六,第1521頁。上文已經指出,這是一種略舉互見的手法,實際應是鄉、遂里高一級的學校可以招收從低一級學校里升上來的學員。《春秋公羊傳》何休解詁稱“十月事訖,父老教于校室。……其有秀者,移于鄉學,鄉學之秀者,移于庠”《春秋公羊傳注疏》卷一六,第2287頁。,進一步證明鄉學里這種升學機制的存在。
西周地方學校的優秀學員也有機會升入國學學習。當時每鄉的鄉大夫,會從自己治域里考評出有德行、道藝的“秀士”,推薦到司徒處,稱為“選士”;司徒再從“選士”里挑選出優秀者,送到國學里學習。由于各自的情況不同,鄉學學員進入國學的始學階段也不一樣。有人從小學開始學習,如《春秋公羊傳》宣公十五年何休注所謂的“其有秀者,移于鄉學,鄉學之秀者,移于庠。庠之秀者,移于國學,學于小學”《春秋公羊傳注疏》卷一六,第2287頁。;有人則從大學開始學習,如《禮記·王制》“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升之學”,鄭玄注“秀士,鄉大夫所考,有德行、道藝者。……學,大學”《禮記正義》卷一三,第1342頁。,選士之秀者是從大學開始學習的。
西周國學的學員絕大多數是“國子”,即“王太子、王子、群后之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嫡子”皮錫瑞:《尚書大傳疏證》卷六,第282頁。,但是也有少部分的“國之俊選”,即“為鄉、遂大夫所興賢者、能者”孫詒讓:《周禮正義》卷四二,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第17111712頁。。
諸侯國學校里的優秀學員也可以升入周王國的國學學習。《漢書·食貨志》記載西周時期的“諸侯歲貢少(小)學之異者于天子,學于大學”,《春秋公羊傳》何休解詁謂“諸侯歲貢小學之秀者于天子,學于大學”《漢書》卷二四,第1122頁;《春秋公羊傳注疏》卷一六,第2287頁。,都證明了這種機制的存在。正因為西周時期大學的生員來自不同的地方,所以孫詒讓謂:“周制大學,所教有三:一為國子,即王大子以下至元士之子,由小學而升者。二為鄉、遂大夫所興賢者、能者,司徒論其秀者入大學。……三為侯國所貢士。此三者,皆大司樂教之。”孫詒讓:《周禮正義》卷四二,第1711頁。可見,國學的學員除了主體的貴族之子,還有來自周王國鄉學和諸侯國推薦來的賢能之士。
除了選優,西周學校也有汰劣的機制。先看地方學校里的淘汰機制,《禮記·王制》記載:
命鄉簡不帥教者以告,耆老皆朝于庠,元日習射上功,習鄉上齒。大司徒帥國之俊士與執事焉。不變,命國之右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左,命國之左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右,如初禮。不變,移之郊,如初禮。不變,移之遂,如初禮。不變,屏之遠方,終身不齒。《禮記正義》卷一三,第1342頁。
鄭玄注:“遠方,九州之外。齒,猶錄也。”孔穎達疏:“司徒命鄉中耆老皆聚會于鄉學之庠,乃擇善日,為不帥教之人習鄉射之禮,中者在上,故曰‘尚功;又習鄉飲酒之禮,老者居上,故曰‘上齒。欲使不帥教之人觀其上功,自勵為功,觀其上齒,則知尊長敬老。大司徒帥領國之英俊之士,與執其事,使俊士與之以為榮,惡者慕之而自勵。”如此看來,當時會將鄉學中不遵循教導的學員上報,然后會再進行四次教育活動,如果他們仍然不悔改,就會將他們流于九州之外,終身不錄用。
再看國學里的汰劣情況,《禮記·王制》又記載:
將出學,小胥、大胥、小樂正簡不帥教者以告于大樂正。大樂正以告于王,王命三公、九卿、大夫、元士皆入學。不變,王親視學。不變,王三日不舉,屏之遠方。西方曰棘,東方曰寄,終身不齒。《禮記正義》卷一三,第1342頁。
孫希旦指出這段文字描述的是“國學絀惡之法也”孫希旦:《禮記集解》卷一三,第366頁。,可見國學中會將不遵循教導的學員稟告到大樂正處,之后再進行兩次教育活動,如果仍然不思悔改,會將他們流于九州之外,終身不錄用。
五、西周時期的學校教育與學員仕進
所謂“學員出路”就是指生徒在學校教育結束之后的去向。一般來說,學員的出路應當有兩種,一種是進入仕途,一種則沒有進入仕途。以下筆者將分這兩方面來探討西周學校學員的出路。
西周時期的國學教育為貴族仕進提供了途徑。在遹簋銘文(《集成》4207,西周中期)中,大學學員遹因為在侍奉周王的“饗酒”禮儀過程中表現“無遣”,周王賜給他“(爵)”。遹的仕進之路與他在大學里所受的教育是密切相關的。上文已經指出,靜簋銘文(《集成》4273,西周中期)中的吳、呂剛即班簋銘文中的吳伯、呂伯(《集成》4341,西周中期);他們在入大學學習之前已經具有了官職,但是在班簋銘文中能夠參與“伐東國滑戎”的戰爭,職位無疑大大提升了。他們職位的提升無疑與大學里教育有關。同時,師簋銘文也記載:
唯十又一月,九月初吉丁亥,王在周,格于大室,即位。宰琱甥入佑師,王呼尹氏冊命師,王曰:“師,在昔先王小學,汝敏可使,既命汝更乃祖考司小輔。今余唯申就乃命,命汝司乃祖考舊官小輔眔鼓鐘。賜汝素芾、金衡、赤舄、鋚勒,用事。敬夙夜勿廢朕命”。師拜手稽首,敢對揚天子休,用作皇考輔伯尊簋。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師龢父胙素芾,恐告于王。(《集成》4324,西周晚期)
這篇銘文中,師在先王的時候擔任的職務是“司小輔”,在時王時,受到新的任命,管理“小輔眔鼓鐘”,職務有所提升。然而,他在先王時的被任命,與他在小學里表現出來的“敏可使”的素質有很大的關系。所以,可以說學校教育是貴族仕進的重要途徑之一。
西周時期的學校教育也為鄉內民眾仕進提供了門徑。西周時期鄉學里的學員應當是鄉里的成員,他們并非貴族,然而學校教育為他們提供了仕進的機會,《禮記·王制》記載:
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禮記正義》卷一三,第1342頁。
陳澔引劉氏曰:“論者,述其德藝而保舉之也。苗之穎出曰秀。大司徒命鄉大夫論述鄉學之士,才德穎出于同輩者而禮賓之,升其人于司徒,司徒考試之,量才而用之為鄉遂之吏,曰‘選士。”陳澔:《禮記集說》,第105106頁。可見,鄉大夫會從鄉學學員中選拔出優秀的成員,他們被稱為“選士”;鄉大夫將他們推薦到司徒處,司徒會量才任命他們擔任鄉遂的官員。
“選士”中的優秀者,如果不甘于在鄉、遂地區任官職,可以進一步地被推薦入國學學習,所謂“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升于學者,不征于司徒,曰造士”《禮記正義》卷一三,第1342頁。。他們在經過一番學習之后,可以通過選拔在更高的層次上仕進,《禮記·王制》謂:
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后官之,任官然后爵之,位定然后祿之。《禮記正義》卷一三,第13421343頁。
陳澔引劉氏曰:“其進士,則必命為朝廷之官。”陳澔:《禮記集說》,第105106頁。可見從國學里選拔出來的“進士”,其中的優秀者可以擔任周王朝的官員。如此看來,學校教育為鄉內的成員提供了兩條仕進的道路:一為選士,擔任鄉遂的官吏;二為進士,擔任周王朝的官員。
除了自下而上的推薦,周王也會親臨地方學校選拔人才。這成為一部分地方學校學員仕進的途徑。《禮記·文王世子》的記載為我們了解這一途徑提供了線索:
凡語于郊者,必取賢斂才焉:或以德進,或以事舉,或以言揚。曲藝皆誓之,以待又語;三而一有焉,乃進其等,以其序,謂之郊人。《禮記正義》卷二○,第1406頁。
鄭玄注云:“語謂論說于郊學。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升諸司馬曰進士,謂此矣。曲藝為小技能也;誓,謹也;皆使謹習其事。又語,為后復論說也。三說之中,有一善則取之,以有曲藝,不必盡善。”鄭玄的注還是過于簡略,不利于理解,孔穎達的疏對其中的情況作了詳細的解釋:
“語謂論說于郊學”,語謂論課學士才能也。郊,西郊也。周以虞庠為小學,在西郊。今天子親視學于其西郊,考課論說于西郊之學,以西方成就之地故也。或遍在四郊。“必取賢斂才焉”者,謂在于西郊學之中,論說取賢,斂其才能者以爵之也。
“或以德進”者,謂人能不同,各隨才用也。德謂有道德者,進謂用爵之也。德最為上,故進之宜先也。“或以事舉”者,事次德者,雖無德而解世事,或吏治之屬,亦舉用之也。“或以言揚”者,次事也。揚亦進、舉之類,互言之,雖無德無事,而能言語應對,堪為使命,亦舉用之。
“曲藝皆誓之”者,曲藝謂小小技術,若醫卜之屬也。誓,謹也。若學士中雖無前三事,而有小小技術,欲授試考課,皆且卻之,令謹習。“以待又語”者,又語謂后復論說之日,令待后時,若春待秋時也。“三而一有焉”者,謂小技藝者所說三事之中,而一事有善者。
“乃進其等”者,等,輩類也;若說三事有一善者,則進于大眾輩中也。“以其序”者,序,次也;雖得進眾而不得與眾為一,猶使與其輩中自為高下之次序也。“謂之郊人”者,雖有次序而待職缺當擬補之;若國子學士,未官之前,俱為俊選;而以小才技藝者,未官之前,而不得同為俊選,但名曰郊人,言其猶在郊學也。《禮記正義》卷二○,第1406頁。
可見周王有時會親臨鄉學,考察學員的才能;只要他們在德、事、言方面有才能,都會被錄用,并被任命相應的官職。哪怕有的學員在德、事、言方面才華不突出,但有曲藝方面的才能,也會被儲備起來,以待日后的錄用。
西周鄉學的學員也是鄉內的居民,他們也是鄉內官員評比、考察的對象。只要他們足夠賢能,完全可以被選拔出來,推薦入仕。《周禮·地官·鄉大夫》記載:
三年則大比,考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鄉老及鄉大夫帥其吏與其眾寡,以禮禮賓之。厥明,鄉老及鄉大夫、群吏獻賢能之書于王,王再拜受之,登于天府,內史貳之。《周禮注疏》卷一二,第716頁。
鄭玄注:“賢者,有德行者。能者,有道藝者。……(厥明)其賓之明日也。……王拜受之,重得賢者。王上其書于天府。天府,掌祖廟之寶藏者。內史副寫其書者,當詔王爵祿之時。”賈公彥疏:“內史副寫一通文書,擬授爵祿。”《周禮注疏》卷一二,第716頁。可見,鄉里的賢者、能者會被鄉老鄉大夫等鄉吏推薦到王處,最后由王授予爵祿。鄉學的教育無疑有助于一些學員成為賢者、能者。
學校教育也為遂里的民眾入仕提供了路徑。《周禮·地官·遂大夫》云:
遂大夫各掌其遂之政令。……三歲大比,則帥其吏而興氓。《周禮注疏》卷一五,第742頁。
鄭玄注:“興氓,舉民賢者、能者,如六鄉之為也。興猶舉也。”孫詒讓正義:
此謂行鄉飲酒之禮于遂序,以興遂之賢能,如鄉大夫賓興六鄉賢能之禮。……六遂與六鄉治教相擬,此遂大夫興氓,即用鄉飲酒之禮。其屬縣正如州長,則縣亦當有春秋以禮會民射于縣學;鄙師如黨正,則鄙亦當有國索鬼神,屬民飲酒正齒位之禮。孫詒讓:《周禮正義》卷二九,第1153頁。
可見,遂內民眾中的賢者、能者,像鄉內一樣,會被推薦去賜予爵祿。遂內的學校教育無疑有助于相應的民眾成為賢者、能者,從而為他們的仕進提供了門徑。
六、學校教育為其他學員帶來的境遇改善和生活便利
西周時期學校里的學員不見得每個人都能入仕或實現向上流動,程子就曾指出學校里的“不可教者”會被“歸之于農”見孫希旦:《禮記集解》卷二八,第771頁。,可見有一些學員并不能入仕。可以合理地推想,西周學校里的絕大多數學員最終都不能入仕,仍然生活在他受教育之前所處的社會階層。那么,學校教育又能為這些沒有實現向上流動的學員——尤其是非貴族學員——的生活帶來怎樣的境遇改善和生活便利?從材料來看,大致有以下一些方面:
其一,學員在受教育期間可以免除一定的徭役。《禮記·王制》記載:
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升于司徒者,不征于鄉;升于學者,不征于司徒,曰造士。《禮記正義》卷一三,第1342頁。
鄭玄注:“不征,不給其繇役。”孫希旦解釋道:“選士不征于鄉,而免于一鄉之繇役;俊士不征于司徒,而免于一國之繇役。……謂其學業有成,故免其繇役以優異之。”孫希旦:《禮記集解》卷一三,第364頁。可見,從鄉里的選拔出來的“選士”就可以免除鄉里的徭役,而被選拔到大學讀書的“造士”,則可以免除一國的徭役。減免徭役將為受教育者減去很大的生活負擔。這無疑是學業之外,學校教育給受教育者帶來的極大的生活便利。
其二,學校教育為學員以后的入仕提供了可能。西周時期一些民眾,在結束學校教育之后,并不能立刻入仕,但這并不妨礙他們成為鄉里的賢能者。只要他們表現突出,仍然有再被任命的可能。當時有官員巡視全國,考察其中的賢者、能者,并會任命勝任者擔任官職,《周禮·地官·司諫》記載:
司諫掌糾萬民之德而勸之朋友……巡問而觀察之,以時書其德行、道藝,辨其能而可任于國事者。《周禮注疏》卷一四,第731頁。
鄭玄注:“可任于國事,任吏職。”受過學校教育的人員很容易成為所在區域的賢者、能者,只要他們表現突出,就容易被司諫類的職官發現、薦舉,并被最終委以官職。
即使他們不能進入都城或在當地擔任職官,他們還有可能擔任自己所在宗族的管理者。2003年刊布的季姬方尊銘文記載:
唯八月初吉庚辰,君命宰茀賜季姬畋臣于空木,厥師夫曰丁,以厥友廿又五家,折(誓)。賜厥田,以生馬十又五匹,牛六十又九,羊三百又八十又五,禾二廩。其對揚王母休,用作寶尊彝。其萬[年子孫]永寶用。蔡運章、張應橋:《季姬方尊銘文及其重要價值》,《文物》2003年第9期。
銘文中的人眾、土地、牲畜、糧食作物構成了一個相對獨立的完整的生產單位陳絜:《周代農村基層聚落初探》,朱鳳瀚主編:《新出金文與西周歷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18頁。。“丁”是“師夫”的名,“友”在西周金文中多為族人之稱韋心瀅:《季姬方尊再探》,《中原文物》2010年第3期;朱鳳瀚:《商周家族形態研究》(增訂本),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333頁。,所以25家是丁的族人。這個生產單位內的居民無疑都是來自同一個姓族的。這個生產單位里有田、馬、牛、羊、禾,農業性質非常明顯,應當就位于遂地。“師”是長,所以丁擔任的是這個生產單位的長。鄉學里的教育為西周時期像丁這樣的人員的任職提供了便利。
其三,受過學校教育的學員能更好地了解國家的政策和法令。西周時期會派官員到各地宣講政策、法令。《周禮》中有職官士師,他的重要職責就是“掌國之五禁之法,以左右刑罰。……皆以木鐸徇之于朝”《周禮注疏》卷三五,第874頁。,即搖動木鐸在外朝宣講法律。布憲也有類似的職責,《周禮·秋官·布憲》記載:
布憲掌憲邦之刑禁。正月之吉,執旌節以宣布于四方。《周禮注疏》卷三六,第884頁。
可見,布憲掌管刑法、禁令,會在每年正月持旌節出外宣講法律。與之類似,一些基層官員還會對其治域里的民眾直接宣講法律。州長在“正月之吉,各屬其州之民而讀法,以考其德行道藝而勸之,以糾其過惡而戒之。若以歲時祭祀州社,則屬其民而讀法,亦如之。……正歲,則讀法如初”。黨正“及四時之孟月吉日,則屬民而讀邦法,以糾戒之。……正歲,屬民讀法而書其德行道藝”。族師于月吉之時,“屬民而讀邦法,書其孝弟睦姻有學者”。閭胥“凡春秋之祭祀、役政、喪紀之數,聚眾庶;既比,則讀法,書其敬敏任恤者”見《周禮注疏》卷一二,第717719頁。。在這一過程中,受教育者無疑能更好地了解國家的政策和法令,從而為安排自己的生活提供方便。
其五,學校教育豐富了學員們的日常生活。西周時期普通民眾的日常生活中,有很多的詩、樂活動。如《禮記·曲禮上》記載“鄰有喪,舂不相”,意為鄰居有喪事,舂米的時候不能唱歌,可見平常百姓在日常舂米的時候會唱歌;又如《詩經·召南·采蘩》是勞動人民采蘩時唱的詩歌;再如《詩經·魏風·十畝之間》是勞動婦女相約同伴一起去采桑,又一起回家回家時唱的歌分見《禮記正義》卷三,第1249頁;《毛詩正義》卷一、卷五,第284、358頁。。生活于社會下層的、受過學校教育的人員,能夠更好地享受這種歌詩樂趣,并能夠學習、推廣和創新周代日常生活中的詩歌和音樂,從而豐富西周時期的文化內涵。
結語
最后,我們可以回答文章開頭提出的九個問題,并總結全文:
學校教育是人們獲取向上流動的資本的重要途徑。所以,考察西周時期的社會流動,必然要研究當時的學校。另一方面,社會流動也為我們探討西周時期的學校提供了一個嶄新的視角。
西周時期的學校主要設立在周王國和諸侯國境內。西周時期周王國境內的學校分國學和地方學校兩大體系。國學是位于都城地區,地方學校位于都城以外的地區。周王國的國學由大學和小學組成,其中大學在級別上高于小學。地方學校由鄉學和遂學組成。鄉學有閭內的塾,黨內的庠、序,州內的序,以及鄉內的庠,它們的級別依次提高。遂學有里內的校室,鄙內的塾,縣內的庠、序,以及遂內的序,它們的級別也是依次提高。其中鄉學的每一級學校要比遂內相對應級別的學校高一級。西周諸侯國的學校體系與周王國的相似,也由國學(包括大學和小學)和地方學校構成。
西周時期最低級別的學校入學條件并不苛刻,普通人均可以入學學習。當時的每一級學校都會對學員進行考核,其中優秀的學員會進入更高一級的學校學習。周王國地方學校和諸侯國學校里的優秀學員,可以被推薦進入周王國的國學學習。當時的學校里也有淘汰的機制,經過多番考核和教育之后仍然不合格的學員,會被流放至九州之外,永不錄用。
西周學校為其中的優秀學員入仕提供了門徑。他們既可以通過各級官員的選拔、推薦入仕,又可以通過周王親自到學校里的考核入仕。可以合理地推想,西周學校里的絕大多數學員是不能入仕的,然而,學校教育也為他們帶來了諸多境遇改善和生活便利。
[責任編輯 孫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