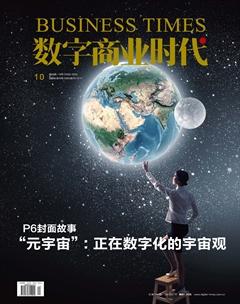人民需要什么樣的小米汽車?
蟲二

做大事,首重出場時機。
如果把新造車勢力比做一日三餐,特斯拉肯定是早午餐Brunch,把最早的嘗鮮消費和優質客群一網打盡,后來的蔚小理,合計交付都跑不贏特斯拉,撐不起正餐,只能算下午茶,小米此時跑步入場,當然不是為了搶一頓夜宵。
2013年4月和7月,雷軍兩次拜會馬斯克,言談中充滿敬佩,“我們干的好像都是別人能干的事情,而馬斯克干的事是別人想都想不到的!”
做大事,首重出場時機。
如果把新造車勢力比做一日三餐,特斯拉肯定是早午餐Brunch,把最早的嘗鮮消費和優質客群一網打盡,后來的蔚小理,合計交付都跑不贏特斯拉,撐不起正餐,只能算下午茶,小米此時跑步入場,當然不是為了搶一頓夜宵。
2013年4月和7月,雷軍兩次拜會馬斯克,言談中充滿敬佩,“我們干的好像都是別人能干的事情,而馬斯克干的事是別人想都想不到的!”
兩人都信奉“硬件+軟件+互聯網”顛覆一切的產品哲學,只不過在蘋果和三星夾縫中打出一片天地的雷軍,迎合中多少藏著“彼可取而代之”的覬覦。
在把握時機上,小米向來是節奏大師。
2014年,特斯拉完成了首次國內交付,以游俠、蔚來、樂視為代表的第一批弄潮兒隨之出現,到2018年共有500多家造車新勢力進場,只憑一張PPT就搞定金主爸爸的公司不在少數,最后量產和交付的屈指可數。
彼時的小米卻如箭在弦上,引而不發,寧愿出錢、出槍讓蔚來、小鵬等小兄弟沖鋒陷陣,自己甘居幕后,拒絕親身犯險,其實以小米的名號,隨便甩出幾張PPT,都能講出漂亮的資本故事,雷軍的低調就是想等一個最合適的時間窗口。
造車之于雷軍,不是做不做的問題,而是封神前的最后一戰,豈容有失。
現在的新造車勢力無非兩種套路。
一種是圈錢自嗨。
游俠號稱投資115億的湖州工廠擱淺,沒有交付任何產品;車里全是大屏的拜騰燒掉了84億,南京棲霞區的工廠仍然荒草遍地;2017年把發布會開到拉斯維加斯的樂視FF,雖然不斷有新聞,卻是“只聞樓梯響,不見人下來”。
另一種是確實想干事,也致力于量產的。
但汽車是規模行業,傳統車企年產15萬輛是盈虧生死線,造車新勢力門檻稍低,李想說,“2020年誰能達到年產10萬輛,才是從娘胎里生出來了,否則就是胎死腹中”。國信證券的研報分析,蔚小理銷量分別達到18萬輛、6萬輛、12萬輛才能盈利。
事實是今年上半年,特斯拉合計生產38.68萬輛,交付38.61萬輛,蔚小理合計交付10.2萬輛,不足特斯拉的3成。
面對已經安全上岸的特斯拉,大家表面風光,內心極度彷徨。
用乘聯會秘書長崔東樹的話說,造車新勢力如果不能自我造血,就需要資本強力“補血”,這樣必然過度透支預期。
蔚小理的尷尬在于,對標特斯拉時機不成熟(營銷上可以,產品力不夠),降維打擊傳統車企,沒有規模和成本優勢,放下身段搶五菱的飯碗,又會讓品牌過度下沉。
這就形成了一個怪現狀,傳統車企的新能源車偏向于代步市場,造車新勢力燒錢做品牌,真正成熟的中端市場相對空白,這是個“午飯已過、晚飯沒到”的空窗期
姍姍來遲的小米反而可機會搶在特斯拉Model Q、蔚來ET3、ES3、理想S02真正放量之前,而且完美避開了冷啟動的尷尬。
當年李斌創辦蔚來,拉了雷軍在內的很多大佬撐場,小鵬甚至曾向陸正耀的神州優車猛拋橄欖枝,這是初創品牌的悲哀,要么示好資本,要么委身渠道。
對造車來說,虧得起也是一種超能力。
2003年成立的特斯拉,去年才實現首次全年盈利,恒大燒了180多億還是一地雞毛,蔚來累計虧損400億,財雄勢大的華為,也只是給車企做解決方案,強如蘋果,真到臨門一腳也是逡巡不前,這就反襯了小米的決心。
但新能源車的“人民選擇獎”,遠比當年的手機難拿。
小米引以為豪的性價比,表面是用戶端的產品力,其實是供應鏈的控制力。
手機是硬件驅動,小米通過秒售罄+長備貨模式,給自己留出了非常良性的現金流量周期,存貨周轉期45天,達到了沃爾瑪的水平,2017年小米免費占用供應商資金是36天,2018年達到77天,雷軍說2016年才學會“交付”這個詞,未免矯情了。
小米汽車很可能是這個玩法的跨界復制。
因為小米不甘于做Tier 1,不屑于做解決方案,目標肯定是整車制造,而且一上來就會走量,這樣占比40%的三電系統成本控制尤為重要。
業界原以為2025年之前動力電池會持續短缺,何小鵬據說為了拿到配額,還在廠方蹲守了一周,其實隨著寧德時代等企業大舉定增擴產,規劃的產能已經超過1712GWh,足以填補1151GWh的產能缺口。
3年后將是“電荒”到“電剩”的轉折點,屆時供應鏈話語權將會轉移到整車廠手中,小米汽車選擇2024年亮相,高管王翔說小米汽車“3年后絕對來得及”,應該是早就算準了這個時機。
今年雷軍把整個車圈跑了一遍,從長安、東風到廣汽,通用,從寧德時代到博世,一個不落,4月的閉門調研會上,數得上名號的業內大佬和友商都來捧場。
小米的規劃據說是3年內每年一款新車,累計銷量達到90萬輛,這樣第一年就算較少,至少有15萬輛的規模,夠不上特斯拉,但絕對秒殺蔚小理了。
現在法系品牌、韓系現代、廣汽菲克都有現成的產能退出,接盤價格合理,為了吸引小米落戶,很多地方也有優惠政策,小米自建工廠也不是問題。
在技術布局上,小米和旗下的順為投資了做自動駕駛的momenta,縱目科技、Deepmotion,做激光雷達的禾賽科技,以及做動力電池的蜂巢能源,材料行業的贛鋒鋰電等等。
在通訊模塊方面,智能汽車的5G SEP(標準必要專利)授權費可能低于智能手機,這是技術的紅利。
小米汽車團隊也快速搭建,翻倍薪資搶人,工程師月薪基本2萬起步,母年14薪,雖然還沒到上海特斯拉的水平。
至于定價,小米真不是“人民要什么,我們就給什么”。
今年5月360周鴻祎拉著哪吒汽車開了一場聲勢浩大的發布會,喊出了“為人民造車”,但到現在為止還只是一句口號。
五菱去年叫響這句話,除了疫情期間的表現,主要是造出了那臺史上最便宜的宏光Mini EV,2.98萬元的價格,最挑剔的人民都不好意思吐槽了。
但是變身網紅的五菱就算有了秋名山神車的名頭,產品力輸出也只限于10萬以下的區間,對優質溢價客群幾乎沒有殺傷力。
小米更有品牌溢價權,但遠不是隨心所欲。
雷軍曾在微博發起投票,“你希望小米的第一輛車是什么價錢?”接近40%的人支持10萬元以下,其次是10-15萬元,選擇30萬元以上的,不到8%。
小米的尷尬在于,拉低到五菱的水平,未必斗得過五菱;要搶特斯拉的客群,短時間辦不到;只是弄死蔚小理有多大意義?
所以雷軍選擇20萬元左右是深思熟慮的。
小米汽車走量的前提是主銷車型打入主流市場,這就不能依賴政策催生的偽需求,因為汽車是比手機更成熟的耐用消費品,那些只圖上牌方便或是不限行才買車的客群,撐不起溢價,也不會貢獻口碑體驗。
所以新能源車兩極分化,10萬元以下和20萬元以上的市場都在蓬勃發展,反倒是中間段的產品力打不過汽油車,有能力突破這個次元壁的,現階段只有特斯拉。
小米汽車定位20萬元,正好支撐40萬體驗,30萬硬件這個邏輯,完美避開了特斯拉和BBA的高端新能源車,與其他造車新勢力有產品錯位,至于廣汽埃安、比亞迪宋等競品,小米有品牌優勢,需要當心的可能只是大眾ID系列。
站穩腳跟的小米就不怕特斯拉了,因為產品再好,不破信仰,強勢品牌自帶粉絲屬性,當年小米手機只怕華為,不懼蘋果,小米和特斯拉之戰一如當年的米粉和果粉,會打得很熱鬧。
定價“中庸”的小米汽車,真正的風險是激進創新。
由于成本透明,新能源車的利潤只有5-10%左右,有些公司明知自動駕駛并不完善,仍然用夸大宣傳支撐溢價空間,活生生把賣點變成了隱患。
造車新勢力的技術儲備也拼不過傳統車企。
小米2013年有意造車,2015年開始專利布局,申請量每年遞增,按智慧芽的統計目前已有951件,其中96%以上是發明專利,從專利估值來看,特斯拉約為2億美元,蔚來1864萬美元,恒大、小鵬、理想都是800萬美元左右,小米大概1億美元。
比起傳統車企仍然是九牛一毛,BBA的專利估值都在10億美元以上,只是大部分專利集中在底盤、發動機等機械工程領域,造車新勢力在數據、檢測、通訊、交互上有錯位優勢。
雙方研發思維不在一個頻道。
小米的突破口是人機交互,關注的還是以應用體驗作為超預期的賣點,這是中國互聯網公司的強項。
超過80%的專利集中在車聯網、自動駕駛和智能座艙等領域,比如根據周邊行人情況控制鳴笛音量,疲勞駕駛檢測,智能提醒車輛限行信息,AI路線和路況提示,駕駛員生物識別,手勢控制等等。
有些甚至“智能”到有一定爭議。
比如行車時自動監測周邊車輛,通過獲取車牌信息,讀取這些車輛的行車記錄,然后進行安全預警,同時自動規避交通違法行為較多的車輛。
小米汽車是比其他造車新勢力更激進的互聯網實踐,一方面以可感知的智能化體驗支撐20萬元的產品溢價,另一方面也有輕視基礎研究,忽略制造業短板的傾向。
這很像當年的國產汽車,李書福說過,“汽車就是四個輪子加幾個沙發。”刻意抹平與全球百年老店的技術差異。
小米汽車可能有不錯的體驗,可能有不俗的銷量,可能把造車新勢力推向新高峰,但遠不到超越特斯拉或是顛覆行業的時候。
小米汽車注定不會是另一個小米手機,現在真不是“我命由我不由天”的時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