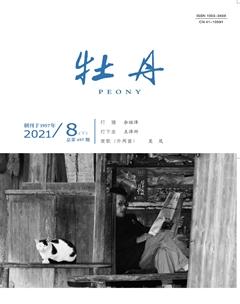老子與黑格爾的美學(xué)思想對中西美術(shù)的影響
老子與黑格爾分別是中西方思想發(fā)展歷程中的代表人物。二者的美學(xué)理念兼具民族性和時代性,在中西方美術(shù)的發(fā)展過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例如,老子美學(xué)奠定了中國山水畫興盛的基礎(chǔ),黑格爾美學(xué)影響了新古典主義繪畫的發(fā)展。
近代以來科技文明不斷進(jìn)步,中西方的文化有了更多的交流途徑,中西方美術(shù)相互吸收,相互借鑒。本文分析老子和黑格爾的美學(xué)思想,除了分析二者的異同及其對各自地域美術(shù)的作用之外,還窺探老子對西方美術(shù)和黑格爾對中國美術(shù)的交互影響。
一、老子與黑格爾的主要美學(xué)思想及異同
老子是中國傳統(tǒng)哲學(xué)中道家思想的代表人物。他的《道德經(jīng)》采用樸素辯證法,以此探尋宇宙的根源,并由此推導(dǎo)人的處世原則,最終達(dá)到與天地同在、與萬物合一的終極目的。他主張“道法自然”“大象無形”“清凈無為”等美學(xué)思想。
黑格爾是歐洲古典主義的集大成者。他的《美學(xué)》對藝術(shù)美有著明確的定義:美是理念的感性顯現(xiàn)。在他看來,理念相當(dāng)于藝術(shù)的內(nèi)容,藝術(shù)的形式就是訴諸感官的形象,而藝術(shù)要把這兩方面調(diào)和成為一種自由的、統(tǒng)一的整體。
(一)相同之處
1.“道”和“理念”是美的本原
老子的“道”和黑格爾的“理念”的美學(xué)精神皆是某種抽象的、虛幻的存在,旨在倡導(dǎo)藝術(shù)作品的背后應(yīng)有某種特定的藝術(shù)意蘊(yùn)。藝術(shù)家借助繪畫作品傳達(dá)主體對自然、宇宙的“道”和“理念”的見解,其可以是中國山水畫中的借景抒情、借物喻人,可以是西方油畫中描繪自然風(fēng)光的風(fēng)景畫,或是描繪光影色彩的印象繪畫。
2.事物的兩端既對立又統(tǒng)一
老子“大成若缺”“大直若屈,大巧若拙”等美學(xué)思想促進(jìn)了中國繪畫中意猶未盡的、若有若無的朦朧美,尤其是士大夫文人畫中水墨的運(yùn)用和黑虛實白的對比。例如,南宋時期,“馬一角,夏半邊”(指山水畫家馬遠(yuǎn)和夏圭畫作的構(gòu)圖風(fēng)格)中畫面的大幅留白;明末清初,八大山人(朱耷的別號)在畫面中只畫魚、花、石、葉,而不畫水和其他多余的背景之物;清代笪重光《畫筌》將這種繪畫風(fēng)格理解為“虛實相生,無畫處皆成妙境”;在筆墨方面,清代華琳的“計白當(dāng)黑”認(rèn)為畫面的空白處也是一種色彩。
黑格爾認(rèn)為美是理念的感性顯現(xiàn),這體現(xiàn)為感性與理性的和諧共處。他所推崇心物合一的代表——古希臘藝術(shù),曾被溫克爾曼評價為“高貴的單純和靜穆的偉大”。古希臘藝術(shù)對人體的理性探索借由藝術(shù)家的作品,感性地呈現(xiàn)在觀眾面前,例如,合理的人體比例,即人們可以從有限的感性形象認(rèn)識到無限的普遍真理。
(二)不同之處
雖說老子的“道”與黑格爾的“理念”都是美的本源,但老子的“道”偏向感性,注重不經(jīng)人工雕飾的自然美,在中國傳統(tǒng)的山水畫中,藝術(shù)家大都以自然山川抒發(fā)心中情感的同時,力求畫中形象和構(gòu)圖渾然天成。而黑格爾的“理念”趨向于理性,他在著作《美學(xué)》第一卷開篇就說:“自然美是無用的,藝術(shù)家是神的代言人。”可見對黑格爾來說,經(jīng)由人工創(chuàng)造的科學(xué)美才是真正的理想美。黑格爾認(rèn)為,東方藝術(shù)受到老子美學(xué)的影響而求諸暗示性或寓意性的外在事物形式來表達(dá)抽象的精神理念,卻因此缺少理想美。
二、老子美學(xué)思想對西方美術(shù)的影響
老子美學(xué)思想對中國藝術(shù)影響極大,無論是美術(shù)學(xué)科的畫種細(xì)分還是畫面意境的品評,文人畫、寫意畫的發(fā)展都離不開其浸染。而其對西方美術(shù)的影響體現(xiàn)在印象派的繪畫風(fēng)格里。在繪畫題材上,“自然”在西方美術(shù)中往往不受藝術(shù)家的重視,如同中國唐代之前也以人物畫為主,受老子“道法自然”“清靜無為”“淳樸本性”的影響后,“自然本位”的思想在山水畫、文人畫中逐漸興起并綿延不絕。西方在文藝復(fù)興之后亦是如此。中國近代文藝家朱謙之先生在評說文藝復(fù)興時期達(dá)·芬奇的畫作時說:“《蒙娜麗莎》描寫他愛人之美,曾費(fèi)五年的功夫在這畫上。卻是這畫背景是一塊中國式的山水,這在西洋畫界中是很特別的,可算是受中國的影響了。”這表明,西方美術(shù)在文藝復(fù)興時期就已經(jīng)受到老子美學(xué)和中國山水畫的陶染。
19世紀(jì),中西文化交流頻繁,印象派繪畫受到老子美學(xué)思想的影響,從古典主義掙脫以人物為主的枷鎖,走出畫室而到野外描繪自然風(fēng)景。在構(gòu)圖上,西方美術(shù)作品大都填塞得非常緊張,畫面動蕩起伏,而老子美學(xué)思想下的中國美術(shù)大都清淡、舒朗,如夢如影。這樣的手法被印象派畫家模仿,例如,莫奈在一片水上的點綴幾朵睡蓮;《日出印象》中,煙霧迷蒙的海面上隱約可見的光源,遠(yuǎn)方若隱若現(xiàn)的船只,畫面籠罩著一層朦朧美,這與老子所說的“大象無形”有著異曲同工之妙。
雷禮錫在《中國藝術(shù)與世界文明》中寫道:“受中國文化的影響,自然美和感性形式趣味在歐洲大行其道,極大地沖擊了傳統(tǒng)基督教精神與理想美理念。”在老子美學(xué)的感染下,西方美術(shù)在近代以來一反“模仿說”所倡導(dǎo)的理性的繪畫風(fēng)格,支配現(xiàn)實主義的思想在藝術(shù)上終不能得勢,因其教人抑制熱情、放棄主觀、閑卻自我。而后印象派、野獸派、立體主義、未來主義、抽象派等各種美術(shù)活動和思潮相繼開展。
伴隨著近代中西文化的頻繁交流,中國藝術(shù)中老子的美學(xué)思想幫助英國繪畫界培育了自然主義新畫風(fēng)。近代英國的部分園林設(shè)計圖已透出中國山水藝術(shù)的自然意趣。中國山水藝術(shù)的自然意趣在山水畫家宗炳的《畫山水序》中有較好的表述,即“山水,質(zhì)有而趣靈”,引人“閑居理氣,拂觴鳴琴,披圖幽對,坐究四荒”,達(dá)到“萬物融其神思”的暢懷境界。這要求山水藝術(shù)努力表現(xiàn)質(zhì)樸、淡靜、幽遠(yuǎn)的自然意象和情趣。
黑格爾曾指出,中國傳統(tǒng)藝術(shù)“讓自然事物保持自然形狀,力圖模仿自由的大自然”。在學(xué)習(xí)中國藝術(shù)的過程中,英國園林風(fēng)景畫間接地吸收了中國山水藝術(shù)的自然意象和情趣特征,這類“以假擬真,有若自然”正是來源于老子的美學(xué)思想。例如,錢伯斯的丘園圖稿就在空間上加大了開闊性,林木增加了疏密對比,雖無中國畫特有的山水審美境界,畢竟透出中國畫的闊遠(yuǎn)意味,與歐洲古典繪畫的寫實完美特征有明顯的區(qū)別。陳志華認(rèn)為,在近代歐洲特別是英國,“從不承認(rèn)自然的美,到喜愛它;從完全不在繪畫里表現(xiàn)自然,到用它作為主要題材,這反映著人們審美意識的重要變化、人同自然的關(guān)系的重要變化”。
三、黑格爾美學(xué)思想對中國美術(shù)的影響
黑格爾美學(xué)中對藝術(shù)的內(nèi)容和形式的自由統(tǒng)一的要求正適用于19世紀(jì)歐洲新古典主義畫派的繪畫風(fēng)格。新古典主義畫派崇尚理性的表達(dá),追求復(fù)古的精神,重視藝術(shù)在人民中所起到的道德教育作用。他們所選用的題材都是比較嚴(yán)肅的歷史題材,重視形式,倡導(dǎo)形式美的原則,摒棄鮮艷的用色,主張減弱畫面的色彩。
黑格爾的理性辯證法對中國美術(shù)發(fā)展也有著重大作用,尤其是近代中國畫的思想改革。嶺南畫派的代表人物——高劍父,1948年他在《前鋒日報》上發(fā)表了一篇名為《國畫的辯證》的文章,其中借助黑格爾“正、反、合”的美學(xué)理念,對中國畫史的發(fā)展過程進(jìn)行分析:他將兩漢六朝之畫稱為“正”,因為那時我國繪畫自成體系,與其他學(xué)術(shù)對立;而后印度美術(shù)輸入漸盛,致使“我國之繪畫,幾全為佛畫所陶溶,其作畫風(fēng)格亦受外來風(fēng)格支配”,此為“反”;唐宋時期,中國畫已然將各類風(fēng)格融會貫通、兼收并蓄,道釋人物、山水、花鳥都有所發(fā)展,此為“合”。一直到近代利瑪竇將歐洲繪畫帶入中國,中國繪畫大受某些醉心歐化、蔑視國粹者貶低,隨后有識之士又致力于“合”的工作,
如此反復(fù)。
黑格爾在《美學(xué)》中強(qiáng)調(diào)色彩的重要性,認(rèn)為顏色的豐富表現(xiàn)力是繪畫能描寫出全部現(xiàn)象。近代中國繪畫受到了以黑格爾美學(xué)為代表的歐洲繪畫思想的影響,也開始重視色彩在畫面中的效果和作用。吳昌碩、趙之謙等海派名家都曾受其影響而采用強(qiáng)烈鮮艷的西洋色彩,變清淡、纖細(xì)為艷麗、厚重。徐悲鴻于1920年發(fā)表的《中國畫改良論》中也說道:“鄙意以為欲盡物形,設(shè)色宜力求活潑。”以中學(xué)為體、西學(xué)為用的改良派運(yùn)用黑格爾的理念對美術(shù)事業(yè)的改革與古人大不相同。
藝術(shù)與宗教密切相關(guān),同時“美”還常常被視作一種高于“善”的境界。黑格爾在《美學(xué)》中說:“宗教往往利用藝術(shù),來使我們更好地感到宗教的真理,或是用圖像說明宗教真理以便于想象,在這種情況下,藝術(shù)卻視為和它不同的一個部門服務(wù)。”這樣的思想被近代留學(xué)于歐洲的蔡元培所汲取,歸國后提出了“以美育代宗教”的理念,他寄希望于普及美術(shù)教育的同時傳播藝術(shù)的“真、善、美”“使人我之見,利己損人之思念,以漸消沮者也”,從而改善藝術(shù)與宗教關(guān)系的同時改造國民精神。
不僅如此,徐悲鴻、康有為等人,于近代思想開放的浪潮中汲取黑格爾的理性辯證法提出改革中國畫、雕塑、油畫等美術(shù)學(xué)科,嚴(yán)格按照西方美術(shù)學(xué)院的學(xué)科設(shè)置和課程安排,并重視素描的作用,為我國的美術(shù)發(fā)展提供專業(yè)性更強(qiáng)的制度和保障。
四、結(jié)語
黃賓虹在《賓虹論畫》中說:“老子言‘道法自然,莊生謂‘技進(jìn)乎道,學(xué)畫者不可不讀老莊之書。”莊子是老子美學(xué)思想的繼承者,從某種程度上說,只有充分了解老子的美學(xué)思想,才能更好地認(rèn)識、體會、感悟到莊子美學(xué)和中國美術(shù)中獨(dú)特的韻味。朱光潛有言:“黑格爾對美學(xué)的最重要的貢獻(xiàn)在于把辯證發(fā)展的道理應(yīng)用到美學(xué)里,替美學(xué)建立了一個歷史觀點。”
更重要的是,老子與黑格爾的美學(xué)思想并不只是桎梏于各自所屬的國度中,它們都曾漂洋過海對另一個時空里的美術(shù)發(fā)展產(chǎn)生了不可或缺的影響。倘若沒有老子的“道法自然”,是否還會有印象派的追尋自然和后來抽象派的繪畫風(fēng)格?假如沒有黑格爾的理性辯證,中國近現(xiàn)代以來的美術(shù)是否還會有如此多思想和改革的碰撞?這些都值得商榷。但可以肯定的是,老子的美學(xué)思想肯定了中西方美術(shù)里“自然”本身對繪畫的重要性,即畫面的題材和內(nèi)容不再左右繪畫者的創(chuàng)作,而是通過畫家本身的自我意識和理念“再構(gòu)”出來;黑格爾的美學(xué)理念在當(dāng)時的社會環(huán)境下系統(tǒng)地闡釋了在藝術(shù)創(chuàng)作中理念和形式的關(guān)系,并且在中西方美術(shù)中,對理念本身的內(nèi)容也作出了一定的規(guī)范和要求。他們二人對中西方美術(shù)的發(fā)展提供了持續(xù)不斷的美學(xué)源泉,令后世的美術(shù)家收獲良多。
(齊齊哈爾大學(xué))
作者簡介:郭銘城(1994-),男,福建廈門人,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為美術(shù)理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