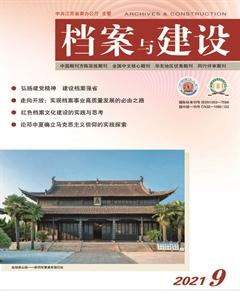論鄧中夏確立馬克思主義信仰的實踐探索
李勇
摘 要:鄧中夏作為中國共產黨創建時期重要人物之一,馬克思主義信仰的確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經歷了一段發展歷程。鄧中夏從新文化運動興起之際開始初步接受民主主義思想,到五四運動時轉變為激進的民主主義者,再到發起成立馬克思學說研究會、創建北京共產黨小組,成長為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最終做出了具有重大意義的人生抉擇。
關鍵詞:鄧中夏;馬克思主義;湖湘文化;五四新文化運動;馬克思學說研究會
鄧中夏作為中國共產黨先驅人物之一,其馬克思主義信仰的確立經歷了一段發展歷程。他從新文化運動到五四運動,從發起成立北京大學馬克思學說研究會到積極參與創建北京共產黨小組,最終確立了堅定的馬克思主義信仰。鄧中夏是當時中國先進知識分子探索救國救民道路的典型。
一、從封建禮教下的意氣書生到初具民主主義思想的進步青年
鄧中夏作為19世紀末出生的湘籍人士,自幼在父親鄧典謨和塾師教導下,深受王夫之、魏源、曾國藩等著名湘籍思想家影響,這些思想家在引領湖湘文化發展時所倡導的心憂天下、敢為人先、經世致用、堅韌不拔等品質在鄧中夏身上得到充分體現。
岳麓書院是湖湘文化的搖籃和象征,是鄧中夏早年接受民主思想啟蒙的重要場所,他從這里開始由舊書生向具有民主主義思想的進步青年轉變。1912年9月,湖南優級師范學堂改名為湖南高等師范學校(簡稱湖南高師),正式遷入岳麓書院辦學。1915年秋,鄧中夏以優異成績考入湖南高師。高師的倫理學教授楊昌濟成為他這一時期思想發生重要轉變的引路人。當時由陳獨秀等人在上海發起的聲勢浩大的新文化運動正席卷全國,為湖南思想界變革提供了良好契機,得到一直呼吁“喚起國民之自覺”的楊昌濟熱烈支持。湖南社會層面不同領域發生著顯著變化,如舊的禮教開始受到人們抵制、西方新思潮開始在湖南大量傳播等。鄧中夏正是在新文化運動興起與湖湘文化開始轉型之際,來到岳麓書院,與毛澤東、蔡和森等進步青年成為楊昌濟的得意門生。[1]
楊昌濟作為當時湖南教育界的著名人物,在學術上善于通過選擇、批判、融合等方式,推動舊學與新學一體發展,最終“自成一種比較有進步性的倫理思想和講究實踐的人生觀”[2]。他對宋明理學研究頗深,贊同湖湘文化中論及個人修養和治學方法的有益成分。楊昌濟在授課中推崇王船山強調的重視個人獨立精神,尤為看重譚嗣同在《仁學》中對儒家“三綱”之說的批判精神,希望鄧中夏等青年能夠養成個人獨立之性格。因此,在當時一個時期內,毛澤東、蔡和森、鄧中夏等湖南學子盛行研讀船山學說和譚嗣同《仁學》的學術風氣。除了力推湖湘文化精髓,楊昌濟還不遺余力地向鄧中夏等人宣傳新思想,甚至自費為他們訂閱《新青年》雜志,鼓勵學生閱讀《猛回頭》《革命軍》等革命書刊,使這些進步青年很快成長為敢于變革社會的熱血青年。受楊昌濟的啟發和教育,鄧中夏的愛國思想和民主主義思想愈發強烈,與毛澤東等人立志“要具有崇高的理想和改革社會、國家的偉大抱負,以及實事求是、刻苦實踐的精神”[3]。從1915年秋到1917年夏,在以資產階級民主思想為代表的“新思想”和以儒家傳統思想為代表的“舊思想”劇烈碰撞下,加之楊昌濟的熱情指導,鄧中夏從傳統的湖湘文化世界中走出來,開始接受民主主義思想。
二、從愛國進步青年到激進民主主義者
1917年8月,鄧中夏考入北京大學國文門(文學系),立志以學習新知識、研究新思想、尋找救國救民道路為主要目的。入學不久,俄國爆發的十月革命引起了北京大學圖書館主任、新文化運動主將李大釗的熱切關注。李大釗開始在中國傳播馬克思主義,先后發表了《庶民的勝利》《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等一系列文章,熱情謳歌十月革命,為追求進步的廣大中國青年指明了前進方向。鄧中夏經常光顧北大圖書館,成為熱心讀者,“認真學習我國近百年來的歷史和外國歷史,研究帝國主義列強對中國的侵略和軍閥統治下中國的政治狀況”[4]。此外,他還多次聆聽李大釗的授課,對其思想觀點推崇備至。在李大釗影響下,鄧中夏開始密切關注十月革命,集中閱讀大量關于十月革命的報道。據鄧中夏在北大的同班同學許寶駒回憶,從1917年底到1918年初,鄧中夏曾短暫呈現過一段起伏不定的狀態,如他時而從談笑風生變得沉默寡言,時而焦慮并感嘆中華民族將陷于亡國滅種危險境地,同時又拼命搜集、閱讀各種進步書刊。經歷過這段特殊的思想波動期后,鄧中夏在學生中又變得活躍起來,他甚至不止一次對許寶駒說:“只有接受馬克思列寧主義,走蘇俄的道路,中國人民才能得救。”[5]
俄國十月革命引起了英美日等帝國主義的干涉,尤其是日本帝國主義,妄圖在干涉俄國革命的同時,趁機擴大在中國的殖民利益。1918年5月16日和19日,中日兩國政府代表先后在北京簽訂了《中日陸軍共同防敵軍事協定》和《中日海軍共同防敵軍事協定》(合稱《中日共同防敵軍事協定》)。5月21日,鄧中夏、許德珩等北大學生與李達、黃日葵等從日本返回國內的留學生代表,帶領北京數所高校2000余學生,赴民國北京政府總統府請愿,強烈要求廢除喪權辱國的《中日共同防敵軍事協定》。然而,北京政府的草率應付及冷漠態度讓鄧中夏等學生意識到,僅僅依靠學生孤軍奮戰發動一兩次游行示威,根本救不了病入膏肓的中國,必須動員更多的社會力量參與到救國實踐中。“五二一請愿”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大規模的學生運動,“為五四運動作了思想上和組織上的準備,也提供了可資借鑒的經驗教訓,它是五四運動的預演”[6]。
“五二一請愿”以失敗告終,但以鄧中夏等為代表的愛國學生在請愿結束后迅速組織了學生愛國會。隨后,學生愛國會與上海、南京、天津等地學界聯絡,發展成為全國統一的秘密愛國組織——學生救國會。鑒于北京學界在全國學界中發揮著重要的聯絡作用,愛國學生決定將學生救國會總部設立于北京,推舉鄧中夏擔任總務部干事,鄧中夏因此成為該會主要負責人之一。但由于北京政府對學生愛國舉動進行嚴密監視,學生救國會一時難以發揮作用,因而鄧中夏等人決定從創辦雜志入手,率先在青年學生中進行反帝愛國宣傳。1919年1月1日,《國民》雜志創刊號在北京正式面向全國出版發行,其宗旨為“增進國民人格,灌輸國民常識,研究學術,提倡國貨”[7]。《國民》雜志的創刊不僅吸引青年學生關注,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同樣對其產生濃厚興趣。在鄧中夏等人邀請下,蔡元培欣然為《國民》雜志作序,并對雜志提出“正確”“純潔”“博大”的殷切期望。鄧中夏是《國民》雜志主要創辦人,也是主要編輯之一,他對雜志欄目認真謀劃、精心設計,開設《政治·經濟》《思想·社會》《哲學·歷史》《教育》等欄目,深受青年讀者喜愛。《國民》雜志作為五四運動前創辦的刊物,與同期其他刊物相比,突出特點是敢于公開談論政治,具有濃厚的反帝色彩。在李大釗、陳獨秀、楊昌濟等北京大學教授影響下,鄧中夏經常以“大壑”為筆名在《國民》雜志上發表時政評論,先后刊載了《歐洲和議吾國委員之派遣》《鐵路統一問題》《中日新交涉》《國防軍與日本》等文章,批評北京政府。鄧中夏的“這些評述性文章,進一步激發了廣大學生及全國人民的愛國熱情,為即將爆發的愛國反帝五四運動奠定了思想和群眾基礎”[8]。
針對《國民》雜志受眾群體主要為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尚未實現喚醒全國民眾共同救國的現實,鄧中夏開始意識到要善于“用熾熱的熱情去點燃民眾智慧的火花,用孜孜不倦的精神去撥開普通勞動者的心扉,用愛國主義的教育去激發民眾的愛國熱情”[9],希望全國的民眾都能為挽救民族危亡貢獻自己的力量。1919年3月7日,《北京大學日刊》刊登了這樣一則消息:“本校學生鄧康、廖書倉等近發起組織‘北京大學平民教育講演團,以教育普及與平等為目的,以露天講演為方法”[10],并附有《北京大學平民教育講演團征集團員啟事》和《北京大學平民教育講演團簡章》。消息刊登后,成立平民教育講演團一事在北大校園內引起了廣泛討論,許多進步青年踴躍報名。3月26日,以《國民》雜志社成員鄧中夏、許德珩、黃日葵等為骨干分子的北京大學平民教育講演團正式成立。他們分成若干小組,在鬧市區和郊區、工廠、農村等處,進行宣傳鼓動,主要圍繞反對封建迷信思想、提倡科學文化知識等內容進行演講,“后來慢慢增加國內外大事述評,以喚起民眾共同投入反帝、愛國、救國斗爭”[11]。
4月30日,英美法日等列強議定將德國在中國山東侵占的各項權益全部轉讓給日本。次日,英國外交大臣正式將該決定通知正在巴黎參加和會的中國代表團。這一消息傳到國內,社會輿論一片嘩然,愛國學生被徹底激怒。5月3日晚,鄧中夏以《國民》雜志社、北京大學平民教育講演團負責人身份主持召開北大學生大會。他在大會上激憤地表示,不做亡國奴,就要外爭國權、內懲國賊,就要用實際行動抗議和反對帝國主義。學生大會決定次日舉行愛國示威游行,明確要求北京政府拒絕在巴黎和約上簽字。4日下午,北京大學等十余所高校的學生發起了聲勢浩大的愛國運動,鄧中夏作為骨干成員,參與了著名的火燒趙家樓行動,始終站在斗爭最前線。他在五四運動的醞釀、爆發、發展等各個階段都表現得可圈可點,為這一偉大愛國運動取得勝利貢獻了智慧和力量。從北京各高校學生5月4日開始游行示威,到6月28日中國代表團拒絕在巴黎和約上簽字,歷時近兩個月的五四運動告一段落。 5月26日,《每周評論》刊登了作者署名為“毅”的《“五四運動”的精神》,對北京學生在五四運動中的表現作了生動的描述:“這次一班青年學生,奮空拳,揚白手,和黑暗勢力相斗,傷的也有,被捕的也有,因傷而憤死的也有,因賣國賊未盡除而急瘋的也有。這樣的犧牲精神不磨滅,真是再造中國的元素。”[12]
然而,當五四運動進入尾聲時,部分學生對國家和民族的前途感知又回到茫然狀態中,逐漸失去運動高潮時的斗爭銳氣,如有的學生繼續埋頭苦讀,有的學生忙于出國等。但對于鄧中夏等信念堅定的進步青年而言,經過五四運動洗禮,他們積極轉向馬克思主義學說研究,希望從中探索出救國救民道路。正如五四運動武漢地區學生領袖惲代英所言:“國不可不救,他人不肯救,則惟靠我自己;他人不能救,則惟靠我自己;他人不下真心救,則惟靠我自己……自己卻不下真心做,此其所以為亡國奴之性根。”[13]鄧中夏作為五四運動主要組織者和重要領導者之一,全程參與運動,是當之無愧的五四運動急先鋒,思想開始迅速地向激進民主主義轉變。無論是發起成立北京大學平民教育講演團,還是組織學生救國會、創辦《國民》雜志,還是在五四運動中勇立潮頭,鄧中夏都為探索救國救民真理付出了不懈努力。
三、從初步掌握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知識分子到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
在李大釗等人影響下,鄧中夏在五四運動前夕和五四運動中對馬克思主義的認識不斷加深,但在當時他仍以極大的精力投入到各項具體實踐中,“不可能坐下來比較系統地鉆研馬列主義理論”[14]。五四運動斗爭實踐讓鄧中夏明顯意識到及時補充革命理論營養是增強斗爭本領的一劑良藥,尤其他在五四運動中看到了中國工人階級顯示出巨大的力量,他開始以主要精力研究馬克思主義學說。據鄧中夏的北大同學楊東莼回憶,鄧中夏善于在閱讀中捕捉有價值的信息,如他在閱讀《新青年》《覺悟》《每周評論》等雜志時,搜集了大量關于馬克思主義學說和十月革命后俄國政局最新變化的報道,并將其中的重要觀點“摘錄在筆記本上,并經常剪報貼報,分別歸類”[15]。
1919年暑假,為響應李大釗“少年中國”之“少年運動”號召,鄧中夏搬出北大學生宿舍,與羅章龍、楊東莼等十余位同學租住在北京東皇城根達教胡同4號的一個大院,并取名為“曦園”,意為住在這里的青年要像晨曦一樣朝氣蓬勃。鄧中夏居住曦園期間,一方面身體力行地踐行“勞工神圣”理念,更為重要的是他為自己制定了詳細的閱讀計劃,主要圍繞馬克思主義原理的基本觀點,從自然科學、歷史進化、哲學思想、思想史等方面進行研究。鄧中夏還注意與京外學界保持密切聯系,如他與遠在長沙的毛澤東經常相互通信,對毛澤東提出的要把主義和問題結合起來以研究中國社會改造問題的觀點頗感興趣,還將毛澤東寄給他的《問題研究會章程》推薦給《北京大學日刊》全文刊載。盡管曦園設立一年即宣告解散,但對鄧中夏而言,曦園“新生活”是其思想發生重大轉變和產生巨大飛躍的時期,在這一年內“開始了他一生中第二次‘集中學習……奠定了他一生的革命事業”[16]。
1920年3月,在李大釗的指導下,鄧中夏與黃日葵、高君宇、何孟雄等19人在北京大學秘密組織馬克思學說研究會,這是我國最早研究和傳播馬克思主義的團體之一。1921年11月17日,《北京大學日刊》發布一則啟事,對馬克思學說研究會正式進行公開宣傳:“本會叫做馬克斯學說研究會,以研究關于馬克斯派的著述為目的”,“對于馬克斯派學說研究有興味的和愿意研究馬氏學說的人,都可以做本會底會員”[17]。研究會定期召開討論會、報告會,組織會員搜集、翻譯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專門設立一個小型圖書館,取名為“亢慕義齋”(“亢慕義”是英文“共產主義”的音譯)。據1922年2月6日《北京大學日刊》刊載的《馬克斯學說研究會通告》記載,當時亢慕義齋已有介紹馬克思主義的英文書籍40余種,中文書籍20余種,基本上涵蓋了馬克思、恩格斯以及列寧的重要著作,如以英文出版的《共產黨宣言》《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哲學的貧困》《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等,中文書籍有陳望道翻譯的《共產黨宣言》、惲代英翻譯的《階級爭斗》、李達翻譯的《馬克思經濟學說》等。
鄧中夏在馬克思學說研究會中深入系統地學習了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積極響應李大釗提出的“知識階級作民眾的先驅,民眾作知識階級的后盾。知識階級的意義,就是一部分忠于民眾作民眾運動的先驅者”[18]的號召。他通過參加馬克思學說研究會的活動,馬克思主義覺悟得到進一步提升,最終完成了從激進的民主主義者與初步具備馬克思主義思想者的“復合體”,到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的偉大轉變。
隨著北京大學馬克思學說研究會蓬勃發展,以陳獨秀、李大釗為中心形成了一批信仰馬克思主義的青年知識分子,他們開始自覺與工人階級結合,直接在工農群眾中開展各項宣傳活動。正如鄧中夏后來回憶五四運動時強調:“真的‘五四運動中有一部分學生領袖,就是從這里出發‘往民間去,跑到工人中去辦工人學校,去辦工會。”[19]這批青年在工農群眾中的活動為即將開始的中國共產黨創建提供了思想準備和干部力量,同時促進鄧中夏等人開始將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運用于中國革命具體實踐中。1920年9月,鄧中夏積極協助李大釗開始籌建北京共產黨小組。10月,在李大釗帶領下,鄧中夏與北京大學馬克思學說研究會其他骨干成員共同發起成立北京共產黨小組。鄧中夏作為北京共產黨小組發起人之一,在其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并由此正式走上職業革命家道路。在這條布滿荊棘的革命道路上,他希望通過自己的努力“喚醒國民的自覺,打破因襲、奴性、偷懶和倚賴的習慣而代以反抗的創造的精神,使將來各種事業,都受著這種精神的支配而改變”[20],最終實現走上“理想的社會——共產主義的社會——的道路”[21]。
四、結 語
1920年11月25日,毛澤東在《致羅璈階信》中指出:“固然要有一班刻苦勵志的‘人,尤其要有一種為大家共同信守的‘主義,沒有主義,是造不成空氣的……主義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趨附。”[22]鄧中夏正是這般“刻苦勵志的‘人”,他從新文化運動到參與北京共產黨小組創立,不斷在復雜的社會實踐中總結升華斗爭理論,對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認識逐漸深化,并付諸新的實踐。北京共產黨小組成立不久,鄧中夏即受李大釗派遣,赴長辛店創辦勞動補習學校。1921年1月1日,長辛店勞動補習學校正式成立,成為我國北方最早的一所工人學校。鄧中夏在較短時間內確立了工人運動道路的奮斗方向,開始有意識地將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具體問題相結合,“努力研究中國的客觀的實際情形,而求得一最合宜的實際的解決中國問題的方案”[23],踏上了探索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艱辛道路。從意氣書生到革命戰士,鄧中夏對馬克思主義信仰的執著追求和艱苦探索是五四新文化時期進步知識分子探尋救國道路的縮影。
注釋與參考文獻
[1]當時毛澤東為湖南省立第一師范學校學生,楊昌濟則同時擔任湖南高等師范學校和湖南省立第一師范學校教員。
[2][3]張靜如主編:《毛澤東研究全書》卷6,長春出版社1997年版,第5470-5471、5471頁。
[4]馮資榮、何培香編著:《鄧中夏年譜》,中國文史出版社2014年版,第27頁。
[5]曉北、姜偉:《鄧中夏》,中國青年出版社1994年版,第3頁。
[6]孔繁嶺:《中國現代史專題研究》,中國科學文化出版社2003年版,第14頁。
[7]張允侯、殷敘彝、洪清祥等:《五四時期的社團》(二),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79年版,第22頁。
[8]中共北京市委黨史研究室編:《中共北京黨史人物傳》第2卷,中共黨史出版社1994年版,第3頁。
[9]楊軍:《鄧中夏思想研究》,吉林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74頁。
[10]《北京大學平民教育講演團征集團員啟事》,《北京大學日刊》,1919年3月7日,第458期。
[11]曾天雄、李小輝:《試析青年鄧中夏共產主義思想形成中的三次轉變》,《湖南社會科學》2008年第6期,第196頁。
[12][20][21][23]江蘇省檔案館編:《紅色記憶——江蘇省檔案館館藏革命歷史報刊資料選編(1918-1949)》,東南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11、35、35、36頁。
[13]惲代英:《惲代英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35頁。
[14][15]姜平:《鄧中夏的一生》,南京大學出版社1986年版,第33、34頁。
[16][19]鄧中夏:《鄧中夏全集》(下),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685、1354頁。
[17]《發起馬克斯學說研究會啟事》,《北京大學日刊》,1921年11月17日,第894期。
[18]李大釗:《知識階級的勝利》,《新生活》,1920年1月25日,第23期。
[22]毛澤東:《毛澤東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55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