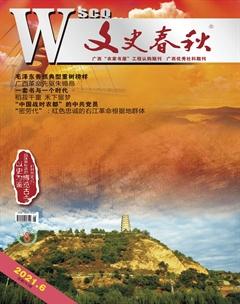傅立魚在大連
李敏
傅立魚(1882—1945),字新德,號西河,出生于安徽英山縣(今湖北英山縣)。1899年考取秀才,1900年于安徽大學肄業,旋以公費赴日本留學,畢業于明治大學分校。在日本留學期間,他加入孫中山創立的同盟會;歸國后,歷任安徽省視學官、巡撫部院參議;辛亥革命期間,參加安徽、江蘇等省的革命軍事行動;南京臨時政府成立時,任外交部參事;國民黨二次革命時,在天津日租界創辦《新春秋報》,因發表激烈反對袁世凱的言論而遭通緝。
1913年秋,傅立魚逃亡到大連,準備去上海時,應一位日本友人的邀請而留在大連。
在大連期間,尤其是五四運動后,傅立魚高擎新思想新文化的宣傳大旗,在《泰東日報》《新文化》等報刊介紹、傳播馬克思列寧主義,這些報刊成為東北地區宣傳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主要陣地之一。
逃亡途中遇知己
在大連,經蒼谷箕藏介紹,傅立魚認識日本著名漢學家金子雪齋。在和傅立魚會面前,金子雪齋曾偶然看到一篇署名“笠漁”的文章,甚為欣賞。“笠漁”正是傅立魚的筆名。因此,他和傅立魚會面后,大有相見恨晚之心,力勸傅立魚到他供職的報社當編輯長。
金子雪齋從小喜歡中國經史,17歲就埋頭苦研中國儒學,后得到中國著名儒學家王治本的悉心教導,漢學造詣頗深。1893年2月,他在札幌擔任《北門新報》編輯,主持撰寫時事評論。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爆發,金子雪齋被征為隨軍翻譯,爾后奉職于臺灣,不久棄職回到東京,繼續研究漢學,并設立振東學會,親自講解中國儒學,吸引了一批留學日本的中國革命黨人,與黃興、宋教仁、張繼等結下友誼。1904年日俄戰爭爆發后,金子雪齋再次被征為隨軍翻譯,后被要求負責搜集、竊取中國機密情報。他稱病拒絕,到大連開辦振東學社,后又創辦日文《遼東新報》。1908年10月,應大連華商公議會之聘,金子雪齋任大連第一份中文報紙《泰東日報》的社長兼編輯長。
起初,傅立魚對于金子雪齋的盛邀存有疑慮。雖然他已經了解到金子雪齋是一位有正義感和同情心的日本友人,其主辦的《泰東日報》,凡中國人不能講、不敢講之事,都會以委婉筆調公諸報端,因而頗受歡迎。但他還是跟金子雪齋約法三章:一是《泰東日報》是中國人辦的報紙,必須為中國人說話;二是遇有兩國爭端及民間糾紛,是非曲直,必須服從真理;三是擔任編輯長是暫時的,一有討伐袁世凱的機會要放行前去。金子雪齋都予答應。后來,傅立魚了解到金子雪齋與中國革命黨人的友誼后,倆人的關系密切起來。
發出時代的呼喚
1915年1月18日,日本駐華公使日置益向中華民國大總統袁世凱遞交企圖把中國的領土、政治、軍事及財政等都置于日本的控制之下的無理要求(即“二十一條”),強迫中國接受,引起中國人民的公憤,金子雪齋支持傅立魚撰文,讓他該怎樣發社論就怎樣寫。后來發生大規模排日和抵制日貨運動,金子雪齋對此表明自己的立場和看法,認為這是中國人不得已而為之,日本是侵略者或侵略主義。金子雪齋的人格和氣節贏得了傅立魚的尊敬。
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后,《泰東日報》陸續登載李大釗、陳獨秀等我國早期馬克思主義者撰寫的文章,成為東北地區宣傳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主要陣地之一。
同年11月28日至12月 10日,《泰東日報》連續刊載由美國記者撰寫的、報道蘇聯十月革命的紀實性專文《六個月間的李寧》(注:“李寧”即列寧,當時的音譯)。該文章是東北地區中文報紙最早觀點鮮明地報道蘇聯十月革命的文章,對于正處在迷茫中的國人特別是青年有很好的點醒作用。它能夠被翻譯出來并見諸報端,有賴于傅立魚的努力和金子雪齋的支持。
1920年3月,日本資本家和田篤郎強占金州三十里堡3000畝左右的水田,當地廣大農民無法生活,很多農民到大連街道游行示威。傅立魚對此事非常關注,向金子雪齋表示要為這些農民鳴不平。于是,《泰東日報》不僅刊載多篇報道支持斗爭并揭露真相的文章,還發表社論《為三十里堡三千農民向山縣關東長官乞命》。金子雪齋不僅支持,還陪同傅立魚趕赴旅順面見關東廳當局,轉呈農民請愿書,指控日本資本家勾結日本官府恃強掠奪農田的行為。當氣急敗壞的和田篤郎以“損害名譽罪”將傅立魚告上法庭時,金子雪齋又親赴法庭為傅立魚辯護。經過長達3年的爭訟,中國農民終于勝訴,三十里堡所有被占的水田都得到一定的補償金。
當年,泰東日報社聚集了大批愛國進步人士和革命志士。關向應(中共早期軍事領導人)1922年從商科學校畢業后,曾在泰東日報社工作。清末秀才畢宗武之子畢庶元曾擔任泰東日報社主筆,后因撰文抨擊日本侵略,被殖民當局驅逐出境。曾任中共大連特支宣傳委員的吳曉天,以泰東日報社編輯的身份為掩護開展工作。
創建青年會
五四運動后,國人日益覺醒,開始尋求自身解放和富國強民之路。
1920年7月1日,傅立魚聯系陳德麟、王建堂等一批有識之士,經過幾個月的努力,創建大連中華青年會(以下簡稱“青年會”),宗旨是“專以輔導青年發揮德育、智育、體育,養成高尚優美之人格,服務社會”,傅立魚被推舉為會長。
青年會是大連地區第一個青年愛國進步團體,它的成立標志著具有民族民主思想的知識分子和不甘當亡國奴的愛國人士的新覺醒。其下設有學校、講演、體育、武術、交際、出版、救濟、童子軍等8個部門。
1921年1月起,青年會講演部在每個星期日舉辦講演活動,定名為“星期講壇”。每次講演一般都在報紙上刊登廣告,講演內容廣泛,既有古今中外的人類社會、自然科學、衛生知識,又有道德修養、婦女解放、游記見聞、時事評論等,主題與青年會宗旨相聯系。講演者除青年會的工作人員,也曾邀請胡適、汪精衛、孫科、歐陽予倩等社會各界名流。共產黨人李震瀛、秦茂軒分別在1924年和1925年應邀發表關于《中國與世界》等題目的講演。據記載,至1926年,星期講壇共舉辦201次,對開闊大連人民的視野、激發民族意識和愛國精神、傳播中國共產黨的革命主張,起到振聾發聵的作用。
1923年元旦后,青年會創立簡易圖書館,除《共產黨宣言》《社會科學概論》《列寧傳》《三民主義》等書籍,還訂閱《新青年》《新中國》《新潮》《覺悟》等國內外著名報刊。
1926年1月,共青團大連地委書記楊志云和傅景陽在聯名寫給中共北方區委的信中道:“中華青年會的星期講壇,完全由我們把持……曾有很多青年來信問我們怎樣和到何處去加入共產黨。此種情形,都是由星期講壇的影響。”(中共大連市委黨史研究室編:《大連中華青年會史料集》)
發行《新文化》會刊
青年會成立后請求許可出版會刊,申請一年之久,日本殖民機關大連民政署才于1923年初勉強允許傅立魚以個人名義出版刊物。傅立魚將刊物定名為《新文化》,同年7月1日正式出版。孫中山先生欣然為創刊號題詞“宣傳文化”。
《新文化》為月刊,是當時東北地區獨一無二的進步刊物,以“發揮中國固有文化之精神,吸收西洋文化之精髓”“開發文化”“改革文化”“謀東北三省文化之發展”“不至為外來文化所風靡”為宗旨,開辟時事評論、哲學、經濟學、史學、文學、青年修養等欄目,每期以傅立魚撰寫的《時事評論》為卷首,以《青年會會務記事》為卷尾。其用稿大部分從北京、上海、武漢、廣州等地征來,有時也轉載國內外報刊上的文章;特約撰稿人主要是全國各界知名人士,如梁啟超、胡適、馬寅初、楊杏佛、陶行知、郁達夫等;曾登載共產黨人李大釗的《史學與哲學》《史學概論》、惲代英的《民治的教育為現代必要之問題》《婦女解放運動的由來和其影響》、蕭楚女的《民治的教育為現在必要之問題》等文章;發表過介紹俄國十月革命的文章,如朱枕薪譯《俄國一九一七年十一月社會革命之回憶》《俄羅斯之赤心》,吳云譯《蘇俄之新印象》等,此外,還發表支持國共合作和喚醒同胞不受帝國主義奴役的文章。
當年,《新文化》不僅在東北三省發行,還發行到上海、北京、石家莊、漢口、廣州等地,不獨在大連,在全國也有相當大的影響。從1924年第三卷第四號起,《新文化》改名為《青年翼》,1925年1月正式成為青年會會刊,到1928年8月被大連日本殖民當局停刊,總計出版7卷67冊。
興辦學校
傅立魚發現大連地區只有十幾處可以讓中國兒童上的小學,無中學;90%以上的適齡兒童不能入學,能夠入學就讀者,也是學習日本語、日本地理和歷史。傅立魚感到有必要提倡創辦社會教育團體,組織中國青少年和工人群眾識字讀書,學習新文化、新思想。
青年會成立后,將教育作為“今日救中國之第一要義”。其《章程》規定“本會會員如果實無資力繳納學費”“二年以上學業優秀,體格強健無疾病者”“如欲向他處求學而無資力者”,經董事會同意,會長可酌量減免其學費或酌量資助其學費。這些規定使大連許多貧困家庭的子弟得到進學校受教育的機會。
青年會興辦的學校分設初小、高小、初中和成人夜學,最興盛時期,中小學和夜學各設9個班,還免費開辦貧民識字班,學生總數有2000余人。學校注重培養學生的愛國觀念,激發學生的民族意識。其教材均采用上海商務印書館和中華書局出版的關內通用課本,學校還供給學生關內出版的進步刊物和課外讀物,如《新青年》《兒童世界》《小朋友》《華盛頓》和《林肯》等,增長青少年的知識,開闊學生的視野。
青年會學校畢業生總計有2000余人。其中不少人升入天津南開中學等內地學府;有的進入黃埔軍校,投身國民革命;有的加入中國共產黨,為中國人民解放事業英勇獻身。
尚武修道
傅立魚大聲疾呼:“古往今來,民族興亡,國家盛衰,無一不是國民元氣的消長,而整日詩酒自娛,游情放逸,國家必定傾覆,民族衰亡。反之,其國民皆尚武修道,加強身心鍛煉修養,使國民之身體強壯,精神剛健,則國家定欲隆盛。”(《大連中華青年會史料集》)在他的大力倡導下,青年會先后成立武術班、游泳隊、足球隊等,經常舉辦表演賽和對抗賽。大連的近代體育由此興起,涌現出劉長春、史興隆等優秀運動員,他們由青年會的賽場走向全國和世界體壇。
1920年7月23日,青年會在老虎灘舉行海上游泳表演,傅立魚率領15位表演者,在上千名市民新奇的目光中縱身躍入大海,這次活動開倡導新風之先河,在社會上引起強烈的反響。
1905年,日本繼沙俄殖民統治大連地區后,每年5月份的第一個星期日開一次運動會,但是禁止中國人參加。青年會成立后,傅立魚等愛國人士決定從1922年開始,在5月的第二個星期天舉行中國人自己的運動會。
1922年5月14日,中華第一屆陸上運動大會隆重開幕,參加的團體有10余個,參賽運動員500余名。到1924年第三屆時,參加的團體達23個,其中日本人辦的金州公學堂、旅順公學堂,沙河口公學會以及電鐵青年團等工人團體均報名參加。更可喜的是,進德女學校的女學生沖破傳統勢力的束縛,也來參加比賽。男女運動員人數有1100余名。
1923年8月26日,青年會舉行第一次中華水上運動大會,到1926年第四次水上運動大會時,一些項目已經超過當地日本人的最好成績。1926年,日本殖民統治當局舉行“滿鐵”游泳大會,邀請青年會的選手參加比賽,這是大連的中國人第一次與日本人在水上公開進行較量,青年會選手不負眾望,奪得6項冠軍。
青年會成立的足球隊,是大連足球發展史上第一支具有現代意義的足球隊。該隊后來相繼獲得1932年至1937年日本殖民主義者組織的各項足球賽冠軍,提振了大連人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在與日本殖民者進行足球比賽中,經常可以看到大連居民簞食壺漿,為足球隊送來飯食、水和慰問品,氣急敗壞的日本殖民當局后來干脆解散了這支球隊。
愛國反帝
因欣賞傅立魚的才華和組織活動能力,日本人以高官厚祿極力拉攏,1921年聘任傅立魚為日本南滿鐵道株式會社囑托,旋又聘為大連市役所議員和南滿洲教育會編輯委員、滿蒙文化協會顧問等職,傅立魚由此成為大連社會名流。但是,傅立魚的表現卻讓他們大失所望,《泰東日報》在數次被處罰后仍然我行我素。
當時在大連以工人的名義公開結社是不允許的,因此,1923年12月,大連滿鐵沙河口工場華人工學會(1924年更名為大連中華工學會、簡稱“工學會”)聘請金子雪齋和傅立魚為顧問,出面向殖民當局辦理合法手續。這是大連地區第一個工會組織,從此大連工人運動進入有領導、有組織的階段。
傅立魚后又相繼被大連中華印刷職工聯合會、中華覺民學校聘為顧問。
1924年8月31日,大連青年會、工學會、中華印刷職工聯合會、中華增智學校、中鐵青年團、埠頭青年團、中華覺民學校等群眾團體代表召開會議,宣布成立大連中華團體有志聯合會,一致推舉傅立魚為委員長。辦事處設在中華青年會會館。該會宗旨是“以謀大連中國人各團體之親睦及合作,以重團體”。
大連中華團體有志聯合會是大連最早建立的具有反帝統一戰線性質的中華社團。該會成立后,大連各中華團體的全市性活動均以它的名義發起和組織,大連人民愛國反帝斗爭力量因此而極大地增強。
同年10月29日,孫科一行完成孫中山交給的與奉軍首領張作霖洽談任務后,應傅立魚邀請到大連青年會作客,孫科發表即興演說,并向青年會捐助大洋500元。爾后,傅立魚向孫科介紹大連的情況,孫科談了廣州的政局和孫中山籌建革命武裝的問題。
1925年3月12日,北上和談的孫中山先生在北平逝世。傅立魚得到消息后,立即發出唁電,組織悼念活動。
5月30日,上海2000余名學生為抗議日本紗廠槍殺中國工人顧正紅的暴行,舉行反帝示威游行,英國租界巡捕開槍鎮壓,制造了震驚中外的五卅慘案。次日,《泰東日報》以《舉國憤怒之上海,外人無理槍殺華人大事件》的文章,揭露慘案的真相。日本殖民當局禁止發售當天的報紙,加強了對工廠、車站、碼頭的警戒和監視。大連特別團支部接到團中央的指示,要求立即組織“三罷”(罷工、罷市、罷課),由于時間倉促,日本殖民當局控制得嚴密,工作未能如期開展。工學會委員長傅景陽電請傅立魚出面指導。傅立魚欣然同意,立即從熊岳城返回大連。
6月15日,大連中華團體有志聯合會召開代表會議,成立滬案后援會,選舉傅立魚、傅景陽、楊志云等9人組成執行委員會,傅立魚為主任委員。會議決定舉行游行示威、散發傳單、開追悼會和募集捐款支援上海工人。
6月21日,滬案后援會舉行五卅殉難諸烈士追悼大會。會后分路游行,沿街呼喊口號,散發傳單,在全市范圍內為五卅殉難諸烈士募捐。1個月的時間內,收到各界捐款11648元,分4批匯寄上海總工會。
日本殖民統治當局對此大為震怒,決定除掉金子雪齋,給傅立魚一個下馬威。他們收買金子雪齋的傭人,在其午睡前必喝的開水中放入毒藥。1925年8月28日中午,金子雪齋無病暴卒于家中。傅立魚揮筆寫下祭文《嗚呼金子雪齋先生》。
1926年2月,國民黨大連市黨部在中共大連特別支部協助下成立,傅立魚被聘為顧問。
3月21日,由大連中華團體有志聯合會發起孫中山先生逝世1周年紀念會。4月28日,中共大連地委通過工學會領導滿洲福紡株式會社(簡稱“福紡”)工人大罷工,此時,失去金子雪齋幫助的傅立魚雖然勢單力薄,但他沒有退縮,領導《泰東日報》支持福紡工人反對日本資本家的斗爭,并對此進行跟蹤報道,直到8月大罷工取得勝利為止。其間,皇姑屯事件發生,傅立魚暗中支持張學良“改旗易幟”。同時,傅立魚還接待途經大連到蘇聯的瞿秋白、蔡和森等共產黨人。
青年會所組織的活動,內容和方法新穎,符合中國百姓的心愿,加入青年會和前來學習的人十分踴躍,到1927年,會員已由最初的400余名,增至3000余名。
堅持反日宣傳
由于青年會堅持不懈的同日本殖民統治當局進行斗爭,因此屢遭日本警察的監視、破壞、迫害,在青年會成立6周年紀念大會上,傅立魚憤慨地告訴大家:“余與同人無一日不在惡戰苦斗之中。”(《大連市政協辛亥革命文匯》)
1928年7月22日,日本殖民統治當局以“擾亂東三省為目的,組織政治秘密結社,策劃種種陰謀”的罪名,逮捕傅立魚,擬判處死刑,后因社會各界的強烈反對,怕激起民變,改為關押15天后驅逐出境。
傅立魚在離開大連之前,剃須明志,來到青年會學校操場告別,他深情地鼓勵大家好好學習,勿忘祖國,大連是中國的領土。
8月17日,大連各界人士前往碼頭送別傅立魚。
傅立魚離開大連后,依然掛念著大連和東三省。1929年,傅立魚在北京創辦《新中華報》,繼續進行反日宣傳。1931年,傅立魚應邀到天津《大公報》從事經營管理工作。九一八事變后,傅立魚主動募捐支持東北的抗日義勇軍。
1932年3月,偽滿洲國成立。8月1日,日本殖民統治當局以“時事關系,中華二字已屬不合”為由,將青年會的“中華”二字去掉,改名為大連青年會,親日派把握領導權。至此,大連中華青年會名不存,實亦亡。
1933年,傅立魚因病辭職隱居。1945年,傅立魚病逝,終年63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