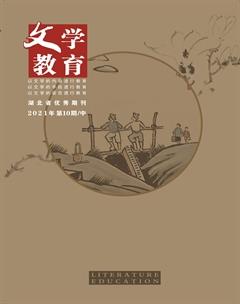從《詩經(jīng)》看西周春秋時期的道路交通
蔡微微
內(nèi)容摘要:自古以來交通就是生活的必要方面,一直與時代發(fā)展息息相關(guān)。關(guān)于先秦時期的交通,雖然可供考究的資料較少,但是發(fā)達(dá)的交通建設(shè)和維護(hù)仍舊可見一斑。《詩經(jīng)》中記錄了不少有關(guān)道路的詩句,生動地再現(xiàn)了西周春秋時期道路建設(shè)、設(shè)施的基本情況,以陸上交通為切入點,為研究該時期社會發(fā)展情況與國家形勢變化提供了獨特的視域。人的社會活動衍生出交通,西周春秋的交通多以陸路為主,戰(zhàn)爭、朝貢、國力、貿(mào)易等諸多因素影響著交通網(wǎng)絡(luò)的興建,同時巨大的交通網(wǎng)也反作用于國家發(fā)展的各個方面。
關(guān)鍵詞:橫向 民族融合 國力 國家發(fā)展模式
《詩經(jīng)》是我國現(xiàn)實主義詩歌的源頭,除卻詩歌的世俗性和沉郁的思想意蘊,它也是研究先秦時期歷史地理的重要文本載體。《詩經(jīng)》中記錄了不少有關(guān)道路的詩句,生動地再現(xiàn)了西周春秋時期道路建設(shè)、設(shè)施的基本情況,以陸上交通為切入點,為研究該時期社會發(fā)展情況與國家形勢變化提供了獨特的視域。
一.西周春秋的交通道路發(fā)展及影響因素
(一)西周時期
1.西周交通道路的發(fā)展
周朝交通道路發(fā)展的歷史幾乎與國家的興衰同步。周朝的經(jīng)濟(jì)生活以固定性的農(nóng)耕文化為主,奔竄于戎狄之間,發(fā)展交通帶有一定的自發(fā)性,目的是生存和發(fā)展,而且多在族群周圍,尚屬于小范圍交通區(qū)域的流動。大型的遷徙活動從未發(fā)起,相對應(yīng)的大交通自然也呈現(xiàn)出凝固態(tài)勢。據(jù)《西周史》所言,后稷至公劉之間從未遷過都。[1]周族自公劉遷都于豳后開始振興,創(chuàng)建國家,統(tǒng)治者能自上而下地聚集民眾的力量興建交通道路,并且讓其成為強(qiáng)制性的工作,因此交通依據(jù)上層意志不斷延伸。但相對先進(jìn)的夏、商處于中原地區(qū),西邊又有戎狄侵襲,周人出于自身發(fā)展的考量,相繼遷都于周原、程、豐、鎬,不斷東進(jìn)。“周人的興起及向東發(fā)展,使當(dāng)時的交通顯得系統(tǒng)化,也顯得網(wǎng)路化。”[2]《詩經(jīng)·大雅》中對于這些大規(guī)模的遷移都有明確的記載,如《綿》《文王有聲》《公劉》等。在此之間,周朝也向四方征伐開拓領(lǐng)土——從季歷開始。以虞國為據(jù)點,趁殷商作戰(zhàn)戎狄的間隙,對山西地區(qū)大力開拓,征鬼方,伐戎狄,因此周朝陸路交通伴隨軍事活動同步向西延伸;及至文王,繼續(xù)用兵西方,并聯(lián)結(jié)諸侯東伐,逐步實行翦商大業(yè),之后的交通發(fā)展就如白壽彝先生所說:“武王克商后,周人的勢力遂渡盟津,而達(dá)于洹上,及周公踐奄,誅飛廉,周人的勢力更東展而到東海之濱。這時,周的南北境雖不見得比殷商廣闊,但東西線路之長,乃得隨軍事及政事的勢力由岐山直到東海,就遠(yuǎn)非殷商所能及了。”[3]隨著周朝的強(qiáng)盛,這條自西向東的交通干線也不斷得到建設(shè)和完善。而且“自夏后氏經(jīng)殷商到宗周,交通區(qū)域的發(fā)展……都是一種橫的發(fā)展。”[3]
無論是殷商自東而西的發(fā)展,還是周朝的自西而東,都在向中心地區(qū)的移動。“天下之中”的位置既充滿中央正統(tǒng)的心理暗示性,也可以由便利的地理延伸出政治的威勢。即使周天子長居宗周,其偏安于西的地理位置不能滿足威懾殷遺民和少數(shù)部族的需要,不利于管理四方。相較而言,“天下之中,四方入貢道里均”[4]的雒邑在監(jiān)督四方、征收貢賦、祭祀行禮等各個方面顯然更有交通優(yōu)勢,成為了西周統(tǒng)治四方的中心,雒邑也利用政治的籌碼加持著它的交通地位。雖然平王遷都于雒后,“由于有些諸侯國的強(qiáng)大,地區(qū)間的交通有所發(fā)展,以雒邑為中心的舊規(guī)逐漸失去其優(yōu)勢,分散到各個地區(qū),從而出現(xiàn)了若干地區(qū)中的一些較小的交通中心。不過諸侯封國往往以尊王為號召,使雒邑交通中心的地位還能夠暫時得以保存。”[2]同樣,距其不遠(yuǎn)而且具備同等交通條件的新鄭成為了春秋時期的交通中心。此時由于西周的自然環(huán)境、生產(chǎn)力和政治等因素,交通區(qū)域的發(fā)展重點在發(fā)展黃河中下游地區(qū),與長江流域聯(lián)系甚少。
2.西周交通道路的建設(shè)與維護(hù)
關(guān)于周朝的交通道路網(wǎng)絡(luò),有學(xué)者指出,周代至少存在以宗周為中心的東、西、南、北四條主干道輻射全國。除了上文的東向干道,西主干道經(jīng)周南、召南、散、矢等國,最終到達(dá)秦國;南向途經(jīng)申國,最終到達(dá)楚國;北向到韓國。[5]P78各諸侯國在主干線上修建一系列互相連接的支線通道,由此匯聚成西周四通八達(dá)的基礎(chǔ)交通網(wǎng)。即使到了春秋時期,西周交通道路也依舊是國家間往來聯(lián)系的大動脈。
西周不僅注重道路的建設(shè),也十分關(guān)注道路的修理與維護(hù)。“關(guān)于道路者,舉出三事。第一,道路按照一定時侯去修理,則潦按照一定時候去坡障,川上按照一定時候建造橋梁。第二,道路旁邊,種植樹木,以作道路的標(biāo)記;四郊設(shè)置屋廬,儲藏食品,作為守衛(wèi)道路的地方。第三,設(shè)置司空,管路路政。”[3]對于這三點,先秦文獻(xiàn)中有著大量的記載,《國語·周語》:“列樹以表道。”[6]《唐風(fēng)·有杕之杜》:“有杕之杜,生于道左。”“有杕之杜,生于道周。”[7]可見道路兩旁種樹的確在當(dāng)時很常見。而相關(guān)的管理隊伍,《周語》中有“司空視涂”,[6]《左傳》中也有“司空以時平易道路”的記載。[8]自周至春秋,國家一直都將道路管理作為政治生活的重要方面從未松懈。而且這種保護(hù)觀念自上而下,深入人心,“岐有夷之行,子孫保之。”[7](《周頌·天作》)正是因為國家的重視與維護(hù),周道才不單只是供人行走的道路,更具有一種盛世泱泱的精神氣象,自有一種威嚴(yán)氣度。“高山仰止,景行行止。”[7]至周朝式微,王權(quán)旁落,交通面貌也破敗不堪,“踧踧周道,鞫為茂草。我心憂傷,惄焉如搗。”[7]
(二)春秋時期的交通道路
在西周建設(shè)的交通基礎(chǔ)上,春秋時期的交通,“在外形之展開上,大體由橫的發(fā)展轉(zhuǎn)成縱的發(fā)展;同時,在交通區(qū)域內(nèi)部之聯(lián)絡(luò)上,也做了許多重要的工作。”[2]其中與長江流域的溝通是轉(zhuǎn)縱的突出表現(xiàn)之一。雄踞于此的楚國此前雖臣服于西周,但卻是暫時性的,西周一直在竭力遏制楚國的北進(jìn),“顯允方叔,征伐獫狁,蠻荊來威。”[7]南北的交通聯(lián)系多伴隨軍事暴力,往來甚少。至春秋時期晉楚爭霸,原本備受歧視的“蠻夷荊楚”由于強(qiáng)盛的國力地位倍增,政治話語權(quán)提高,與華夏諸國頻繁交往;同時,楚國得天獨厚,資源豐富,擁有發(fā)展商品經(jīng)濟(jì)的雄厚資本。因此雖然政治上相持,與中原的經(jīng)濟(jì)交往也不曾中斷。這種商業(yè)的流通沖破了南北的地理障礙和國家壁壘,加快著南北區(qū)域的交通流動。“從春秋初葉起,宗周舊域和長江流域已慢慢地有了一種正常的交通關(guān)系。”[2]春秋的交通外形上就有了縱向的大發(fā)展。
春秋初期各國均勢制衡,周王尚能號令諸侯,而隨著各國力量的消長,周王王公信力衰減,朝聘制度日漸廢弛,各國與東周往來減少,使得洛陽的交通地位大幅度下滑。但是這條東西干道卻因秦國的崛起又恢復(fù)了一定的交通作用,“豐鎬傾覆,這條道路的西段不免失去了重要作用。秦國繼起,雍代替了豐鎬,而雍還在周原之西。這是說這條道路的西段不僅得到恢復(fù),而且還能有所發(fā)展。”[2]P24由洛陽分散的交通力被強(qiáng)大的諸侯國所承接,通過戰(zhàn)爭、聯(lián)姻、談判等手段擴(kuò)大了交通的領(lǐng)域,如齊、晉、秦、楚疆域的變化,“通過春秋時百十年的戰(zhàn)爭,齊先后滅了三十余國,成為東方大國。楚先后滅四十余國,成為南方大國。晉先后滅二十余國,征服四十余國,成為中原大國。秦并十余國,成為西方大國。”[9]除此之外,國家也用和平方式友好地延伸交通區(qū)域,如晉戎聯(lián)姻,魏絳和戎等。春秋大國先發(fā)展出可能的交通范圍,再利用政治影響力以及軍事實力重新對管制的地區(qū)進(jìn)行規(guī)劃管理,整合交通的資源,充實交通內(nèi)部聯(lián)系。另外,春秋各諸侯國漸漸略過周室直接交往,大國稱雄,弱國求存,交通也不似之前以宗周和成周為中心輻射四方,而是形成以幾個大國為主的若干小中心相互聯(lián)系。
二.交通對西周社會的影響
《中國交通史》指出在先秦時,“中國歷史上的最大事件,是民族與民族間繼續(xù)不斷地進(jìn)行著一種混合運動。……周民族與殷民族之間的運動,成了宗周時期的局面。”[3]周族雖也與其他少數(shù)部族發(fā)生沖突,但狹小的領(lǐng)土和粗糙的交通系統(tǒng)使得外部聯(lián)系較少。而且周人明白軍事勝利獲得的僅是暫時性的交通聯(lián)系,只有“翦商”獲得政治上的統(tǒng)攝力才能進(jìn)一步同化或征服天下部族。“后稷之孫,實為大王。居岐之陽,實維翦商。”[7]周朝“橫”的交通發(fā)展就是在逐步拉近與殷商的交通距離,促進(jìn)周、殷民族之間的混合運動;克商后又用交通網(wǎng)絡(luò)將殷遺民分散給主要的封國,如魯國的“殷民六族”,衛(wèi)國的“殷民七族”等,抑制殷貴族的力量,減少民族磨合的阻力。而“天下之中”東都成周的更是便于交通巡視,監(jiān)督管理殷遺民以及調(diào)動軍隊平定叛亂。西周的交通極大地加快了中原各民族的交流,為春秋周民族與蠻夷戎狄各民族間的融合奠定了基礎(chǔ)。
楊升南先生認(rèn)為,“在西周時期已建立起了具有一定規(guī)模的陸上交通路線,這些道路的修建對西周王室實施其對整個國家的統(tǒng)治,具有很大的作用,概括起來,主要有三個方面:1.在政治上便于周王到各地巡察和各諸侯國到王都朝見周天子;2.在經(jīng)濟(jì)上便于周王室向各諸侯國征取貢賦;3.在軍事上便利軍隊的調(diào)動,以加強(qiáng)對各地諸侯的控制和抵抗周邊少數(shù)族的內(nèi)侵。”[10]周王、各諸侯、邊境少數(shù)部族是在交通中鞏固王權(quán)的三方主體,周王巡守諸侯,派遣使臣等行為既正名分又能控制和使用諸侯,從而借此抵御四方夷戎。“時邁其邦,昊天其子之,實右序有周。”[7]《烝民》中也有“出納王命,王之喉舌。賦政于外,四方爰發(fā)。”[7]對于臣服的少數(shù)部族,他們有向王室“歲貢”和“終王”的職責(zé),“昔有成湯,自彼氐、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曰商是常。”[7](《商頌·殷武》)否則武力鎮(zhèn)壓,據(jù)資料顯示在西周王朝先后有二十多次較大的對外戰(zhàn)爭,這背后離不開交通的支撐作用。“荒服者”如此,其余的周室封國更是要履行朝覲、貢賦的義務(wù)。《小雅·采菽》就描繪了諸侯朝王,天子賞賜諸侯的盛況,同樣主題的還有《大雅·韓奕》、《周頌·載見》等。這些政治活動都依靠著西周龐大的交通體系才得以完成。
周人的生活也離不開交通道路。在管理國家具體事務(wù)上,統(tǒng)治者能通過交通頒布政令、巡察街道、勘探資源、開發(fā)山林、貿(mào)易運輸?shù)取τ谄胀ò傩盏纳鐣顒樱绯鲇巍⒓奕ⅰ⑷穗H交往更是與交通道路息息相關(guān),承載他們的喜怒哀樂。奔波趕路的官吏,“厭浥行露,豈不夙夜,謂行多露。”[7]挽留情人的女子,“遵大路兮,摻執(zhí)子之袪兮。”[7]出獵相逢的獵人,“子之茂兮,遭我乎峱之道兮。”[7]辛苦勞作的姑娘,“女執(zhí)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7]無論哪個階級,無論是小到個人行動,大到施行國策,交通行走都是生活的日常。
三.交通對春秋社會的影響
春秋時代是中國大變革的時期,而交通的發(fā)展對于社會的革新無疑具有積極的促進(jìn)作用。“春秋時代的交通相當(dāng)發(fā)達(dá)。這種情形由列國之間會盟的頻繁和戰(zhàn)爭的不時發(fā)生可見一斑。”[11]除了對戰(zhàn)爭與會盟的影響,交通還是國家邦交的重要因素。晉楚弭兵后的盟約“交贄往來,道路無壅。”[8]將道路的通達(dá)作為兩國和平友好的標(biāo)志,而且交通條件也是談判的重要籌碼。如燭之武說服秦伯退兵的理由就是“若舍鄭以為東道主,行李之往來,共其乏困,君亦無所害。”[8]P259解除了秦晉兩國夾擊的困境,促使了兩國的邦交。除此之外,交通也影響著春秋的民族融合、商業(yè)、國家發(fā)展模式等方面。
西周時“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7]殷民族已經(jīng)逐漸滲入了殷商,到春秋時期,民族矛盾的重點在與蠻夷戎狄的碰撞。大國兼并小國的過程,同樣也是周民族與四方部族融合的過程。但要形成“中華民族”,粗魯?shù)能娛率侄沃荒軓牡貓D上抹滅諸蠻夷戎狄的名字,取得文化的認(rèn)同和形成民族精神才是凝聚的基礎(chǔ)。分封制可以說是民族融合的催化劑,周王給予了各分封諸侯征服和開拓封地的權(quán)利,如齊國,“五候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8](《左傳·僖公四年》)于是各封國大肆對周圍地區(qū)開發(fā),壓縮著對方的生存空間,如齊、晉,這種開拓使得交通有了大面積的接觸,雖產(chǎn)生了更頻繁的戰(zhàn)爭沖突,但地域上交通的連接的確成了雙方雜居、通婚、經(jīng)濟(jì)交流的前提,文化習(xí)俗也向中原農(nóng)耕文明靠攏,各族之間生產(chǎn)與生活方式逐漸接近,民族差別也漸漸縮小。
交通對于商業(yè)發(fā)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新鄭商業(yè)的興盛就得益于通達(dá)的交通,成為各國商品的中轉(zhuǎn)站,也是商人獲取商業(yè)信息的最佳地點。雖然春秋的商業(yè)自由流通,不受限制,但各國的政治時事和商業(yè)政策等仍影響商業(yè)發(fā)展。交通的暢達(dá)與否是傳遞商業(yè)信息的關(guān)鍵,誰更快掌握信息誰就能站在商業(yè)的制高點。而各國對于交通的良好建設(shè)與維護(hù)也為商人的長途販運提供了安全條件。同樣以交通發(fā)展商業(yè)的還有齊國。新受封的齊國,土壤質(zhì)量大多為鹽堿地,存在大量未經(jīng)開墾的土地,人口卻不多,只能因地制宜發(fā)展魚鹽等海產(chǎn)和手工業(yè)與其他諸侯國進(jìn)行商業(yè)貿(mào)易,發(fā)展經(jīng)濟(jì)的就是便利的交通條件。國富民強(qiáng)、安居樂業(yè)的齊國才能有底氣進(jìn)行國家政治改革,從外至內(nèi)發(fā)展,稱霸春秋。而鄭國,春秋初期便因交通得益,北靠黃河,西接周王室,再加上蓬勃的商業(yè)得以小霸,可國土褊狹難以長期維持政治話語權(quán),在晉楚等大國強(qiáng)大后反而因為四通八達(dá)的條件成了強(qiáng)國兼并的對象,夾縫生存。再看秦國,首先先天交通條件匱乏,又處于衰落的宗周成周線路的西段,而且東進(jìn)關(guān)卡桃林塞被強(qiáng)晉所遏制,無力東進(jìn),向中原發(fā)展。物質(zhì)貧瘠,不能以外部條件壯大實力,因此,秦國的發(fā)展模式是自內(nèi)到外的發(fā)展。憑借地理上進(jìn)可攻退可守的“四塞之地”,以西活動增加戰(zhàn)略縱深,致力改革和經(jīng)營國家內(nèi)部,以堅實的國力打開交通出口。
人的社會活動自然衍生出交通,而國家創(chuàng)建后的西周春秋的交通發(fā)展更帶有主觀性,或服務(wù)于王權(quán)或爭霸;從橫轉(zhuǎn)縱,從黃河流域發(fā)展到長江流域,卻奠定了中國古代基本的陸上交通基礎(chǔ)網(wǎng)絡(luò)。基于便利的交通,戰(zhàn)爭與和平在中原大地輪番上演,國家間的社會活動也更緊密和復(fù)雜。回顧這段精彩的歷史,交通更是不可或缺的條件支撐,發(fā)揮著積極的作用。
參考文獻(xiàn)
[1]楊寬.西周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2]史念海.春秋以前的交通道路[J].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0(3):9-24.
[3]白壽彝.中國交通史[M].武漢:武漢大學(xué)出版社,2012.
[4](漢)司馬遷.史記[M].北京:中華書局,1950.
[5]羅訓(xùn)鵬,譚德興.從《詩經(jīng)》看周代道路發(fā)展情況[J].樂山師范學(xué)院學(xué)報,2016(5):78.
[6]鄔國義,胡果文,李曉路譯注,周語譯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
[7]金啟華譯注,詩經(jīng)全譯[M].江蘇:江蘇古籍出版社,1984.
[8]趙生群,春秋左傳新注[M].陜西:陜西人民出版社,2004.
[9]朱順龍,顧德融.春秋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10]楊升南.說“周行”“周道——西周時期的交通初探”西周史研究[J].1984(2):65.
[11]史念海.春秋以前的交通道路[J].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0.(3):59.
(作者單位:湖南師范大學(xué)文學(xué)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