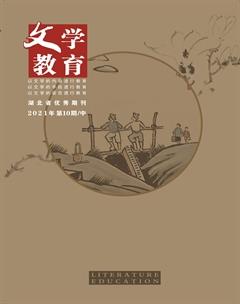花鼓戲《秦雪梅》主角角色的認知
謝婷婷
內容摘要:在舞臺表演中如何走進飾演的角色的心靈,可以說需要去琢磨的太多太多了,如同不可能踏進同一條河流一樣,人都是有認知差的,戲曲表演有著不可復制性的規律。演員的每一次演出都不會完全一樣,一定會有一些即興的創造。觀眾也會有新的感覺和新的藝術享受,這種鮮活的舞臺呈現讓觀眾感受到戲曲靈動的斑瀾色彩和美學價值。
關鍵詞:戲曲表演 舞臺藝術 秦雪梅 荊州花鼓戲
作為一名花旦演員,當我拿到《秦雪梅》的劇本,飾演秦雪梅的時候,對我卻產生了一定的挑戰,因為飾演秦雪梅和我之前飾演的旦角有著很大的區別。《秦雪梅》是荊州花鼓戲的傳統保留劇目,在江漢平原可以說家喻戶曉,作為國家非物質文化傳承人,我有責任也有義務把這出戲傳承下去。
花旦在荊州花鼓戲旦角行當中占有重要地位,是花鼓戲舞臺上一道亮麗的風景。它分有“閨門旦”“玩笑旦”“潑辣旦”“刺殺旦”“小旦”等五種。“閨門旦”扮演的是還沒有出嫁的少女,其中性格內向、靦腆的,一般都是大家閨秀,大門不出,二門不邁,如荊州花鼓戲經典名劇《站花墻》中的王美蓉、《秦雪梅》中的秦雪梅。“玩笑旦”扮演的是喜劇、鬧劇中愛說愛笑、好打好鬧的人物。我之前扮演大多是像《站花墻》里春香丫鬟一樣,大大咧咧、風風火火,快言快語、熱情好動。《秦雪梅》中的秦雪梅確是一個大家閨秀,文質彬彬,受封建社會的束縛,一言一行,獨顯深閨小姐的矜持。因此,如何走進秦雪梅的心靈,需要進一步的探索,是擺在我面前的一個挑戰、一道難題。
作為湖北三大地方戲之一的荊州花鼓戲,是江漢平原廣大人民勞動生活的產物,是楚文化的重要表現形式之一。荊州花鼓戲極具生活氣息,源遠流長、博大精深。
花鼓戲的“美乃是靈魂與自然相一致所產生的結果。”首先,花旦的臺詞能夠幫助演員成功的塑造人物形象。眾所周知,人物形象的塑造通常是從動作、語言、神態、心理活動幾個方面來著手,那么戲劇表演作為一種舞臺形式,有其局限性,《秦雪梅》的臺詞刻畫人物就顯得更加必要而且至關重要。別出心裁的花旦臺詞給戲劇注入生命,優秀的演員不僅可以準確的表現出作者的意圖,還可以更好的發揮,使人物形象越發生動傳神,獨具特色。
荊州花鼓戲《秦雪梅》給人感到身臨其境,為劇中人物的幸福而歡呼雀躍,也會為花旦角色的命途多舛而感慨萬千。這就要求在飾演秦雪梅時情感上無可比擬的感染力。除了荊州花鼓戲獨具魅力的音樂外,秦雪梅作為花旦的表演藝術是最具殺傷力的情感炮彈,很多表演藝術能夠在一瞬間觸碰到觀眾心靈最脆弱的地方,再加上動情的表演自然讓人聞之落淚;同理,諸如《站花墻》中春香丫鬟獨具喜劇色彩的臺詞也常常采用強力度的語言,能夠烘托出歡喜的氛圍,讓人不由心生喜悅,這便是花旦的神奇之處。作為一名優秀演員,能夠正確把握并詮釋花旦舞臺是必須具備的基本功,在處理表演舞臺時不能機械訴說,不能千人一格,而是要力求準確的把握和處理各種表演,如《秦雪梅》舞臺上的語調的高低,語氣中的抑揚頓挫等與表演中塑造的角色合二為一,舞臺表現是花旦演員表達思想感情的手段,花旦演員要真實感受人物,跟著人物感覺走,使臺詞成為發自內心的由衷之言。這樣,才能感染觀眾,體現花旦在戲劇表演中舞臺情感表達的作用。
《秦雪梅》是一出在演出過程中不斷完善的戲。這和荊州花鼓戲《站花墻》一樣。我在荊州花鼓戲《站花墻》中飾演的春香丫鬟,和胡新中和李春華老師搭檔多年,對這出戲,對人物的表演略有一點點體會。
《站花墻》原本只有《梳妝》、《摘花》、《站墻》幾折,屬典型的荊州花鼓戲“三小”戲。表現的是小生小旦的愛情和丫環穿針引線的情節,延續至今近百年。在演出的過程中,各專業劇團不斷整理改編,陸續增加了“趕考”“認婿”“對詩”“換獄”“探監”“法場”等戲,擴展為一個完整的大型戲。上世紀80年代,珠江電影制片廠將《站花墻》更名為《花墻會》,拍攝成彩色戲曲片在全國發行放映。無論是舞臺本還是影視本,各類各團各有版本不同,但“梳妝”“摘花”“站墻”始終是該劇的核心和亮點。尤其是“摘花”表演,永遠是觀眾的重要看點。隨著歷史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摘花”技藝不斷地豐富更新,成為一朵永不凋謝的玫瑰。而表演“摘花”絕活的春香丫環,從來都是全劇的重要人物,光彩照人。
春香所以搶眼,首先是因為她有一顆善良的心。她雖然只是個天官府千金小姐的貼身丫環,但卻憑借她純樸的品質和靈巧的能力,以年輕的生命代價成就了劇中主人公揚玉春與王美蓉的美好姻緣。而春香丫環耀眼絕倫的“摘花”、“梳妝”、“鴨子步”等絕技表演,則是她吸引觀眾眼球的另一重要原因。
“摘花”絕活最早是荊州花鼓戲“四大門頭”的掌門人汪春保先生,根據江漢平原一帶出嫁、陪嫁和鬧洞房過程中“認花”、“報花”、“摘花”的喜慶習俗編創的。最初只能摘三四朵花,舞臺上的花是在開演前臨時向觀眾借用的實花。后來發展到五六朵和七八朵。到荊州花鼓戲先輩程蘭亭、胡憶菊等老師時,舞臺上所用之花已開始采用絲線制作,數量也增加到了十余朵。
春香的第一次出場是一段“占子”道白:“一棵樹彎又彎,一長長在太行山。太行山鳳點頭,我是王府的小丫頭……”這段念白,本是傳統的“自報家門”程式,但卻不能以傳統的程式化表演進行演繹。這段念白在文學上富有詩意,在內容上超出了傳統意義上的“姓甚名誰,身份地位”的自我介紹套路。因此,在表演方面,除盡力突顯其詩韻風格外,還應表現出春香這一人物的個性特點。語氣方面應剛勁中含幽默,調侃里顯威嚴,突顯春香這個小人物的剛正不阿與活潑可愛性格。我在語言表達上力求字正聲清,情緒方面則盡量明快輕松,節奏與擊樂鼓點嚴絲合縫,形體與眼神配對渾圓。當念道“哪一個大膽的惹了我——嘿嘿——”,我配合插腰動作,夸張性的做聳肩擺頸、搖頭閃眼,最終將某一觀眾席位作為舞臺視點,霸氣中略顯嬌嗔地道出“我就與他不罷休!”使一個正直聰慧而勇敢活潑的丫環小人物活現于觀眾眼前。
“梳妝戲”是在美蓉小姐被說服外出之后。因此,春香的此段戲應比前段戲更為歡快熱烈,整個梳妝的節奏和動作應更加明快緊湊。比如擺放銅鏡、擦鏡持梳、捋絲顧盼、左右打理等形體表演,應力避施沓繁瑣,盡量流暢俐索、干脆輕快。來到花園之中,從認花報花、觀花賞花到贊花摘花,是整場戲的高潮和亮點。
結合我飾演《站花墻》春香丫鬟的經歷,可以說我對人物的內心有一定的了解,但飾演《秦雪梅》里的雪梅難度更大,對走進雪梅的內心有著更高的要求。
每一個有經驗的演員,平時都很留心觀察生活,并將生活中美妙的事例存在腦海備用,一旦在某一個戲某一個角色需要排練的時候,就會和大腦中的人、事聯系起來構成形象思維——這就是所謂的“角色種子”。
秦雪梅這個角色作為花旦雖然并不是花鼓戲表演的全部,但卻是它的精髓所在。一場深入人心的戲劇表演必然離不開精彩的舞臺詮釋,運用唱念做打舞等各種程式技藝,運用外部的表演形式刻畫中華民族的古典美,道德美,心靈美。
《秦雪梅》是一出膾炙人口的荊州花鼓戲,“觀畫”是該劇中的經典一折,重點反映了商林和秦雪梅的愛情。
世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愛,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恨,很多傳統戲里面的小生小旦一見面就愛的死去活來,那是原始的沖動,沒有感情的愛,使人感到空虛和尷尬,傳統的《秦雪梅》就是這樣的一出戲,雪梅和商林的感情沒有依據,就憑一紙婚書商林氣極而亡,雪梅碰靈而死,無緣無故的為封建主義付出了生命的代價。
編劇在改編時,著重加強了兩個青年人的感情戲,豐富了《觀畫》時的思想交流,他們二人從小在一起讀書、一起游戲、一起長大,失足落水,救命結緣,描容觀畫、吟詩作對等等情節。回憶少年的時候青梅竹馬、兩小無猜,內心感情自然流露,因此,給雪梅和商林空洞的內心增加了許多真實內涵和情感,也因造訪觀畫,勵志共勉而加深了兩個年輕人的情愫,為后面的戲產生了令人信服的鋪墊。
秦雪梅不是鄉野村姑,她是皇親國戚(她姐姐秦雪納在西宮伴駕),雪梅知書達理,自幼接受封建主義的傳統教育,她對商林有深入肺腑的愛,但她又不敢跨越雷池一步,她行為穩重,舉止端莊,身在相國府第,在父親等級觀念的淫威下,只能屈服,不敢爭斗,不求同生但求同死,做了封建禮教制度下的殉葬品。
《觀畫》一折是《秦雪梅》中承前啟后的愛情戲,第一場投親是鋪墊,第二場《觀畫》是描述雪梅和商林純真的愛情,唱腔和表演并重。做為相國府的千金,暗訪書齋私會男友本來就“違章”但她忠于愛情,大膽的走了這一步,繼而看見畫像和詩詞,頓生愛意。當商林突然回到書齋,馬鑼加滾錘的打擊樂伴奏,雪梅合著擊樂的節奏顯得驚慌失措,慌亂中躲在扇后唱出“只嚇的雪梅女無處藏身”極為貼心地表現出少女的矜持……隨后又不時的在扇后、水袖下偷窺商林。恰到好處的表現出少女的羞澀和對商林的愛意。這一切為后面的《商林歸天》《雪梅吊孝》留下了可信的伏筆。唱不好《觀畫》就絕對演不好《吊孝》,只有掌握了人物的內心才能準確的決定人物的行動。
《秦雪梅》是一出對唱腔要求極高的戲。在舞臺表演中如何走進飾演的角色的心靈,可以說需要去琢磨的太多太多了,就像你不可能踏進同一條河流一樣,人都是有認知差的,戲曲表演有著不可復制性的規律。比如聆聽名家錄音或者觀看光盤錄像,至多一兩遍就膩了,但是看他(她)們的現場演出,往往十遍百遍興致不減。這是什么緣故呢?這是因為,演員的每一次演出都不會完全一樣,一定會有一些即興的創造。觀眾也會有新的感覺和新的藝術享受,這種鮮活的舞臺呈現讓觀眾感受到戲曲靈動的斑瀾色彩和美學價值。
(作者單位:湖北省花鼓戲藝術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