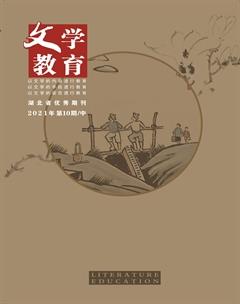“X+得我不行”的構式解析及話語功能
章近勇
內容摘要:從構式語法角度探討網絡和日常口語中構式“X+得我不行”的構式義和話語功能。通過對構式常量“我”“不行”和變量“X”的互動關系分析,探究其構式義——主體對出乎意料的情態的強調和褒貶評價的浮現機制。基于其構式義,我們發現其話語功能有評價性和理據性。
關鍵詞:構式 互動機制 意象圖式 褒貶評價
現代漢語中,可以看到形如“嚇得我不行”這樣的“X+得我不行”結構,表某情態的極性,以描述“我”的評價,暗含主體的某種需求。基于Goldberg(1995)的研究,C是一個構式且C的形式或意義的某些方面不能從C的構成成分或其他先前已有的構式中得到完全預測。因為“X+得我不行”的“評價或強調”義是無法從其構成成分直接得出,所以我們推知結構“X+得我不行”具有不可預測性,是一個典型構式。
一.“X+得我不行”的構式解析
“X+得我不行”的構式義可概括為主體對出乎意料的情態的強調和評價。其中“出于意料”“強調”“評價”義既不能由“X”也不能由“我不行”推知,例如:
(1)困得我不行,好幾次早上起來睜不開眼睛,去衛生間時迷迷糊糊直接撞門上了。(木星《愛情落地簽》)
上述用例中,“困”“折騰”“冷”都超越了主體對某一情態的預期,呈現出“出乎意料”的意義。例(1)“困得我不行”表達主體對“困”的強調,由此詮釋下文“撞門”的合理性。由此可見,“X+得我不行”的構式義是由變量“X”和常量“我”“不行”來浮現的,下文將分別通過對常量和變量的分析探究其構式義浮現機制。
(一)“我”及其主觀性
“我”作為第一人稱代詞指主體自身,具體來說用于主體的情感和狀態及對某事某物的態度和評價,因此呈現出強主觀性,從而表現出“X”和“我”在認知和情感上的刺激反應關系。構式的主觀性可以通過對比“X+得我不行”與“X+得不行”看出,例如:
(2)即便餓得不行了,吃一小塊瘦肉,也沒增加多少熱量,這一天也會是很成功的。(李斕編《28天懶人減肥計劃》)
(3)這會兒是什么也好,就是我總吃不飽,餓得我不行!(衛明喜《往事不寂寞 裴鴻恩口述平遙軼事》)
對比例(2)與例(3)中的“餓得不行”與“餓得我不行”,在前者中,張誼生(2000)認為“不行”是一個正在形成中的唯補準副詞,表示程度深;在后者中,“餓”是“我”的狀態,整個結構呈現主體對“餓”的刺激反應,表達難以忍受的主觀情感。“我”表明了“X”直接起作用的對象,強調了主觀性,為表達主觀色彩和強烈語氣建立基礎。
(二)“不行”及其評價義
“不行”一般意義為不可以、接近死亡等;作準副詞時,用在“得”后面表示極性。“不可以、接近死亡”表達的都是將要達到某種極限,結合“我”的主觀性能夠讓構式在識解的過程中表達出評價義,例如:
(4)暑熱盛夏酷暑已來臨,真是熱得我不行。汗流浹背又焦躁,如此哪有好心情?(賈旭磊《新世紀作家 2003年鑒》)
(5)誰知道我們的江南水鄉也會吸引霧霾光臨?咳嗽得我不行。(陳楫寶《白手套 一類特殊人群的財富秘密》)
羅耀華、周晨磊、萬瑩(2012:362)認為人類認知不同范疇的方式不盡相同,其基本的認知能力體現為心智掃描,包括“總括掃描”和“次第掃描”。因此,例(4)和例(5)中,“熱得我不行”和“咳嗽得我不行”中的“熱”和“咳嗽”都是先和“我”組合,即:我(感到)熱、我咳嗽,這一過程反映了主體認知的次第掃描。而后“不行”是與“我(感到)熱”“我咳嗽”共同起作用的,反映了認知的總括掃描過程。構式中的“不行”居于主體反映的最關鍵地位,描述的是“熱”和“咳嗽”在當時的環境下對主體心中的某種界限的逼近甚至超越,主體形成的整體畫面即自身的底線被某情態所超過。林正軍、王克非(2013)提及感知經驗以認知意象的形式呈現在人腦中,經過大腦的認知加工形成一些基本的概念結構。因此,構式表達出主體對這種“超越”的評價。
將“X+得我不行”與“X+得我不行不行”進行對比更可以看出其評價性,“不行”的重疊形式可以理解成“連續超越”,例如:
(6)我表姐家小外甥女,長得跟洋娃娃似的,喜歡得我不行不行了。(陸濤波《誰的青春不怒放》)
(7)你那圈女是好閨女。喜歡得我不行。(河北省戲曲研究室《河南戲曲傳統劇本匯編》)
例(6)中,“喜歡得我不行不行”是對主體心中關于“喜歡”的標準的二次超越,對比例(7)中的一次超越,前者更加能夠將“評價”義放大化,所以在客觀描述到主觀評價的過渡關系。所以,“不行”表示“X”對主體心中某種界限的超越,通過識解可知,“不行”隱含的超越義描繪出一種“出乎意料”的狀況。
(三)“X”及其準入條件
我們隨機統計了BCC語料庫和新浪微博中“X+得我不行”構式,共108個用例,其中“X”為單音節形容詞和動詞為主,并且都具有[+能感知]的語義特征,即“笑、氣、感動、折磨”等動作和“困、萌、冷、熱”等描述都是能被主體所感知。詞類對構式義有一定影響,以下分別從形容詞和動詞這兩個詞類對“X”的準入條件作具體分析。
1.動詞
當“X”為動詞時,能進入“X+得我不行”這一結構中的“X”主要有行為他動詞、行為自動詞、心理活動詞這三類。
當“X”為行為他動詞時,主要有虐、折磨、嚇、吵、逼等,“X”直接作用于主體身上,以致超過了主體承受限度,例如:
(8)和家里人通完平安的電話后,思鄉愈來愈折磨得我不行,我當時下了決心:無論如何我得回去了。(北京文學雜志社《2004中國文學最新作品排行榜》)
當“X”為行為自動詞時,主要有笑這個動詞,表示“我”因為句中某事物而導致“笑”地逼近了主體的能力限度,例如:
(9)馬揚也點了不少高音歌,唱到高潮還會走調,笑得我不行。(飛藍飄雪《假如不曾愛過》)
當“X”為心理活動詞時,主要有氣、感動、樂、擔心等,表達“我”的心理情態的極性,并隱含著主體的評價,例如:
(10)小時候你對我多壞啊,虧我那么多年還以為你是為我好,所以對我那么嚴,感動得我不行。(無袖攏香《太后也瘋狂》)
2.形容詞
當“X”為形容詞時,主要是表達主體對可感知到的事物性質的評價,如:冷、熱、燙、冰、痛、疼、美、帥等,大體有事物溫度、褒貶事物、主觀情態這三類,都是通過其對主體的作用和影響體現程度,以激發主體對其評價。例如:
(11)三四年之前在東北,一個冬天,喝酒,完了在外面等車,風吹受寒了,冷得我不行。(田原,趙中月主編《中醫人沙龍》)
上述用例都說明了“X”是主體感知到的事物性質,主體通過這種性質對自己心理基線的超越來表評價。
二.“X+得我不行”的話語功能
曾君、陸方喆(2013)認為構式語法把詞匯、語法、語用作為一個整體來分析,對構式的分析采取“所見即所得”的方法。構式“X+得我不行”的話語功能也可采用這一方法,發現其具有評價性和理據性。
(一)評價性
“X+得我不行”的主觀評價性來源于句子成分與“我”的互動關系,以及“不行”暗含的“逼近或超越”某一心理限度義所激發的主體評價,例如:
(12)這創意我是服氣的,萌得我不行。(新浪微博)
例(12)中“萌得我不行”是對這個創意的主觀評價,創意的“萌”刺激了“我”,我做出肯定、贊揚的評價。
(二)理據性
“X+得我不行”能夠為表達主體某種潛在需求提供理據。例如:
(13)因為去了一批軍代表,幾天幾夜的車輪大戰,實在困得我不行。(王永久《傳奇作家陳登科》)
例(13)中的“困得我不行”描述的“困”的狀態的極性為“我”想要休息的潛在需求提供理由,也為其評價充當理據。
構式語法為“X+得我不行”的研究提供了一條新的解釋途徑。正如張娟(2013)表示構式義“不可預測性”的顯著化是構式語法成為一種新的語法理論的關鍵。本文對構式“X+得我不行”從構式義和話語功能兩個角度進行了探析,其構式義為主體對出乎意料的情態的強調和褒貶評價;該構式的話語功能主要體現在評價性和理據性。
嚴辰松(2006)認為凡是構式都有自己獨立的形式、語義或功能。通過對構式的常量“我”“不行”和變量“X”的分析,我們能得知其整體意義的生成機制。常量“我”讓構式帶有主觀性的特點,常量“不行”與“我”“X”的互動機制是評價義產生的原因。通過統計,我們從動詞和形容詞這兩個方面分析變量“X”的準入條件,一般只有[+能感知]語義特征的動詞或形容詞才能進入該構式。該構式具有評價性和理據性。評價性是主體對逼近或超越一定范圍的情態的應激反應,需要以其所表達的極性情態為理據。
參考文獻
[1]林正軍,王克非. 論非典型復雜構式產生的理據性[J].現代外語(季刊),2013, (4):364.
[2]羅耀華, 周晨磊, 萬瑩. 構式“小OV著”的構式義、話語功能及其理據探究[J].語言科學,2012, (59):362.
[3]王寅. 構式語法研究:理論思索(上卷)[M].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11.
[4]嚴辰松. 構式語法論要[J].解放軍外國語學院學報,2006, (4):7.
[5]張娟. 國內漢語構式語法研究十年[J].漢語學習,2013, (2):65.
[6]張誼生.程度副詞充當補語的多維考察[J].世界漢語教學,2000, (52):4.
[7]曾君, 陸方喆. 認知語言學與漢語第二語言教學[J].云南師范大學學報(對外漢語教學與研究版),2013, (1):5.
[8]Goldberg, Adele E. Constructions: A construction grammar approach to argument structure[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5.
(作者單位:上海交通大學人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