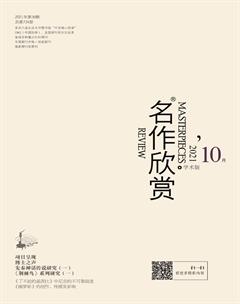重塑英語文學(xué)研究的格局與秩序
摘 要:朱振武教授的專著《非洲英語文學(xué)的源與流》,對非洲英語文學(xué)的緣起、發(fā)展與流變進(jìn)行了清晰的梳理和歸納。這一學(xué)術(shù)成果于我國學(xué)界大有裨益,有利于我們重視非洲英語文學(xué)研究,從而重識英語文學(xué)的疆界與圖景;有利于我們重構(gòu)英語文學(xué)的研究格局,并彰顯非洲英語文學(xué)研究的獨(dú)特價值;有利于我們重塑非洲英語文學(xué)的學(xué)術(shù)秩序,讓我們既關(guān)注文化價值論和社會功能論的認(rèn)知范式,又重視文學(xué)審美論的批評模式,以此彌補(bǔ)非洲英語文學(xué)批評話語研究相對闕如的現(xiàn)實狀態(tài),最終以非洲英語文學(xué)研究助推中非戰(zhàn)略交流與合作。
關(guān)鍵詞:非洲英語文學(xué) 地理圖景 研究格局 學(xué)術(shù)秩序
朱振武教授于2019年在上海人民出版社推出的新著《非洲英語文學(xué)的源與流》(以下簡稱《源與流》),系其對“非主流英語文學(xué)”十余年關(guān)注和研究的新結(jié)晶,構(gòu)筑起一道非洲英語文學(xué)研究的新景觀,也成為朱振武最新的代表性成果,其中閃現(xiàn)的思想和智慧,勢必有效推進(jìn)我國非洲英語文學(xué)研究的新進(jìn)展,勢必在重塑我國英語文學(xué)研究格局和學(xué)術(shù)秩序的努力中產(chǎn)生積極的促進(jìn)作用。
一、重識英語文學(xué)的地理圖景
《源與流》指出,“英語文學(xué)擴(kuò)容是英帝國殖民拓展與英語的世界化帶來的必然結(jié)果”。以英語為媒介的文學(xué)書寫,在地域分布上本來有著寬廣的范圍,不僅包括英國和美國,還廣泛涉及非洲、美洲、大洋洲、亞洲、歐洲的很多國家和地區(qū)。但長久以來,學(xué)界重視英美文學(xué),以英美文學(xué)代指英語文學(xué),縮小了英語文學(xué)的指稱范圍,窄化了英語文學(xué)的地理圖景,讓強(qiáng)勢的英美文學(xué)掩蓋和遮蔽了其他國家和地區(qū)的英語文學(xué)成就,這明顯有礙于英語文學(xué)的整體觀照,很容易在無形中銷蝕掉非英美國家英語文學(xué)的獨(dú)特貢獻(xiàn)。之所以出現(xiàn)這種局面,一方面是由于歷史上殖民心理的余波在作祟,另一方面則與政治、經(jīng)濟(jì)、軍事、文化的國別實力有關(guān)。英國曾經(jīng)是“日不落帝國”,美國更是現(xiàn)今的超級大國,兩國的影響力奠定了其文學(xué)的國際地位。但是,一向被忽視、被冷落的非英美國家的英語文學(xué)書寫,并不是一個可有可無的存在;相反,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印度、新加坡、拉美國家開始勃興,非洲英語文學(xué)也異軍突起,備受矚目,其文學(xué)成就已經(jīng)得到國際文學(xué)界認(rèn)可,其文學(xué)作品連獲國際文學(xué)大獎,像拉賓德拉納特·泰戈爾(1913)、沃萊·索因卡(1986)、納丁·戈迪默(1991)、維迪亞達(dá)·蘇萊普拉薩德·奈保爾(2001)、約翰·馬克斯韋爾·庫切(2003)等作家甚至將諾貝爾文學(xué)獎收入囊中,這無疑給英語文學(xué)界帶來了巨大的沖擊和震撼,人們開始重新審視英美以外的英語文學(xué)作品,開始重新認(rèn)識英語文學(xué)的地域構(gòu)成,而《源與流》一書,對非洲英語文學(xué)的歷史嬗變和當(dāng)下發(fā)展做出了清晰的勾勒和闡釋,在幫助我們重識英語文學(xué)的地理圖景方面頗具開創(chuàng)之功,極富啟示意義。
在《源與流》中,朱振武先后提及“非主流英語文學(xué)”和“非英美英語文學(xué)”的概念,兩者所指意涵大致相同,都是指英美以外的國家和地區(qū)用英語寫作的文學(xué)作品,其中,非洲英語文學(xué)逐漸蔚為大觀,已經(jīng)成為“非主流”英語文學(xué)的重鎮(zhèn),正在獲得學(xué)界越來越多的關(guān)注和重視。也就是說,英語文學(xué)的地域空間得到拓展,非英美國家的英語文學(xué)正在從“非主流”向著“主流”遞延,這必將改變英語文學(xué)研究的面貌,因為“非英美國家英語文學(xué)創(chuàng)作的崛起拓展了文學(xué)研究的范圍,使得開展文學(xué)研究基于的文本跳出了歐美中心主義的藩籬”,各種文學(xué)理論和批評流派也在世界范圍找到了更大的操演舞臺。按照朱振武的判斷,英語文學(xué)從“一枝獨(dú)秀”的英國文學(xué)到“花開兩朵”的英美文學(xué),然后在全球范圍內(nèi)“開枝散葉”的發(fā)展演變,正是英語文學(xué)從英美本土向非英美國家擴(kuò)散的過程,正是在這一發(fā)展過程中,非英美國家英語文學(xué)體量不斷增大,藝術(shù)境界不斷提升,創(chuàng)作特色日益彰顯,文學(xué)貢獻(xiàn)成就斐然。這就勢必要求英語文學(xué)研究做出適當(dāng)?shù)恼{(diào)整和變更,將這些文學(xué)書寫納入學(xué)術(shù)視野,進(jìn)行深入研究,從而一新中外學(xué)界英語文學(xué)研究的面貌。細(xì)讀《源與流》,我們首先會形成三點(diǎn)深刻的印象:一是非洲英語文學(xué)分布范圍極為廣闊,它覆蓋了南非、西非、中非、東非等幾千萬平方公里的區(qū)域面積,涉及人口規(guī)模達(dá)十億以上,重要性不言而喻;二是非洲英語文學(xué)作品繁多,其中不乏精品佳構(gòu),在主題思想和藝術(shù)創(chuàng)新方面毫不遜色于英美文學(xué),南非、尼日利亞、肯尼亞等國堪稱典型;三是特殊的地理景觀和歷史境遇造就了非洲英語文學(xué)的族裔特色和反殖民特征,這尤為學(xué)界看重。基于這樣的印象,我們會憬悟于非洲英語文學(xué)向來不被重視的弊端,會警醒地重新規(guī)劃英語文學(xué)的疆界,會重新調(diào)整英語文學(xué)研究的版圖,畢竟均衡吸納和借鑒世界各國文學(xué)和文化的精粹,“才能持續(xù)推動包括中非文學(xué)在內(nèi)的中外文學(xué)文化間的交流,才能在‘中國路、中國夢與‘非洲路、非洲夢的交互中更好地弘揚(yáng)中國文化,從而為樹立高度的文化自信、文化自覺和建設(shè)社會主義文化強(qiáng)國添磚加瓦”。在逆全球化暗流涌動的今天,在個別國家孤立主義、單邊主義和民粹主義盛行的今天,加強(qiáng)中非交流與合作對于我國有著特殊的戰(zhàn)略意義,而體認(rèn)非洲英語文學(xué)的重要性并加以深入研究,自然是中非交流合作應(yīng)有的題中之意。《源與流》啟示我們,在“主流”與“非主流”的演進(jìn)變幻中,非洲英語文學(xué)正在發(fā)生位移,正在形成新的中心,正在受到中外學(xué)界更多的關(guān)注。重視非洲英語文學(xué),重識英語文學(xué)的地理圖景,不光有益于學(xué)界與學(xué)人,更對我國的戰(zhàn)略發(fā)展具有重大現(xiàn)實意義。
二、重構(gòu)英語文學(xué)的研究格局
英語文學(xué)地域分布的新圖景,要求我們適時擴(kuò)大學(xué)術(shù)研究的視域,適當(dāng)調(diào)整學(xué)術(shù)研究的格局,對包括非洲英語文學(xué)在內(nèi)的非英美國家英語文學(xué)給予足夠的重視。
在非英美/非主流英語文學(xué)的整體脈絡(luò)中,《源與流》聚焦非洲英語文學(xué)的發(fā)展流變,概括非洲英語文學(xué)的流散特征,按國別梳理非洲英語文學(xué)的肇始、勃興與影響,探討非洲英語文學(xué)的主題意蘊(yùn)與藝術(shù)表征,以津巴布韋為中心揭示非洲殖民英語文學(xué)的創(chuàng)作傾向,并在界定流散文學(xué)的基礎(chǔ)上回顧相關(guān)研究,最后描繪出我國非主流英語文學(xué)研究的概貌,提示出非主流英語文學(xué)研究的走勢和趨向,為我們研究非洲英語文學(xué)提供了基本的學(xué)術(shù)框架。
《源與流》明確指出,非洲英語文學(xué)與傳統(tǒng)的英美文學(xué)判然有別,存在著明顯的差異性,這就決定了非洲英語文學(xué)研究的獨(dú)特價值。非洲獨(dú)特的地理風(fēng)貌,獨(dú)特的人文景觀,獨(dú)特的歷史文化,都決定了非洲英語文學(xué)的鮮明特色。從描繪內(nèi)容和表達(dá)主題上判斷,非洲英語文學(xué)著力刻畫地域生活,著力書寫民族歷史,著力接軌國際前沿,著力彰顯多元文化,著力揭示移民流散體驗,而這些異質(zhì)性內(nèi)容無一不帶有卓爾不群的質(zhì)地,也一度吸引了英美多位作家,包括文學(xué)成就斐然的名家去進(jìn)行文學(xué)表達(dá),但他們的非洲書寫卻表現(xiàn)出了種種偏見。不管非洲本土作家是否流散到英美等發(fā)達(dá)國家,即便他們再努力歸附英美標(biāo)準(zhǔn),也都會在作品中留下鮮明的非洲本土烙印,英語語言中難免混雜著本土方言,表達(dá)內(nèi)容離不開非洲文化的根底,民間傳說、民間歌謠、民間神話常常在文本中出沒,而非洲的自然風(fēng)光、人文景觀、殖民史與族裔性更是文學(xué)書寫的客體對象,更是文學(xué)表達(dá)的天然主題。因此,以恰當(dāng)?shù)难芯糠妒剑沂痉侵抻⒄Z文學(xué)的獨(dú)特價值,揭示非洲英語文學(xué)的審美意蘊(yùn),揭示非洲英文學(xué)區(qū)別于英美等其他國家文學(xué)的標(biāo)識性特征,是學(xué)界亟待解決的問題,也是學(xué)界調(diào)整學(xué)術(shù)研究格局的新契機(jī),只有將非洲英語文學(xué)“置于世界性的框架之下從而才能衡量出其本身具備的價值和意義”,對此我們一向有所忽視。
我國學(xué)界對非洲英語文學(xué)給予了一定的研究,并表現(xiàn)出“深厚的諾貝爾獎情結(jié)、重點(diǎn)作家研究一枝獨(dú)秀、對后殖民理論以及流散英語作家的厚愛、對作家作品主題思想的偏重、對中外作家比較研究的癡迷”的主要特征。比如庫切,他在我國受到格外的眷顧,特別是他獲得諾獎后,關(guān)于他的研究呈井噴之勢,積累了大量的論著。相比之下,其他作家卻少人問津,即便是重要作家也存在著研究上的盲點(diǎn)。我們對非洲英語文學(xué)的關(guān)注,有著相對固定的路向,對文學(xué)作品的批評模式也往往聚焦于殖民、族裔與流散,未能豐富多樣地對非洲英語文學(xué)展開深入的探究,這不能不說是頗為遺憾的事。“如何認(rèn)識作為一個整體的非洲英語文學(xué)以及如何把握非洲英語文學(xué)呈現(xiàn)的總體特點(diǎn)并對之進(jìn)行正確的評價和定位,一直未引起足夠的重視”。當(dāng)然,把握非洲英語文學(xué)的整體風(fēng)貌,離不開國別文學(xué)的研究,離不開重要作家的研究。但迄今為止,除南非之外,我們對非洲英語文學(xué)的國別研究尚顯稚弱,我們對諸多重要作家、詩人、批評家的關(guān)注仍然不足。比如《源與流》中提及的大名鼎鼎的諾獎作家內(nèi)丁·戈迪默,我國還沒有一部研究其作品的專著問世。因此,構(gòu)建研究團(tuán)隊,引進(jìn)優(yōu)秀作品,借鑒研究方法,開拓研究視角,擴(kuò)寬研究途徑,形成我國非洲英語文學(xué)的研究體系尤為迫切。首先,我們需要在英語文學(xué)研究的格局中,增添非洲英語文學(xué)的砝碼;其次,我們有必要更為均衡地關(guān)注非洲英語文學(xué)的國別構(gòu)成,以往我們研究南非、尼日利亞、津巴布韋等國的英語文學(xué)較多,今后還需要關(guān)注肯尼亞等國,以切實改變國別關(guān)注不均衡、作家研究不平衡的狀態(tài)。唯有如此,我們才有可能在深入研究小說家、戲劇家、詩人、批評家的基礎(chǔ)上,更為準(zhǔn)確地認(rèn)知國別文學(xué)的特征,從而從整體上把握和定位非洲英語文學(xué)。
在調(diào)整英語文學(xué)研究格局、聚焦非洲英語文學(xué)時,突出中國視角和中國立場,不對歐美批評模式亦步亦趨,不對西方既有結(jié)論盲目推崇,是我國學(xué)界必須秉持的學(xué)術(shù)態(tài)度。同樣遭受過歐美列強(qiáng)的殖民壓榨,同為第三世界發(fā)展中國家與地區(qū),同時面臨著發(fā)展的時代使命,這就使我們與非洲在諸多方面存在相似性,也使得以中國視角開展非洲英語文學(xué)研究尤為必要。在國外的研究中,歐美學(xué)界的學(xué)術(shù)探索有其特定的傾向,意識形態(tài)色彩成為許多研究的標(biāo)志,把非洲異國情調(diào)化,捏造和塑造特定意義的“東方”,為殖民歷史辯護(hù),為新的資源盤剝背書,這是我們必須加以警惕的。“當(dāng)下的現(xiàn)實的確是新殖民主義依然盛行,第三世界心靈去殖民的進(jìn)程也舉步維艱。在此情形下,我們更應(yīng)清醒地知曉在這個脈脈相通的‘地球村里,沒有誰可以是自足的孤島。人類是相互依存的命運(yùn)共同體,因此,任何形式的歧視、剝削、壓迫和爭奪最終都會是兩敗俱傷”。職是之故,中國和非洲諸國均須反思?xì)v史、正視現(xiàn)實、面向未來,更要凝聚共識、加強(qiáng)交流、深化合作,在努力構(gòu)建人類命運(yùn)共同體的愿景中譜寫新篇章,其中,文學(xué)文化事業(yè)自然擔(dān)當(dāng)著不可推卸的職責(zé),非洲英語文學(xué)研究自然占據(jù)著較為重要的地位。非洲很多國家先是殖民地,后屬英聯(lián)邦,現(xiàn)在獨(dú)立自主,其間文學(xué)的演進(jìn)變化需要學(xué)術(shù)清理,濃重的種族主義色彩需要學(xué)理批判,深厚的殖民文學(xué)本質(zhì)需要深刻揭橥,我們在這一過程中獲得的成果與經(jīng)驗,將有助于中非人文交流和文明互鑒的深度拓展。有鑒于此,站穩(wěn)中國立場,突出中國視角,彰顯中國特色,應(yīng)該成為我們非洲英語文學(xué)研究的基本質(zhì)地,這樣的研究將精準(zhǔn)辨識非洲文學(xué)精神和文化內(nèi)涵,從而為中非交流與合作奠定基石。
必須指出的是,作為英語文學(xué)界的著名學(xué)者,朱振武先以英美文學(xué)的研究和譯介著稱于世,后對西方漢學(xué)家譯介中國文學(xué)作品加以探究,并積十余年之功,致力于非洲/非主流英語文學(xué)研究,于2013年主編《中國非英美國家英語文學(xué)研究導(dǎo)論》一書,于2019年主編《非洲英語文學(xué)研究》和《非洲國別英語文學(xué)研究》兩部皇皇巨著,加之同樣于2019年推出的專著《源與流》,構(gòu)成了朱振武個人嶄新的學(xué)術(shù)面貌和研究格局,其背后蘊(yùn)藉著一位中國學(xué)人的學(xué)術(shù)責(zé)任與擔(dān)當(dāng)。
三、重塑非洲英語文學(xué)的研究秩序
《源與流》的重要價值還體現(xiàn)在,讓我們對非洲英語文學(xué)的研究秩序做出必要而合理的調(diào)整。首先,我們的研究秩序要盡量做到均衡和平衡。朱振武在指出我國學(xué)者研究非洲英語文學(xué)的重要特征時,也對存在的問題進(jìn)行了精到的分析。這些問題突出地表現(xiàn)在我們對研究對象、研究角度和研究內(nèi)容的選擇方面,特別是我們的研究在國別分布上還不均衡,在小說、詩歌、戲劇、批評的文類選取上存在偏頗,小說研究占據(jù)了絕對多數(shù),其他文類的研究明顯不足,而對文學(xué)批評的觀照幾乎付之闕如。這是學(xué)術(shù)生態(tài)的失衡,也是學(xué)術(shù)秩序的缺失,如不調(diào)整,恐將影響我國對非洲英語文學(xué)的整體把握。
其次,我們要及時調(diào)整對非洲英語文學(xué)的認(rèn)知范式。現(xiàn)有研究主要從價值論和功能論的視域展開,主要探討非洲英語文學(xué)的國族想象、族裔認(rèn)同、共同體構(gòu)建、移民流散、反殖民潮流等維度,從這些維度勾勒出非洲英語文學(xué)的社會價值和文化功能,并在學(xué)界積累了較為豐富的成果。仔細(xì)考量,其背后有著根深蒂固的合理性,與非洲文學(xué)的本土化特征及其對全球化的回響密切相關(guān)。但是,這些認(rèn)知范式卻多屬文學(xué)的外部研究,還沒有深入到文學(xué)文本的內(nèi)部肌理,還沒有從文學(xué)審美的向度深入掘進(jìn)。“作為豐富人類心靈、哺育人類精神、深化人類思想、表達(dá)人類情感、培養(yǎng)人類悲憫情懷的重要手段”,文學(xué)必然有情感的審美維度,必然蘊(yùn)含著小說家、劇作家和詩人匠心獨(dú)具的藝術(shù)創(chuàng)造,而這就需要我們從文本中去挖掘文學(xué)符號的美學(xué)價值,去闡發(fā)文學(xué)文本的審美意蘊(yùn)。客觀地講,非洲英語文學(xué)存在著天然的優(yōu)勢,讓學(xué)人自然而然地從外部切入,但隨著文學(xué)創(chuàng)作的積累,隨著精品力作的增多,非洲英語文學(xué)的內(nèi)在價值逐漸成為寶藏,有待我們深入探究和開發(fā)。簡言之,面對非洲英語文學(xué),我們在注重社會價值論和文化功能論認(rèn)知范式的同時,還要在文學(xué)性和審美性的向度上精耕細(xì)作,從而把非洲英語文學(xué)納入更為全面合理的認(rèn)知視域中。
再次,我們要更新非洲英語文學(xué)批評話語。非洲英語文學(xué)研究的認(rèn)知范式存在現(xiàn)實功用化的傾向,而審美之維嚴(yán)重缺失不能不說是遺憾。與認(rèn)知范式相適應(yīng),我們的非洲英語文學(xué)批評話語,多以文本之外為價值取向,族裔、種族、身份、殖民、女性、流散等批評話語各擅勝場,在文學(xué)研究實踐中占據(jù)要津,相關(guān)論著和言說不勝枚舉。這些批評話語固然有其合理性,固然有其獨(dú)到的存在價值,長時間以來也讓非洲英語文學(xué)研究取得了不俗的成績,卻也有著明顯的不足,最為關(guān)鍵的一點(diǎn)便是“將作品的美學(xué)價值讓位于政治需要”,從而從根本上貶抑了非洲英語文學(xué)的文學(xué)性和審美意蘊(yùn)。朱振武在《源與流》中對“異邦流散”“本土流散”“殖民流散”的論述詳備周至、發(fā)人深省;對身份等話語的分析也鞭辟入里,切中肯綮。其實這些批評話語在當(dāng)下都面臨著刷新,身份政治話語目前在歐美遭到了認(rèn)同危機(jī),福山“反對身份政治”的立場就令人警醒。在這種情形下,我們的文學(xué)批評話語面臨著必要的更新和調(diào)整。英美新批評遺留下的文本分析策略,經(jīng)典與后經(jīng)典敘事學(xué)的學(xué)術(shù)積淀,認(rèn)知詩學(xué)的可貴探索,“新審美主義”的再次勃興,如此等等,不一而足,都可成為我們非洲英語文學(xué)研究的批評話語。更新后的非洲文學(xué)批評話語,既應(yīng)該統(tǒng)攝文本之外的功能與價值,又必須抵達(dá)文本中文學(xué)性的內(nèi)核,唯其如此,我們才可望以豐富多樣的批評話語推進(jìn)非洲英語文學(xué)研究結(jié)出更多碩果。
當(dāng)然,《源與流》一書尚有需要改進(jìn)之處,比如若干段落重復(fù)、有的譯名前后不統(tǒng)一、個別文字出現(xiàn)錯漏等,但白璧微瑕,瑕不掩瑜,該著在重塑英語文學(xué)研究格局和秩序方面居功甚偉,必將在我國英語文學(xué)學(xué)術(shù)史上留下重重的印跡。
參考文獻(xiàn):
[1] 朱振武. 非洲英語文學(xué)的源與流[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文中有關(guān)引文均出自此書,不再另注)
[2] Fukuyama, Francis. Identity: The Demand for Dignity and the Politics of Resentment[M]. London: Profile Books,2018.
基金項目: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一般項目“消費(fèi)社會的審美資本化研究:西方鏡鑒與本土經(jīng)驗”(項目編號:19YJAZH090)
作 者: 王敬民,文學(xué)博士,河北大學(xué)外國語學(xué)院教授,研究方向:西方文論和英美文學(xué)。
編 輯: 水涓 E-mail:shuijuan3936@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