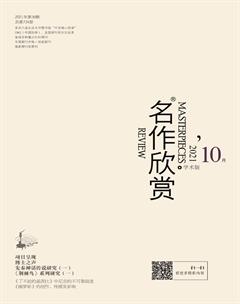《楚辭》之發問文體
摘 要: 《楚辭》與《詩經》是中國古代文學的兩大源泉。自漢武帝立五經博士以來,《詩經》在官方就有齊、魯、韓三家,更被今文經學家列于五經之首。《楚辭》雖為“雅頌之博徒”,然而絲毫沒有影響其在文學史上所應有的地位。《漢書·藝文志》就已把“屈原賦之屬”置于“詩賦略”之首。《隋書·經籍志》的集部始以《楚辭》為首,從此自成一類。本文就試圖將其中《天問》《卜居》《漁父》典型的發問文體與春秋戰國時的相關問語聯系起來,揭示此種文體產生的社會性,并從縱向上考察其對后世文學的影響。文末將以比較文學的視角羅列出《梨俱吠陀》中的相似片段,以闡明《楚辭》發問式文體在世界古代文學史中的重要意義及其所體現出的人類文學共性。
關鍵詞:《楚辭》 發問文體 文體探索 文學創作心理
《楚辭》中的屈宋辭賦產生于戰國時期,是繼《詩經》之后具有濃郁楚地風格特點的優秀詩歌作品。宋黃伯思《校定楚辭序》謂《楚辭》“皆書楚語,作楚聲,紀楚地,名楚物”。其記載的楚地物產風俗、神話與民歌樣式是我們研究楚史的最佳資料。其在句式上長短錯綜、變化多端,打破了《詩經》四言句式的局限,又下啟磅礴大氣的漢賦。《離騷》《九章》《遠游》三篇自傳式敘事詩抒情長詩又有意識地構造出“三階段”的敘述結構(先從現實愿望出發,因其不能實現而遠游高舉,然又“忽臨睨夫舊鄉”而返回故都,至放逐江南后九年不復,最后“依彭咸之遺則”,“伏清白以死直”,了結一生),堪稱自敘傳抒情長詩的典范。
以上這些多為早期研究者所提及,然《天問》《卜居》《漁父》三篇發問式文章對戰國時人文體探索的體現卻罕有人問津(此三篇皆因問句的運用而成獨特之文體,但也有各自可相區別的特點。《漁父》為主客問答體;《天問》由一百七十多個問句組成,有問無答,在此姑且稱之為連篇發問體;《卜居》整體上看為主客問答體,但屈原不知“何去何從”的連續詰問占了大半篇幅,因此也與《天問》相似,只是其選擇疑問句與《天問》各種特殊疑問句不同)。因此,筆者試圖將此三篇發問式詩作與同時期相似的問語聯系起來,加以分析,淺談發問文體產生的背景及其影響,并摭拾古代東方文學中此類實例,試從比較文學的角度說明人類寫作的共同心理。
一
《漁父》篇幅不長,全文僅以屈原與漁父的問答反駁展開,簡潔明了,卻能完美地傳達出每一句話的情感語意。此篇以“屈原既放……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開頭,漁父隨即出場,見屈原此狀問道:“子非三閭大夫與?何故至于斯?”作者顯然有意將漁父設計成熟悉了解屈原的角色。此兩句讀起來,猶見其驚詫之情狀,讓讀者不得不對屈原昔日為三閭大夫而今被棄草野的境遇而惋惜哀嘆。屈原的回答益顯其獨行忠直而不得用的苦悶。“舉世皆濁我獨清,眾人皆醉我獨醒”一語最是扣人心弦,成為流傳千古、婦孺皆知的佳句。漁父卻對屈原此行深為不解,連用了三處為什么加以追問(原文問句都以“何”開頭)。其對屈原勸導的語氣與內在的隱逸氣質瞬間躍然紙上。屈原對此答以反問兩句,鏗鏘有力,讀之仍聞其聲。文末又以漁父之歌作結,飽含哲理、意蘊悠長,如撞鐘余音之不絕也,頗得漁父悠然自得之神態,而屈原在旁的悄愴心境亦仿佛可見。這自然是緣于主客問答體在描寫聲音形貌上的獨特優勢。《文心雕龍·詮賦》就提到:“及靈均唱騷,始廣聲貌。”實際上,這不僅是《楚辭》的文學追求,也是此時代文學的普遍特點。戰國時思想多元,諸子百家每每廣聚門徒,奔走四方,以推廣其思想。因此,互為問答中立論、反詰等技巧也逐漸為一些好辯之士所掌握。孟子之于梁惠王、墨子之于楚王即是明證。假托主客二人討論辯駁(洪興祖云:“《卜居》《漁父》皆假設問答以寄意耳”),以問答之聲貌增添文采、推動情節、構造層次,使主客問答成為一種文體,也自然成為彼時文學創作的發展趨勢。正所謂:“述客主以首引,極聲貌以窮文,斯蓋別詩之原始,命賦之厥初也。”
《莊子·雜篇》中的《漁父》不僅在名稱上與《楚辭·漁父》相同,就連漁父的形象也與之相似。其在行文結構上則顯得更為成熟,敘述的邏輯也更為嚴密。文章以孔子于杏壇上弦歌鼓琴開頭。此時漁父自江“行原以上”,“距陸而止”,“持頤以聽”。他并不認識孔子,于是招來子貢和子路詢問情況(此處有異于《楚辭》中漁父一眼就能認出屈原的設計,二子之回答也與他們的性情相符)。得知孔子乃一儒者后,漁父嘲笑其“苦心勞形,以危其真”,往回就走。子貢還報孔子,孔子推琴而起,連忙下壇至澤畔請教此“圣人”,正趕上漁父還沒離去,孔子亦得以向其求教(文章此前的情節與《論語·微子》中子路遇丈人之事相似,其后卻竭力闡釋道家的“真”以批判孔門,一改《論語》對子路在“道之不行”的現實下仍積極入世的贊揚。這似乎能說明《莊子》假托問答以述其主張的創作意識),并于“請問何謂真”一處進入了高潮。漁父實在很有高人的風范,其回答先從給“真”下定義開始,接著列舉出強笑、強怒、強親等不真的世俗行為,然后從正面說出“真”之于日常生活的體現,最后得出“禮者,世俗之所為也,真者所以受于天,自然不可易也,圣人法天貴真”的結論。晚聞大道的孔子由此被批得一無是處。文末孔子問漁父舍所在,請因受業而卒學大道。漁父則故作清高,表示他不會與不能迷途知返的人交往,遂刺船而去。此文充分發揮了主客問答體的長處,給儒家學派以當頭一棒,有力地說明了道家返璞歸真的正確與高妙。
《莊子》中此類假托互為問答的篇目還有不少,如《逍遙游》之肩吾問接輿于連叔,《齊物論》之罔兩問景、嚙缺問乎王倪,《人間世》之顏回問仲尼等。另外,諸如《黃帝內經》《公孫龍子》等文學創作意識較為薄弱的著作也采用了主客問答的形式。20世紀馬王堆三號墓出土的《十大經》中也有假托黃帝、力黑、高陽等人的發問片段。他們與《楚辭·漁父》相互發明,共同代表了此時人們在文體探索上取得的突出成果。
《楚辭》在中國文學史上一直享有很高的地位。《漢書·藝文志·詩賦略》中大部分的賦都是楚辭。《隋書·經籍志》的集部始以《楚辭》為首,此后相承不易。其主客問答體也因此對后世文學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洪邁《容齋五筆》卷七云:“自屈原詞賦假為漁父、日者問答之后,后人作者悉相規仿。”洪邁還舉出司馬相如《子虛賦》《上林賦》、揚雄《長楊賦》、張衡《兩都賦》、左思《三都賦》與枚乘《七發》等為例,且特贊蘇軾《后杞菊賦》破題之妙不蹈前人習氣。此外,蘇軾的代表作《前赤壁賦》亦值得一提。其文借觀點相殊的主客二人,提出應從不變的方面觀察天地,不應為生之須臾而哀傷的豁達主張。明張岱《湖心亭看雪》中“余”偶遇知音一情節也應視為假托虛構。其對話僅以寥寥數筆來交代,卻巧妙地以偶遇者“是金陵人,客此”的回答,傳達出自己遺世獨立的孤寂心境與身為明朝遺民的故國之思。
二
《卜居》《天問》兩章皆有連續的發問句式,且非一問一答的形式。前者兩句為一節,每節為一韻(指“何去何從”以前),亦出現了不規律的四句為一節、每節為一韻的用法(“何去何從”以后)。后者通篇全用問語,以四言為主,通篇四句為一節,每節為一韻,亦有兩句為一韻者。然其例極少。
王逸《楚辭章句》解《卜居》此題云:“屈原體忠貞之性而見嫉妬……己執忠直而身放棄,心迷意惑,不知所為。乃往至太卜之家,稽問神明,決之蓍龜,卜己居世何所宜行,冀聞異策,以定嫌疑。”如前所引洪祖興之注,我們應將其視為“假設問答以寄意”的篇章。然王逸所謂“心迷意惑,不知所為”也的確是此章的情感基調。此種心理狀況在文中接連不斷的選擇疑問句中得到集中體現。此章句式較《天問》更為復雜(句子就表面看來更長)。作者或用“以”表示對最終結果或目的卜問,或用“若”對不同的處境進行比喻,又時而穿插補充性的描寫,還綜合運用各種形容詞,有效地增強了問句的氣勢。此時的屈原既放三年,不得復見,心煩意亂。不知所從的他也難怪會被這些問題所困擾:是保持純潔忠直的品行,還是去追隨世俗之人呢?是躬耕種稼,還是去巴結貴戚以贏得名譽呢?是冒死進諫,還是為保住俸祿以茍且偷生呢?……正因不知何去何從,屈原往見太卜,意欲以龜策之事斷個吉兇,然而卻以詹尹釋策謝言而告終。真可謂問己則疑,問天不應,最后也只能無奈地將自身的不幸歸結到獨行忠直的美德罷了。《楚辭補注》謂此章問語:“上句皆原所從也,下句皆原所去也……時之人去其所當從,從其所當去。其所謂吉乃吾所謂兇也。此《卜居》所以作也。”此話從選擇疑問句的表面形式切入,指出了此章發問組句在表現作者情感心境上的藝術感染力,無疑是十分高妙而貼切的。
相對于其他文學作品而言,《天問》一章的內容和形式都可謂是獨具一格的。屈原于楚先王之廟及公卿祠堂“仰見圖畫,因書其壁,呵而問之”,或對不合理、不知曉的事物加以詰問,或表面上為問,實則抒發自己對天地人事的見解。全詩前半部分問日月星辰、人類起源等自然現象,側重于興;后半部分則借問句之形式就大量的神話故事、歷史傳說及事實發表議論,突出何故由興而亡。新出土古佚書中假托黃帝對天地政體的發問表明此時人們的天地觀已經相當確定。然而,屈原在《天問》中仍發出“天命反側,何罰何佑”及“皇天集命,惟何戒之”等疑問。這大概是屈原當時的心情極為苦惱,以至于對宇宙、歷史、人生都持有懷疑的態度,因而通過向天叩問來發泄心中的抑郁。《史記·屈原賈生列傳》云:“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太史公此語可謂深得屈原之創作動機。
在圍繞此中心思想呵問天地人事的基礎上,《天問》形成了他篇所不及的獨特文學形式。第一,全文幾乎通篇用韻,從開頭一直呵問到底,有問而無答,與其他問答文體判然有別。第二,其句式雖以四言為主,缺乏“兮”“只”“些”等語氣助詞,但句子長短富于變化。最短的有三言,最長的有七言,又有五言、六言,錯綜統一,兔起鶻落,增強了文章的節奏感。明蔣之翹《七十二家評楚辭》引孫鑛語:“或長言,或短言,或錯綜,或對偶,或一事而累累反復,或聯數事而熔成片語;其文或峭險,或淡宕,或佶屈,或流利,諸法備盡,可謂極文之變態。”第三,篇中所用疑問代詞(何what、誰、孰)、疑問副詞(焉why or where、何why、安how)、形容詞(“光明”用昭、明表示,“黑暗”用冥、瞢、闇、晦表示)亦極為豐富,神明變化,不可方物。
如果我們從縱向的時間維度考察《卜居》《天問》這類連篇發問文體,就不難發現其“體憲于三代,而風雜于戰國”的蛛絲馬跡來。筆者僅細檢《老子》就發現了多處連續發問而不作答的用法。當中不少句式還與《楚辭》發問式篇章相似。茲舉一例:“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專氣致柔,能嬰兒乎?滌除玄覽,能無疵乎?愛民治國,能無知乎?天門開闔,能無雌乎?明白四達,能無為乎?”據羅根澤《管子探源》的觀點,《管子》所有篇章都不會出自戰國之前。傳世《管子·心術上》《心術下》《白心》皆為戰國中世以后道家所作,而《內業》則是戰國中世以后兼雜儒道思想之作。今見馬王堆《老子》乙本卷前四篇佚文與《心術上》《白心》《內業》三篇韻律相近,且含有與《管子》此四篇相同或相近的段落,可知羅根澤定為有戰國道家之言的篇章確與出土佚文有著密切的親緣關系,韻律相近的三篇甚至可能同為楚人所寫。也許是受道家著作影響的緣故,《管子·心術》《內業》中亦不乏有與《老子》第十章相近的連續發問句式:“能專乎?能一乎?能毋卜筮而知兇吉乎?能止乎?能已乎?能毋問于人而自得之于己乎?”“能搏乎?能一乎?能無卜筮而知吉兇乎?能止乎?能已乎?能勿求諸人而之己乎?”幾乎與《楚辭》處于同一時代的《莊子》也有此類實例。《莊子·庚桑楚》引用的老子原話與《老子》第十章的發問句式相仿,內容上又與《管子》相似,且加以鋪排擴展,營造出長短錯綜、鏗鏘有致的藝術效果。其文云:“衛生之經,能抱一乎?能勿失乎?能無卜筮而知吉兇乎?能止乎?能已乎?能舍諸人而求諸己乎?能翛然乎?能侗然乎?能兒子乎?”如果說以上這些相類的連續反問(以句首的“能”表示“難道不能”的反問語氣。其在思想上皆提倡精神內守、反求諸己、清靜無為的做法)只是道家學派說教時口耳相傳的習慣性口吻,而仍不具備自覺的文體探索意識,那么《莊子·天運》則表現出時人對天地與世界本源的追問和日趨理性的宇宙觀。其發問段落簡直就與 《天問》異曲同工(其疑問詞與提問方式雖不如《天問》豐富,但其一般疑問句、選擇疑問句、特殊疑問句的自然混用無疑比《老子》《管子》諸句更勝一籌):“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日月其爭于所乎?孰主張是?孰維綱是?孰居無事推而行是?意者其有機緘而不得已邪?意者其運轉而不能自止邪?云者為雨乎?雨者為云乎?孰隆施是?孰居無事淫樂而勸是?……孰噓吸是?孰居無事而披拂是?敢問何故?”又《莊子·天下》載有黃繚“問天地所以不墜不陷,風雨雷霆之故”一事。黃繚之文今雖不存,然其內容定是問天呵地的知識性疑問無疑,形式也應與《天問》和《天運》此段相類。類似文法還出現在《逸周書·周祝解》中。以上這些資料足以展現春秋戰國時人們不斷探索并運用連續發問句式的過程。其文字雖未成通篇或大篇幅發問之文,但也足以為《楚辭》連篇發問體的創作基礎。《天問》一經問世就促成了不少后人的系列創作,如北齊顏之推《歸心篇》,唐楊炯《渾天賦》、柳宗元《天對》、劉禹錫《問大鈞賦》。此風氣至明一代大盛,又以方孝孺《雜問》,黃道周《續天問》為杰出代表。
三
事實上,若以開放的視野把世界古代文學史上的相關資料一一羅列,加以比較,由此推尋這種文體形成發展的過程,那么《楚辭》無疑為這一研究方向提供了古代東方最重要的“文學人類學”資料,而諸如印度、阿拉伯、希伯來等文學作品也必定能為我們提供更為嶄新的詮釋視角。盡管因宗教與哲學思想的差異性,這些作品中雖無像《天問》一樣通篇詰問的長詩,卻表現出與《楚辭》及其他戰國文學資料的內在一致性。其對宇宙起源也多有發問,如《梨俱吠陀》第10卷第129首的“創世頌”(共有7節)中第一節:“何物隱藏,藏于何處?誰保護之?深廣大水?”(什么覆蓋著?在哪兒呢?誰給予庇護?是無垠而深不可測的水嗎?)又第六、第七節:“誰真知之?誰宣說之?彼生何方?造化何來?……誰又知之,緣何出現?世間造化,何因而有?是彼所作,抑非彼作?”(誰真正知道?誰將在這兒宣告,這創造生于何方,來自何方?……那么誰知道它最早出自何方?這創造出自何方?是締造出來的,抑或不是?)再如《婆樓那贊》第二節中對婆樓那的祈求簡直勝似屈原對湘君的呼喚。《由誰奧義書》開端數句更是將此種哲學溯源式的發問延伸至對人類意識現象起源的探討:“由誰所馳遣,心思赴如射?由誰所羈勒,生氣初前適?由誰所策動,人作此言語?由誰神所驅,眼耳從所役?”(由誰的意愿和指令,思想出現?由誰促使最初的生命氣息啟動?由誰的意愿,人們說這樣的語言?是哪位天神,安排這眼睛和耳朵?)以上這些例子都體現出中外文學創作相似的心理與寫作技巧。我們對此類文體的進一步分析、比較也無疑是很有必要的。
綜上所述,《楚辭》是中國文學史上一部優秀的詩歌總集。我國的發問式文體早在春秋時就萌芽并得到發展,而成熟于戰國時期。《漁父》是主客問答體的典型代表,而《卜居》《天問》則是連篇發問體之成就的集中展現。由于《楚辭》之于中國古代文學的重要地位,歷代不斷有人對這種文體加以模擬,創作出一批又一批動人之作來。另外,這種連續發問的文法(此處不能稱為文體,《天問》充分使用發問句式的創作意識是其他民族作品中所罕見的)在諸如《梨俱吠陀》《奧義書》《火教經》《圣經》等世界古代經典中并不罕見。有關資料尚有待進一步發掘與探討。
參考文獻:
[1] 洪興祖撰,白化文等點校.楚辭補注[M].北京:中華書局,1983.
[2] 吳平,回達強.楚辭文獻集成[M].揚州:廣陵書社,2008.
[3] 劉勰著, 范文瀾注.文心雕龍注[M].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9.
[4] 張少康.中國文學理論批評史教程[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
[5] 姜亮夫著,沈善洪、胡廷武主編.姜亮夫全集 楚辭學論文集[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
[6] 徐志嘯.《莊子·漁父》與《楚辭·漁父》[J].文學遺產,2009(4).
[7] 陳國慶.漢書藝文志注釋匯編[M].北京:中華書局,2015.
[8] 魯惟一(M.Loewe)主編,李學勤等譯.中國古代典籍導讀[M].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7.
[9] 顧頡剛編.古史辨(第四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10] 洪邁著,穆公校點.容齋隨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11] 馬王堆漢墓帛書整理小組.長沙馬王堆漢墓出土《老子》乙本卷前古佚書釋文[J].文物,1974 (10).
[12] 龍晦.馬王堆出土《老子》乙本前古佚書探原[J].考古學報,1975 (2).
[13] 瀧川資言,水澤利忠.史記會注考證附校補[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14] 高明.帛書老子校注[M].北京:中華書局,2018.
[15] 郭慶藩.莊子集釋[M].北京:中華書局,2004.
[16] 黎翔鳳.管子校注[M].北京:中華書局,2018.
[17] 饒宗頤.梵學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18] 林太.《梨俱吠陀》精讀[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8.
[19] 徐梵澄.五十奧義書(修訂本)[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
作 者: 梁文健,河南大學文學院漢語言文學專業在讀本科生,研究方向:古代文學、古典文獻學、敦煌學。
編 輯: 曹曉花 E-mail:erbantou2008@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