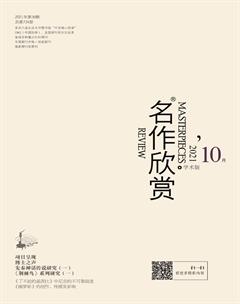“水”的生命歌吟
摘 要:茅盾是浙江省嘉興市桐鄉市人。茅盾的小說受江南水文化的重要影響,水是《水藻行》中的主要線索、血脈和靈魂。河流孕育、滋養了這片土地上的人,淚水和冰暗含了人物的多重情緒,汗水指向的是財喜和秀生的生命力,而雪花和冰也隱喻著如死水一般的舊中國必將被新中國取代的命運。
關鍵詞:水 情緒隱喻 生命力象征 死亡
茅盾出生在浙江省嘉興市烏鎮,這里自古就是江南水鄉。“江南水鄉的氛圍與氣質造就了特定的茅盾,而茅盾也在他的作品中呈現了特定的江南文化氣息。”江南文化主要表現在“得天獨厚的水文化、精巧雅致的橋船文化、義利兼顧的工商文化、尚文重教的育人文化”。茅盾的《水藻行》一直被認為是其文學世界中獨特的一處風景。整部小說的敘述如在水流之中穿行,各種狀態的“水”成為《水藻行》的血脈。河水不受時代和外在社會背景的影響,始終默默地為生命提供滋養。汗水象征了小說中人物的生命狀態——財喜生長在港汊相間的江南水鄉,擁有如水般的生命形態,體現了如活水一般的靈性和生命強力。相比之下,秀生個體生命狀態的疲弱如死水一般毫無生氣。而雪花和冰箸在文本中指向的是秀生奄奄一息的生命狀態和當時如死水一般的舊中國。
一、水之于生命的滋養
古希臘哲學家泰勒斯認為“萬物皆源于水”。人的個體生命最初在母親的腹中孕育之時,也是被羊水包裹著的。巴什拉認為“水應是一種乳汁”,甘甜的水滋養和孕育生命。因此,水是萬物之源,也是人類生命的源泉。
杭嘉湖平原的人們自古以來就臨水而居,依水而生。茅盾在《水藻行》的一開始就交代了故事發生的外在環境:南方、冬季、鄉村。七八座矮屋、新稻草垛、烏桕樹等坐落在鄉村的河邊,接著是對河流的具體描寫:“河流彎彎地向西去,像一條黑蟒,爬過阡陌縱橫的稻田和不規則形的桑園,愈西,河身愈寬,終于和地平線合一。”茅盾在這里對周邊風物,尤其是對河流的描寫,猶如人物出場的前奏,像“一支單純的短笛,緩緩吹起,吹奏出一段過門,等閱讀的注意力漸漸聚成,故事與人物才開始初露文字”。稻田和桑園是當地村民的衣食來源,而河流如一條黑蟒,護衛稻田與桑園。港汊交錯、水流縱橫,這就是當地的自然景觀。目之所及都是水,水是這片土地的經脈和靈魂——自然而然地勾連起稻田、村落,養育著一切生命。
小說中多次出現“蘊草”,“蘊草”就是當地水中生長的植物,茅盾的這篇小說緊緊圍繞“打蘊草”這一情節鋪展開來。蘊草是為第二年開春的稻田施肥而準備的,原本稻田要分別在插秧和水稻高及人腰時施肥兩次。第二次施肥向來是用豆餅,但是豆餅的產地發生了所謂的“事變”,導致豆餅生產商和農民雙重破產,對當地農民的生存產生了巨大的沖擊。因此,“每年春季‘插秧時施一次肥”的“頭壅”就變得尤為重要,而這“頭壅”最好的材料就是生長在河里的蘊草。河流汩汩,“自然流淌,靜止時變得水平如儀,沉淀雜質,澄清自我,忍受外在的強力而最終消磨堅石”。河流自然地堅守自我,不受外界的影響。不管時代怎樣變遷,河流依然在那里,如同一條“黑蟒”,為稻田的生長和當地人們的基本生存提供保障。河流一直在默默地滋養和孕育著她的子民。
二、“淚水”和“冰水”的多重情緒隱喻
淚水中蘊含著多種情緒。海德格爾認為,“從存在論上來看,現身中有一種開展著指向世界的狀態,發生牽連的東西是從這種指派狀態方面來照面的。從存在論原則上看,我們實際上必須把原本的對世界的揭示留歸‘單純情緒”。秀生的淚水作為一種生命存在的感官表現,指向的就是他面對世界的情緒狀態。秀生聽到財喜唱民間的歌謠,認為他是在嘲諷自己,說自己寧愿死也不要做“開眼烏龜”。他看到妻子的大肚子就氣憤,他對老婆的肚子又打又踢。但是當財喜說“你罵她,她從不還嘴,你打她,她從不回手。今年夏天你生病,她服侍你,幾夜沒有睡”時,秀生“惘然聽著,眼睛里充滿了淚水”。秀生的眼淚是他此時情緒的一種表達,而他的情緒又是復雜和多重的。首先,秀生是羞愧的。他常年患病,喪失了勞動的能力,也不能給妻子幸福的生活,因此他對妻子有愧疚之情。其次,他的妻子確實也是一個好妻子。秀生常年患病,不能自理,但是妻子并沒有嫌棄他,依然操持家務,盡心盡力照顧他,秀生對妻子的照顧又有感激之情。最后,秀生對自己的妻子是怨恨的。他恨自己的妻子與財喜“睡了覺”,他認為這是給他戴了“綠帽子”,他的心情是怨恨、悲痛而冷酷的。想到自己身體的孱弱,秀生是羞愧的;想到妻子毫無怨言地忍受著自己的打罵,他又是自責和不忍的;但想到妻子與財喜的事情,他又會充滿恨意……怨恨、感激、羞愧、不忍、自責、無奈以及委屈的情緒交雜在一起,最終混合成此刻的眼中之淚。
“冰水”也蘊含著復雜的情緒。財喜看到秀生孱弱的身體狀況,想到自己雖然一心一意地出死力幫工,承擔了這個家庭中絕大部分的體力勞動,但因和秀生的老婆發生了男女之事,似乎顯得自己的幫工有了別的企圖一般。他本是搖櫓搖得出汗,連身上的破棉襖都穿不住要脫下的時候,卻突然覺得脊背發涼,似乎“有一道冰水從他背脊上流過”。他認為自己對不起侄子,這時候的“冰水”中蘊含著自責、后悔和羞愧等復雜的情緒和情感狀態。看到秀生滿身是雪,縮成一堆,他是又病又窮,幾乎沒有生存下來的力量,財喜的內心又充滿了不忍和憐憫。想到正是因為自己的緣由,才讓秀生大著肚子的妻子依然要承受丈夫的打罵,財喜內心是充滿愧疚的。但“冰水”無法澆滅財喜旺盛、健壯的生命力,他的眼里放光,他內心像有一團火。雖然有“冰水”,但為了大家的生存,他依然選擇留下來,繼續用自己的勞動承擔起這個家庭的生計。
三、“汗水”的生命力象征
“水是形象的載體,而且是形象的供給,是奠定形象的原則。”小說中多次出現“汗水”這一意象,而秀生和財喜的汗水在這里都是彼此生命力的表征。
賽珍珠在《大地》中塑造了貧困、懦弱的中國農民形象,但是這樣的農民形象并不能代表當時中國農民的現狀。《水藻行》最初是應魯迅之邀為日本文學雜志《創造》而寫的,茅盾說他創作這部小說的目的就是:“想塑造一個真正的中國農民的形象,他健康,樂觀,正直,善良,勇敢,他熱愛勞動。他蔑視惡勢力,他也不受封建倫理的束縛。他是中國大地上的真正主人。我想告訴外國的讀者們中國的農民是這樣的,而不是賽珍珠在《大地》中所描寫的那個樣子。”茅盾在這篇小說中著力塑造了一個如活水一般充滿靈性且富有生命活力,健壯、靈活、開放、豁朗的農民形象——財喜。
財喜的“汗水”象征了其旺盛的生命力。小說中有六次提到財喜的汗水,如“抹一把汗”“全身淌著勝利的熱汗”“滿臉的汗”“臉上是油汗”等。財喜是一家的主要勞動力,他的胳膊如鐵臂一樣,他的聲音雄渾有力,時而發出一聲雄壯的“長嘯”。打蘊草時,財喜“突出的下巴用力扭著;每一次舉起來,他發出勝利的一聲叫,那蘊草夾子的粗毛竹彎得弓一般,吱吱地響”。他干活的時候精神百倍,渾身充滿力量。雖然冰冷的河水浸濕了他的草鞋,但是他依然熱得把棉襖脫去,只穿一件單衣。他全身就像“一只蒸籠,熱氣騰騰地冒著”,“他放下了竹夾子,撈起腰帶頭來抹滿臉的汗,敏捷地走到了船艄上”。船櫓在他手里像一條“怒蛟”,“豁嚓嚓地船頭上跳躍著浪花”。浪花似乎是在為雄渾有力的財喜唱頌歌。
財喜就像一泓“活水”般靈活、開放,他不僅承擔了一家的主要勞動,還充分運用自己的聰明才智為這個家庭帶來更多的利益。小說一開頭就寫到秀生抱怨贖冬衣是財喜的主意,這說明財喜是一個有主見的人,他具有主動承擔家庭責任的意識。財喜憑經驗預判要下雪了,就要馬上去打蘊草,而秀生雖有遲疑,最終還是會相信財喜,選擇跟他一起打蘊草。離村二十多里的一條港汊里蘊草是最多的,只有趕到別人的前面才能更快地打到更好的蘊草。財喜看到在他們出發之前就已經有兩條船開過去了,他沒有跟在別人后面,而是靈活地選擇另外一條水路,最后反而趕到別人的前面。與其說財喜是“狡猾”的,不如說他是聰明的,且頭腦靈活,懂得變通。當他們的船已經裝滿了蘊草時,其他的船才一個個趕來。
財喜是開放的,他的腦中沒有濃厚的封建思想。他淳樸、本真,尊重人的自然本性。面對秀生,他的內心雖然有憐惜和自責,但是他依然認為瘦弱、頹廢的秀生配不上他健康的妻子。秀生的妻子是一個好妻子,除了多和一個男人睡過覺,凡是她分內的事,她都盡力做而且做得很好。財喜不像秀生一樣腐朽,他不認為女人應當遵從封建社會的女性貞德觀念。他沒有受過教育,但他會從淳樸而自然的人性出發,認可人的原始欲求。
秀生的“汗汁”卻暗示了他生命力的孱弱與衰竭。與財喜的“滿臉油汗”不同,秀生的汗是“略帶浮腫的臉上鉆出汗汁來了”。一個“鉆”字形象生動地表現出秀生汗水的細弱,而這樣細弱、蒼白、無力的汗水直接指向的是秀生衰退的生命力。小說中,秀生第一次出場就是在屋角,“一個黑魅魅的東西”在蠕動。他雖然年齡小財喜十歲,卻比財喜更顯出一副老相,這是一個未老先衰的男性形象。他的臉是“浮腫”蒼白的,胳膊如干柴似的。打蘊草的時候,他還沒有做什么事情,就已經用完了體力,只有“水聲潑魯魯潑魯魯地響著”,水鳥“啼哭似的叫著”。水的語言是“直接的詩的實在”,“潑魯魯”的水聲似乎是一曲挽歌,表達了對秀生孱弱生命的哀悼。
四、“雪花”和“冰箸”的死亡隱喻
《水藻行》中還有關于死亡的象征與隱喻。小說第三節中寫水面漸漸開闊起來,“發亮的帶子似的港汊在棋盤似的千頃平疇中穿繞著。水車用的茅篷像一些泡頭釘,這里那里釘在那些‘帶子的近邊”。就是在這樣平和且充滿活力的田野中,遠遠近近傲然挺立的是富人家的墳園。江南水鄉的冬季,水以“雪和冰”的姿態出現。這時候的水就成了巴什拉筆下的“狂暴之水”,惡劣的天氣暗示的是人與水之間展開的一種“惡的較量”。
這時候的水,作為一種自然的強力將秀生這樣孱弱的生命直接置于死亡的境地。“雪”和“冰”是秀生這樣虛弱的生命力的強勁威脅。故事發生在江南的冬季,雪花的出現表面上表明了天氣的寒冷,實質上卻指向了秀生個體生命的虛弱與死亡。秀生和財喜本想換一個地方繼續打蘊草,但這個時候“風也大起來了,遠遠近近是風卷著雪花”。兩個人急忙趕回家的時候,秀生卻連搖船中最輕松的“拉繃”也支撐不住了。整個村莊都變成一個銀白的世界,矮屋的瓦上,掛著“手指樣的冰箸”。瘦弱的秀生開始發熱,他的身體無力抵抗這“狂暴之水”。
雪和冰也暗示了當時的社會環境對農民生命的摧殘。秀生一開始就時刻擔心鄉長來催討利息,生病之后他還要面對鄉長的壓迫——三天的征工筑路。蘊草之所以變得如此重要,也是因為第二次施肥時需要用的豆餅,由于產地發生了“事變”,而出現了農民買不起,豆餅行也破產的現象……這就是當時中國農村的現狀,普通的生命個體是不受尊重的,官僚軍閥爭相壓榨最底層的人民。發著高燒的秀生面對這種壓榨和剝削,幾乎喪失了生存下去的意志——“錢是沒有的,只有這一條命!”
秀生虛弱的生命力,象征著封建的舊中國所孕育的衰頹生命,這樣的生命早已喪失了自我生存的意志和能力。秀生所代表的封建腐朽的舊社會,如聞一多的《死水》中所提到的舊中國,是必將走向重生的。這是秀生個體生命死亡的預言,也是封建社會必將滅亡的隱喻。
《水藻行》就如在江南村鎮的港灣河汊中穿行回環的一首關于生命的歌謠。河流滋養和孕育著江南水鄉的生命,淚水和“冰水”彰顯出人物的多重情緒,汗水象征著人物的生命力,雪花和冰箸隱喻的是生命的消亡。小說中既有如活水一般充滿活力的財喜,也有如死水一般傳統、保守且衰頹的秀生。最終,秀生及其所代表的腐朽的封建社會必然會走向滅亡,而財喜必將作為真正的主人昂首挺立在新中國的大地上。
參考文獻:
[1] 徐可.吳文華視野中的浙西現代作家[M].呼和浩特:遠方出版社,2006.
[2] 張偉.吳文化與蘇州文化產業發展的實踐和探索[M].蘇州:蘇州大學出版社,2016.
[3] 鄧杉,趙蓉,徐志英.解讀古希臘[M].昆明:云南大學出版社,2011.
[4] 巴什拉.水與夢[M].顧嘉琛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9.
[5] 茅盾.茅盾小說[M].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2017.
[6] 曹文軒.小說門[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0.
[7] 艾蘭.水之道與德之端——中國早期哲學思想的本喻[M].張海晏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4.
[8] 馬丁·海德格爾.存在與時間(修訂譯本)[M].陳嘉映,王慶節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9.
[9] 丁帆.中國鄉土小說史論[M].南京:江蘇文藝出版社,1992.
作 者: 程亞楠,文學碩士,嘉興南湖學院助教,研究方向:中國現當代文學、秘書學。
編 輯:趙斌 E-mail:mzxszb@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