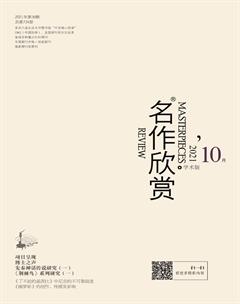論梁斌《紅旗譜》中的土地意識
摘 要:梁斌的小說呈現出鮮明的土地意識,這種意識在《紅旗譜》中一方面表現為農民對土地熱愛又不失敬畏的復雜感情,另一方面表現為新興地主階級與父輩之間對待土地觀念的差異。土地意識反映出梁斌濃厚的鄉土情結和對于土地問題的關注,尤其是對土地在革命歷史進程中的重要意義的思考。《紅旗譜》被譽為“中國農民革命的史詩”,是紅色經典的扛鼎之作,其中重要的原因在于作者選擇土地問題切入革命,燭照歷史。有了對“土地”的思考與把握,才呈現出“史詩”的真實感與厚重感。
關鍵詞:梁斌 《紅旗譜》 土地意識
一
中國現當代文學屢屢以“土地”作為書寫對象——以魯迅為代表的鄉土小說是國民性批判的必然結果;抗戰以來“東北作家群”對于故土的描繪,對于生命的思考與鄉土文學密不可分;京派作家對文化和道德變革的思考,使他們的鄉土小說呈現詩的意境和散文化的傾向;當代文學有專門的“土改合作化”小說;“尋根小說”的倡導中不僅形而上地討論“文學之根”應深植于民族傳統的文化土壤中,在現實的創作中作家們也聚焦于真實的“土地”;莫言在《生死疲勞》中寫“一切來自土地的都將回歸土地”;即使是張愛玲這樣和“土”看似不沾邊的作家,也在《秧歌》中寫出飽經滄桑的農村土地。
梁斌1914年出生于蠡縣梁家莊的農民家庭,在農村度過了自己的童年和少年時光,耳濡目染農村的田園牧歌和蟲草之鳴。新中國成立前,梁斌在博野領導了兩年“土改”工作;新中國成立后,梁斌南下湖北期間仍有“土改”工作的經歷。梁斌的半生都深入農村,與農民和土地聯系在一起。1978年,他完成了小說《翻身記事》,真實、生動地反映了“土改”運動,顯現了梁斌對于對農村、對于土地問題的深入思考。但是,梁斌對于農民和土地的把握顯然早有準備,回溯到《紅旗譜》的創作中就已經體現出來。分析《紅旗譜》呈現的土地意識,對我們理解作品思想價值與藝術特色,特別是對作者“史詩”的寫作預期有重要意義。
二
《紅旗譜》的土地意識首先表現在作者對農民與土地之間賴以生存的關系的展現。《鄉土中國》中費孝通先生早就對土地之于農民的意義進行了概括:“土字的基本意義是泥土,鄉下人離不了泥土,因為在鄉下住,種地是最普通的謀生方法。”這種依存的關系導致了傳統農民對土地的主導感情始終是深深的依戀。嚴志和家的“寶地”是從嚴老祥那一代傳下來的,嚴老祥被迫出走關東前,鄭重其事把土地留給了家人。他說:
“這二畝地,只需你們種著吃穿,不許去賣。……咱窮人家,土地就是根本,沒有土地就站不住腳跟呀!”
嚴老祥走后,家里人精耕細作,不僅將土地視若珍寶,也將嚴老祥對于土地的認識傳承下去。運濤早早就明白了土地和農民的關系,當弟弟江濤不解為何離家二三里路去經營這樣一片著實不便的土地時,運濤學著父輩的口氣向他解釋農村人沒有土地就不能站穩腳跟的道理。接下來運濤參加北伐被捕,身陷囹圄,嚴志和籌措路費被迫賣地。作者濃墨重彩地寫出了農民與土地之間難舍難分的深情:
嚴志和拖著帶病的身子,扶著江濤的肩膀,走到自家那兩畝“寶地”上,眼里淌著淚,一個趔趄,跪在土地上,他匍匐下去,張開大嘴,啃著泥土,咬嚼著,伸長了脖子咽下去。
嚴志和嘴里嚼著泥土,唔噥地說:“孩子!吃點吧!吃點吧!明天就不是咱們家的啦!從今以后,再也聞不到它的氣味!”
而這時候的江濤面對家庭的變故和父親的悲傷,也燃起了對馮老蘭的仇恨。他除了安慰父親,還向父親保證一定要奪回“寶地”。嚴志和一家對于土地的“別樣情深”,一方面寫出了農民與土地難舍難分的關系,一方面也反映了土地在農村生活中的重要性。農民對于土地這種深沉的愛,建立在土地對于農民的重要性之上。土地之于農民是工具,是生活的希望。自己的希望被剝奪,能否生活下去成為未知,引發的是雙方的矛盾與沖突,為之后矛盾的激化埋下伏筆,做好鋪墊。
然而農民對待土地的感情除了“愛”還有“敬”,這種敬畏體現在人對自然法則的遵守、對文化傳統的傳承。中國古代歷法本就是勞動人民為了農業種植而孕育出來的智慧的結晶,許多時令節氣和民俗文化與土地息息相關。在《紅旗譜》的前半部中,依照時令節氣,春季耕地點瓜,夏季修果看瓜,秋季農忙收割,冬季消閑便看戲。不同的季節有不同的景象、不同的農事及娛樂安排,空間和時間一同構筑了北方農村特有的生產生活秩序,這體現出農民遵守節氣時令的民間傳統,更深層次來說是對土地和農事的敬畏。
本地時令:每年春天,麥穗剛剛黃尖的時候,就有藍靛頦鳥兒由南往北去。每年秋季,棉花掉朵兒的時候,就有紅靛頦鳥兒由北往南去。
這一段描寫是典型的地方風俗時令的描寫,除了展現北方特有的風土人情和農事安排,也是作者用來謀劃結構、展開敘事的手段。作者并未交代時間,但通過北方農作物的成熟,展現時間的演變和自然界的規律。更重要的是,鳥兒隨著季節遷徙的描述為作者即將展開“脯紅鳥事件”做好了鋪墊。作者在這里除了表現農民對自然的認識,還賦予時令節氣以敘事的功能。
除此之外,小說中作者以詩意的筆墨對土地的深情描繪,可以讓讀者感受到土地的盎然生機。而這些描繪無一不透露出,土地是農村生活不可抹去的底色;土地如同母親一樣,給予農民生命,滋養他們成長。作者極盡描繪景物之能事,在小說中反復描寫土地,與作品中其他的風景相互映襯,熔為一爐,表現出農民對于土地的敬愛之情。
三
《紅旗譜》不僅寫出了農民與土地之間的關系,也在對地主形象描繪的過程中,寫出了地主與土地之間的關系。在楔子部分,馮蘭池(年輕時的馮老蘭)一出場便頂著賣鐘頂賦稅的名目砸鐘霸地,將官產變為私產,引發了一場悲劇,土地之于地主的重要意義不言而喻。多年后,馮蘭池在朱虎子回鄉后隱憂悔恨沒能斬草除根,回顧當年與朱家結仇時的情景,對兒子馮貴堂說:
“我費了多少年的籌謀,費了多少心血,才把大銅鐘砸碎,把四十八畝官地摳在咱的手心里。這樣一來,咱家這片宅院愿怎么升發就怎么升發。”
馮蘭池的一席話印證了土地與地主之間的關系——如果說土地之于農民而言,是謀生的工具;那么土地之于地主而言,則是積累財富的重要手段,是擴大家業的根本。從根本上看,傳統農民與地主對于土地的觀念別無二致。
然而在地主階級內部,兩代地主對于土地的態度卻是不同的。作者專門拿出一節來寫父親馮老蘭與兒子馮貴堂之間關于“民主”和“改良”的論爭:以馮老蘭為代表的“保守派”堅持來錢的正路是“地租”和“利錢”,種莊稼才是持家之法;而以馮貴堂為代表的“改良派”主張“少放賬”“做買賣”,發展多種經濟才能擴大家業。馮貴堂的觀點實則體現了他與父輩的土地觀念的差異——“改良派”的地主希望能夠改變父輩完全依附于土地的局限,增加生產和生活方式的靈活性與主動性,實現資本積累途徑的多樣性。小說中的“割頭稅”看似與土地無關,其實卻是“改良派”地主想要通過脫離土地,拓寬資本積累途徑的一種掠奪方式。馮老蘭質疑馮貴堂不務農事,妄圖通過包稅賺錢不切實際時,馮貴堂反駁道:
“只要能收到百分之六十,不,只要能收上一半,就能賺八千到一萬元。你在家里坐著,這一萬塊洋錢就竄到你手里來了。”
馮貴堂將之前父親通過控制土地“收租”改為“收稅”實現資本積累的做法,看似與農民在土地方面的矛盾有所緩和,但是無論是堅持土地為財富根本的“保守派”,還是反對土地作為財富唯一來源的“改良派”,其實最終目的都是實現個人財富的積累與擴大,而財富的來源都一致地指向了底層農民。
從兩代地主對于土地的不同態度,我們可以看到“土地革命”這一真實歷史事件的深層原因。第一代地主通過剝削農民,完成資本的積累,這勢必會引起階級的矛盾;而第二代地主雖然希望通過改良來緩和階級矛盾,但是原始資本擴大化的根本目標,使他們換湯不換藥,甚至變本加厲地掠奪。縱觀小說故事情節和發展脈絡,可以發現沒有地主與農民對土地所有權的爭奪,《紅旗譜》的故事不會逐漸深入——“朱老鞏大鬧柳樹林”表面是護鐘,實則是護地,矛盾由此而生;朱虎子回到鎖井鎮后,本打算帶著“金瓜子”回來好好種莊稼,無奈舊仇添新恨,老友嚴志和被迫賣“寶地”,實在過不下去,矛盾為此激化;而“反割頭稅運動”則使失去土地幾乎一無所有的農民再次受到生存的威脅。所以,“土地”實則構筑了《紅旗譜》故事的起因和發展,某種意義上成為敘事的原動力。
四
童慶炳認為:“在文學創作中,理智與感情兩者缺一不可:沒有感情徒有理智,理智便有束縛想象力的副作用;失去理智而徒有感情,感情也有將作家推向不知所往的可能。”《紅旗譜》中呈現出的土地意識,不但是特定時代鄉土社會的客觀反映,也融注了作家們的感情和理智的思考。
反映到作家身上,土地情結在一定程度上顯示了梁斌的審美理想,蘊含了作家對故土深厚的情感。對于滋養過自己的冀中平原,對于伴隨自己成長的故土,梁斌始終念念不忘。梁斌在回憶中反復提及故鄉對他的影響:“家鄉、童年和少年時代的生活,對于一個作家的影響實在太大了。直到現在,我寫起作品來,還是向往兒童時代在家鄉的情景:村邊的樹林,葦塘荒冢,小橋流水,棗林瓜圃。”在充滿硝煙戰火的抗日戰爭中,梁斌在晉察冀抗日根據地進行文藝宣傳工作,后跟隨部隊參加游擊活動;但無論走到哪,梁斌始終心懷故土。部隊行進到平山,面對同為冀中平原人的史立德,梁斌感慨“冀中是塊好地方,是富庶的地方,我也要回去的”;隊伍行進到北洪城山區時,梁斌與戰友吳立人交談時透露出想要回到冀中深入生活寫文章的想法,因為他不忍丟棄在水深火熱的冀中;夜晚行進,越過重重阻隔,穿過敵人防守的重鎮保定城時,梁斌第一時間的反應是感慨終于回到冀中的懷抱;抗日戰爭勝利后,梁斌被分配到勝芳作為公安局秘書長,準備進駐天津,然而他卻婉拒領導好意,回到家鄉蠡縣工作;新中國成立后,梁斌三次辭官,回到故土保定完成《紅旗譜》的創作已經成為文壇佳話。從梁斌這幾次回鄉的經歷,我們不難發現,梁斌對于故土的留戀是《紅旗譜》土地意識的重要原因,無形之中指引著梁斌的創作。
梁斌自幼參加勞動,深諳土地之于農民的重要性,他追憶自己的童年生活時,多次聯想到鄉間的土地。“鄉村里有一句老話,叫作‘七月十五定旱澇,八月十五定收成。農民種地并不是一帆風順的。在我的記憶里,我的兒童時代,不是旱就是澇,要不就是蟲災、兵患。一年到頭,沒有松心的時候。”梁斌看到了農民對于土地的精心呵護,看到了土地對于農民命運的影響。在長期的革命工作中,梁斌感性之余又理性地認識到:只有使廣大農民在革命中取得了他們期望的土地所有權,才能使農民深入土地革命中來,成為革命的主體力量。感性與理性的交織,使梁斌特別關注土地,以土地作為農民革命的切入點。小說中,江濤不明白“反割頭稅運動”的目的,作者特意借賈湘農之口解決了江濤的疑惑:“運動在目前是為了發動群眾,組織群眾嘛。組織起來向包商主,向封建勢力進行斗爭,他們是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將來要在運動里吸收一批農民積極分子,打好建黨的組織基礎。”“反割頭稅運動”的最終指向則是“奪取政權”,這也是當時發動農民運動的最終目的。《紅旗譜》中的土地意識最終指向了革命敘事,是對歷史進程中土地政策的注釋,是革命歷史合法性的佐證。梁斌圍繞農民和土地問題的書寫是符合時代聲音和歷史要求的,只有抓住農民問題,解決了土地與農民之間的權屬問題,中國的革命才會取得勝利。有論者借用“底線倫理”解釋《紅旗譜》中的革命歷史,認為“以底線倫理為基礎建構歷史認知思路,《紅旗譜》就既廣泛地表現了特定歷史環境中的各種斗爭道路及其精神邏輯,又深入地揭示出這種種精神邏輯與階級斗爭觀念、革命文化傾向的意義,從而將階級革命的必然性、必要性及其在歷史與文化邏輯層面的普遍性,藝術地呈現了出來”。事實上,土地是農民的底線,是決定農民命運的最重要的經濟因素。梁斌對于土地的思考與書寫是理性認識到這一問題的主觀反應,是理智與感情雙重作用的結果。
透視《紅旗譜》中的土地意識,我們不僅可以感受到土地在20世紀早期農村生活中的特殊位置,也能在一定程度上理解作家梁斌的創作觀念。他始終關注農民的命運,他的創作既是為革命,又是為農民。他的鄉土情結,使他熱愛農民,熱愛生于斯長于斯的土地。而對于土地問題的思考,尤其是土地問題對于革命歷史進程的重大意義的書寫實現了他創作的多重指向,既迎合了主流意識形態對于對歷史真實的把握,鑄就了《紅旗譜》大氣磅礴的格局;又滿足了農民的審美趣味,同時還完成了自我回顧、審視與建構。
參考文獻:
[1] 費孝通.鄉土中國[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21.
[2] 梁斌.紅旗譜[M].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57.
[3] 童慶柄.文學理論[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
[4] 關于文學作品民族化問題——梁斌同志訪問記[N].人民日報,1960-12-28.
[5] 梁斌.一個小說家的自述[M].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91.
[6] 劉起林.《紅旗譜》的底線倫理與生活本位邏輯[J].寧波大學學報,2017(6).
作 者: 聶晶晶,碩士,保定學院文學院講師,研究方向:中國現當代文學。
編 輯:趙斌 E-mail:mzxszb@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