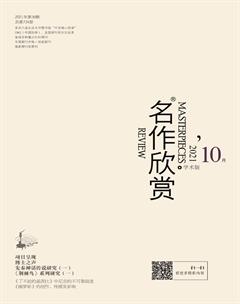出走與回歸
摘 要:電影《納爾齊斯與歌爾德蒙》改編自赫爾曼·黑塞的同名成長小說。小說主人公歌爾德蒙的成長旅程由出走開始,以回歸結束,是一段受到了母親感召而去,向著母親回歸的旅程,也是一段“向死而生”的旅程。電影以有別于小說文本的藝術處理方式,通過對歌爾德蒙成長旅程的三個重要階段——出走、被迫回歸與回歸的空間呈現,探索了存在最普遍的可能性——死亡。電影還通過歌爾德蒙自為性的死亡的展現,實現了父性與母性、個人與集體、“怕”與“死”的和諧統一,從而使人成為完整的人而存在。
關鍵詞:《納爾齊斯與歌爾德蒙》 死亡空間 向死而生 兩極性
一、引言
“兩極”是德國文壇“浪漫派最后一位騎士”黑塞作品中的重要主題,黑塞筆下主人公的精神危機也大多由“兩極”分裂引起。在中晚期作品《納爾齊斯與歌爾德蒙》中,黑塞將兩位主人公納爾齊斯與歌爾德蒙分別置于父性與母性的世界之中,讓二人飽嘗了父性與母性的分裂帶來的痛苦。堅守父性的智者納爾齊斯留守在修道院內,繼續找尋通向上帝的路;追尋母性的歌爾德蒙則受到“母親”的呼喚而去,走上了凡俗的流浪之路。黑塞并未清楚指出哪一條才是正確的道路,只是致力于在這場父性與母性的博弈之中找尋實現“兩極”的調和與統一的方式。于2019年上映的同名電影也循著黑塞的步伐,由始至終探索著父性與母性有可能的和解方式。“母親”是黑塞賜予歌爾德蒙的引誘者,是擁有無限可能性的塵世生活本身。但若“母親”僅引導歌爾德蒙擁抱生命的無常與變化,歌爾德蒙遲早會迷失在無盡的漂浮漫游之中。黑塞想要展現的自我追尋之路絕非如此,因此黑塞筆下的“母親”不僅是不確定的世俗生活本身,她還扮演著死神的角色,手執死之刈鐮等候在終點,又時時與歌爾德蒙同行。電影保留了“母親”與“死亡”的重要命題,將母親當作生,又當作死,將歌爾德蒙向著“母親”的追尋當作一段向著“死亡”的追尋。因而在這場中世紀版的公路電影中所展現的歌爾德蒙向死追尋之旅的每一程都是不同階段、不同形式的“死亡”的空間呈現。但在對“死亡”主題的展現上,電影不滿足于小說娓娓道來的方式,打亂了成長小說典型的線性敘事方式,并對小說文本中的多處“死亡”進行了不同程度的改編。通過對“死亡”的藝術處理,電影實現了以空間推動或限制情節發展的效果,傳達出有別于小說文本的自為性的“向死而生”的寓意。
二、《納爾齊斯與歌爾德蒙》中的死亡主題
(一)“去存在”:出走
在歌爾德蒙年幼時就已缺席的“母親”是感性者歌爾德蒙始終的“欠缺”。一旦歌爾德蒙覺察到這份“欠缺”,他就不再滿足于帶著“欠缺”存在,而渴望將其填滿。歌爾德蒙渴望追尋著“母親”而存在,于是他首先必須要逃離父性世界的包圍,因此歌爾德蒙“去存在”的第一件要緊事就是從修道院中出走。歌爾德蒙的出走是逃離父性與集體,向著母性與個體的出走,是他流浪之旅的開始,也是“死亡”之旅的開端。有學者僅將歌爾德蒙途經的瘟疫區當作死亡空間,但若將歌爾德蒙的整個旅程看作一段向死的旅程,那么他途經的每一個空間都可被看作死亡空間的一種,而電影第一處對“死亡”的呈現就通過歌爾德蒙出走前所處空間的呈現來完成。
出走前,歌爾德蒙在修道院的苦修室與父性世界的好友納爾齊斯做了告別。電影對小說出走前空間的展現并非是簡單的復述與重現,而是對小說中寥寥幾語帶過的苦修室進行了豐富和擴充,并以歌爾德蒙的視角呈現出來:狹小逼仄,暗淡無光,有窗無門。納爾齊斯就處于苦修室內,隱于黑暗中,前方無門無路。電影空間中的歌爾德蒙與納爾齊斯甚至無法共處一室,更不必談實現小說文本中的交談與觸碰。在場景的布置上,電影隱去了小說中歌爾德蒙用于探知苦修室內動靜,得以與納爾齊斯相見的門,代之以一扇高懸的、可望而不可即的小窗。歌爾德蒙透過窗戶觀察,苦修室這一密閉空間就透過歌爾德蒙的視角得到了展現。這一“去門”的處理,暗含了一道無法跨越的邊界。窗外的歌爾德蒙剛剛領略了塵世的歡愉,窗內的納爾齊斯卻在進行極端的自我懲罰。歌爾德蒙已經下定決心出走,而納爾齊斯尚面臨著難以逃離的艱難處境。由此,電影著重刻畫了納爾齊斯的內心掙扎與歌爾德蒙的沉迷享樂,弱化了納爾齊斯與歌爾德蒙之間的共性,而強調二者的差異與距離。
兩位主人公之間的差異與距離在二人各自的特性還未合二為一時,本質上還是納爾齊斯所代表的集體與歌爾德蒙本身的“異質”之間的對立。一心想要追尋母性的歌爾德蒙害怕自己作為個體,作為“異質”,最終淹沒在被父性所籠罩的修道院之中,因此選擇出逃。而作為個體的歌爾德蒙一旦逃離父性集體的包圍,對于他曾經置身的集體而言,就已經算是“死去”。電影將第一處“死亡”處理得更加極端,將歌爾德蒙與父性集體間的差異和對立以不可調和、無法消弭的方式呈現出來。小說中所描寫的二人之間的平靜告別這種有可能的妥協形式也隨著門的消失而不可獲得。不同于小說中呈現出的安寧平和的告別氛圍,電影將歌爾德蒙出走的場景處理得更加戲劇化,也由此奠定了歌爾德蒙自我追尋之旅的流浪基調。
(二)塵世之“怕”:被迫回歸
歌爾德蒙因與總督的情婦偷情而被關入地牢,等待處決。至此,歌爾德蒙的旅程已經過半,他也已在一位又一位女性給予他的愛與情欲中逐漸收獲了母性,并因不停地奔波流浪而感到厭倦。此時“母親”再次對歌爾德蒙發出召喚,歌爾德蒙也清楚地讀懂了“死亡母親”:“母親”永生永死,是塵世的“怕”,又是超脫塵世的“死”,是歌爾德蒙最終要走向的地方。“母親”是歌爾德蒙的母親,也是人類的母親,是人的存在最普遍的可能性。但理解是一回事,接受卻是另一回事。即便早已厭倦了流浪,歌爾德蒙也尚未厭倦世俗生活本身,未厭倦無常生活的無盡可能性;因而在巨大的對肉體死亡的畏懼面前,歌爾德蒙不愿接受“死亡”。面對“死亡”,他僅僅想把握這并不安穩的、擁有諸多不確定性的塵世生命,僅僅想要真切地活著。
囚牢是歌爾德蒙距離母親最近的地方,也是他流浪至此距離死亡最近的地方。電影以囚牢這一空間的展現來實現歌爾德蒙流浪之旅的轉折,由此帶來歌爾德蒙的初次回歸。電影將小說中通過歌爾德蒙對四周的感知構建出的這一囚禁空間以更為直觀、更具視覺沖擊力的形式呈現出來。“地牢”這一封閉而陰森的空間隨著前來探視的納爾齊斯的視角展開。電影對歌爾德蒙在黑暗中感知到的空間并未加以呈現,“地牢”在畫面中一經出現就已被納爾齊斯的火把照亮,同樣被照亮的還有歌爾德蒙首次返回修道院的歸途。隨著納爾齊斯向著歌爾德蒙而去,歌爾德蒙所處的完整空間得到了完全呈現,歌爾德蒙衣衫襤褸、飽受折磨的形象也暴露在納爾齊斯的觀察之下。電影省略了小說中歌爾德蒙身處囚禁空間中被無限放大的心理活動,縮短了歌爾德蒙的心理體驗時間,將小說中用了近十頁的篇幅才完全展現的囚禁空間以短短的幾個畫面便呈現出來,以此來弱化小說著重展現的歌爾德蒙在這一時刻對“肉體死亡的怕”。這一省略恰好符合了電影世界中歌爾德蒙的行為邏輯,電影在此前就已經通過出走空間的呈現有意為歌爾德蒙的旅程增添一絲動亂。與小說中歌爾德蒙相對平靜的流浪之旅相比,電影中時刻處于不平穩狀態之中的歌爾德蒙顯然對于死亡多了一絲領會而少了一份“怕”。而正是因為這一份“怕”的缺失,才讓歌爾德蒙的初次回歸少了一絲“被迫”的意味,也讓影片最后歌爾德蒙自為的死亡成為可能。
(三)“死”之無畏:回歸
人不能永遠漂泊,無休止的流浪也讓歌爾德蒙心生厭倦。歌爾德蒙輾轉于一位又一位女性之間,感官與情欲已達到了滿溢,而滿溢之后則為枯竭。歌爾德蒙就在此時遇到了“藝術”,見到了尼克勞斯師傅的圣母像。這尊圣母像從此便成為歌爾德蒙心中“母親”的化身,成為他走向藝術的開端。然而作為溝通父性與母性世界橋梁的“藝術”,是充滿著矛盾與悖論的。藝術家本身并非圣者,是最遠離父性而親近母性的,而圣母像本身卻處于宗教與父性的包裹之下,站在藝術的對立面。因此出自藝術家之手,作為藝術品而存在的圣母像是自相矛盾的。歌爾德蒙以內心的母親作為素材創作出的圣母像是人類之母的形象,是拋棄了博學、苦修、德行等一切父性世界的元素而存在,受原始欲望驅使的世俗生活本身。世俗生活包含著無限的可能性與不確定性,然而歌爾德蒙同時又試圖打破生活本身的不確定性,將圣母像當作跳出生命的變化無常的外在形象,為圣母像又增添了一重矛盾。
凡俗生活的歡樂隨著女性的窮盡與圣母像的完成達到了巔峰,歌爾德蒙內心的“感官與藝術兩種火焰也均已熄滅”。懷著對“死亡”的渴望與好奇,小說中的歌爾德蒙回到最初的修道院,躺在病榻之上,在自己親手創作出的圣母像的凝視之下,在納爾齊斯的目光中死去。小說于是以平和的方式呈現出封閉、安寧的死亡空間,將歌爾德蒙胸中的痛楚與歡樂和平地結合在一起,以此來達成父性與母性的和解。電影則將歌爾德蒙的死亡處理成一次悲劇性的意外,一次生命的無常。歌爾德蒙因沖進火場拯救被人蓄意毀壞的圣母像而身負重傷,最終在一片廢墟之上完成了他的死亡。同時,包含著父性與母性的圣母像在大火中付之一炬,這是電影對小說最徹底的一處改編。歷經滄桑的歌爾德蒙已經失去了前進的動力,電影就以“火”為他提供兩極歸一的助推力。大火中的圣母像不再是連罩布都不曾揭開的凝視者與旁觀者,而是親自參與了死亡活動的參與者,又或是再次引誘著歌爾德蒙向其回歸的“母親”,一個誘導者。電影世界中歌爾德蒙堅持要從“巨大的死之舞”中拯救出的圣母像,最終帶著小說未曾解決的圣母像本身的矛盾與悖論,隨著大火化為灰燼。電影尾聲,影片畫面從火場轉移到了修道院外的廢墟之上,完成了歌爾德蒙最終的死亡空間的構建。昏暗的畫面中吞噬圣母像的火焰就要完全熄滅,眾人圍站在一旁,見證著歌爾德蒙的死亡。電影選擇由修道院的眾人代替圣母像來發出凝視的目光,將歌爾德蒙最終帶回了曾迫切逃離的群體之中,在人群的見證下讓其懷著對納爾齊斯的憂懼閉上了眼睛。此時天空似乎將要破曉,天地間一片寂靜,一切都歸于虛無。
小說中由圣母像才能構建起的完整死亡空間被搬上大銀幕后,卻主要依靠圣母像的毀滅來完成構建。電影以一次歌爾德蒙主動選擇的死亡來實現其自身存在的諸多矛盾的和解,同時將其本就被削弱的塵世之“怕”最小化。歌爾德蒙不再有“怕”,也就不再為躲避“怕”而選擇擁抱生命的不確定性,而是選擇以一次生命的不確定性來揭示生命最大的確定性——“死亡”。主動赴死是歌爾德蒙“去存在”過程中不確定的可能性,而以此實現的“死亡”卻是存在的最確知的確定性。以不確定性來實現確定性,塵世的“怕”就不再與“死”對立,二者也就自此達成了和解。小說中歌爾德蒙“向死而生”的旅程是自然地降臨在他身上的,僅僅需要被接受;而電影卻是通過歌爾德蒙自為的選擇來完成了“向死而生”最重要的一環。極端的父性世界的人毀壞了他的圣母像,歌爾德蒙毅然以母性世界的身軀前往解救。最后父性與母性無人勝出,雙雙落敗。歌爾德蒙的死亡與圣母像的毀滅則有力地證明了這本是一場無意義的爭辯。歌爾德蒙最終在父性集體的包圍中,在納爾齊斯的注視下死去。父性與母性、個人與集體,都在歸于虛無時實現了和解。
三、結語
僅追尋父性的納爾齊斯與僅追尋母性的歌爾德蒙都是“不完整的人”。歌爾德蒙因跟隨母性而出走,領略了塵世的歡愉后找到了自己的母親。流浪使歌爾德蒙領略了過多“去存在”的可能性,并由此感受到了不自由。作為塵世生活本身的“母親”是神秘而無常的,而無常中的有常即為“死亡”,因此“死亡”便是存在最大的自由。但僅擁有母性的歌爾德蒙始終無法被動地接受死亡,無法擁有死亡的自由。死亡于他而言仍是外化的,只因他一極已經滿溢,一極仍為枯竭。歌爾德蒙與納爾齊斯本就是人性的兩極,本應是合二為一的,他只有回到納爾齊斯身邊,回到父性之中,實現父性與母性的統一,死亡于他而言才算是最終的歸宿。
藝術是黑塞用于連接互不干涉的父性與母性世界的橋梁,而死亡則是調和藝術自身矛盾的方式。“死亡”是一種“去存在”的方式,是填滿歌爾德蒙欠缺的方式,也是其欠缺填滿后的生存狀態。歌爾德蒙的出逃即為存在,因要“去存在”而擁有了諸多可能性。在這諸多的可能性中,“死亡”是最普遍、最確知的一種,也恰是迷茫混沌中的歌爾德蒙所能夠把握的一種。電影通過對歌爾德蒙旅程中死亡空間的改編,將這種可能性以更為激烈、更為極端的方式展現出來。小說中被安靜接受的死亡成為被主動選擇的東西,在電影中得到了充分展現。電影通過省略“門”,省略“怕”而增加“火”,減弱了畏懼,增強了對立,增加了“死”的自為性。歌爾德蒙作為“不完整的人”的旅程結束了,但他也許像小說結尾那樣,以“完整的人”繼續存在著;也許像電影尾聲那樣,成為“完整的人”后即歸于虛無。
在迷茫混沌中追尋的歌爾德蒙是“孤獨的人”。人究竟因何存在,又該如何去存在?上映于21世紀的電影《納爾齊斯與歌爾德蒙》在有限的畫面之中重現了一個人一生的追尋;在盡力展現中世紀生活圖景的同時,也將歌爾德蒙的精神困境映射到當下。歌爾德蒙的流浪之旅本就向死而去,那么他在旅途中的任何一程都生著也同時死著。電影以最具視覺沖擊的方式安排歌爾德蒙在父性與集體的回歸中死亡,或許這能夠帶來觀眾對“死亡”這一哲學命題的思考與探索,也能夠喚起生活在當下的人們對個人與集體意義的重新審視。
參考文獻:
[1] 余匡復.德國文學史[M].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1991.
[2] Wright,Colin. The Theme of Polarities in Russian and German Twentieth-century Literature:Mikhail Bulgakov and Hermann Hesse as Literary Cousins [J]. Canadian Slavonic Papers,1983(3).
[3] 方曉明.追蹤生活之母——讀黑塞《納爾齊斯與歌爾德蒙》[J].山東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90 (6).
[4] 赫爾曼·黑塞. 納爾齊斯與歌爾德蒙[M].楊武能譯.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2020.
[5] 申丹.西方敘事學:經典與后經典[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
[6] 馬丁·海德格爾.存在與時間[M].陳嘉映,王慶節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4.
[7] 吳海林.空間作為建構主體的元素——試析赫爾曼·黑塞小說《納爾齊斯與歌爾德蒙》[D].四川外國語大學,2018.
[8] Kurt,Ficker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Outsider Concept in Hesses Novels [J]. Monatshefte,1960(4).
[9] 姜淑楠.走向“慈母”之路——對黑塞教育小說《納爾齊斯與歌爾德蒙》的解讀[D].山東師范大學,2014.
[10] 謝瑩瑩.生命之愛與塵世之怯——獨行者赫爾曼·黑塞(一篇虛構的訪談錄)[J].外國文學,1997 (1).
[11] 威廉·巴雷特.非理性的人[M].段德智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92.
[12] Narzi und Goldmund. Dir. Stefan Ruzowitzky. Perf. Jannis Niew hner,Sabin Tambrea. Deutsche Columbia Pictures Filmproduction,2019.
作 者: 黃靖,揚州大學外國語學院2019級在讀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英美文學與文化。
編 輯:趙斌 E-mail:mzxszb@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