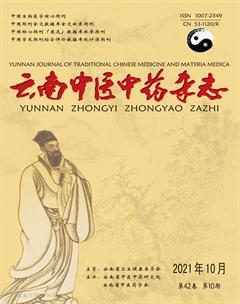李廷荃教授濕邪致病初探
侯文慧 李廷荃 韓杰
摘要:通過對“濕邪”的概述、致病特點、以及部位層次和病機深入探討李廷荃教授治療濕邪選方和用藥規律,從不同角度為臨床治療濕邪提供指導。
關鍵詞:濕邪;皮膚;肌肉關節;五官九竅
中圖分類號:R256.3??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7-2349(2021)10-0003-04
濕邪致病在臨床廣泛多見,病情繁雜,變化多端且不易診斷。濕性蘊含著濕潤、遲緩、黏滯、重濁、趨下等義,易傷脾陽及阻滯氣機,易夾雜它邪為患,所致疾病纏綿難愈。李廷荃教授為山西省名醫,從事教學、醫療、科研近30年。在多年臨證中對消化系統疾病及一些疑難雜癥等都有獨到見解,在學術主張“致中和”思想,善用“和”法治療。李教授認為消化系統疾病病機多為肝脾胃不和,寒濕熱錯雜。治療原則包括脾升胃降調病勢,溫運脾陽以培本,清化濕熱以除邪。溫運脾陽以治本,加之祛除濕熱之邪,調節脾胃升降,使人體中焦之氣暢則脾胃自和。
1 “濕邪”概述
在中醫學中,“六氣”“六淫”中均含有“濕”,但其含義和意義[1]卻是大相徑庭,前者表示人類及自然界生物賴以生存的條件,稱為濕氣。如《素問·陰陽應象大論》云:“天有四時五行,以生長收藏,以生寒暑燥濕風”;后者則表示對機體有害的致病因素,稱為濕邪。濕邪經過后世醫家的繼承和發展,對該學說認識不斷得到完善,臨床中疑難雜病從濕論治具有良好的治療效果。
濕邪是導致疾病發生的主要因素之一。中醫學認為,“濕”分內濕和外濕[2],外濕為外感六淫邪氣之一,多由氣候潮濕或涉水淋雨,居處潮濕等外在濕邪侵襲人體所致;內濕則是由于脾失健運,水濕停聚所形成的病理狀態。二者雖有不同,但在發病過程中又常相互影響。
李廷荃教授認為當濕氣太過或者人體正氣不足,超出人體自身所能調節的范疇,人體的陰平陽密狀態被打破,侵入人體發展成為濕邪就會誘發疾病。而濕邪不僅涉及脾的功能失常,肝腎失調亦是其重要的病機。在治療上主張以調理肝脾腎功能為基本原則,以祛濕為主,同時不忘行氣疏肝,調暢氣機。臨床用藥善用經方,喜用藿香、佩蘭等芳香化濕之品。
2 致病特點
《中醫濕病證治學》[3]提出“無論外濕、內濕致病,基本病機皆為水濕內停,氣機失常”。二者具有濕邪共性特點:其一,易重濁。正如《素問·生氣通天論》云:“因于濕,首如裹,濕熱不攘,大筋軟短,小筋弛長,軟短為拘,弛長為痿。”脾虛不能為胃行其津液,致奏理間濕氣盛,因而可現頭重,身重等證[4];其二,易損傷人體陽氣,阻遏氣機。如《素問·六元正紀大論》云:“濕勝則濡泄,甚則水閉胕腫。”水濕泛濫,溢于皮膚肌腠之間,則發為水腫;其三,易下趨,襲陰位。如《素問·太陰陽明論》[5]云:“傷于濕者,下先受之”,濕氣傷人,多從人體的下部侵入;其四,易黏滯,病程纏綿,易兼它邪為患。李廷荃教授認為由于濕邪變化多端、致病特點表現多樣,在臨床上更要注重在四診合參的基礎上抓主癥,抓病機。辨證準確則事半功倍。
3 臨床表現
濕邪臨床表現復雜多樣,在內、外、婦、兒疾病中均有涉及,《金匱要略·痙濕暍病脈證治》:“濕家之為病,一身盡疼,發熱,身色如熏黃也”。張仲景認為濕邪較重患者多身體肢節沉重疼痛,發熱、頭汗出,胸滿,小便不利等癥[6]。李教授看來濕邪的表現主要為“重”“濁”二字,不論是身體困重,頭重昏蒙,記憶力差,口膩,面垢,大便溏、黏滯,還是小便渾濁如米泔,白帶量多黏稠等都是這兩個字的提煉,都應該考慮濕邪,從濕論治。
4 濕在皮膚、肌肉、關節、五官九竅
4.1 “濕”在皮膚—脂溢性脫發 脂溢性脫發是伴有皮脂溢出且頭頂部禿發性的疾病,中醫稱之為“發蛀脫發”、“蛀發癬”[7],病因為濕熱內壅,加之脾虛轉運無力,膏粱之物堆積,脾胃健旺,嗜食肥甘,以脂質潴留,李廷荃教授認為:“脂溢性脫發病機核心在于濕熱壅盛,上溢頭皮,與脾有關,同時由于腎臟其華在發,故在治療上主要以清利濕熱、涼血活血,佐以滋養肝腎來生發”,基礎方主要為蒼術、苦參、土茯苓、牡丹皮、生薏米、車前子、女貞子、旱蓮草、甘草等。蒼術、土茯苓、生薏仁燥濕健脾,使得濕邪生化之源脾氣健旺以固本,加之牡丹皮清利濕熱,車前子利水滲濕使濕熱之邪從小便而走,分消走瀉以除標,旱蓮草滋補肝腎同時兼顧涼血止血。
4.2 “濕”在肌肉—慢性疲勞綜合征 慢性疲勞綜合征內涵闡釋:排除其它疾病的情況下疲勞持續6個月或者以上,并且至少具備以下癥狀中的四項:(1)短期記憶力減退或者注意力不能集中。(2)咽痛。(3)淋巴結痛。(4)肌肉酸痛。(5)不伴有紅腫的關節疼痛。(6)新發頭痛。(7)睡眠后精力不能恢復。(8)體力或腦力勞動后連續24 h身體不適。《溫病條辨·濕》云“脾主濕土之質,為受濕之區,中焦濕證最多”,李廷荃教授認為濕邪浸淫肌肉,主要表現為肌肉活動的不利,中焦處于樞紐位置,治療濕病尤為重中之重,濕性重濁,蘊結在肌肉可致頭身困倦,四肢沉重,精神不振,方可用升陽益胃湯,方藥黃芪、人參、白術、茯苓、半夏、橘皮、柴胡、澤瀉、防風、白芍藥、羌活、獨活、黃連、炙甘草。升陽益胃湯健脾除濕,益氣升陽。脾主四肢,故可有效地改善怠惰嗜臥,四肢不收,口苦舌干,飲食無味,食不消化,大便不調等脾虛癥狀,同時用柴胡疏肝行氣解郁,注重氣機的調暢,進而可以有效的改善慢性疲勞綜合癥。
4.3 “濕”在關節—高尿酸癥(痛風) 痛風是臨床常見的代謝性疾病,從中醫來說,屬于“痹癥”,癥狀主要表現為關節肌肉沉重、酸痛或麻痹拘攣等。脾胃是參與機體代謝的重要臟器,脾胃運化失司,則尿酸濕濁內阻,蘊而化熱,導致關節腫痛急性發作[8]。李廷荃教授認為濕在關節,累及關節周圍的筋肉系統,造成關節牽扯痛、局部腫脹等。濕邪侵犯人體,常引起筋肉關節病變。基于“諸濕腫滿,皆屬于脾”理論來從濕邪論治痛風,在健脾治本虛的同時,注重關節疼痛標實的存在,治療上采用以下常用藥物,方選麻黃、杏仁、生薏米、車前子、甘草健脾為基礎方的同時輔以丹皮、銀花藤、全蝎、活血祛瘀,通絡止痛。痛風之病,年代久遠必瘀久化熱,故可加入生石膏清熱瀉火。[JP]
4.4 “濕”在五官九竅—口腔潰瘍 脾主升清,胃主降濁,脾胃受損則其升降失常,痰濁邪熱上犯于口,發為口腔潰瘍。口腔潰瘍發作的根本在于脾胃的寒熱錯雜、虛實相兼,以致中焦失和,氣機升降失常。故在治療上李廷荃教授主張以“和”為法,從濕邪論治口腔潰瘍,方選半夏瀉心湯+丹皮、生地。半夏瀉心湯辛開苦降,寒熱平調的功能也符合脾升胃降的生理特點。方中半夏散結消痞,降逆止嘔;干姜溫中散寒;黃連、黃芩苦寒而泄熱開痞。四藥相伍,平調寒熱、辛開苦降之用。加之人參、大棗甘溫益氣,以補脾虛,使以甘草補脾和中而調諸藥[9]。
4.5 “濕”在五官九竅—鼻淵 鼻淵的主要臨床表現為鼻塞、清涕、噴嚏、鼻癢、下鼻甲肥大水腫,鼻黏膜蒼白等。其主要病機為中焦失運,清陽下陷,精微物質滯留中焦,形成濁、濕、痰、飲等病理產物有關,濕濁上擾清竅,纏綿不愈[10]。李廷荃教授從“濕邪”論治鼻淵基礎方為:全瓜蔞、桔梗、杏仁、藿香、黃芩、苦參、全蝎、蜈蚣、白頭翁、生薏米、蘆根。其中生薏米和中護胃,健脾以除痰生化之源。杏仁宣通氣機,瓜蔞,桔梗,蘆根祛痰排膿。上下同治,氣機調暢,鼻淵自除。
5 典型病案
患者劉某,男,18歲,初診時間為2019年9月4日。主訴:尿酸偏高6 a。現病史:患者于6 a前體檢時發現尿酸偏高,約500 umol/L(未見單),6 a間定期復查,波動在500~600 umol/L之間,未予系統診治,間斷口服中藥治療。2019年8月31日于山西大醫院復查尿酸:764.3 μmol/L,遂來就診。現:無小關節疼痛,納眠可,二便調。無明顯不適。舌淡紅苔心白黃膩脈滑。診斷為高尿酸血癥(脾虛濕阻)。方藥:黃芪30 g,防己10 g,生白術15 g,麻黃6 g,杏仁10 g 生薏米18 g,澤瀉10 g,甘草6 g,7劑,日1劑,水煎服,早晚分服。二診:2019年9月11日。現:納眠可,二便調,無明顯不適,繼續調理。舌淡紅苔心白黃。治宜健脾利濕。方藥:生黃芪30 g,蒼術10 g,防己10 g,麻黃6 g,杏仁10 g,生薏仁18 g,澤瀉10 g,車前子30 g,甘草6 g。7劑,水煎服,日1劑,早晚分服。三診:2019年9月25日,現:納眠可,二便調,余無不適,欲繼續調理。2019年9月20日于山西大醫院行尿酸檢查:604.1μmol/L。舌淡紅苔白脈弦。治宜健脾除濕清熱。方藥:生黃芪30 g,蒼術10 g,防己10 g,大黃5 g,麻黃6 g,生薏仁18 g 車前子30 g,澤瀉10 g,甘草6 g,丁香18 g。10劑,水煎服,日1劑,早晚分服。
按:高尿酸血癥是由于過度尿酸無法通過正常途徑排泄或嘌呤代謝紊亂導致。患者苔心白黃膩脈滑,則辨為脾虛濕熱。方選防己黃芪湯合麻黃杏仁薏仁甘草湯。功效為益氣祛風,健脾利水,主治風水或風濕,癥見汗出惡風,身重浮腫,小便不利,肢體關節疼痛。方中重用黃芪補氣固表,健脾行水消腫;防己祛風行水,與黃芪相配,補氣利水作用增強,且利水而不傷正;白術健脾勝濕,與黃芪相配,益氣固表之力更大;麻黃疏風散邪,除濕溫經;杏仁宣降肺氣,通調水道,使水濕得以下輸;薏苡仁除濕祛風,兼能運脾化濕,使濕從前陰而去;澤瀉利水滲濕;甘草和諸藥。患者二診時無明顯改變,故在原方基礎上白術換成蒼術,加車前子滲濕利尿。三診時行尿酸檢查為604 μmol/L,較之前好轉,明顯降低,故仍在原方基礎上加大黃,清熱瀉火。在日常生活中也要注意生活方式,包括健康飲食,應以低嘌呤食物為主,嚴格控制肉類、海鮮和動物內臟等食物攝入;多飲水,戒煙戒酒,堅持運動。
6 小結
濕邪致病纏綿難愈,致病繁多,涉及內、外、婦、兒等多個學科,可以看到觀察的角度不同,濕邪的病機各異,治療也不同。李廷荃教授認為治療濕邪必然要先掌握濕邪的性質和致病特點,明確濕邪的性質和病位所在,才能采取更具針對性的治療方案,因勢利導,從而提高療效,達到治愈疾病的目的。
參考文獻:
[1]孫帥玲,馬曉北.從濕邪論治變應性鼻炎[J].環球中醫藥,2020,13(12):2098-2100.
[2]車振文,李有田.淺談健脾化濕法[J].吉林中醫藥,2003(11):3.
[3]路志正.中醫濕病證治學[M].北京:科技出版社,2010:4-5.
[4]張洋,依秋霞.濕邪致病脈象的變化淺析[J].湖南中醫雜志,2020,36(12):106-108.
[5]方威政,丘述興,蔣筱.中醫“濕”義考[J].中醫學報,2021,36(1):50-53.
[6]馬學,張怡,曾進浩,等.從“宣、化、利”法淺析張怡治療濕病經驗[J].中醫藥臨床雜志,2020,32(2):236-238.
[7]趙靜,楊志波,李兆晟.楊志波教授辨治脂溢性脫發經驗[J].湖南中醫藥大學學報,2020,40(7):880-883.
[8]賀明玉,劉健,韓馨悅,等.痛風性關節炎患者免疫指標的變化及中醫藥干預的數據挖掘研究[J].風濕病與關節炎,2019,8(10):9-13.
[9]賀怡然,李廷荃.李廷荃教授運用半夏瀉心湯臨證舉隅[J].光明中醫,2016,31(4):571-572.
[10]孫雅玲,龔東方.從《脾胃論》論點試論過敏性鼻炎的取穴思路[J].社區醫學雜志,2014,12(21):39-40.
(收稿日期:2021-05-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