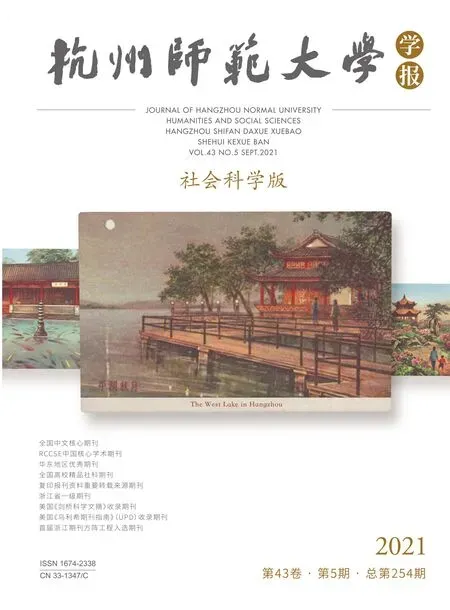當代中國人口婚姻嬗變及風險治理
穆光宗,林進龍,江 砥
(1.北京大學 人口研究所,北京100871; 2.黃岡師范學院 地理與旅游學院,湖北 黃岡 438000)
面對連創新低的結婚登記數和結婚率以及持續上升的離婚登記數和離婚率,媒體與公眾輿論不斷發酵,“中國超2億人單身”“為什么現在找個婚戀對象這么難”等網絡報道鋪天蓋地,正勾勒出一種逐漸“式微”的婚姻圖景。而2021年1月1日開始實施的“離婚冷靜期”規定以及7月20日公布的《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于優化生育政策促進人口長期均衡發展的決定》關于婚姻問題治理的建議,(1)2021年5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在審議“三孩政策”配套措施時強調,要加強適婚青年婚戀觀、家庭觀教育引導,對婚嫁陋習、天價彩禮等不良社會風氣進行治理;7月20日公布的《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于優化生育政策促進人口長期均衡發展的決定》再次提出,要提倡適齡婚育,破除高價彩禮等陳規陋習。似乎也真實反映了政府在某種層面上的擔憂。
然而,學界關于中國婚姻態勢的研究卻呈現出一種斷裂和混沌的景象。不同學科之間對婚姻研究的學術對話嚴重不足,這限制了對中國婚姻態勢全面客觀的認識。即便面對中國同一時期的離婚現象,研究結論也不盡相同,甚至大相徑庭。有觀點認為改革開放以來離婚越來越成為中國社會的普遍現象[1],反對聲音則主張迄今為止普遍結婚仍是國人的整體現狀,離婚水平仍處較低水平[2]。針對當前中國“離婚熱”暴露出的家庭關系問題[3],部分學者發出預警,持續上升的離婚率會造成中國婚姻制度失范[4],影響家庭功能的正常發揮[5],甚至還可能引起社會的動蕩[3];但亦有學者認為,離婚率的上升彰顯著婚姻文明化的社會趨勢[6],對當下中國婚姻的高穩定性沒有實質影響[7]。
國內婚姻問題研究的學術爭鳴表明,當前中國婚姻圖景有待進一步厘清。因不同研究對指標的使用側重有所不同,其得出的結論也不盡相同。目前,學界最常使用的結婚率和離婚率指標除受真實的事件水平影響以外,還與人口的結構特征有關。因此,為全面反映中國婚姻的真實狀況,有必要具體分析不同年齡、性別、城鄉和地區人口的婚姻態勢。全國婚姻統計數據集中見于歷年人口普查和抽樣調查數據,主要報告不同婚姻狀態人口的分層特征。盡管不能利用這些數據計算結婚和離婚的事件水平,但可以用以考察處于未婚和離婚狀態人口的特征,從而一定程度反映中國人口的婚姻態勢。由于不同的婚姻狀態指標之間容易相互影響,(2)我國人口普查和抽樣調查將婚姻狀態分為未婚、有配偶(初婚和再婚)、離婚和喪偶四種情況。從人口統計角度看,處于離婚狀態的人口規模受其他三種婚姻狀態人口規模的影響。譬如,一個再婚率高的國家,其離婚率往往也較高,但其處于離婚狀態的人口比例就要低一些。因此還有必要利用隊列數據專門考察中國人口的初婚和離婚風險。
在此基礎之上,如何評價中國的婚姻態勢同樣值得關注。亦即中國婚姻態勢的嬗變究竟是閃爍著婚姻文明的現代光芒,還是某種意義上可能殃及家庭和社會發展的歷史倒退。一國人口的宏觀結婚和離婚態勢,實際上是由一個個鮮活個體自發能動的微觀決策和行為聚集而成的,因而代表了人們真實有效的婚姻意愿和選擇權利。因此,如果中國離婚水平上升是真實不虛的話,其背后折射的似乎是婚姻制度的文明化、自由化和現代化的價值取向。然而,從國家治理和社會發展的訴求出發,我們又并不希望婚姻態勢嬗變的消極傾向繼續蔓延。這就要求我們在描繪中國婚姻圖景的基礎上,尋找其嬗變的動力并對其進行客觀評價。
綜上,本文將綜合運用時期、時點和隊列指標(3)時期指標指一定時期內各個時點發生的人口事件的總和,反映人口在一定時期內的變動情況,比如某一年度的結婚數(率)和離婚數(率)指標;時點指標指連續不斷變動過程的一個橫斷面,反映某一時點的人口數量及其狀態特征,比如未婚狀態人口比例和離婚狀態人口比例指標;隊列指標指隊列成員在人口過程中發生各種事件的時間分布、頻率概率等,比如回顧隊列的平均初婚年齡和初婚隊列的離婚風險指標。這三類指標對一國婚姻圖景的刻畫,可以說各有依歸、認知互補。考察中國人口的婚姻態勢,歸納我國婚姻態勢的基本特征,并在此基礎上分析中國婚姻態勢變動可能帶來的消極影響,最后對中國婚姻問題的治理之道提出思考和建議。
一、中國人口婚姻狀況的統計學圖景
目前學界對我國婚姻態勢的量化考察主要使用結婚率和離婚率指標。這兩個指標統計簡單、數據易得,并能一定程度反映人口在某一時期內婚姻事件的頻數和頻率。但結婚率和離婚率除受真實的結婚和離婚水平影響以外,還與人口的自然和社會結構有關。為客觀刻畫中國婚姻圖景,下面運用時期指標、時點指標和隊列指標全面考察我國人口的結婚和離婚態勢。
(一)總體狀況
學界通常說的結婚率和離婚率實際上是粗結婚率(Crude Marriage Rate,CMR)和粗離婚率(Crude Divorce Rate,CDR),即某一年的結婚/離婚對數除以同期該地區的全部人口數,表示每千人中結婚/離婚人數的比例。通過考察結婚率和離婚率的變動情況,可以一定程度反映我國人口結婚水平和離婚水平的高低及其走勢。計算公式寫作:

如下圖1所示,除個別年份以外,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離婚對數和離婚率呈現持續增長的趨勢。1978年,我國離婚數僅28.5萬對,離婚率為0.2‰;2019年,離婚數超過470萬對,離婚率達到3.4‰。40余年,中國離婚數和離婚率的增長幅度分別達到15倍和16倍。同期,中國的結婚對數和結婚率則波動不定,在1981年達到高峰后又波動下降并于2002年跌至低谷,2013年回升至新一輪高峰后持續下降至今。結婚數的變動與適婚人口規模及其年齡結構有關,因此僅據此并不足以研判中國真實的結婚水平走勢。
根據圖1,可以初步得到的結論是,中國離婚態勢已然走高。這是因為離婚事件只能發生在已婚人口中,因此離婚事件的頻數和頻率的變動對結婚事件的變動而言具有一個應激反應的滯后效應。在離婚水平不變的前提下,基期結婚人口下降時,暴露在離婚風險下的當期人口規模也隨之減少,應當導致離婚數和離婚率降低。然而,我國的離婚數和離婚率卻持續呈現穩步上升態勢,與結婚事件的變動趨勢截然不同,可能的解釋是我國離婚水平的提高抵消了一些年份結婚人口下降的基數效應。但僅根據結婚率和離婚率并不足以研判一國人口婚姻狀況的真實情況,有必要對結婚和離婚狀況做進一步分析。

圖1 1978-2019年中國粗離婚率和粗結婚率數據來源:歷年全國人口普查、全國1%人口抽樣調查和人口變動情況抽樣調查。
(二)結婚狀況分析
1.初婚和初育年齡
初婚年齡是重要的婚姻形成測量指標。女性人口的平均初婚和初育年齡的變動態勢,可以為國人的婚育觀念和婚姻模式轉型提供一個佐證。下圖2顯示,20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女性的初婚和初育年齡不斷推遲,婚育模式表現為晚婚和晚育。1990年中國女性人口的平均初婚和初育年齡分別為21.6歲和23.8歲,2018年則上升至26.3歲和27.5歲,分別延遲4.7和3.7歲。女性初婚初育年齡推遲現象,表明現代女性不必再像傳統一樣絕對依附于婚姻和男性,而選擇通過延遲婚育來增加發展機會和上升通道,以滿足自身的發展需求,在某種意義上反映了婚姻對女性發展的順次序位降低。

圖2 1990-2018年全國女性人口的平均初婚初育年齡數據來源:根據中國家庭追蹤調查(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CFPS)2010-2018年調查數據計算得到,由于2015-2018年樣本量較小對其進行了修正。
2. 未婚和終身不婚人口比例
晚婚不代表不婚。圖3顯示,我國未婚人口比例隨著年齡的增長而逐漸降低,從20-24歲的80.77%下降至65歲及以上的1.47%,因此從相對數看終身不婚的人口比例相對較低。盡管結婚年齡有所推遲,但結婚仍是絕大多數國人的選擇,普婚依舊是國人的現狀。與此同時,未婚狀態的兩性差異則十分明顯,以30-34歲年齡組人口為例,2015年每100名男性人口中就有14人仍然未婚,而女性則僅有7人;45歲以后女性未婚比例已降至0.5%以下,但男性未婚比例卻仍接近3%,充分體現出性別比畸形帶來的男性婚姻擠壓現象。而結婚成本畸高使一些低收入家庭和男青年望婚興嘆,成為當代中國結婚難的重要原因。例如,2021年山西、河南、湖南等地的農村走訪發現,娶妻必備的車、房、彩禮等新“三大件”花費竟然飆漲到上百萬元,結婚已成為部分農村大齡男青年家庭的沉重負擔,甚至成為部分農村家庭負債、致貧的重要原因。

圖3 2015年中國各年齡組未婚人口比例數據來源:2015年全國1%人口抽樣調查。
(三)離婚狀況分析
1.哪些地方離婚率高?
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2000年我國離婚率高于1‰、2‰和3‰的省份分別為12個、3個和1個,超過一半省份離婚率低于1‰;2019年中國各省離婚率中,最低的西藏自治區也達到了1.5‰,最高的重慶市更達到了5.0‰,離婚率超過2‰和3‰的省份分別達到30個和18個。圖4示意2000-2019年中國各省的年均離婚率增長幅度,進一步提示了近年來中國各地區的離婚態勢。由圖可知,過去20年幾乎所有省份的離婚率都實現了正增長,只有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的離婚率呈現微弱的負增長(-0.2%),但2000年時的新疆離婚率就已高達3‰。在離婚率正增長省份中,除上海、北京和遼寧的年均離婚率增幅不足4%,絕大多數省份的離婚率年均增長幅度達到6%左右,河南、貴州和安徽等少數的年均增長率更是超過8%。總之,數據顯示離婚率增長并非局部現象,而是已經成為一種全國性的普遍現象。

圖4 2000-2019年中國各省(直轄市、自治區)粗離婚率年均增長幅度數據來源: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使用幾何級數法測算,圖片使用ArcGIS軟件繪制。
2.哪些人處于離婚狀態?
(1)分年齡的人口分析
圖5顯示了2000-2018年中國各年齡組人口處于離婚狀態的占比情況。數據表明,近年來中國不同年齡段人口處于離婚狀態的比例均呈明顯上升趨勢。即便以離婚狀態人口比例最低的20-29歲年齡組人口為例,在未婚人口比重快速上升背景下,(4)根據本文對2000年全國人口普查和2018年人口變動情況抽樣調查數據的測算,2000-2018年中國20-29歲人口的未婚狀態比例從329.3‰上升至558.7‰,測算對象為20歲及以上人口。該年齡組人口的離婚狀態比例在2000-2018年仍從5.3‰增長至9.2‰。同期,40-49歲年齡組人口的離婚狀態比例從13.6‰上升至34.0‰,相當于2018年每一千個“70后”(1970-1979年出生人口)中就有34人的婚姻狀況是離婚狀態;而50-59歲年齡組人口的離婚狀態人口比例則從不足10‰提高至26.6‰,上升速度最快,增長幅度達到180%。此外,根據本文測算(5)以2000年普查人口的年齡結構為標準,對2000年全國人口普查和2018年全國人口變動抽樣調查的離婚狀態水平進行標化計算,發現標化前后的2018年中國離婚狀態人口比例幾乎沒有變化。,人口年齡結構變化對近年來中國離婚狀態人口比例走高的影響極小。中國離婚態勢不僅是趨高的,而且相當程度上是由分年齡或者說年齡別離婚水平的提高推動的。盡管圖3表明,普婚仍是中國婚姻態勢的基本現狀,但圖5又清晰明確地提示中國的婚姻穩定性正在下降,并且持續地發生在各個年齡段,越來越多的人在離婚后選擇保持單身而非再次結婚。

圖5 2000-2018年中國各年齡組離婚狀態人口比例數據來源:根據2000年和2010年全國人口普查、2005年和2015年全國1%人口抽樣調查以及歷年人口變動情況抽樣調查數據推算。由于中國法定婚齡至少為20周歲,因此推算對象為20歲及以上人口。
(2)分性別的人口分析
圖6顯示了2000-2018年中國處于離婚狀態人口的比例。在兩性未婚比例均上升情況下(6)根據本文測算,2000-2018年,中國男性人口處于未婚狀態的比例從146.6‰上升至160.4‰,女性則從74.3‰上升至97.6‰。測算數據來源同上,測算對象為20歲及以上人口。,離婚狀態人口比例走高意味著我國兩性人口暴露在離婚狀態的風險變高了。其中男性處于離婚狀態的比例從2000年的12.5‰增長至2018年的24.7‰,不到20年的時間翻了一番;女性處于離婚狀態的比例變化幅度更大,離婚狀態比例從7.6‰上升到了20.2‰,相當于每一千個婦女就有20人的婚姻狀態是離婚。女性離婚狀態人口比例的快速增長,透視出社會對女性“離婚”負面評價的淡化,經濟、社會和文化的進步增強了女性自身和社會對離婚行為的包容性。2010年全國人口普查數據顯示,城市、城鎮和鄉村處于離婚狀態的男女性別比分別為81、116和245,表明城市處于離婚狀態的女性“過剩”,而鄉村男性的“婚姻擠壓”現象十分突出。

圖6 2000-2018年中國兩性離婚狀態人口比例數據來源:根據2000年和2010年全國人口普查、2005年和2015年全國1%人口抽樣調查以及歷年人口變動情況抽樣調查數據推算,推算對象為20歲及以上人口。
3.離婚風險
婚姻存續時間及其解體風險對婚姻壽命和穩定性的考察具有重要意義。表1示意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不同初婚隊列人口在婚后若干年內的離婚比例。根據中國家庭跟蹤調查數據,1990-1999年初婚隊列在婚后5年、10年和20年內的離婚比例分別達到28.5‰、54.2‰和76.7‰,比1950-1959年初婚隊列分別高出11.6‰、30.4‰和52.0‰。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的初婚世代人口離婚風險明顯增高,2000-2009年初婚隊列的每一千對夫妻中就有36對在婚后5年內離婚,比改革開放前的初婚隊列(1970-1979年)婚后5年內的離婚比例高出28.8‰。

表1 中國不同初婚隊列人口婚后若干年內的離婚比例(單位:‰)
從婚姻的存續時間看,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的初婚隊列解體風險主要集中在婚后10年內,其中又以婚后5年內離婚居多(72.2%),婚后11-20年內離婚的夫妻占比不足2‰;其后的初婚隊列人口在婚后11-20年內的離婚比例開始走高,1980-1989年和1990-1999年的初婚隊列在婚后11-20年離婚的比例分別達到26.8‰和22.5‰,而婚后5年內離婚對數增長同時,婚后6-10年內的離婚風險也在明顯上升。這表明改革開放以前,中國的婚姻存續時間越長,解體風險就越小,夫妻可能因為歲月相守、也可能因為得過且過,甚至被迫妥協而延續婚姻,但這一規律在改革開放后的中國婚姻實踐中并未得到復現。相反,改革開放以來,初婚隊列的婚姻不穩定性發生了較大幅度增長,我們可以有把握地說離婚風險趨高的特征至少貫穿著這些初婚人口婚后20年的婚姻生活。
4.離婚方式
離婚主要包括民政部門登記離婚和法院判決/調解離婚兩種情況。圖7顯示了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離婚登記情況。數據顯示,進入21世紀以來,我國法院判決和調解離婚數保持著穩定態勢,基本維持在60-70萬例。而民政部門登記離婚數在1978-2019年則從17萬例(59.6%)增至405萬例(86.1%),漲幅達到法院判決和調解離婚數的7倍之多。根據蘇州市民政局統計,該市2014年離婚16432對,其中“沖動型”離婚占1/3以上。(7)參見苑廣闊《“專家勸和政府買單”值得肯定》,《湖南日報》,2015年1月30日。2019年寧波市婚姻大數據顯示,離婚當事人婚姻維系時間不足一年的婚姻占比約1/10,不足三年的婚姻占比1/5,“80后”“90后”多是“沖動型”離婚,“閃婚”“閃離”現象不容小覷。(8)寧波市鎮海區人民政府:《2019年寧波婚姻大數據出爐,“沖動型”離婚夫妻挺多》,中國寧波網,2020年1月8日,http://www.zh.gov.cn/art/2020/1/8/art_1229033277_43725381.html。民政部門登記離婚例數激增,雖然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社會對婚姻自由的尊重和保護,但青年夫妻輕率離婚現象也反映了新生代對婚姻的草率和責任感的淡薄。[8]缺乏外部調和的輕率型離婚,實際上是對婚姻制度穩定性的打擊,在某種意義上是婚姻自由化和現代化的副產品。

圖7 1978-2019年中國離婚登記情況數據來源:《中國民政統計年鑒2020》。
二、婚姻狀況的基本特征和嬗變風險
當代中國婚姻圖景是一幅“矛盾”的景象,在流變之中呈現二分屬性,即在婚姻制度上表現為穩定性和脆弱性,在婚配關系上表現為平等性和擠壓性,在婚姻決策上表現為主體性和自我性,在婚姻文化上表現為傳統性和現代性的消長,其中婚姻狀況的負向嬗變及其影響尤其值得關注。
(一)中國婚姻狀況的基本特征
1.穩定性與脆弱性
中國婚姻圖景特征在婚姻制度的演進趨勢上表現為穩定性和脆弱性。穩定性是指婚姻制度仍是維系中國家庭和社會發展的重要紐帶,婚姻狀態對國人而言仍是一個重要的身份標識。這種穩定性體現在,當前普婚仍是中國婚姻狀況的基本特征,結婚仍是國人的普遍選擇。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人口的結婚對數和結婚率的浮動變化主要受全國人口年齡結構和適婚人口規模的變動影響,從2013年開始雙雙走低的結婚對數和結婚率并不足以說明中國正成為“單身大國”。相反,我國終身不婚人口的比例仍相對較低,真實的結婚水平仍然較高。
脆弱性是指婚姻關系在現代社會轉型過程中表現出的不穩定性和解體風險逐步顯化的傾向。這種脆弱性體現在,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人口的離婚風險正逐漸蔓延至全人口和全家庭生命周期。一方面,我國離婚態勢走高已非地方局部現象,而是一種全國性的普遍現象,并且在相當程度上是由年齡別離婚水平的提高推動的;另一方面,中國婚姻的解體風險也不再局限于家庭成立之初,離婚風險趨高的特征至少貫穿在初婚人口婚后20年的家庭生命周期。
2. 平等性與擠壓性
中國婚姻圖景特征在婚配人口的性別格局(9)本文定義的性別格局是指人口在自然性征和社會權力分布上的性別關系。上表現為平等性和擠壓性。婚姻作為兩性社會結合,兼具生物性和契約性,由此決定了婚姻制度同時受一國人口的生理性別結構和社會權力的性別分布之雙重影響。婚配關系上的平等性是指兩性社會結合在法理意義和實際意義上彰顯著性別平等的價值元素。中華人民共和國用一部《婚姻法》埋葬了封建包辦的婚姻制度,離婚女性人口的快速增長,也表明女性離婚的負面社會評價正在淡化,取而代之的是社會對女性離婚行為的包容與尊重。
擠壓性是指婚姻市場上“男多女少”的性別生態失衡產生了婚配的“女方市場”,形成男性擇偶擠壓。尤其在不少農村地區,適婚青年正面臨著男多女少的尷尬和無奈。[9]從未婚人口和終身不婚人口的比例看,男性顯著高于女性,充分體現了婚配人口性別生態失衡帶來的婚姻擠壓現象。這種男性婚姻擠壓效應還延續到了婚姻解體的生命階段,離婚之后的男性人口保持離婚狀態的風險仍要明顯大于女性。男性離婚狀態人口比例的走高,透視出社會分層和市場經濟背景下婚配的“女方市場”和大齡單身男性的無奈,[10]這可以從鄉村離婚狀態男性人口“過剩”中得到一定程度的佐證。
3. 主體性與自我性
中國婚姻圖景特征在當代青年的婚戀決策上表現為主體性和自我性。主體性是指個體在婚戀決策上的意識和地位得到進一步凸顯。這種主體性一方面體現在婚戀自由上,另一方面體現在婚姻退出的法律門檻不斷降低并愈來愈取決于兩性對婚姻質量和婚姻價值的評判上。人們擁有了過去無可比擬的婚姻自主權,面對婚內沖突與矛盾,自主離婚取代了被迫妥協,成為個體在不幸婚姻關系中爭取自由和獨立的重要途徑。改革開放以來,民政部門登記離婚例數的激增態勢就體現了社會對戀愛自由和婚姻自主的人文保護。
自我性是指婚姻家庭本位讓位于個人本位,主張個體婚戀自由,不喜外部調和干預,缺乏倫理約束,導致家庭責任感和社會責任感淡化甚至缺失。伴隨婚姻決策的“主體性”的崛起,“自我性”在婚姻和家庭關系中也不斷膨脹。“閃婚”“閃離”現象雖然是某種意義的戀愛自由和婚姻自主,但“沖動型”離婚、婚姻維系時間短等“80后”“90后”青年夫妻輕率結婚離婚的社會現象也反映了新生代對婚姻的草率與責任感的淡薄。
4. 現代性的增長與傳統性的消亡
中國婚姻圖景特征在社會主流的婚姻文化上表現為傳統性與現代性的消長嬗變。現代性是指婚姻的功能和目的不再局限于生兒育女的傳宗接代需求,更加趨向理性。不斷推遲的婚育模式表明婚姻對個體發展的順次序位正在下降,特別是中國女性不再像傳統社會一樣淪為婚姻的附庸品而絕對依附男性,而是通過延遲婚育和積累發展資本來提高自身在家庭與社會中的地位。
婚姻文化的現代化在某種層面上發展成了婚姻制度主體的異己力量,從而威脅婚姻制度的穩定性和可持續發展。一方面,隨著兩性婚姻觀念的轉變,經濟理性正在取代文化感性,成為國人婚姻決策的重要評價因素,結婚決策越來越受婚姻市場調控,甚至出現了“商品化”的擇偶傾向和高度物質化、炫耀性、講面子、重人情的婚嫁民俗(如天價彩禮)等不良社會風氣;另一方面,盡管婚姻狀態的多樣性是現代文明的某種表征,體現了社會對多元文化的包容,但單身主義、不婚主義(同居戀愛但不結婚)乃至丁克主義的婚姻文化也越來越在青年人口中被盲目推崇和流行開來,不能不引起我們的警惕。
(二)婚姻嬗變的潛在風險
1. 婚姻脆弱性打擊家庭功能
婚姻失敗的個體和家庭代價顯而易見。一個瀕臨解體或者已然死亡的家庭,顯然無法實現生養教育、養老照料和情感支持的功能,對個體和家庭的發展而言不能不說是一個創傷。婚姻關系與親子關系的疊加使得婚姻不僅關乎感情問題,而且關乎親情問題和責任倫理,婚姻承擔了家庭義務和安老懷少的功能。
一方面,婚姻關系的建立是婚內生育的前提和親子關系建立的基礎,婚姻事件顯著地影響生育模式和生育水平。結婚率降低和離婚率的上升會降低婚內生育率,進一步惡化生育少子化情形,形成結婚率下降—晚婚率上升—生育率低迷的惡性循環。婚姻制度的脆弱性在當前生育意愿不振情況下顯然不是好事。
另一方面,一旦家庭生命周期進入“擴展”階段,婚姻的解體就不僅僅是夫妻雙方的事,還會殃及家庭和孩子。離異型單親家庭兒童的自我行動和道德自立表現均要顯著低于完整家庭的兒童,[11]并且更容易社會越軌,在個體社會化過程中將面臨更多的坎坷。[12]家庭破裂引發的養老問題也相當復雜。因此,婚姻的破裂不僅僅是夫妻雙方的感情失敗,而且是對親子關系和家庭發展的沉重打擊。
2. 婚姻擠壓性破壞社會和諧
性別生態失衡和男性婚姻擠壓不利于社會和諧。一方面,長期嚴峻的婚姻擠壓問題將使部分未婚男性游離正常婚姻家庭生活之外,降低其生命質量,[13]還可能引發“買賣婚姻”死灰復燃、性犯罪和地下色情產業增加,對社會正常秩序產生沖擊。另一方面,為應對過剩男性婚姻擠壓,部分未婚男性必然選擇擴大婚齡差的擇偶策略。然而,不適當的婚配年齡差也可能導致年齡代溝和家庭矛盾,[14]從而侵蝕家庭的幸福感和婚姻的穩定性。作為社會的基本單元,家庭功能如果受損也會影響社會的發展與進步。適婚人口性別生態失衡將沖擊主流性別文化,甚至影響社會經濟秩序,不利于兩性和諧與社會穩定。[15]
3. 婚姻自我性滋生道德風險
隨著“雙獨婚姻”和“單獨婚姻”(10)“雙獨婚姻”和“單獨婚姻”分別指夫婦雙方均為獨生子女和夫婦雙方一方為獨生子女的婚姻。上升成為中國婚姻的主流模式,新生代婚戀決策的“自我性”也將不可避免地隨之凸顯。由于獨生子女出生和成長在“小皇帝”“小公主”的家庭環境之中,疊加人際疏離、無序互動的社會原子化傾向影響,因此在婚姻結離上習慣性地高舉“自由”與“權利”的旗幟,而婚后卻對夫妻關系的倫理要求和家庭責任選擇性地“缺失”。婚姻權利濫用疊加家庭責任懈怠影響,不可避免地要滋長新時期的婚姻家庭倫理道德的風險。特別是伴隨著家庭的小型化,家長在婚姻關系中的權威勸說功能開始消退,社會外部的倫理約束力量也在減弱,然而當代青年卻并未相應地表現出自我約束力的增強。外部保護機制的缺失和內在調和能力的不足相互疊加,容易導致騙婚、出軌以及將婚姻當作兒戲的“想結就結”和“說離就離”等現象,引發中國傳統婚姻倫理道德的淪喪。
4. 婚姻文化異化腐蝕婚姻制度
婚姻制度是人類文明發展的必然產物,也是經濟社會發展的基石。當前中國婚姻態勢的嬗變不僅極大地影響國人的家庭和社會生活,本身也會反作用于婚姻制度的可持續發展。當代中國婚姻文化的異化表現是多維的,并在不同程度腐蝕中國的婚姻制度。其中,擇偶的“商品化”傾向和非主流婚姻文化逐漸興起兩大趨勢值得我們警惕。“商品化”擇偶傾向注重審美的愉悅、感官的享受、肉體的親昵和物質的豐裕,與婚姻持久結合的情感需求和倫理追求相背離,從而侵蝕婚姻制度的價值內核與精神實質;非主流婚姻文化(比如單身/不婚/丁克主義)作為對現代婚姻制度的反抗,也可能引發“恐婚恐育”文化在社會流行開來,最終導致婚姻制度的坍塌。
三、當代婚姻問題的治理之道
婚姻和家庭對中國社會而言具有特殊而重要的意義。面對中國婚姻狀況表現出的婚姻制度的脆弱性、婚配關系的擠壓性、婚戀決策的自我性以及現代婚姻文化的傳統與現代的矛盾特征,國家要提前防范和積極治理,避免婚姻問題演化成為人生失敗和社會亂象之源。
第一,加強社會調控,提升對婚姻制度的人文關懷,遏制婚姻脆弱性嬗變的消極趨勢。婚姻制度的優化發展需要社會的共同呵護,應圍繞婚姻生命周期優化設計社會干預網絡。例如,婦聯或基層社會組織可以建立“婚戀指導中心”,幫助婚姻當事人在婚前明確婚姻道德觀念,以便雙方能夠自覺調解婚后可能的沖突;對于婚姻沖突者,社區和村委會應當建立各類婚姻咨詢機構,培育婚姻導師隊伍,引入社會工作專業力量,在婚姻遇到危機時能夠善加勸說、指導、減壓和緩解,轉變執念,挽救那些尚有感情的無過失婚姻,幫助當事人走出困境。還可以通過法律調解手段防止人們濫用離婚自由權,2021年1月1日起實施的“離婚冷靜期”規定,對社會轉型及其裂變本身就是一種人文保護。除此之外也可以探索和試行“試離婚”或“熟慮期”制度。需要指出的是,社會調控不是要禁止人們離婚,而是動用社會力量降低對婚姻當事人的傷害,人文呵護婚姻的制度文明。
第二,重視出生性別比治理,優化可婚人口婚配機制。過剩男性婚姻擠壓現象給我國提出的一個重要預警是,當前出生人口的性別生態關系到未來中國婚姻制度和家庭社會的發展,我國出生性別比失衡的治理屬“國之大者”。不過,當下婚配人口“男多女少”的性別生態失衡是目前無法完全消解的,只能通過優化婚配市場的資源配置方可預期在一定程度上緩和“結婚難”問題。一方面,要降低婚姻市場的信息不對稱問題,如基層社區和村委會可以積極組織集體相親活動并定期發布交友信息;另一方面,應持續推進鄉村振興,加大對弱勢“光棍”群體的技能培訓力度,提高貧困家庭收入水平。此外,還應加強和創新婚姻管理制度,在依法打擊買賣婚姻和性犯罪的同時,完善社會保障體系,適當調整以家庭為單位的社會保障制度,保障大齡單身男性的基本社會福利。
第三,強化婚姻倫理道德建設,重視對新生代兩性之愛的教育和家庭責任感的培養。一夫一妻制度是人類經過漫長的歷史進化而來的婚姻文明。人們普遍接受的愛情觀和婚姻觀是一對一的,具有天然的排他性。改革開放以來,舊有的婚姻倫理道德規范逐步瓦解。只有在全社會樹立正確的婚姻倫理觀,才能減少離婚亂象。青年的婚姻倫理道德建設與家庭責任意識的培育是不可分離的。沒有責任的愛是自私的愛,缺乏責任的婚姻是不穩定的婚姻。現實經驗表明,“雙獨婚姻”和“單獨婚姻”由于夫妻育嬰責任感差、家務分擔不均和雙方個性太強等原因容易造成沖突。[16]因此,要構建性別平等對話的現代婚姻文明,強化青年對情感生活的尊重意識和責任意識,強調家庭責任共擔和合理角色分工,以便婚后男女更好地進入家庭角色和減少摩擦。
第四,積極培育新型婚姻文化,破除高價彩禮等陋習,大力倡導適齡婚育。一方面,要引導當代青年樹立健康文明的婚姻觀,降低物質化的擇偶傾向,避免過分物化的婚姻,要倡導婚事新辦,培育文明結婚之風,減輕農村大齡青年及其家庭的結婚成本。另一方面,當前我國越來越多的年輕人不再將結婚生子當作人生的必選項,婚姻文化存在不婚不育、晚婚獨育的一面。考慮我國當前的婚育形勢及其對社會發展的潛在風險,需要在家庭、學校和社會層面宣傳婚姻和家庭的價值,將優秀傳統文化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融入新型婚姻文化的建設當中,在尊重多元婚育基礎上,鼓勵和引導青年將婚姻組建、家庭發展和人生的成功與幸福聯系在一起,提升婚姻的社會效用和家庭的發展能力。
四、結語
針對中國婚姻狀況研究的長期爭鳴,本文綜合運用時期、時點和隊列指標,從婚姻事件、婚姻狀態以及婚姻的形成和解體風險等角度對當代中國的婚姻態勢進行了歷史的和現實的分析。本研究發現,當前學界關于中國婚姻問題的爭鳴看似矛盾對立,但其實是并行不悖的。首先,普婚仍是中國婚姻制度的基本特征,但離婚態勢走高和婚姻的脆弱性風險增加亦是不爭的事實;其次,國人在婚配關系、婚姻決策和婚姻文化上表現出的婚姻圖景,一方面體現了現代化轉型的進步意義,凸顯平等性、主體性和現代性,但也同樣暴露出擠壓性、自我性和傳統性衰退的客觀問題。總之,當代中國婚姻態勢的負向嬗變及其消極影響值得關注,應當使婚姻制度在符合現代化價值取向的基礎上,更好地融入中國本土社會與文化,降低離婚潮對我國家庭、社會和人口發展的多重傷害和打擊,使婚姻制度更好地惠及國家和人民。婚姻的形式可以現代化,但其歷史使命和精神內涵特別是婚姻的責任倫理卻要回歸傳統,這恐怕也是民族復興和文化自覺的題中應有之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