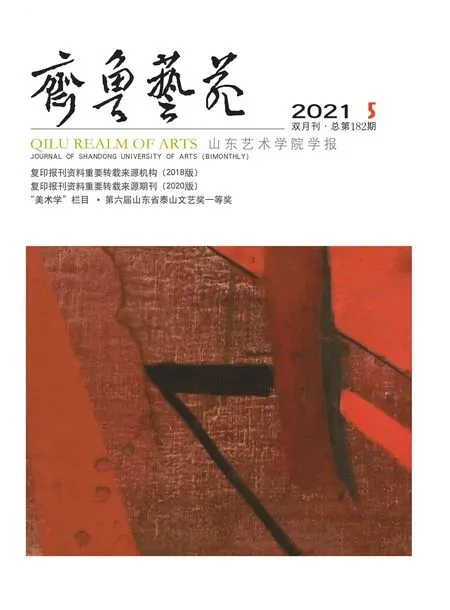中西合璧 多元融合
——民族歌劇《沂蒙山》的和聲技法研究
宮富藝,田新奇
(1.山東藝術學院學報《齊魯藝苑》編輯部,山東 濟南 250014;2.棗莊學院音樂與舞蹈學院,山東 棗莊 277160)
一、民族歌劇《沂蒙山》
民族歌劇《沂蒙山》是當下“中國民族歌劇復興浪潮”(1)2014年10月,習近平同志在北京文藝座談會中號召文藝界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其后以2015年復排中國第一部大型民族歌劇《白毛女》并在全國各大主要城市巡演為開端,繼而在2017年開展了“中國歌劇創作座談會”,“中國民族歌劇傳承發展工程”,推出重點扶持劇目評選等一系列重要舉措推動下,中國民族歌劇創作迎來復興浪潮。中涌現的佳作。該劇由山東省委宣傳部、山東省文化和旅游廳出品,山東省歌舞劇院創排,于2018年12月開始在全國各地巡演達150余場次。2021年7月7日,以該歌劇為藍本創作的歌劇電影《沂蒙山》在北京舉行首映禮,成功將這部“時代大劇”從“劇場”搬到了“大熒幕”。《沂蒙山》大量的創演實踐表明,優秀的藝術作品不僅能將深刻的思想立意與專業的創作技法有機融合,以特有的方式來表情達意、感染人心,更能在廣泛的受眾群體中獲得經久不衰的強大生命力。
歌劇是一門綜合性舞臺藝術,它涉及到音樂、文學、舞美、戲劇與編劇等諸多藝術領域,但其中理論家們普遍認為 “音樂在歌劇中占主導地位”[1],需要“以音樂承載戲劇”[2]。居其宏教授在討論此問題時還進一步提出“中國當代歌劇的旋律創作是個重大問題”,我國傳統音樂具有“優美旋律這一傳統優勢”,因而,中國當代作曲家在歌劇創作中尤為重視把握好旋律的“優美性與技術性之間的關系”[3]。事實證明,《沂蒙山》的作曲家欒凱很好地處理了這對關系:如在民歌素材的運用上,將時代精神與《沂蒙山小調》《趕牛山》《誰不說俺家鄉好》等山東經典民歌以動機化的形式映射,貫穿到歌劇的不同唱段中,在既保證音樂濃厚民族風格的同時,又展現出強烈的時代感召力與感染力,讓在場者身臨其境地感知到這種藝術沖擊力和視聽享受的魅力。可以說,《沂蒙山》給觀眾帶來的感性體悟很大程度上來源于旋律上的共情。
然而旋律聽覺上的感性離不開多聲部層次表達上的理性設計。在作曲家欒凱的自述中,《沂蒙山》至少滲透、融合了“民族唱法、管弦樂隊的烘托、現代音樂劇風格”[4]三種元素。該劇為達到歌劇音樂抒情、感人、震撼的戲劇效果,作曲家根據旋律特點與情感表現進行多聲部的構思設計,運用了恰當、可聽性強的大小調和聲、民族和聲、流行和聲等多種不同風格的和聲技法。這些和聲技法與鮮明的民族特色旋律相結合,必然為歌劇音樂帶來張力與色彩,使歌劇音樂具有了普適性的受眾范圍,更體現了用動人的音樂與歌劇的感人魅力表達對黨的衷心熱愛與崇高的敬意。
二、多元和聲技法的運用
(一)五聲化旋律與半音化和聲的融合
1.運用離調和弦增強五聲旋律的動力感
《沂蒙山》音樂在和聲上運用副屬和弦、副下屬和弦等離調和弦來襯托五聲化旋律,用半音化和聲的力度性與色彩性來突顯樂曲的音樂內容。“半音化,是指音樂中運用非自然音的、半音的聲部進行與半音和聲的手法與風格的總稱”[5](P2)。在西方音樂風格林立的歷史演變過程中,半音化對音樂的調式流變、結構形成與感情表達都產生了影響,也是作曲家最常拿來構思譜曲的技術手段。筆者在對《沂蒙山》音樂分析中發現,西方音樂中的半音化風格影響了作曲家的歌劇創作,特別是在具有強烈矛盾沖突亦或強烈情感宣泄的情節段落中,半音化和聲發揮了極強的藝術表現作用。
譜例1 第12曲《一雙鞋子針兒密》第11—15小節

譜例1為第12曲《一雙鞋子針兒密》的一個5小節樂句。從旋律角度看,該樂句既可以理解為bE徵六聲調式,也可以分析為bE宮六聲調式,但從記譜、聽覺習慣上一般理解為前者。和聲為bA大調主和弦開始到屬和弦結束的開放結構,第3—5小節以重屬和弦導向半終止。從主到屬的宏觀進行與鑲嵌于其中的重屬到屬的進行都充分說明了和聲的力度性。其中,形成半音變化的重屬和弦(譜例第3小節)起到了關鍵的調制作用,它將旋律與和聲的異調矛盾在終止時統一起來。
譜例2a 第21曲《再看一眼親人》第10—13小節

譜例2b 第2曲《以命博命保家鄉》第1—3小節

除上文所述的徵調式開放樂句用法外,作曲家在絕大多數情況下運用離調和弦時都有意避免直接導向其臨時主和弦。例如譜例2a中,D7/TSVI后連接S和弦形成了離調和弦的阻礙進行;譜例2b例中的Sii7/D到tsvi7進行,上方三個共同音保持,低聲部做半音下行運動,增強了和聲緊張感的延遞。當然,這樣的離調和弦的意外進行手法在西方傳統調性和聲音樂中屢見不鮮,但作曲家在《沂蒙山》中的此類運用顯然是為了一定程度上削弱和聲進行的功能力度,并進一步利用半音化的聲部運動,使和聲進行更能適應在特定劇情中音樂戲劇性與民族性的需要。
譜例3 第19曲《怎么辦?怎么辦?》第1—4小節

將多個離調和弦連續使用的連鎖進行也經常被作曲家使用。譜例3中,從d小調主和弦到屬七加六音和弦的運動中,穿插了兩個半減七結構與一個減七結構的和弦。一方面,它們從功能上不斷傾向第4小節主和弦,另一方面連續的不協和音響也很好地營造了危急時刻的緊張氛圍。
譜例4 第20曲《世間哪有這樣的情》第1—9小節和聲略縮圖

譜例4節選的是第20曲的一個完整樂段。從結尾看這是停留在F大調屬和弦上的一個開放結構,然而該樂段之前的一系列和聲進行并未明確指向F大調。原因是作曲家全部運用了半音化的七和弦(第2小節除外)。根據譜例標記可看到,雖然他們都是屬功能的,但七和弦結構是變化的:第1、3小節是減七和弦;第4、5小節是屬七和弦;第6、7小節是減小七和弦。整體上來看,和聲緊張度趨緩,調性感隨之逐漸清晰。連續副屬七和弦連接帶來的半音變化,迎合了劇情所表達的悲壯感和對子弟兵的真摯情感。
2.運用交替和弦豐富五聲旋律的調式內涵
同主音大小調交替和弦與原調和弦結合,以及遠關系調式交替音列,構成了多元的調式交替和聲手法,突出了遠關系調式音列交替色彩與調式交替和弦的不同色彩。這種和聲手法在浪漫派特別是晚期浪漫派作曲家作品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作曲家在《沂蒙山》中沿襲了這一技術,使其發揮了色彩斑斕的藝術效果。
譜例5a 第24曲《愛永在》第103—107小節

譜例5b 第15曲《跟著隊伍上戰場》第11—14小節

譜例5c 序曲第34—37小節

將小調主和弦的三音升高形成含“辟卡迪三度”的大主和弦,這在西方傳統音樂中屢見不鮮,終止處的大主和弦一般仍由屬功能和弦導入,使小調樂曲形成較為明亮的終止。《沂蒙山》的第24曲終止處(譜例5a)便使用了這種手法。但作曲家對于這類運用同主音主和弦的手法并未限制于此。第15曲《跟著隊伍上戰場》,主調為d小調,譜例5b節選了該曲前奏的終止處,可以看到作曲家使用了D大三和弦作為終止和弦。但是,該大主和弦并不是由d小調屬和弦導入的,而是運用平行大調S到D的兩個大三和弦引入。將連續的上二度和弦運用在終止處不失為一種創新,搭配大主和弦的明亮色彩形成了新穎鮮明的音響效果。再如譜例5c中,作曲家甚至在大調的樂句終止處將同主音小三和弦與大三和弦直接并置起來。這里,前小三和弦、后大三和弦的安排,以及將半音上行運動的三音置于低聲部的處理方式無疑產生了一種上揚式的和聲語氣感,迎合了音樂歡快喜慶的氣氛。
譜例6 序曲第1—9小節

利用多元關系調交替和弦來替代原調和弦,或與原調和弦并置產生色彩對比也是《沂蒙山》很重要的和聲手法。在《沂蒙山》序曲的開始處,即以《沂蒙山小調》的旋律素材貫穿全曲的主題動機,作曲家多次使用了多元關系調交替和弦。這個片斷開始于D宮,在第5小節上四度模進至G宮。在主題動機第一次呈示時(譜例1—4小節),其和聲配置為D大調主三和弦與降VII大三和弦的并置,也就是D大調同主音小調的七級和弦與主和弦的并置。同時,主和弦的聲部流動體現D五聲宮的進行,降VII和弦是主和弦的下二度移位,其流動的聲部構成了C宮的進行,二者和弦上的同主音大小調交替與兩個遠關系五聲宮調的聲部進行形成了多元的調式交替;主題第二次呈示時(譜例第5—9小節),和聲終止在E大三和弦上,該和弦可理解為G大調平行小調的同主音大調的主和弦,是一種多元關系調交替的結果;此外,終止處的E大三和弦也被同主音大小調交替tsVI和弦所修飾。可以看到,在和聲層面,作曲家對傳統民歌《沂蒙山小調》的改造主要運用了多元的調式交替和聲的手法,使具有典型的五聲性民族風格的旋律蒙上了西方晚期浪漫風格的神秘面紗,從而給整個歌劇建立了民族性與幻想性兼具的風格基調。
譜例7 序曲第223—230小節

譜例7的旋律動機來源于我國經典交響曲《紅旗頌》,但其和聲設計別出心裁。我們可將譜例的八個小節平分為兩組呈模進關系的四小節,后四小節是前四小節的上大三度模進。同時,在單個音組內的三個和弦是以連續的三度根音關系上行續進的(先小三度后大三度),且均為大三和弦結構。在傳統調性和聲思維里,這種三度關系和弦可由為多元關系調交替產生。顯然,無論是音組內的小三度關系還是音組間的大三度關系,和聲進行間的色彩感是強烈的,和弦不斷按三度上升的過程產生愈發明亮的藝術效果。
譜例8 序曲第208—211小節

將“色彩和弦”插入功能性和聲序列的手法在《沂蒙山》中是十分普遍的。譜例8的調性為C大調,其在屬和弦上形成半終止。譜例中的第2小節的重屬和弦導向半終止的過程中,插入了降III級七和弦(譜例第3小節前三拍),再經過下屬和弦最終到達屬和弦。同主音交替和弦的插入為和聲續進營造出輝煌、鮮明的色彩。
3.運用線條性半音與五聲旋律形成多層次對比
當和聲進行更加強調半音化的橫向線條發展時,便形成了線條性半音和聲。《沂蒙山》中,線條性的半音運動常發生在低聲部。
譜例9 第11曲《海棠呀,讓他去吧》第14—21小節和聲縮譜

如譜例9,該唱段的低聲部為F—bE—D—C—B—bB—G級進下行的全音與半音結合的低音線條。從和聲續進上來看,作曲家為完成這樣的下行級進線條運用了小屬和弦(譜例第2小節)、屬功能和弦的連鎖(譜例第4—5小節)以及重屬和弦的意外進行(譜例第5—6小節)等方式。可以說,和弦間的功能關系是相對薄弱的,和聲續進為低音的線條所控制,而不斷下行的低音線條也推進了音樂情緒的發展。
譜例10 第19曲《怎么辦?怎么辦?》第14—21小節

這里與譜例9類似,但其下行的低音是完全按照半音關系運動的。這是一個轉調樂句,從d小調轉到其平行大調F大調。低音從d小調的主音半音下行級進到六級音,它也是F大調的四級音,從而按完全終止的方式完成F大調上的終止式。半音的低音運動方式使和聲運動更加緊湊,烘托出生死抉擇時刻的緊迫感和矛盾沖突。
譜例11 第21曲《再看一眼親人》第1—7小節

上例節選了唱段《再看一眼親人》的前奏部分,低聲部同樣是半音級進下行的運動線條。在譜例前四小節中,上方聲部持續的C—E更加反襯出低音線條半音運動的張力。從和聲功能上來看,第2小節第二轉位的SII9和弦、第3小節的TSVI2和弦等都明確表現出作曲家是以一種橫向的線條運動邏輯來設計的。顯然這些和弦與低音位置均是按照線條化構思安排的,加之力度的漸強和外聲部的反向,使和聲的張力得到了很好的釋放。
譜例12a 第5曲《封壇酒》第7—10小節

譜例12b 序曲第42—47小節

《沂蒙山》中還存在完全以橫向的半音線條思維構思的音樂片段。如譜例12a中,唱段的兩個間奏旋律,在低聲部(譜例虛線箭頭所示)配以下行半音級進為主的線條,形成了半音線條與五聲化旋律的對位,對比強烈而又十分新穎。在譜例12b中,低聲部甚至形成了小三度音程的半音下行級進(譜例前三小節)。在第4小節的屬七和弦導向主和弦的過程中,第5小節又穿插了低音半音級進上行,保持了低聲部整體的半音風格,旋律歡快、詼諧的氣氛得到了很好地渲染。值得注意的一點是,以上兩例的旋律都是五聲化,而低聲部都是半音化,這種中西元素的融合豐富了歌劇的思想內涵、藝術情境與音樂表現力。
(二)不同旋律結構中插入半音化的增三和弦與減七和弦
《沂蒙山》中常見增三和弦的使用,在功能上多為升五音的屬和弦。和聲小調的三級和弦與該調升五音的屬三和弦相等,也具有較強的屬功能意義。
譜例13a 第6曲《五子炮》第1—3小節

譜例13b 第6曲《五子炮》第69—72小節
《五子炮》主調為g小調。在譜例13a中,半音階的上行旋律結合和聲小調的下行低音音階進行,在其第1小節運用了升五音的屬增三和弦導向和聲小調的主七和弦。值得注意的是和聲小調主七和弦的三、五、七音也構成增三和弦結構。第2、3小節,外聲部反向快速運動的半音階與和聲小調音階包圍著內聲部的主七和弦,配合著增三和弦的不協和音響,將整個前奏引入戰斗來臨的緊張氛圍當中。
整體上,作曲家將《五子炮》按半音關系不斷升調,譜例13b節選的是由#g小調轉入a小調的節點。簡單來說,這里同全曲開始時相同,在#g五聲旋律與和聲和a和聲小調之間插入新調升五音屬增三和弦,前調#g小調的主和弦與該增三和弦有一個共同音#g,雖作旋律連接,其轉調過程還是順暢不突兀的。此外,兩例中的增三和弦都是按照該調的DtIII6和弦記譜的,揭示了前文所述的增三和弦等音特性。
譜例14 序曲第188—191小節

譜例中的序曲選段為bB大調,第188小節運用了bB大調的#5D/D的增三和弦,后接典型的功能和聲進行連接到bB大調主和弦。此處增三和弦的緊張音響逐漸被解決,順利地引出主題旋律動機。
譜例15 序曲第97—104小節

減七和弦在調性中為七級導七和弦,連續的半音減七和弦會造成調性的模糊,故此例不作具體的調性和弦級數標記。本例是序曲中的黑暗勢力主題。作曲家運用了兩個相距半音的減七和弦來描繪日軍掃蕩時的殘暴行徑,柱式減七和弦與分解減七和弦的旋律的不協和音響營造了緊張氣氛。由此可見,這里的減七和弦旨在運用其音響特性而非功能特性,為塑造特定的音樂形象發揮了重要作用。
(三)調式的模糊性與和聲手法的多義性
譜例16a 第12曲《一雙鞋子針兒密》第11—15小節

譜例16b 第12曲《一雙鞋子針兒密》第11—15小節

譜例16a、16b為12曲《一雙鞋子針兒密》第11—15小節的五小節的樂句。上文在譜例1中對這個同主音的六聲調式做了旋律與和聲的異調配置的分析。由于旋律中宮角的不確定使調式上具有“模糊性”,那么作曲家對該片段的和聲配置也具有了多義性的理解,除了例1的分析外還有以下兩種解釋:一是譜例16a,從bA大調主和弦開始到bE屬調主和弦結束的轉調結構,第2—5小節以bE大調的二級七和弦至屬七和弦導向主和弦的完全終止,四五度根音和弦的連續突出了力度性;二是譜例16b,將該樂句分析為bE大調,是始于下屬和弦的完全終止的力度性和聲進行。這三種分析結論(包括例1)可以看出,作曲家充分利用調式上的“模糊性”進行與和聲力度性的處理,使和聲上既有開放性也有收攏性的特點,將大小調功能和聲與民族調式做了有機的融合。類似的和聲處理在《沂蒙山》中被作曲家廣泛運用,特別是在大量的抒情性唱段中,如13曲《等著我,親愛的人》第9—12小節的樂句,16曲《鄉親把苦嚼成甜》第5—8小節的樂句,21曲《再看一眼親人》第12—15小節的樂句,24曲《愛永在》第9—12小節,等等。
(四)和聲的民族化與旋律的五聲化相統一
從前文的分析可以看到,《沂蒙山》在和聲的和弦結構與橫向續進承襲了西方傳統調性音樂的思維邏輯,旋律的五聲化與各類半音化的和聲手法的結合為唱段帶來了戲劇性的藝術效果。然而,《沂蒙山》作為地地道道的“民族歌劇”,其歌劇音樂民族風格的形成除了得益于作曲家所原創、改編以及借用的大量五聲性旋律唱段以外,在多聲層面對和聲進行民族化處理是十分必要的,這關系著整個歌劇風格的統一問題。
雖然我國傳統音樂更加注重橫向的旋律線條,但和聲性思維仍能很好地作用于傳統音樂當中。一般來說,大二度、小三度和純四度、純五度等音程更能體現五聲音階的調式特點,在縱向和聲處理中強調這些音程便能很好地體現和聲的民族風格。
如譜例6,在鋼琴縮譜的左手能明顯地看到作曲家有意地強調了純五度音程。和弦排列為至少由兩個從下往上連續的五度音程(見方框內)。雖然通過低音可以明確和聲級數及它們的序進邏輯,但強調五度音程的排列方法不失為是對西方三和弦的民族化特殊處理。進一步看,若將每小節和聲層的音單獨組合排列,我們將發現每個小節和音分別來自不同的宮調系統,如第1小節為D宮、第2小節為C宮的和音,這種“把橫向的調式音列、旋律音調予以縱向的結合”[6](P87)的“縱合性結構”和聲設計使得民族風格清晰、意蘊悠長。
譜例17 序曲第25—27小節

在上例的最后一小節終止處,和聲停留在E上是明確的。與其說是一個省略三音附加二度音和四度音的E大三和弦,不如理解為在E徵調式上的五聲“縱合化”處理。該和弦包含的大二度、純四度和純五度音程含量自然突出了和聲的民族風格與韻味。
譜例18 第4曲《你要讓她幸福一生》第16—18小節

我國五聲調式與西方大小調式另一明顯的區別為五聲音階無導音傾向性。如譜例18的終止處所示,作曲家在運用屬和弦時,有意去掉了三音(音階導音),并采用省略三音的屬十一高疊和弦,使其和弦音高短暫進入bA宮五聲,從而模糊了和弦的功能特性,削弱了和聲續進的功能力度感,更加適應了五聲性風格的需要。
譜例19 第34曲《蒼天把眼睜一睜》第5—7小節

上例是一段C徵清樂七聲調式的終止處,該唱段表現了海棠失去孩子的悲憤心情,在重屬減七和弦、二級七和弦后運用了省略三音附加四度音的屬和弦,該屬和弦如果采用三度結構大三和弦,會大大削弱表現痛苦的情緒內容,而此處降低了和弦的協和性,并與模仿戲曲伴奏“緊打慢唱”的和弦節奏相結合,很好地詮釋了歌劇中主人公的悲憤心情,展現了民族化和聲技巧的魅力。
譜例20 第31曲《等著我,親愛的人》第1—4小節

上例低音運動構成G—E—D的五聲三音列,和弦上突出五度排列與小七和弦結構。第1、3、4小節為G宮五聲縱合性的主和弦與六級小七和弦,第2小節是C宮五聲縱合性的小七和弦,其五聲縱合性和聲、流動的織體與《沂蒙山小調》為素材的優美旋律相得益彰,民族化風格盡顯。
譜例21 第32曲《一雙鞋子針兒密》第1—6小節

上例以五聲音階為基礎形成五聲化的旋律流動。第1—3小節為bD宮,在第3、4、5小節為bA宮,下行的兩條三連音旋律的縱向結合上,突出四度音程平行的同時穿插“宮—角”大三度結構,神似我國傳統撥弦樂器掃弦的音響效果,蘊涵十足的民族風味。
(五)受眾性“歌劇色調”的統一
《沂蒙山》的成功表現在音樂、劇本、舞美等專業角度的創作上,并獲得了廣大觀眾對該劇的接受與認可,可謂真正做到了雅俗共賞。作曲家欒凱在音樂的受眾性問題上做出了深入的思考與設計,例如他將現代音樂劇風格元素融入到歌劇音樂中,使音樂更加符合現代觀眾普遍的審美需求。然而,多種風格元素絕不能以簡單的加法進行拼貼復制,這并不能使音樂迎合所有觀眾不同的審美傾向,它們的結合一定是潛在的、深入的、有機的,如此,《沂蒙山》的音樂才能夠“既熟悉又陌生”,“既符合當代觀眾對民間藝術傳承的期待,又滿足了當今觀眾日益增長的藝術審美需求”[7]。那么,作曲家是如何做到的?其有沒有一條有理可循的技術理路?
在此,筆者需引入“歌劇色調”的概念以做進一步的分析闡釋。“歌劇色調”指的是“一部歌劇作品最鮮明的音樂品格,這種音樂品格捕捉與反映了貫穿在該部歌劇多個場景中的情景、氣氛、性格與詩意風格”[8]。《沂蒙山》的“歌劇色調”是以西方傳統音樂技法形式為基礎,結合現代音樂劇風格點綴,著重在音樂橫向線條與縱向和聲中展現我國民族音樂風味與講述民族故事的總體音樂品格。這種品格貫穿在整部歌劇的情節場景與唱段音樂當中,為《沂蒙山》營造了獨特且統一的風格烙印。在和聲技法層面,其上述多種元素的結合上是縱橫交織的、有機統一的,下面舉例作以分析。
譜例22 第25曲《等著我,親愛的人》第5—8小節

這是《沂蒙山》最膾炙人口的唱段之一。該唱段的旋律僅以五聲性音高形成,而其旋律發展與節奏的抑揚頓挫具有音樂劇風格式的抒情性,可謂一種融合性旋律特色。再看和聲層面,其橫向和聲進行符合西方傳統功能和聲的常見續進,且包含有重屬和弦參與的半音化聲部運動。但是,前三小節中SII7、TSVI的交替出現產生一定程度的非功能性的流行和聲風味。且在旋律與織體的縱向結合上,如第1小節主和弦實際上是附加六度音的,是為典型的和聲民族化處理。由此看來,三種和聲風格元素縱橫交織,彼此滲透,性格鮮明的《沂蒙山》式“歌劇色調”凸顯。
結語
綜上所述,《沂蒙山》在多聲部創作上技法運用合理恰當,以此很好地烘托、渲染了民族化的旋律與歌劇的內容,用軍民情深的情結,借特色化、多樣化豐富感人、身心震撼的音樂,充分表達了歌劇“水乳交融、生死與共”的思想內涵和藝術情境。這樣的藝術效果,不僅與作曲家對多樣和聲手法的獨特理解與感知息息相關,又得益于作曲家運用恰當的和聲技法對情節故事的藝術化表達,從而達到《沂蒙山》所獨有的個性化“歌劇色調”的要求,創造了在眾多沂蒙山背景的藝術表現中,此“沂蒙山”非彼“沂蒙山”的獨特藝術作品。在當下民族歌劇創作愈發火熱的時代背景下,如何兼顧好專業性與可聽性、藝術性與受眾性,民族歌劇《沂蒙山》給予了我們嶄新并可行的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