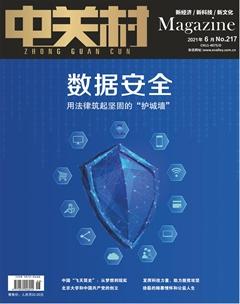如何看待“三孩政策”
周清杰 杜云潔
“全面三孩”政策是在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結果公布20天后發生的,兩者因果關系清晰可辨。可以說,正是人口普查所揭示出的嚴峻人口形勢助推了這次生育政策的提速。
5月11日,國家公布了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結果,到2020年,我國60歲及以上人口有2.6億人,比重達到18.70%,其中65歲及以上人口1.9億人,占比為13.50%,已接近深度老齡化社會。另一方面,未來人口形勢不容樂觀。2020年我國育齡婦女總和生育率為1.3%。根據國際標準,這一數據遠低于2.1%的更替水平,也低于美國、日本、法國等發達國家的水平,表明我國已經進入“低生育率陷阱”。
我國的總和生育率數據雖然爭議頗多,但我們也可以從相關的信息中看到愈來愈近的人口危機“陰影”。
2000年和2010年,我國第五次、第六次人口普查登記的總和生育率分別是1.2%和1.18%。由于當時仍在實施嚴格的計劃生育政策,極有可能存在瞞報、漏報,數據可能偏低,因而一直沒有被計生部門采信。2007年11月,國家計生部門發布了《國家人口發展戰略研究報告》,指出2006年我國育齡婦女總和生育率為1.8%。
2010年,我國第六次人口普查結果公布后,某著名人口學者對調查和普查時存在的人口漏報問題進行了修正,預測總和生育率在1.5%至1.65%之間。如果這一數據可信,那么這一數據已經較計生委2006年的數據有明顯下降。
對比本次人口普查的數據,大致可以看出人口變化的趨勢。雖然我國育齡婦女的生育意愿子女數為1.8,但實際生育的數據只有1.3。換言之,只有72.2%的愿望變成了現實。因此,“三孩政策”的出臺是我國審時度勢,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問題,破解勞動力不足和人口結構失衡難題的正確選擇。
“三孩政策”是生育政策糾偏的需要
“三孩政策”不僅是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維護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的重要舉措,其實也是對以往生育政策的糾偏。
中國自古就有多子多福、兒孫滿堂的傳統生育觀念,這是中華民族歷經五千年能夠立于世界之林的基礎。然而,因建國后人口暴漲和資源相對匱乏、生產力低下之間存在矛盾,某些所謂的專家在缺乏了解社會發展與人口演進互動規律的情況下,對未來可能的人口增速和峰值做出了過于夸張的預測。這些錯誤的理論和預測結果一度對我國的生育政策產生誤導,導致了過于嚴苛的計劃生育政策出臺。
進入新世紀后,即使已經出現了人口危機的征兆,某些質量存疑的研究成果阻礙了生育政策的及時調整。例如,2007年在《國家人口發展戰略研究報告》中預測,2020年我國總和生育率為1.8,人口將達到14.5億。這個由十多位兩院院士、300多位專家學者,歷時兩年多完成的大項目,其研究結論與現實相去甚遠。又如,有著名人口學者在2014年預測,若“全面放開二胎生育政策,未來4年內,我國年度出生人口將分別達到3540萬、4995萬、4025萬、3540萬”。但事實是,在2015年全面放開二孩后的4年里,我國的出生人口分別為1786萬、1723萬、1523萬、1465萬,比該專家的預測結果少了近1億。
十八大以來,黨中央根據我國人口發展變化形勢,對生育政策多次做出重大決策部署。可以說,這些舉措是對以往過于嚴苛的生育政策及時糾偏。中央在第七次人口普查結果公布不久就出臺“三孩政策”,是生育政策不斷優化的延續,同時這種快節奏也反映出糾偏的緊迫性。
如何提升“三孩政策”的效果
從我國2015年末全面放開二孩的生育情況看,二孩政策對生育的刺激效果十分有限。除了短暫的反彈外,遠未達到預期的效果。從高昂的生育、養育、教育成本,到高企的房價,導致“二孩政策”未能達到理想效果的因素至今依然存在。如何提升新政策的效果,不同領域的專家學者已經給出了非常多的建議。在此,我們也將在合理分析的基礎上探討一些可行的途徑。
第一,重塑合理的生育觀。二戰后國外的人口演進史表明,即使沒有計劃生育政策,一個社會的生育觀也會隨著經濟發展朝著“晚稀少”轉變。而我國30多年的計劃生育政策,加快了傳統生育文化和觀念的淘汰。目前,“養兒防老”“無后不孝”等根深蒂固的傳統觀念已經逐漸消亡,不婚不育等抑制生育的觀念深刻影響著育齡人口。因此,想要從根本上扭轉人口形勢的惡化,不僅要通過放開生育的政策,更應營造、培育合理的社會生育文化環境,在潛移默化中改變個體生育意愿和觀念,盡可能提高生育政策的效果。
第二,實質性解決“生不起”問題。高額的撫養、教育、住房等成本,給處于生育高峰的80后90后夫婦帶來了巨大的經濟壓力。在直接成本、機會成本和收益之間的反復權衡后,導致不少家庭傾向于少生或不生孩子。面對這些“能生生不起”的群體,政府應該且必要的出臺獎勵的經濟刺激政策給予支持。例如,國家可以設立專項資金為家庭提供累進獎勵政策,實施多生多發的獎勵機制,引導育齡婦女多生育。再如,政府應對育兒家庭的個稅抵扣政策可以實施邊際遞增設計,多生多抵扣,大幅降低多子女家庭的育兒成本。另外,政府應完善各類配套保障,包括對多子女家庭的奶粉、紙尿褲等費用進行適當補助,增加幼兒園、托兒所,降低托幼費用,提高托幼服務的可獲得性等等。
第三,對“想生不能生”的家庭提供更人性的幫助。受制于早期計劃生育政策的影響,我國社會中有百萬計因某種原因失去獨生子女的家庭。絕大多數的失獨家庭由于母親生育能力的喪失,變成了無助的悲劇家庭,帶來了不少社會問題。對這種“想生不能生”的群體,政府可以探索調整相關政策,適當放開輔助生育技術,甚至可以允許不收報酬的愛心助孕。實際上這也是政府對過往過嚴政策所造成的負面影響的某種補償,可以最大限度幫助那些想要個孩子的失獨家庭。
人口問題不僅是關乎國家發展的全局性、長期性、戰略性問題,也是關乎普通百姓生育權和家庭幸福的民生問題。此次“三孩政策”的放開,距離生育決策完全回歸家庭又近了一步。未來,決策者應該更多地從普通夫婦的角度出發,尊重其生育選擇,放松生育的法律、政策限制,增加生育獎勵,降低生育成本,讓生育成為民間的一種自發行為。唯有此,我國的人口形勢才有可能根本好轉。
(作者分別為北京工商大學經濟學院教授、碩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