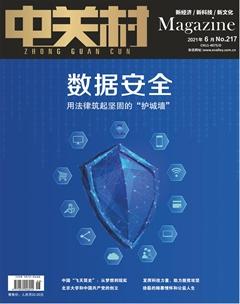英氣長歌
如始
八月的北京是多雨的季節,東二環朝陽門附近的人群依舊像往日一樣步履匆匆,哈佛大學設計女博士——朱冰的家和公司就在朝陽門一帶。從天辰大廈穿過朝陽門北大街后往東轉入朝陽門外大街居住小區,幾乎每個不出差了日子,朱冰都會在這條路上穿行。與大多數職場女性一樣,每天定時定點出現在公司的辦公樓里,下班回家。不同的是,除了公司與家里,其余時間要想找到朱冰本人,我們不得不把目光投向鄉村,投向全國各地的城市規劃一線中。
對于大部分人來說,外出旅游堪稱是最愉悅的休閑方式,一邊欣賞勝地美景,一邊品嘗當地特色小吃。然而,這些對設計師朱冰來說,每去一個地方,會下意識地觀察周邊的景觀布局是不是合理,游客導覽的路線是不是清晰,甚至去餐廳吃飯都會想到桌子的擺放是不是合適,桌子間的間距是不是符合人流穿行。至于為什么會選擇做設計,為什么會從哈佛大學博士畢業后,現在又從事一線的調研、策劃?這得從三十年前說起。
赴美留學,重歸祖國懷抱
三十年前,小時候的朱冰家住德勝門附近,每天上學都會經過德勝門城樓,那時候的朱冰有個疑問,“長大以后要做什么?要給這個世界留下些什么樣的痕跡。”有一天,當車子又轉過德勝門城樓的時候,正在上初一的她突然一想:“這個城樓已經存在了很多年了,就像北京城已經存在了很多年一樣,如果我要做一個建筑師的話,即使我走了,我的作品還存在,這將是一件多么有意義的事情啊!”從那時候開始,小小的朱冰心里就埋下了一顆夢想的種子,那就是長大以后當建筑師。
1989年,19歲的朱冰以優異的成績報考了北京工業大學建筑系,之后又在香港大學攻讀城市設計專業。畢業后,出于對外面世界的好奇,她決定去國外求學,一次偶然的機會,她接觸到了哈佛大學的學生,他們的理念和談吐,讓朱冰的內心產生了很大的震動。就這樣,朱冰申請了哈佛大學,在哈佛大學英才聚集的設計學院里,朱冰的設計理念,在各種思維的碰撞中逐漸明晰起來。
朱冰回憶說:“設計學院是一個五層樓的一個房子,是一個三角形的房子,整個頂是玻璃頂,站在五層的臺階上,能夠一直看到一層的人的大圖板上在畫什么圖,電腦畫什么圖,各個專業一共600個學生,全部在這個五層里分布。打破專業的,從不同的理念、不同學科的背景,來嘗試進行跨界、進行融合、進行碰撞、進行創新,因為最終任何的設計的結果,一定是創新的,前人所沒有的一個東西。”創新的理念在朱冰的心里扎下了根,她希望能夠找到一片天地施展才華。
正在這時,身在美國的朱冰收到了一份來自遠在北京的母親的信:“好好學習,報效祖國!”這短短八個字深深影響著她,也使她更加堅定了回國的信心。而這封母親一生中唯一一封寫給女兒的信,也成了她的珍藏。與此同時,哈佛大學的師兄對朱冰說:“朱冰,你想回國創業,可能會經歷重重困難。如果哪天你想賺錢了,回來美國,我們一起干!”36歲的朱冰毅然決然地拒絕了,她說:“我必須回去,因為我的祖國需要我!”而國內正是開展城鎮化的歷史時期,朱冰決定回國跟上這股浪潮。
致力鄉村改造,為百姓謀發展
2007年底,朱冰在北京創辦了都市意匠城鎮規劃設計中心。然而國內的市場卻并沒有伸手歡迎這位滿腔抱負的哈佛大學的女博士,朱冰只能轉戰一些沒人愿意接手的鄉村改造的項目。朱冰稱之為“農村包圍城市”,把目光投向鄉村,愿意接、愿意做的原因,就是因為朱冰從美國回來,她知道中國的鄉村早晚會成為市場的重點。天津市薊縣郭家溝村莊建設規劃就是其中一個最為明顯的案例。
郭家溝村地處天津北部,下營鎮東部,自古以來就是一個山清水秀的美麗小山村。占地面積1.23平方公里,然而生活在這個小小的村莊的只有46戶,168位人口在鄉村改造之前人均收入不到3000元。然而,面對漫天塵土飛揚的鄉村,如何開始改造、如何改變郭家溝村民窘迫的生活現狀,成了朱冰思考的首要問題。
在朱冰的帶領下,整個都市意匠的團隊三赴郭家村調研考察。為了呈現出記憶中的美麗鄉村,朱冰準備給深山里的郭家溝村設計一件青磚青瓦、田園風光的美麗外衣。讓設計成為一個“裸妝”,讓設計師隱在設計的后面,呈現生態的、自然的鄉村的效果。
在做之前,朱冰采訪了很多從農村出來的,已經在城里生活的人,詢問他們覺著農村是什么樣,小時候農村是什么樣?如果能回到大家兒時印象里的那種鄉村,就覺得很美了。
然而朱冰要完成這個“裸妝”,首先就需要把村民們原先自己花錢貼在墻上的白色的、黃色的瓷磚片全部拆了,退回到青磚墻瓦的北方民居的建筑風格,但是這遭到了很多村民的反對。
鄉村的人是向往城市的生活,覺著貼著瓷片的平頂房子是城市和現代化,要說服村民回到原本的傳統民居上,對他們來說好不容易現代化了,要讓我退回去,有一個很大的觀念上的差異。為此郭家溝的老支書張志剛帶頭拆掉自己花錢貼的白瓷片,但他也不能理解朱冰的改造方案,他說:“特別不樂意改的就是這個墻,欄桿不樂意拉,但是應該有改的必要吧,因為全村都是統一格調,我不動也不好,我要不改,別人更不改。”
除了村莊的外部景觀需要改造,朱冰還得提升農家客棧的房間標準,而這就必須改變村民家里現有的客棧格局,有的甚至要減少一半的客房,這又引起了村民們的抵制。他們也是接受不了,因為沒有看到。觀念上的差異讓工程推進得很艱難,有的村名甚至將朱冰的團隊趕出了門。幾乎所有人都在質疑朱冰要打造的這個鄉村“裸妝”效果的創新,到底對不對?甚至她的團隊也有人因此退出,能證明她的唯一辦法就是堅持下去。
朱冰只能說:“如果這樣做的話,你們的收入會提高,游客人會多。”“我們就是完完全全是來服務的,為別人好的,但是人家還這樣對待我們,心里肯定是有一些不舒服的地方。但是話又說回來,就覺得越是這樣的話越覺著自己做這個事情有意義。因為做任何一件創新的事情,或任何一個前人沒做過的事情,沒碰見困難的話才奇怪呢。那時候逃跑的話只能是印證了別人的質疑是對的,所以當別人所有的人都在質疑你的時候,你只能堅持把這件事做下來,把這個結果拿出來。”
那時這個改造工程的合同還沒敲定,整個郭家村的改造設計費用,其實都是朱冰墊資的。從商業上看,這無疑是一場失敗的生意,但卻是朱冰作為一名理想主義者檢驗真理的戰場。甚至最嚴重的時候,朱冰將自家的房產都抵押給了銀行。
“有那種壯士斷腕的悲涼感覺,因為覺著我這么一心一意在做著事,知道這樣做一定是對的,但是沒有人相信,到后來我們就惶恐,我們害怕自己錯了,害怕自己堅持半天,最后是錯了。”面對諸多質疑,朱冰只能咬著牙堅持,但是只有她心里清楚。在誠惶誠恐的堅持的日子里,張大爺在朱冰給他設計的葫蘆架上種上了葫蘆,在院子里的花墻下種了花,屋頂上用木柵欄圍了起來,坐在樹蔭下乘涼還能看到遠山,以及成群結隊的游客。
終于郭家溝村莊建設規劃獲住建部“2014年全國村莊規劃示范項目”。2019年7月28日,郭家溝村入選第一批全國鄉村旅游重點村名單。改造工程完成的那一年,村里最多的一個人收入翻了三番,那時候大家都沒有話了,當老百姓的收入真的是因為改造翻番的時候,朱冰的心才算真正落了到肚子里。
郭家溝的項目終于完成了,隨之而來是來自全國各地,從區域、城鎮、社區、園區、到旅游區、公共空間,從鄉村、城鎮綜合體、建筑,到室內設計、小品、展示,大大小小的項目六十余項,每一項從策劃、調研到落地,朱冰都是身體力行,奔赴在工作一線中。十余年來,江西景德鎮瑤里世界級旅游度假目的地、北京海淀區中關村數字電視產業園改造、北京通州國際人才港、貴州黔西南州安龍養生養老基地、廣東佛山南海大瀝鎮慧谷產業CBD、芬蘭赫爾辛基古根海姆博物館、都市意匠微睡產品等,成了朱冰都市意匠團隊共同努力的成果。相繼而來的是北京市特聘專家、海英人才、中關村十大海歸新星、北京市專家聯誼會建工組副組長、北京城市規劃學會理事、北京歐美同學會理事等,各種榮譽、地位紛至沓來。這無疑成了對朱冰最大的鼓勵。
立足企業根本,放眼未來世界
在朱冰的家中、公司辦公室的書架上,《中國農村》、《一個村莊里的中國》、《城市記憶》、《環境美學》等,除了關于鄉村城鎮改造的書,另一部分更多的是關于企業經營的。
在朱冰的書中,幾乎每一本讀過的書中都會鈐印一枚印章。在《鞋狗》的扉頁后,她這樣寫道:“在這里,我讀到了掙扎,以及和掙扎在一起的不失的熱情。”《鞋狗》是耐克創始人菲爾·奈特的親筆自傳,關于寫這本書的初衷,他這樣說:“獻給我的孫輩,他們將會知道耐克當年的故事。”目錄前,聯想控股董事長、聯想集團創始人柳傳志的一句話與朱冰產生共鳴,她拿起筆在這一行下面輕輕地畫了一條長長的波浪線:“一家企業只顧自己活著是不夠的,還得幫其他人活得更加充實。”
2018年朱冰給公司里的每一位項目經理都分發了一本世界500強企業京都陶瓷公司和日本KDDI公司董事長稻盛和夫親筆撰寫的《活法》。在《利他拓展視野》一文中稻盛和夫也寫了類似的話,他說:“經營企業不光是自己公司要盈利,也要考慮客戶的利益,還要對消費者、股東、地區作出貢獻。”可謂英雄所見略同。這無疑與朱冰十多年的創業經歷息息相關,才能讓她在讀到這些話的時候心生感觸。“堅持每天往前走,保持這種狀態度過最絕望的時候,即使看不到希望,也要堅持走完,并且相信會越走越好。”
每一本書的印記都一一刻畫在朱冰的心上。她說:“很多情況下,我們的工作相當于在沙漠上建立一個拉斯維加斯。周期長的項目一次能夠持續5年時間,最短的也需要1年。”在中心城市,早在2008年,作為規劃顧問,完成上海閔行區“郊區CBD”的策劃工作。2010年在鄭州提出以汽車產業園為發展契機,對鄭州國家級經濟開發區進行“城市升級”。自2010至今,為中關村數字電視產業園做持續的戰略規劃,使之列為“十二五中關村科學城重點項目”并隨著產業的升級,發展為“超硅巷”的城市發展模式。自2018年起,以北京國際設計周為抓手,為西城老城復興探討新的模式,提出“從院落開始的城市復甦”,以新型產業的活力細胞植入給予老城自我生長的新興力量。在小城鎮,完成國家級的特色小鎮——黑龍江省渤海鎮、江西瑤里鎮以及湖北無人機產業特色小鎮的策劃及規劃。在鄉村,北京市門頭溝區靈水村是中國傳統文化村落提升的試點項目。在深入理解國際規劃建設的理論與實踐,以及中國城鄉發展歷程和現狀問題之后,朱冰帶領著都市意匠團隊以多專業背景和多角度的視角為中國城鎮發展提供以問題為導向,以可持續發展為目的的規劃設計解決方案。
朱冰信心滿滿地說:“中國正在經歷一個絕無僅有的城鎮化的過程,這個過程200多年前英國已經完成了,100多年前在美國也已經完成了,坦白說作為一個知識分子,活在這樣一個歷史的大時代里是一種幸運,因為在這樣的時代里,可以把所學變為所用,這些年來,行走于京津冀的大地,行走于城鎮以及鄉村之間,我感覺這塊土地給人以希望。回國的這些年,我感覺到特別踏實,還有內心的充實。這個充實一部分原因在于我們的項目一個個落地,另外一種來源于身邊的人,來源于家人、朋友的陪伴,就像我們公司能夠有自己的合伙人,我們能夠在一起體驗創業的酸甜苦辣,這樣使我們的事業能夠做得更好。”
當我以“做女人難,做女強人更難”來概述她的時候,朱冰像以往一樣,露出平和的笑容說:“其實在當下的環境中,想要實現自己的夢想自然會辛苦些,但其中的快樂也是非常大的。我沒有覺得難,反而覺得很幸運。”
近期排列在出差行程里的京、津、冀、魯、鄂、貴、疆、贛的24個明確的項目編號按序排列在都市意匠的項目表上,跟緊每個項目的進展工作,督促、指導項目負責人實地調研,探討完成策劃方案。相信朱冰會帶領著自己的團隊,在中國的大地上更好地完成自己的作品和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