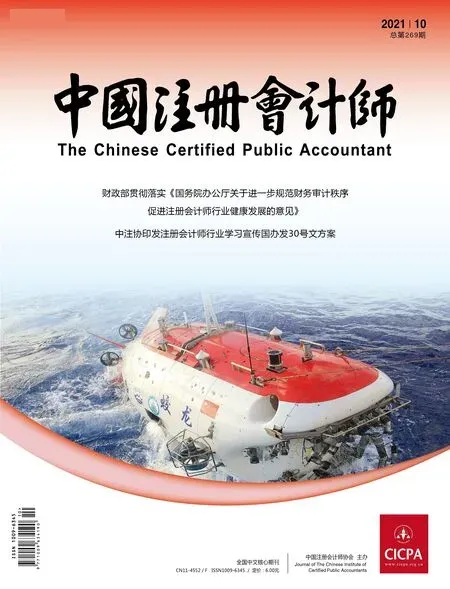上市公司年報審計風險評估程序缺陷及對策研究
陳艷芬 彭俊英 姚莉
風險評估是風險導向審計工作的重要環節,是設計與實施進一步審計程序的基礎。2007年我國開始推行風險導向審計,2010年我國修訂了審計準則,進一步強化了風險導向審計的思想,將風險導向審計理念全面徹底地貫徹到審計準則中。本文選擇中國證監會及其32個派出機構2011年至2020年針對上市公司年報審計的違法行為發布的45份行政處罰決定書進行分析,對從中篩選出涉及風險評估程序缺陷的19份行政處罰決定書開展深入研究,歸納總結上市公司年報審計風險評估程序缺陷的總體情況后,深入分析了風險評估程序缺陷的具體表現,并提出優化對策,以期能對實務工作提供一定的借鑒,推動風險導向審計的有效實施。
一、上市公司年報審計風險評估程序缺陷分析
我國自2007年開始推行風險導向審計,由于證監會對審計違法行為查處時間大致為3-5年,本文在選取行政處罰決定書進行分析時,先瀏覽2007-2020年證監會發布的64份行政處罰決定書,并統計其審計違法事實發生年份,進而確定本文研究對象區間為2011年至2020年的發布的45份行政處罰決定書。再次以風險評估及風險評估程序為關鍵詞篩選出19份涉及風險評估程序缺陷的行政處罰決定書進行深入分析。19份行政處罰決定書中,有9份行政處罰決定書中單獨列示了風險評估程序的缺陷。從審計違法行為發生年份來看,證監會查處的審計失敗案件中存在風險評估程序缺陷的案件數呈現倒U型的變化趨勢,風險評估程序存在缺陷的案件集中發生在2012年至2014年,詳見圖1。可知,2010年我國審計準則修訂后,監管者加強了對風險導向審計實施情況的監管。在嚴厲的監管環境下,我國注冊會計師風險導向審計思維不斷強化,風險評估程序存在缺陷的案件數逐年減少。分析發現,注冊會計師風險評估序的缺陷主要表現在四個方面:未實施風險評估程序、風險評估程序未能有效執行、風險評估程序與總體應對措施和進一步程序銜接不到位,風險評估工作底稿不規范,詳見表1。風險評估程序缺陷具體分析如下:

表1 風險評估程序缺陷分析表

圖1 風險評估程序缺陷發生次數
(一)未實施風險評估程序
在執行審計時,未實施風險評估程序這一缺陷反應了部分注冊會計師忽視風險評估的重要性,認為風險評估程序僅為形式流程,并不能據此減輕實質性程序工作。因此,在實施程序時仍以傳統的賬項導向審計為主,沒有了解被審計單位的行業狀況、經營風險等方面,未實施風險評估程序。例如,利安達會計師事務所對華銳風電審計失敗案例中,受國家風電行業政策的較大影響,華銳風電2012年整體業績出現大幅下滑,注冊會計師未執行風險評估程序以獲取相應審計證據,審計工作底稿中未見風險識別軌跡。注冊會計師對“競爭激烈或市場飽和,且伴隨著利潤率的下降”、“客戶需求大幅下降,所在行業或總體經濟環境中經營失敗的情況增多”的風險評估結果是“不存在”,其風險評估結果與當時企業所處的行業狀況明顯不符。
(二)風險評估程序未能有效執行
風險評估程序未能有效執行在審計失敗案件中發生次數占比最高,達55.17%。這一缺陷具體表現在三個方面:
1.部分風險評估程序未實施。例如在立信會計師事務所對超華科技審計失敗案例中,立信所針對超華科技營業收入執行了風險識別與評估程序,但審計程序只涵蓋了主營業務收入,未覆蓋其他業務收入。超華科技主營業務模式與其他業務模式存在明顯區別,同時,立信所在審計過程中關注到,超華科技“本年其他業務收入有5000多萬,成本300多萬,若無其他業務收入,公司本年的利潤為0”這一重要情況,卻仍未對超華科技其他業務收入補充執行風險識別與評估的審計程序。
2.實施了風險評估程序,未能識別風險。部分注冊會計師在識別和評估重大錯報風險時,注冊會計師在了解被審計單位及其環境(包括風險相關的控制)的整個過程中,沒有結合財務報表中各類交易、賬戶余額和披露的考慮識別風險,或是評估識別出風險后,并未評價其是否廣泛跟財務報表整體層次相關。或是,沒有結合對擬測試的相關控制的考慮,將識別出的風險與認定層次可能發生錯報的領域相聯系,導致未能識別報表層和認定層的重大錯報風險。如北京興華會計師事務所對新綠股份審計失敗案例中,注冊會計師在該項目底稿中顯示已識別出新綠股份實際控制人與基金合伙企業簽《增資協議》之外的補充協議,約定2013至2015年稅后利潤最低目標,而2012年新綠股份實際利潤遠低于約定利潤,承受過度業績壓力的信息,但注冊會計師卻沒有將該業績壓力與財報層次重大錯報風險聯系,未能識別出財報層次的重大錯報風險。此外,部分注冊會計師雖實施了風險評估程序,但未能識別出特別風險,主要包括未識別舞弊風險、未識別關聯方交易風險和未識別異常重大交易風險三大情形。針對特別風險,注冊會計師需要識別并了解與該特別風險相關的內部控制,根據風險的性質、潛在錯報的重要程度和發生的可能性,判斷風險是否屬于特別風險。在確定風險性質時,應考慮風險是否為舞弊、重大關聯方交易、重大交易等。但不少注冊會計師在風險評估時,并未專門識別被審計單位是否存在特別風險。例如,立信會計師事務所對風華高科審計失敗案件中,立信所經過風險評估,識別出風華高科理財產品的購買時間、金額與應收賬款轉讓時間、金額高度一致,且投資顧問費的支出明顯高于投資收益的收入,購買理財產品的交易行為存在重大異常,立信所未考慮該項重大交易是否存在特別風險,最后引發審計失敗。
3.未適時修正風險評估結果。風險評估是一個連續的、動態的不斷收集與更新信息的過程,貫穿整個審計業務過程始終。若有證據表明風險評估結論不合理,注冊會計師應及時修正風險評估的結論。實施進一步審計程序時獲取的審計證據,與之前風險評估所依據的審計證據不一致時,部分注冊會計師未能及時修正風險評估結論,未修改進一步審計程序的性質、時間安排及范圍。如2019年公布的瑞華會計師事務所對零七股份審計失敗案例中,注冊會計師對控制環境的描述、評價與實際情況不符,對舞弊風險因素的識別與實際不符,未關注實際情況與管理層風險評估結果的差異,在執行審計業務期間也未就零七股份披露的相關公告對其風險評估結果進行適當的修正;也未全面評估舞弊導致的財務報表層次重大錯報風險,導致對客觀存在的舞弊風險因素采取的應對措施不足。
(三)風險評估程序與總體應對措施和進一步審計程序銜接不到位
注冊會計師應針對評估的財務報表層次和認定層次的重大錯報風險,設計和實施恰當的總體應對措施和進一步程序,否則,風險導向審計無法貫穿整個審計過程,進而將嚴重影響審計工作的效率和效果。例如在北京興華會計師事務所對欣泰電氣的審計失敗案例中,在欣泰電氣IPO期間,注冊會計師將收入評估為“可能存在較高重大錯報風險的領域”,并在審計工作總結中將“收入及利潤上漲風險”認定為“評估的特別風險”,但對與其相關的應收賬款明細賬中存在的大量大額異常紅字沖銷情況未予關注,未保持職業懷疑,繼而未設計和實施有效的應對程序以獲取充分、適當的審計證據,使得風險評估結果未能發揮指引作用。
(四)風險評估底稿填寫不規范
按照審計準則規定,注冊會計師應該對制定的審計計劃、實施的審計程序、獲取的相關審計證據,以及得出的審計結論都記錄在工作底稿中,包括對實施的風險評估程序,即便沒有識別出相關風險也應據實記載。從行政處罰決定書中得知,部分注冊會計師在執行風險評估程序后未把實施程序的結果和獲取的審計證據、審計中遇到的重大事項和得出的結論以及在得出結論時做出的重大職業判斷記錄在工作底稿上,最后在聽證會上百口莫辯。如2018年公布的大華會計師事務所對佳電股份審計失敗案例中,佳電股份2014年12月記入賬面的銷售費用存在明顯波動,大華所在銷售費用審計工作底稿中記錄了各費用明細科目的各月發生額,但未見對費用波動情況進行風險評估的審計工作底稿。又如2018年公布的立信所對武漢國藥科技審計失敗案例中,注冊會計師在對鄂欣實業鋼材銷售進行穿行測試時,未取得“銷售合同審批單”,對上海淙遠實業有限公司開具的要求憑發貨碼單結賬的提貨單,注冊會計師既未關注,也未收集發貨碼單,穿行測試審計證據獲取不充分,且未記錄測試結論。
二、優化風險評估程序的對策建議
風險評估是注冊會計師風險控制的起點,風險評估旨在識別和評估被審計單 位報表層和認定層的重大錯報風險,進而為風險應對環節總體應對措施和進一步審計程序的設計與實施提供基礎。針對風險評估程序的缺陷,筆者認為可以從如下幾個方面進行優化:
1.強化風險導向審計思維。從風險評估缺陷的分析來看,當前還存在部分注冊會計師不重視風險評估,風險評估程序流于形式的情況,才會出現未實施風險評估程序、風險評估程序實施不全面、風險評估過程與結論不一致、未記錄風險評估底稿等問題。風險導向審計是以風險為核心開展審計工作,在風險評估階段,通過了解被審計單位及其環境,識別和評估重大錯報風險,以確定財務報表的重點審計領域。在風險應對階段,依據風險評估的結果,設計與實施具有針對性的進一步審計程序。強化注冊會計師風險導向審計思維,將有效促進注冊會計師在審計工作中落實風險導向審計工作,認真、全面實施風險評估程序并記錄在工作底稿上,適時修正風險評估結論。
2.注重重大錯報風險的識別和評估。風險評估工作的目的在于識別兩個層次的重大錯報風險,若注冊會計師未能充分識別重大錯報風險,則表明注冊會計師未能充分了解被審計單位及其環境。在風險評估環節中,注冊會計師在了解被審計單位及其環境的整個過程中,需結合對財務報表中各類交易、賬戶余額和披露的考慮,識別風險。對識別出的風險進行評價,看其是否更廣泛地與財務報表整體相關,進而潛在地影響多項認定;并結合對擬測試的相關控制的考慮,將識別出的風險與認定層次可能發生錯報的領域相聯系;最后考慮發生錯報的可能性,以及潛在錯報是否足以導致重大錯報。也就是說,注冊會計師需要識別報表層和認定層的錯報風險并且判斷其是否重大。
3.重點關注特別風險。特別風險,是指需要注冊會計師特別關注的風險。審計準則要求注冊會計師應當根據職業判斷,確定識別出的風險是否為特別風險。隨著新經濟、新業態的發展及監管環境的變化,企業的財務報表審計可能存在諸多特別風險。針對特別風險,注冊會計師不僅需要識別它,還需了解被審計單位與該風險相關的控制,以獲取充分、適當的審計證據。值得注意的是,特別風險中舞弊風險的識別與應對是導致審計失敗的重要原因之一。學者們對于風險導向審計是否能有效識別舞弊風險存在爭議。筆者認為,風險評估程序在設計與實施過程中,一方面應注重審計程序的不可預見性,另一方面可有效利用人工智能、區塊鏈、云計算、大數據、物聯網等信息技術以應對舞弊風險等特別風險。
4.注重風險評估與風險應對環節的銜接。風險評估程序識別兩大層次的重大錯報風險,為風險應對環節進一步審計程序的設計與實施提供基礎。如果未能有效利用風險評估程序的結果,在風險應對環節可能出現兩大問題,一是更多依靠實質性程序獲取審計證據,增加審計工作量,降低審計效率。二是未能對已識別的重大錯報風險設計與實施具有針對性的審計程序,以致于未能發現重大錯報,嚴重影響審計效果。注冊會計師應貫徹風險導向審計理念至整個審計過程,尤其需要注重風險評估與風險應對環節的銜接,有效發揮風險評估的指引作用。
5.強化風險類審計工作底稿的質量控制。風險類審計工作底稿反映了注冊會計師實施風險導向審計的過程。會計師事務所應強化風險類審計工作底稿的質量控制,防止出現風險評估工作底稿未記錄、未記錄的風險評估過程與結論不一致等問題。
作者單位:廣州新華學院 廣州醫科大學附屬腦科醫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