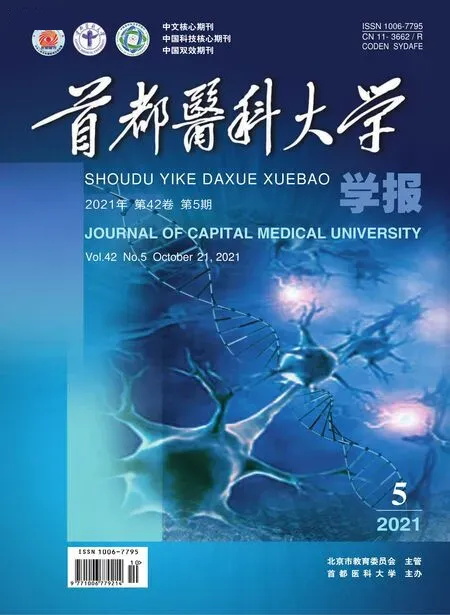初診2型糖尿病患者中肝臟胰島素清除率與臨床特點及胃腸激素相關性的初步分析
張冬雪 文 禎 孫玉燕 姜 濤
(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世紀壇醫院內分泌科, 北京 100038)
近年來研究[1]顯示,胰島素抵抗患者中出現高胰島素血癥的原因中,除胰腺代償性分泌胰島素增加以外,胰島素清除率下降(insulin clearance,IC)是另一個重要的發病機制。而人體內絕大部分胰島素的清除過程是在肝臟中完成的,因此肝臟胰島素清除率(hepatic insulin clearance,HIC)在調控高胰島素血癥中發揮舉足輕重的作用。HIC參與患者胰島素抵抗及胰島功能損傷等糖尿病的重要病理生理機制,且是預測2型糖尿病的重要的獨立危險因素[2],甚至HIC的下降可能加速胰島細胞衰竭,是糖尿病發病的始動環節[3]。此外,胰島素清除率在不同種族的糖尿病患者[4]及不同血糖狀態之間存在較大的異質性[5-6],故我國初診的2型糖尿病(type 2 diabetes mellitus,T2DM)患者中HIC的變化情況,及其是否與胰島素抵抗、胰島功能存在相關性、參與糖代謝,仍需探討。
此外,研究[7]顯示,靜脈注射葡萄糖后HIC改變并不明顯,但口服葡萄糖后患者HIC顯著下降[8],HIC的改變似乎與胃腸激素引起的“腸促胰素效應”存在異曲同工之處。且與HIC類似,胃腸激素在T2DM患者中亦與其胰島素抵抗及胰島功能密切相關。同時,脂肪肝是誘發HIC下降的重要原因[9],腸抑胃肽(gastric inhibitory polypeptide,GIP)及胰高血糖素樣肽-1(glucagon-like peptide-1,GLP-1)均參與肝臟脂肪代謝,因此筆者推測胃腸激素有可能參與HIC的改變。目前,少量研究[5,10]已經開始逐步關注GIP及GLP-1與HIC的相關性,但其研究結果有仍有一定的爭議。此外,饑餓素(ghrelin)是近年來發現在2型糖尿病中舉足輕重的另一種胃腸激素,且被證實參與肝臟脂代謝、炎性反應等非酒精性脂肪肝病的多個環節[11]。但目前仍未有關于ghrelin與2型糖尿病患者的HIC相關性的報道發表。因此,ghrelin、GIP及GLP-1與HIC是否存在相關性,在漢族2型糖尿病患者中亦是十分值得探討的問題。
故本研究擬納入初診2型糖尿病患者,分析肝臟胰島素清除率與其胰島素抵抗及胰島功能的相關性,同時探索胃腸激素ghrelin、GIP及GLP-1是否與HIC存在相關性,為我國T2DM患者防治工作提供新的理論依據。
1 對象與方法
1.1 研究對象
納入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世紀壇醫院內分泌科初次診斷且未經藥物治療的2型糖尿病患者112例,平均年齡(46.21±1.53)歲,其中女性患者31人,占所有患者的27.70%。納入標準:①明確診斷為2型糖尿病,符合《中國2型糖尿病防治指南(2020版)》[12]的診斷標準;②年齡≥18歲,性別不限;③未開始使用降糖藥物及胰島素治療;④自愿參加本研究并簽署知情同意書。排除標準:①合并酮癥或高血糖高滲綜合征;② 肝、腎功能不全;③哺乳或妊娠狀態;④合并惡性腫瘤;⑤酗酒或精神類藥物使用史;⑥感染狀態;⑦合并甲狀腺功能異常等內分泌功能異常疾病。HIC計算方法[2,5]:HIC=AUCIns/AUCC-P,其中AUCINS為OGTT試驗過程中0~120 min胰島素(insulin, Ins, pmol/L)濃度的曲線下面積(area under the curve, AUC),AUCC-P表示同期C肽(C-peptide, C-P, nmol/L)的曲線下面積。本研究中把肝臟胰島素清除率中位數6.63作為切點,將患者分為低HIC組(n=56)及高HIC組(n=56)。低HIC組的HIC值為5.01±0.15,高HIC組的平均值為24.40±14.51,兩組間差值的平均值為19.40±14.51。本研究方案經過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世紀壇醫院倫理委員會審批(批號:2017年科研倫審第13號),且受試者已經簽署知情同意書。
1.2 臨床指標收集
收集患者性別、年齡等一般資料。患者隔夜禁食10~12 h后,進行口服葡萄糖耐量(oral glucose tolerance test, OGTT)、胰島素釋放試驗及C肽釋放試驗:分別于0 min(試驗前),口服75g葡萄糖后30、60 及120 min分別采血。收集患者OGTT試驗過程中血糖(glucose, Glu)、胰島素及C肽檢測結果。同時收集空腹三酰甘油(triglyceride, TG)、總膽固醇(total cholesterol, TC)、低密度脂蛋白膽固醇(low density lipoprotein cholesterol, LDL-C)、高密度脂蛋白膽固醇(high density lipoprotein cholesterol, HDL-C)、丙氨酸氨基轉移酶(alanine aminotransferase, ALT)、門冬氨酸氨基轉移酶(aspartate aminotransferase, AST)、谷氨酰胺轉肽酶(γ glutamyl transpeptidase, GGT)、尿酸(uric acid, UA)及糖化血紅蛋白(haemoglobin A1c, HbA1c)等代謝指標,上述檢測均在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世紀壇醫院檢驗科完成。
1.3 胰島素抵抗及胰島功能指標計算
胰島素抵抗指標評估:①穩態模型胰島素抵抗指數(homeostasis model assessment-IR, HOMA-IR);②Matsuda指數(Matsuda index)。
胰島功能評估指標:①穩態模型胰島β細胞功能指數(homeostasis model assessment-β,HOMA-β);②β細胞早期分泌功能用以下指標評估,胰島素生成指數(insulinogenic index,IGI),其中AUCIns/AUCGlu用于評估β細胞分泌胰島素的總體水平。
1.4 胃腸激素檢測
患者OGTT試驗期間,分別于0、30、60及120 min采血。收集患者血標本3 mL,離心15 min (3 000 g), 留取血清,凍存于-80 ℃待檢測。取25 μL血漿,根據說明書操作步驟,使用Millipore免疫試劑盒(Millipore Corp, 美國),在Luminex多重檢測系統(Luminex 公司, 美國)中檢測患者血漿中Ghrelin、GLP-1及GIP濃度。
1.5 統計學方法

2 結果
2.1 不同HIC組患者一般情況及代謝指標的比較
高HIC組及低HIC組患者在年齡、性別、BMI及腰圍方面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在血糖控制方面,兩組患者糖化血紅蛋白及空腹血糖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表1),75 g葡萄糖負荷后不同時間點血糖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01),但高HIC組患者負荷后30 min(P=0.026)及120 min(P=0.013)的血糖濃度明顯高于低HIC組(圖1A)。高HIC組患者OGTT曲線下面積亦高于低HIC組患者(1 702.45±54.90vs1 543.40±30.06,P=0.013)。高HIC組患者基礎胰島素(P<0.001)與葡萄負荷后30 min(P<0.001)、60 min(P=0.001)及120 min(P=0.001)胰島素濃度均明顯低于低HIC組(圖1B、表2)。同時,不同HIC分組患者隨著攝入葡萄糖時間的推移,出現不相同的變化趨勢(P=0.016),且胰島素曲線下面積均明顯高于低HIC組(2 228.7±251.1vs4 452.4±492.1,P<0.01),但兩組之間C肽曲線下面積差異無統計學意義(表2)。進一步分析發現,高HIC組患者中血脂(TG、TC、LDL-C、HDL-C)、尿酸及肝功能(ALT、AST及GGT)在兩組患者中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表1)。

表1 不同肝臟胰島素清除率患者的一般情況及代謝指標比較 Tab.1 Demographic and metabolic characteristics in patients with different hepatic insulin

圖1 口服糖耐量試驗中不同肝臟胰島素清除率組患者葡萄糖及胰島素釋放曲線比較Fig.1 Glucose and insulin curve during an oral glucose tolerance test in patients with different hepatic insulin clearanceA: glucose curve in patients with different HIC. *P<0.05 vs low HIC; B: insulin curve in patients with different HIC. #P<0.05 vs high HIC; HIC: hepatic insulin clearance.

表2 不同肝臟胰島素清除率患者的胰島素敏感性及胰島功能比較
2.2 HIC與患者胰島素抵抗及胰島功能的相關性
在胰島素抵抗方面,低HIC組患者的HOMA-IR明顯高于高HIC組(P=0.011),Matsuda指數在低清除率組中也明顯降低(P=0.038),低HIC組患者的胰島素抵抗程度相對嚴重。但在胰島β細胞功能方面,高HIC組患者的空腹胰島素及HOMA-β濃度均明顯降低(P<0.001)。此外,雖然兩組患者早期胰島素分泌指標IGI間差異無統計學意義,但AUC-Ins/AUC-Glu在高HIC組明顯下降(P<0.001,表2)。
2.3 HIC與患者胃腸激素的相關性
高HIC組患者的空腹血ghrelin濃度明顯低于低HIC組(P=0.044, 圖2A),且葡萄糖負荷后高HIC組患者中葡萄糖對的ghrelin的抑制作用減弱,即120 min 時高HIC組患者血清ghrelin較基線值下降的更少 (P=0.027, 圖2B)。空腹GIP及GLP-1在兩組不同肝臟胰島素清除率的患者中差異無統計學意義。同時,GIP及GLP-1(P>0.05)在兩組患者服用75 g葡萄糖后30、60、120 min及曲線下面積差異亦無統計學意義(P>0.05)。

圖2 不同肝臟胰島素清除率患者胃腸激素比較Fig.2 Gut hormone in patients with different hepatic insulin clearanceA: ghrelin secretion curve in patients with different HIC,*P<0.05 vs high HIC; B: increment for ghrelin after glucose loading in patients with different HIC; C: GIP secretion curve in patients with different HIC; D: GLP-1 secretion curve in patients with different HIC; HIC: hepatic insulin clearance; GIP: gastric inhibitory polypeptide; GLP-1: glucagon-like peptide-1.
3 討論
本研究收集初診未治的漢族2型糖尿病患者的臨床資料,行OGTT試驗,同期檢測75 g葡萄糖負荷前后的胰島素分泌及胃腸激素濃度,發現肝臟胰島素清除率影響患者胰島素濃度,與患者胰島功能及胰島素抵抗相關,且較高的肝臟胰島素清除率與空腹低ghrelin相關,同時葡萄糖對ghrelin的抑制作用幾乎消失,但GIP及GLP-1與肝臟胰島素清除率無關。
本研究中,高HIC組患者葡萄糖負荷后血糖濃度較高。研究[6]顯示,患者HIC狀態與血糖濃度存在一定的相關性。早在糖耐量正常的肥胖患者及代謝綜合征患者中就已經出現胰島素清除率明顯下降的情況[2],而清除率下降誘發的代償性高胰島素血癥,在這部分患者維持正常的糖耐量狀態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6]。患者出現糖耐量異常后,HIC仍然代償性下降;但患者達到T2DM診斷標準后,雖然其HIC較正常人代償性降低,但其降低程度遠低于糖耐量異常患者,提示T2DM患者中HIC下降的代償機制可能受到損傷,造成血糖進一步升高。且隨著糖尿病進展,HIC亦出現較大的異質性:與本研究類似在血糖較高的T2DM患者中HIC相對升高,可能失去了HIC的代償機制[12]。HIC與胰島功能存在一定的相關性,本研究中較高的HIC對應較低的HOMA-β及AUCIns/AUCGlu,即相對較差的胰島功能。與本研究相同,Okura等[5]發現血糖控制欠佳的T2DM患者中HIC與HOMA-β呈負相關,糖耐量正常的代謝綜合征患者的研究[2]中HIC與胰島素濃度也呈負相關。同時,本研究中,HIC較低的患者中胰島素抵抗相對嚴重。此外,研究[13]顯示,ALT與肝臟胰島素清除率呈負相關,同時與肝臟胰島素抵抗呈正相關。本研究中雖然兩組患者ALT差異無統計學意義(可能受樣本量局限影響),但低HIC組患者的ALT濃度相對較高,胰島素抵抗較重。HIC較低的糖尿病患者,可通過降低HIC代償胰島素抵抗,提高胰島素濃度,甚至形成高胰島素血癥,以利于血糖的控制;但慢性高胰島素血癥會進一步加劇肝臟脂肪堆積,下降的HIC亦會造成肝臟脂肪變性,肝臟脂肪堆積、變性可進一步降低HIC,最終較低的HIC可能成為連接高胰島素血癥與肝臟脂肪變性的重要紐帶[14],本研究中未測定肝臟脂肪含量,略有不足。綜上,HIC相對較高的患者中,HIC似乎失去了其代償功能,引起胰島素濃度下降,雖然胰島素抵抗減輕,但對應較差的胰島功能,可能是其血糖升高的重要原因。
研究[8]顯示,口服葡萄糖可降低糖尿病患者的肝臟胰島素清除率,但靜脈注射葡萄糖并不影響HIC濃度[7],因此筆者推測胃腸激素可能參與其中。但是,本研究中高HIC組與低HIC組初診漢族T2DM患者的空腹及葡萄糖負荷后GLP-1、GIP濃度差異無統計學意義。與本研究結果相似,一項T2DM患者研究[5]中,采用本文中的方法及葡萄糖鉗夾同時評估患者肝臟胰島素清除率,采用饅頭餐代替葡萄糖,亦未發現HIC與GIP、GLP-1的相關性,且在另一項糖尿病患者的研究[8]中也未發現口服葡萄糖后HIC的下降與GLP-1、GIP有相關性。但與本研究不同的是,在10例血糖控制較好的T2DM患者的研究[10]中,雖然發現HIC與GLP-1呈正相關,與GIP呈負相關,但上述研究中患者服用的是異麥芽酮糖,與本研究中使用的葡萄糖的吸收、代謝過程存在差異,異麥芽酮糖誘發較輕的負荷后高血糖及較輕的高胰島素血癥,而這種差異可能來源于胃腸激素的參與。綜上,目前仍沒有充分的證據支持T2DM患者GLP-1及GIP與HIC之間存在相關性。
饑餓素是主要由胃黏膜細胞(少量ghrelin由小腸內分泌細胞及胰島ε細胞)分泌的短肽,可與生長激素受體結合,促進生長激素釋放,且可直接開放β細胞上延遲開放鉀通道,調控胰島素釋放:空腹狀態ghrelin濃度較高,抑制胰島素釋放,預防低血糖;餐后狀態下ghrelin快速下降,解除對β細胞的抑制作用,促進胰島素釋放,進而發揮降低餐后血糖的作用[15]。本研究中,低HIC組患者的空腹ghrelin濃度較高。研究[16]顯示,增加大鼠腸道中ghrelin的濃度,可造成肝臟細胞胰島素受體后信號通路活性降低。人體內胰島素與肝細胞上胰島素受體相結合,被肝細胞攝取、降解,完成胰島素在肝臟中的清除過程[17]。此外,ghrelin升高可能造成肝臟脂肪堆積[11],而肝臟的脂肪堆積本身就是造成HIC下降的重要原因[9]。故推測本研究中較高的空腹ghrelin濃度與較低的HIC相關,可能與ghrelin介導的胰島素信號通路受損及肝臟脂肪堆積有關,但這一假設仍需相關分子實驗進一步驗證。除此之外,本研究中高HIC組患者口服葡萄糖2 h后對ghrelin的抑制程度較低HIC組明顯減弱。多數糖尿病患者與健康受試者類似,葡萄糖負荷后或進餐后患者ghrelin受到抑制,解除對β細胞的抑制作用[15],胰島素分泌增加,降低負荷后血糖。但在部分肥胖及T2DM患者中餐后ghrelin被抑制的程度受到損傷[18]。且對多囊卵巢綜合征患者的研究[19]結果,也與本研究類似,不但空腹ghrelin下降,同時餐后ghrelin被抑制的程度也減弱。同時,ghrelin餐后受抑制的程度亦受種族差異的影響[18]。因此,本研究中高HIC組患者葡萄糖負荷后對ghrelin的抑制作用受損,可能造成其對胰島素釋放的抑制作用較強,影響該組患者胰島素濃度。與此同時,胰島素濃度反過來亦會影響ghrelin濃度,即胰島素與ghrelin之間存在相互作用[20]。故筆者推測,在本研究較高的HIC造成的胰島素濃度下降,對ghrelin的抑制作用減弱,可能是造成該組患者葡萄糖負荷后ghrelin下降不明顯的原因。由此可見,HIC與ghrelin在葡萄糖負荷后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相關性。
本研究中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雖然葡萄糖鉗夾是評估HIC的金標準,但葡萄糖鉗夾技術難度較高,招募患者相對困難,故本文中采用文獻[2,5]報道的相對簡易的方法估計患者HIC,有可能存在一定偏差。此外本研究中只是對不同HIC患者進行胃腸激素的初步探討,將來需要進一步擴大研究的樣本量的深入研究。同時ghrelin是否直接作用于肝臟,調節糖尿病患者的胰島素清除率,是否影響肝臟脂肪堆積及其胰島素信號通路,該機制需要深入的試驗研究進一步探討。
綜上所述,本研究發現初診2型糖尿病患者的肝臟胰島素清除率與胰島β細胞功能及胰島素抵抗密切相關,雖然胃腸激素GLP-1及GIP參與其中的證據不足,但空腹ghrelin升高及葡萄糖負荷對ghrelin的抑制作用減弱均與肝臟胰島素清除率存在一定的相關性,可能患者葡萄糖代謝中發揮潛在的調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