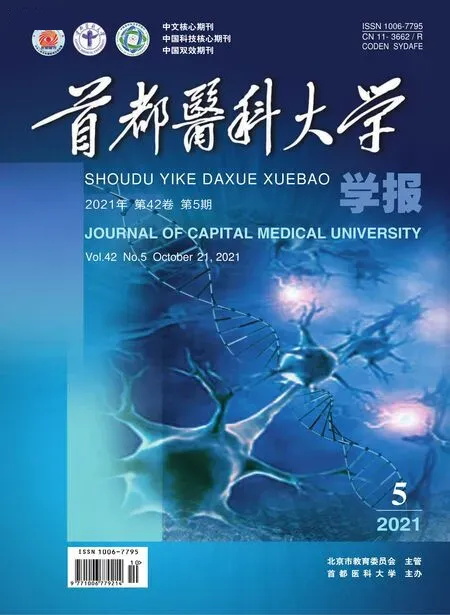多汗癥患者焦慮抑郁狀態及睡眠情況研究
林雪霏 吳 楠 張海萍
(首都醫科大學宣武醫院皮膚性病科, 北京 100053)
多汗癥是指軀體出汗超出體溫調節需求,導致全身或局部出汗過多的綜合征,可累及手足、腋窩、頭面部等區域[1]。多汗癥可分為原發性多汗癥和繼發性多汗癥,超過90%的患者為原發性多汗癥,其具體病因不明,可能與各種原因導致的交感神經異常興奮有關[2]。多汗癥嚴重影響患者的工作、生活及人際交往,還會帶來一系列情緒及心理問題。本研究對多汗癥患者焦慮、抑郁狀態及睡眠情況進行了現況調查。
1 對象與方法
1.1 研究對象
本研究收集2019年1月至2020年12月就診于首都醫科大學宣武醫院皮膚性病科門診的多汗癥患者。納入的患者符合多汗癥診斷標準[3]:出汗過多持續6個月以上,并至少滿足以下6條中的2條:①雙側對稱性出汗;②每周至少發作1次;③影響日常生活;④25歲前發病;⑤夜間睡眠時出汗停止;⑥有家族史。所有患者均自愿參加本研究,并已簽署知情同意書。
1.2 研究工具
本研究使用醫院焦慮抑郁量表(Hospital Anxiety and Depression Scale, HADS)及匹茨堡睡眠質量指數(Pittsburgh Sleep Quality Index,PSQI)量表進行評估。前者用于評估患者焦慮、抑郁情況,后者用于評估患者睡眠情況。
HADS可快速評估患者近1個月的焦慮、抑郁情緒,廣泛應用于綜合醫院。全表按照Zigmond 原始的兩因子結構模型進行分析,由14個條目組成,7個條目評定抑郁情況,7個條目評定焦慮情況。每個條目按照0~3分計分,焦慮、抑郁亞量表得分范圍均為0~21分,0~7分屬無癥狀,8~10分屬可疑存在焦慮癥狀或抑郁癥狀,11~21分屬肯定存在焦慮癥狀或抑郁癥狀[4]。患者得分以7分為界,得分>7分認定焦慮或抑郁癥狀陽性,若焦慮、抑郁量表得分均>7分則認為患者可能同時存在焦慮和抑郁癥狀,即焦慮抑郁共存的狀態。
PSQI用于評定受試者近1個月的睡眠質量,PSQI由19個自評條目及5個他評條目組成,其中第19個自評條目和5個他評條目不參與計分,參與計分的18個自評條目組成了7個維度,分別為主觀睡眠質量、入睡時間、睡眠時間、睡眠效率、睡眠障礙、安眠藥物和日間功能。每個維度以0~3分計分,各維度的得分相加為測評總分,范圍為0~21分,PSQI總分≤7分表示睡眠質量較好,總分>7分則存在睡眠障礙[5]。
1.3 陰性對照
本研究設立的陰性對照取自文獻[6]中于綜合醫院內科門診就診的患者,共6 172例,患者使用HADS量表進行自評,其中焦慮平均得分為(3.3±2.4)分,抑郁平均得分為(2.6±2.2)分[6]。因該研究數據樣本量大,專業性強,常被用作HADS 的國內常模,篩查住院、門診患者及社區人群的焦慮抑郁狀態。
1.4 統計學方法

2 結果
2.1 一般情況
本研究共入組163名多汗癥患者,其中男性87名,女性76名,年齡19~72歲,平均年齡(32.61±9.81)歲;學歷方面,中學及以下學歷21人(12.88%),大學學歷96人(58.90%),研究生及以上學歷46人(28.22%);工作環境方面,室內工作者152人(93.25%),室外工作者11人(6.75%);工作性質方面,腦力勞動者146人(89.57%),體力勞動者17人(10.43%)。出現焦慮或抑郁癥狀陽性者154人(94.48%),睡眠障礙者53人(32.52%)。
本研究的多汗癥患者HADS焦慮評分為(6.47±2.89)分,高于國內常模(3.3±2.4)分(P<0.05);HADS抑郁評分為(10.29±2.22)分,顯著高于國內常模(2.6±2.2)分(P<0.05);PSQI評分(6.21±3.16)分,整體睡眠質量尚好。
2.2 多汗癥患者焦慮狀態概況
本研究的多汗癥患者中焦慮癥狀陽性者47人(28.83%),平均得分(9.81±2.55)分,其中可疑焦慮(8~10分)35人(21.47%),肯定焦慮(11~21分)12人(7.36%)。
焦慮癥狀陽性患者中PSQI得分(8.17±2.95)分,顯著高于患者整體[(6.21±3.16)分]及焦慮癥狀陰性患者水平(P<0.05),詳見表1。

表1 多汗癥患者焦慮狀態及睡眠情況
2.3 多汗癥患者抑郁狀態概況
本研究的多汗癥患者中抑郁癥狀陽性者共146人(89.57%),其中可疑抑郁(8~10分)71人(43.56%),肯定抑郁(11~21分)75人(46.01%),多汗癥患者抑郁狀態發病率(89.57%)高于焦慮陽性患者(28.83%)(P<0.05)。
抑郁癥狀陽性患者PSQI評分(6.04±3.20)分,與患者總體評分[(6.21±3.16)分]相比,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詳見表2。

表2 多汗癥患者抑郁狀態及睡眠情況
2.4 多汗癥患者焦慮抑郁癥狀共存情況
參與研究的多汗癥患者同時存在焦慮、抑郁狀態者41人(25.15%),焦慮評分(9.51±2.05)分,抑郁評分(10.00±1.57)分。焦慮抑郁癥狀共存患者PSQI評分(8.22±2.99)分,高于患者平均水平(P<0.01),其中存在睡眠障礙者24人(58.54%),提示同時存在焦慮、抑郁狀態陽性者有一半以上存在睡眠障礙。
2.5 多汗癥患者睡眠障礙概況
存在睡眠障礙的患者53人(32.52%),其焦慮癥狀陽性評分(8.13±3.49)分,顯著高于患者整體焦慮得分(6.47±2.89)分(P<0.05),抑郁評分(9.51±2.22)分,與患者整體抑郁得分(10.29±2.22)分相比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焦慮癥狀陽性者28人(52.83%),抑郁癥狀陽性者43人(81.13%),焦慮抑郁共存狀態者24人(45.28%),無情緒問題者6人(11.32%)。詳見表3。

表3 睡眠障礙患者睡眠情況及焦慮、抑郁情況
2.6 不同人群焦慮、抑郁及睡眠評分比較
本研究分別對比了不同性別、年齡、學歷、工作環境及工作性質的多汗癥患者HADS焦慮、抑郁癥狀陽性評分及PSQI評分,結果發現室內工作者睡眠質量較室外工作者差(P<0.05),不同性別、年齡、學歷、工作性質的多汗癥患者組間評分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詳見表4。

表4 不同人群焦慮、抑郁及睡眠評分比較
3 討論
出汗在人類的日常生活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它可以維持體溫、應對情緒壓力和幫助新陳代謝。但多汗癥患者會出現身體特定部位過度且不受控制地出汗,常使患者在日常社交中壓力增大,缺乏自信,產生沮喪、自卑等不良情緒,極大地降低了患者的生活質量[7]。多汗癥常在兒童期或青少年期起病,其在美國患病率約為4.8%[8],在中國特定地區15~22歲學生中的患病率達4.36%[9]。目前已發現原發性多汗癥具有遺傳基礎,48%~65%的多汗癥患者具有陽性家族史,58%的患者為父母-子女共患病例,由此支持該病為常染色體顯性遺傳模式的假說[10]。
人類的汗液分泌受中樞神經系統和自主神經系統的調節。目前研究[11-12]顯示,多汗癥的發生可能是由于某種神經系統障礙,導致汗腺被神經系統釋放的乙酰膽堿過度刺激,而汗腺的大小、數量及組織學外觀均沒有明顯變化[13]。當自主神經系統紊亂時,可引起反射回路的神經元興奮性過高,破壞交感神經及副交感神經的正常調節作用。有研究[14]顯示,多汗癥患者瓦爾薩爾瓦(Valsalva)動作后反射性心動過緩減少,冷水浸泡手指后血管收縮增加,交感神經皮膚反應性增強,這些結果都提示多汗癥患者存在自主神經系統功能障礙。情緒控制中樞異常也會導致多汗癥的發生。情緒出汗是通過邊緣系統的前扣帶回與下丘腦精密調節完成[15],情緒性出汗主要影響腋窩、手掌、腳底、前額和頭皮,與多汗癥患者異常出汗部位吻合,由此推測,導致多汗的下丘腦調節中樞與一般體溫調節中樞不同,它完全受皮質的影響而與體溫信號無關。因此,多汗癥可能由情緒導致的中樞神經系統調節異常引發[11]。
有研究[16]表明,多汗癥患者更容易出現情緒問題,其中抑郁和焦慮在多汗癥患者中十分常見。有報道[17]稱,63%的多汗癥患者感到不快樂或抑郁,Bahar等[18]的研究顯示,多汗癥患者抑郁的發病率更高,為27.2%,而健康患者則為9.7%,另一項研究[19]表明,多汗癥患者焦慮的發生率是抑郁的4倍以上。本團隊對多汗癥患者焦慮、抑郁狀態的調查顯示,有94.48%的患者出現焦慮或抑郁癥狀陽性,提示多汗癥患者情緒問題較普遍,其中焦慮癥狀陽性者占28.83%,HADS焦慮評分平均為(6.47±2.89)分,顯著高于國內常模。筆者對患者抑郁狀態的調查發現,多汗癥患者抑郁狀態陽性率高達89.57%,HADS抑郁評分平均為(10.29±2.22)分,超過可疑抑郁區間,可見多數多汗癥患者呈現抑郁狀態,本結果與Bahar等[18]的研究結果相似。另有47人出現焦慮抑郁癥狀共存,其發病機制可能與下丘腦-垂體-腎上腺軸(hypothalamic-pituitary-adrenal axis,HPA)功能障礙及5-羥色胺能系統的級聯變化有關[20]。目前尚不清楚是情緒問題導致的多汗癥還是多汗癥導致的情緒問題,但二者可以相互影響,加重患者病情。
筆者統計了多汗癥患者的睡眠情況,有32.52%的患者出現了睡眠障礙。研究[21]表明,睡眠不足會使個人偏向消極情緒,更易發生焦慮、抑郁情況,并可以通過炎癥途徑對多種疾病造成影響。本研究的結果顯示,睡眠障礙患者普遍存在焦慮、抑郁情況,僅有6人(11.32%)無情緒問題,另外焦慮患者的睡眠障礙情況相較抑郁患者人數占比多,評分高,睡眠質量更差,尤其焦慮抑郁癥狀共存患者睡眠障礙更為嚴重。情緒狀況與睡眠障礙相互關聯的具體機制尚不清楚,可能與應激相關的分子影響睡眠覺醒的調節有關。
本研究還對比了不同人群HADS焦慮、抑郁評分及PSQI評分,發現不同性別、年齡、學歷、工作性質組間差異無統計學意義,但室內工作者睡眠質量較室外工作者差。本研究某些分組中樣本量較小,故雖平均值差異明顯,但并不能證實其差異有統計學意義,故今后將繼續擴大樣本量,以獲得準確的組間差異。
多汗癥患者常并發睡眠障礙、焦慮、抑郁等不良情緒,對生活產生多種負面影響,在臨床工作中,醫生在關注患者皮膚狀態的同時,也應關注其情緒、睡眠等情況,必要時進行有針對性的心理干預和抗焦慮抑郁藥物治療,以改善皮膚疾病治療效果,提高患者的生活質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