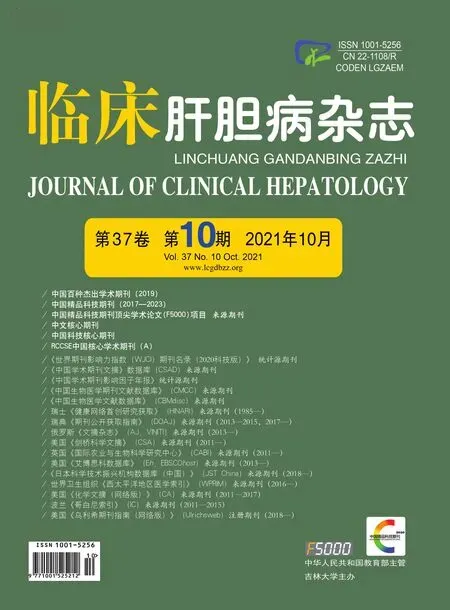HBV/HCV相關肝細胞癌抗病毒治療專家共識(2021年更新版)
中華醫學會肝病學分會肝癌學組
據世界衛生組織(WHO)的國際癌癥研究機構(International Agency for Research on Cancer,IARC)數據顯示,在原發性肝癌(primary liver cancer,PLC)中,肝細胞癌(HCC)占比80%以上,PLC的發病率居惡性腫瘤的第6位,死亡率居第3位。2020年,全球有90.57萬新發病例,83.02萬死亡病例;其中,我國肝癌發病例數占全球的45.27%,死亡數占全球47%[1]。據該機構預測,至2040年,肝癌的新發病例及死亡病例將進一步增加[2]。
乙型肝炎病毒(HBV)和丙型肝炎病毒(HCV)感染是HCC發生的重要病原學及疾病進展因素。我國近年發布的《慢性乙型肝炎防治指南(2019版)》[3]和《原發性肝癌診療規范(2019版)》均強調了HBV/HCV相關HCC患者管理中抗病毒治療的重要性。為規范HBV/HCV相關HCC抗病毒治療在臨床實踐中的應用,中華醫學會肝病學分會肝癌學組多次召開專題討論會,依據病毒相關HCC 抗病毒治療的循證醫學證據,綜合多數反饋專家建議,曾先后制定了《HBV/HCV相關性肝細胞癌抗病毒治療專家建議(2013年)》[4]和《HBV/HCV相關性肝細胞癌抗病毒治療專家共識(2014年)》[5]。本版在以往專家建議/共識基礎上,對近年新證據結果進行分析,經數十位專家多次會議討論,最終形成新一版共識更新。本共識主要受眾為肝病專科及感染科和這些科室以外從事與肝癌診療工作相關的臨床醫生及社區服務中心、基層醫療機構等相關工作人員。本共識對最終臨床決策制定提供具有參考價值的推薦意見,臨床實踐中尚需結合具體情況綜合評價做出臨床決策。
本次更新重點從HCC二級/三級預防層面強調抗HBV/HCV治療對HCC發生或復發的影響。本共識的證據質量和推薦意見分級采用評估、制訂和評價(GRADE)分級系統(表1)。

表1 推薦意見的證據等級和推薦等級
在前述共識基礎上,本共識采用以下HCC“分級預防”定義:HCC一級預防,防止可導致HCC發生的危險因素對普通人群初始侵害的措施;HCC二級預防,對于已具有慢性肝病背景(本共識主要關注HBV/HCV慢性感染)患者的HCC危險因素所采取的控制措施,目的是減少/延緩HCC發生;HCC三級預防,對已經發生HCC的患者除抗肝癌手術等治療以外,通過抗病毒治療等措施,減少HCC復發,保障HCC綜合治療效果,延長患者生存期的措施。
推薦意見1:HBV/HCV慢性感染是發生HCC的重要病因,通過抗病毒治療將慢性乙型肝炎(CHB)患者體內的HBV復制抑制至最低水平或達到功能性治愈,將慢性丙型肝炎(CHC)患者體內的HCV清除以達到治愈,均可明顯減少HCC發生,是HBV/HCV相關HCC二級預防最有效的手段(1A);抗病毒治療是HBV/HCV相關HCC發生后有效的基礎治療措施之一,可減輕肝炎病毒對肝臟的損害,減輕甚至逆轉肝纖維化或肝硬化,延緩腫瘤病情進展,減少HCC復發,保護肝功能,保障其他綜合治療效果,提高總生存率,是三級預防的重要手段之一(1B)。
1 HBV相關HCC
1.1 流行病學及危險因素
HBV感染呈世界性流行,WHO估算全球有約2.96億慢性HBV感染者;全球每年約有82萬人死于 HBV 感染相關疾病,其中HBV相關肝硬化和HCC死亡分別占52%和38%。 2018年數據[6]顯示,中國大陸由于HBV感染造成的HCC新發病例高達250 000例,占全球HBV感染造成的肝癌新發病例的69%,CHB患者HCC年齡標準化發病率(ASIR)為11.7/100 000人年,我國HCC由HBV引起的比例高達84%[3]。
CHB患者抗病毒治療可減少HCC發生。在已知CHB患者發生HCC的風險預測中,肝硬化和高病毒載量是主要的HCC發生危險因素,HCC家族史、飲酒、吸煙、糖尿病等是HCC發生的促進因素。基于患者HCC家族史、HBsAg定量和HBV DNA水平、HBeAg狀態等建立REACH-B、mPAGE-B、mREACH-B及aMAP等預測模型[7-10],可協助計算亞洲CHB患者未來進展到HCC的風險比。針對這些危險因素的防控措施中,抗病毒治療與HBV DNA、HBeAg、HBsAg等危險因素的控制直接相關。按抗HBV應答順序,CHB患者的抗病毒治療應達到以下目標:(1)HBV DNA達到檢測不到水平;(2)保持丙氨酸轉氨酶(ALT)長期在正常范圍內;(3)實現HBeAg陽性CHB患者HBeAg陰轉/血清學轉換;(4)HBsAg水平降低或消失,或HBsAg血清學轉換。達到上述指標可將HBV相關HCC的發生率降到最低水平,但仍有部分患者發生HCC,尤其是已進展至肝硬化的患者。
1.2 HBV相關HCC二級預防中的抗病毒治療
1.2.1 核苷(酸)類似物(NUCs)對HBV相關HCC的二級預防 目前抗HBV藥物中NUCs是一類作用機制明確且效果肯定的藥物,通過降低CHB患者的HBV載量可以顯著降低HBV相關HCC的發生率。在證實拉米夫定(Lamivudine,LAM)對HBV相關HCC的二級預防作用后[11],至今已有大量研究證實NUCs預防HCC的有效性。來自中國的27個研究的Meta分析[12]顯示,3165例NUCs治療的CHB患者和未行抗病毒治療的10 896例CHB患者對照,HCC的危險因素分別為:高HBV載量、HCC家族史、男性以及未進行抗病毒治療。系統性回顧總結LAM、阿德福韋酯(Adefovir dipivoxil,ADV)、恩替卡韋(Enticavir,ETV)和替比夫定(Telbivudine,L-dT)等不同種類NUCs對HCC的預防作用,其中包括1個隨機對照研究和7個隊列研究,證實NUCs的應用可以顯著減少HCC的發生[13]。 亞太肝病學會(APASL) 2017年有關肝癌管理的指南[14]指出,CHB患者長期有效的抗病毒治療可作為HBV相關HCC發生的二級預防措施。本共識中所謂一線NUCs是指現階段推薦使用的高效高耐藥屏障的NUCs,即ETV、富馬酸替諾福韋酯(Tenofovir disoproxil fumarate,TDF)、丙酚替諾福韋(Tenofovir alafenamide,TAF)和艾米替諾福韋(Tenofovir amibufenamide,TMF)[15-16]。
ENUMERATE研究[17]回顧了646例CHB患者,其中亞裔540例,肝硬化61例。經過ETV治療隨訪4年,共17例被診斷出HCC,8例來自肝硬化組(13.1%),9例來自非肝硬化CHB組(1.5%)。與REACH-B模型預測的HCC發生率相比,非肝硬化ETV治療組的HCC發生率明顯下降,隨訪4年標準化發生率(SIR)下降63%(SIR=0.37; 95%CI:0.166~0.82);包括肝硬化患者在內的所有患者的靈敏度分析顯示,在8.2年的最長隨訪時間內,HCC發病率明顯低于預測,SIR為0.56(95%CI:0.35~0.905)。634例TDF治療的HBV慢性感染者,其中152例為肝硬化。經過384周的觀察隨訪共有14例(4例在隨訪第1年)診斷為HCC,其中9例為HBeAg陰性,6例為基線肝硬化患者,12例為男性。與REACH-B模型預測的HCC發生率相比,非肝硬化TDF治療組的HCC發生率明顯下降,384周時下降60%(SIR=0.40; 95%CI:0.199~0.795)[18]。
不同品種的高效高耐藥屏障NUCs藥物在HCC預防方面是否存在差異?在一項真實世界研究[19]中,355例初治CHB患者經過4年隨訪共有17例患者診斷HCC,其中7例來自ETV組(183例),10例來自TDF組(172例),2組之間HCC發生率并無差異。另一項研究[20],582例CHB患者,ETV組406例,TDF組176例,平均隨訪57.1個月,ETV組診斷新發HCC共31例,TDF組7例,兩組之間沒有統計學差異(P=0.068)。
2019年,韓國發表的大樣本國家層面回顧性研究[21]分析了ETV和TDF在預防HCC發生的差異。研究者建立了24 156例的全國隊列及2701例的醫院隊列,結果發現隊列中TDF組HCC發病率遠低于ETV組(0.64/100人年 vs 1.06/100人年),多因素調整分析結果提示,TDF比ETV可更明顯降低HCC的發生(HR=0.61; 95%CI:0.54~0.70)。傾向性匹配(propensity score-matched,PSM)分析結論支持上述說法。同年,來自韓國4所醫科大學教學醫院的2897例初治CHB患者,分別為ETV組1484例及TDF組1413例。隨訪后共發生240例(8.3%)HCC,ETV組 1、3和5年HCC累計發生率分別為1.0%、4.8%和 9.3%,TDF組分別為1.0%、4.7%和7.7%,兩組比較并無統計學差異(P=0.516);多因素分析得出的兩組之間的調整后危險比(adjusted hazard ratio,aHR)為0.975(95%CI:0.747~1.272;P=0.852)。應用PSM和逆處理概率加權法(inverse probability of treatment weighting,ITPW)得出的HR分別為1.021(P=0.884)和0.998(P=0.988),均提示兩組之間對于HCC的預防效果沒有差別[22]。上述報道在學術界引發熱議[23-24]。肝硬化是影響HCC發生的最主要混雜因素,由于所有的研究均為回顧性研究,對CHB患者的肝硬化背景的評判標準可能存在差異,造成研究結果的偏移。近來多數研究報告[25-28]表明,ETV與TDF治療CHB降低HCC發生率無差異,Choi等[29]最近的Meta分析也支持這種觀點。
經過NUCs抗病毒治療,HBV呈現低水平復制,對HCC發生的影響近年引發關注。根據目前檢測手段的不斷進展,提出新的HBV檢測節點:維持病毒學應答組(MVR)患者HBV DNA水平持續性低于12 IU/mL;低水平病毒組(LLV)患者HBV DNA持續性或間歇性在12~2000 IU/mL波動。通過5年隨訪,LLV組HCC發生率明顯高于MVR組(P=0.016),肝硬化組差異更為明顯[30]。對CHB患者的抗病毒治療應該最好將HBV DNA降到高靈敏度檢測方法測不出更好,而非102~103IU/mL這種檢測下限。目前,HBV定量中存在一個灰色區域,即在可檢測下限(lower limit of detection,LLoD)之上同時又在可定量下限(lower limit of quantification,LLoQ)之下的無法精確定量的部分。在治療78周的患者如果HBV DNA仍可檢測到(20~200 IU/mL),肝纖維化仍呈進展趨勢(OR=4.84;95%CI:1.30~17.98;P=0.019),其中部分患者也可進展到HCC[31]。現有LLoD可達5.9 IU/mL(血清)或4.8 IU/mL(血漿),LLoQ可達10 IU/mL,近年來已經出現了靈敏度更高的檢測試劑,檢測下限更低。臨床醫師應在臨床實踐中重視HBV低水平復制,并在適當節點選擇高靈敏度檢測方法。
NUCs,尤其是目前的一線NUCs在HBV相關HCC的二級預防中發揮重要作用,有充分證據證明,應用NUCs可顯著減少HBV相關HCC的發生,如未達到功能性治愈(臨床治愈),應堅持有效的長期抗病毒治療而不要隨意停藥。
1.2.2 干擾素(IFN)對HBV相關HCC的二級預防 雖然IFN類在抑制HBV DNA復制方面無法與高效高耐藥屏障、低副作用的NUCs相比,但其在防治HBV相關HCC方面仍具有獨特的作用。近年來有證據表明,IFN類尤其是聚乙二醇IFN(PEG-IFN)可以較NUCs更好的預防HBV相關HCC的發生。
中國臺灣地區回顧性隊列研究[32]顯示,330例治療前接受肝活檢的CHB患者,分別接受PEG-IFN或NUCs治療,以是否發生HCC為研究終點。抗病毒過程中盡量維持血清HBV DNA低于2000 IU/mL;每3個月檢查1次HBV DNA 水平,若發生病毒學突破,則進行序列分析,加用或換用其他有效藥物進行挽救治療。根據年齡匹配的PEG-IFN組和NUCs組各120例,PEG-IFN組HCC發生率低于NUCs組(P=0.031),而且HBV相關肝硬化患者應用PEG-IFN的預防效果更好;在這個基礎上,又匹配PEG-IFN組和ETV組各52例,PEG-IFN組HCC發生率明顯低于ETV組(P=0.022)。在該研究中,雖然樣本量、對比的NUCs種類都存在一定爭議,但該研究顯示了應用PEG-IFN可以更好地預防HCC的發生。另有回顧性研究[33]納入1112例CHB患者,IFN組430例,NUCs組682例,應用PSM方式予以配對。結果顯示IFN組和NUCs組10年HCC累計發生率分別為2.7%和8.0%(P<0.001);以IFN為基礎的治療較NUCs組HCC的發生率更低(HR=0.15;95%CI:0.04~0.66;P=0.012)。在對HBeAg陽性CHB患者的前瞻性隊列觀察[34]也證明了這種趨勢的存在,研究共納入444例患者,215例為PEG-IFN組,229例為ETV組,經過PSM配對,2組各119例。結果顯示,應用PEG-IFN的CHB患者HCC發生率低于ETV組,盡管無統計學差異(P=0.36),但明顯低于REACH-B模型推算出的HCC發生率(P=0.038)。
近年來,回顧性研究和Meta分析提出IFN類,尤其是PEG-IFN可以較NUCs更好地減少HBV相關HCC的發生,但由于應用PEG-IFN的研究病例數遠少于NUCs類,該結論需進一步前瞻性研究證實。目前對于PEG-IFN聯合NUCs的抗病毒治療,因經濟效益比不顯著(除基因型A外),未被主流學會指南推薦。但從HBV相關HCC二級預防角度,一線NUCs降低HBV DNA水平,PEG-IFN降低HBsAg水平,兩者聯合或序貫治療在二級預防方面具有較好的經濟效益比,未來尚需進一步前瞻性隊列研究驗證。
1.2.3 抗病毒治療在HBV相關HCC的二級預防的時效因素
抗病毒治療在HBV相關HCC的二級預防方面獲得了一定的證據支持,但也有研究[35]質疑抗病毒治療預防作用的有效性。因此,在臨床實踐中需要有具體可操作指標評估抗病毒治療對HCC預防的有效性。指標可分為2個部分:預防HBV相關HCC有效的指標和達成這些指標所需的理想時間。
經過抗病毒治療所要達到的預防HBV相關HCC有效指標可分為2類人群:一是經過治療達到HBsAg消失或功能性治愈(臨床治愈)的少數CHB患者,二是大部分經過治療后至少獲得HBV DNA持續在常規檢測下限以下的患者。完成IFN療程的CHB患者4年后有8%達成HBsAg消失(基因型A型居多);而以ETV或TDF治療5年的HBsAg消失率很低[36]。如果CHB患者獲得HBsAg清除,HBV相關HCC的發生率更低[37],但仍有一定的HCC發生率,而并非完全消除HCC風險。在獲得HBsAg消失的CHB患者群中,HCC年發生率仍可達0.55%,其中大于50歲或合并肝硬化患者風險更高[38]。對于未獲得HBsAg消失的CHB患者,具體指標以HBV DNA小于LLoD[30]、HBsAg小于1000 IU/mL[39]和ALT低于正常值上限(ULN)[40]作為較為滿意的替代指標,長期穩定達到這種程度者HBV相關HCC的發生率較低。由于國內無法出具低于LLoD的報告,也可考慮以高靈敏度的LLoQ為備選指標,以HBV DNA持續小于10~20 IU/mL而不是小于500 IU/mL為預防HCC發生的重要指標之一。近期有研究[41-42]提出HBV RNA水平可以作為肝內炎癥、纖維化程度的指標,其可能對HCC的發生發展起作用,尚需要進一步研究。
上述主要指標達成需要一定的時效性,原則上是越早越好。從絕對年齡層面,小于50歲患者更易發生HBsAg清除;在CHB自然史中,相較于肝硬化形成后,HBsAg清除更易發生于慢性肝炎階段[38]。抗病毒治療有效時間的差異對HBV相關HCC的預防作用也將產生影響[40]。以ALT復常為指標,在NUCs治療6個月內即獲得ALT復常的CHB患者,HCC發生率顯著低于6~12個月、12~24個月、24個月以上的復常組,aHR分別為1.40、1.74和2.45(P<0.001),并且是獨立于肝硬化的危險因素。因此,在NUCs治療的初期12個月ALT復常是減少HCC發生的重要指標[40]。
近年來,前述回顧性研究和極少數前瞻性研究以HCC發生為終點,揭示了PEG-IFN和NUCs的應用能夠起到HBV相關HCC的二級預防作用,但證據等級仍有待于提高。在臨床實踐中,在高覆蓋的NUCs治療中合理選擇患者規范聯合應用PEG-IFN是目前在探索的方案。通過聯合應用抗病毒藥物,結合更為嚴格的監測指標,強調達成替代指標的時效性,必要時及時調整治療方案,努力使更多的CHB患者切實達到HCC二級預防的目的。
推薦意見2:對CHB患者予以積極有效的抗病毒治療是防范HBV相關HCC發生的重要二級預防措施(1A)。對于CHB患者的抗病毒治療,建議選擇一線NUCs或PEG-IFN治療(1A),并根據患者對藥物的應答情況及時調整治療方案。
推薦意見3:對正在進行抗病毒治療的CHB患者,評估HBV相關HCC二級預防效果的替代指標為:HBV DNA小于高靈敏度檢測方法的下限,HBsAg陰轉以及ALT長期在ULN以下(2B)。
推薦意見4:對于具有HCC高風險的CHB患者,以一線NUCs為基礎進行抗病毒治療,無PEG-IFN應用禁忌證可考慮PEG-IFN聯合NUCs治療(2A)。對于正在使用NUCs治療的患者,如未能達到相關指標(HBV相關肝硬化患者在24周內或非肝硬化CHB患者在48周內實現推薦意見3)可考慮換用或合用其他一線抗HBV藥物,密切隨訪,必要時進一步調整優化治療方案;對于有功能性治愈前景的CHB患者可選擇聯合PEG-IFN治療(2A),以增強抗病毒效果,最大程度減少HBV相關HCC的發生。
推薦意見5:對于CHB患者的抗病毒治療,其主要目標是應盡可能利用目前藥物和治療方案爭取達到HBsAg清除,即功能性治愈,進一步降低HCC發生率(1A)。對于通過抗病毒治療達到HBsAg消失的肝硬化患者(臨床治愈),仍需定期隨訪監測HCC的發生(1B)。
1.3 HBV相關HCC三級預防中的抗病毒治療
HBV相關HCC的三級預防是指應用綜合措施防止HCC復發并延長總體生存期而采取的措施,包括對癥治療和康復治療。HCC復發分為早期(術后2年內)或晚期復發(術后2年后)。早期復發多由原發灶轉移所致,侵襲性腫瘤的血管浸潤導致肝內復發或肝癌切除術中腫瘤轉移。晚期復發多因肝硬化基礎上新發腫瘤所致。
HCC復發的主要宿主因素為:年齡大于40歲、男性、酗酒、基線高甲胎蛋白(AFP)水平、低血小板計數、低白蛋白水平、肝硬化高Child-Pugh評分、初始腫瘤直徑大等[14,43]。HBV相關HCC復發的主要病毒學因素為:血清高病毒載量和HBeAg陽性。術前基線血清HBV DNA高載量(>2000 IU/mL,OR=22.3)是HCC術后復發的重要危險因素[44]。HBV相關HCC主要死亡原因除腫瘤因素外,還與慢性肝功能衰竭、消化道出血、肝性腦病等肝病終末期事件相關,而這些肝病終末期事件與HBV復制有關。因此,對于HBV相關HCC患者應用抗病毒治療不僅有助于降低HCC治療后復發率,而且有助于保護肝功能,保障其他綜合治療效果,提高患者的總體生存率。
NUCs的應用可能減少HCC復發;IFN類應用并不降低無復發生存率,但可能增加患者總體生存率;對于可以切除病灶的HBV相關HCC患者,以IFN類為基礎的抗病毒治療可以減少HCC復發率且提高生存率。HBV相關HCC患者,若HBsAg陽性,建議應用ETV、TDF、 TAF或TMF進行抗病毒治療。因此,應重視HBV相關HCC患者綜合管理中抗病毒藥物的合理應用。
1.3.1 NUCs在HBV相關HCC三級預防中的作用 HBV DNA水平是HCC復發的重要危險因素,應用NUCs抗病毒藥物是直接且安全性良好的重要基礎治療。在HCC手術切除、射頻消融(radiofrequency ablation,RFA)、肝移植、經肝動脈化療栓塞術(transarterial chemoembolization,TACE)、放射治療、分子靶向治療、免疫治療以及FOLFOX4方案系統化療等進行前后均需要給予抗病毒治療。
HBV相關HCC患者接受根治性治療后予以抗病毒治療可以減少HCC復發。Meta分析表明,對可切除HBV相關HCC患者給予抗病毒治療,NUCs可減少HCC術后復發并改善預后。來自15項研究的8060例患者,NUCs對1年和3年復發有保護性作用,1年復發和3年復發的相對危險度(relative risk,RR)分別為 0.41(95%CI:0.28 ~ 0.61;P<0.000 01)和0.63(95%CI:0.43 ~0.94;P=0.001),5年的總生存期(overall survival,OS)和無疾病生存期(disease free survival,DFS)均明顯增高[45]。另一項Meta分析包括9009例患者,其中2546例給予抗病毒治療,6463例未給予抗病毒治療,抗病毒治療可顯著提高OS (HR=0.58;95%CI:0.51~0.67;P<0.001)和無復發生存期(recurrence-free survival,RFS)(HR=0.68;95%CI:0.63~0.74;P<0.001);在抗病毒組的亞組分析顯示,基線高病毒載量組(>20 000 IU/mL)抗病毒治療可顯著延長OS(HR=0.69;95%CI:052~0.92;P=0.01)和RFS(HR=0.58;95%CI:0.49~0.70;P<0.001),獲益度更大[46];在基線低病毒載量組(<20 000 IU/mL)抗病毒治療對OS和RFS無顯著延長。中國大陸地區202例HBV DNA高載量HCC中期患者,手術后分為抗病毒組(LAM)和未抗病毒組。抗病毒組3年和5年OS高于未抗病毒組(P=0.019);抗病毒組1、3、5年RFS高于未抗病毒組(P=0.002);抗病毒組的HCC復發率明顯低于未抗病毒組(P<0.01);術后抗病毒可減少HCC復發(HR=0.882; 95%CI:0.712~0.938;P=0.042)[47]。一項早期單中心前瞻性研究[48]證實了抗病毒治療對HCC復發的影響。研究納入根治術后200例患者,分為2組,一組給予ADV抗病毒治療,另一組不予抗病毒治療。隨訪發現兩組之間1、3、5年的RFS和OS有顯著差別(P=0.026和P=0.001)。進一步研究[49]納入根治術前HBV DNA<2000 IU/mL的HCC患者200例,一組給予L-dT抗病毒治療,一組不予預防性抗病毒治療,隨訪60個月發現兩組之間1、3、5年的RFS和OS均有顯著差別(P=0.016和P=0.004)。雖然這兩個研究應用的NUCs并非目前推薦的一線藥物,但屬于三級預防中少有的前瞻性研究,為抗病毒治療在HCC三級預防的作用提供了強有力的臨床證據。
目前有證據表明,一線NUCs藥物對于HBV相關HCC的三級預防作用更強。607例根治性治療的HBV相關HCC患者,其中261例為未抗病毒組,90例為非一線藥物抗病毒組,256例為一線藥物抗病毒組(ETV或TDF)。發現三組的RFS分別為29.4、25.1和88.2個月,一線藥物抗病毒組獲益度最高(P<0.001, log-rank test)[50]。233例肝硬化背景手術切除的HBV相關HCC患者,107例采用TDF,126例采用ETV治療,TDF組的DFS明顯長于ETV組(P<0.05),多因素研究發現,TDF是降低HCC發生的主要因素(HR=0.35; 95%CI:0.33~0.84)[51],TDF較ETV更好地減少HCC復發。1695例BCLC分級0或A級HBV相關HCC患者,根治術后分別采用ETV(n=813)或TDF(n=882),經過PSM配對后進行多因素分析。結果表明,TDF組較ETV組有更低的HCC復發率(HR=0.82; 95%CI:0.68~0.98;P=0.03)和病死/肝移植率(HR=0.62; 95%CI:0.44~0.88;P=0.01),TDF是HBV相關HCC早期(HR=0.79;P=0.03)或晚期(HR=0.68;P=0.03)復發的獨立保護因素[52]。也有研究[53]認為,ETV組和TDF組對于改善HBV相關HCC根治性治療后預后的療效無統計學差異。替諾福韋(TFV)類藥物是否較ETV更顯著降低HBV相關HCC術后復發率尚需更多的大樣本臨床研究進一步證實。
TACE是HCC常用的非手術治療方法。TACE治療可引起HBV再激活的原因主要有[54-55]:(1)化療藥物直接激活HBV DNA復制;(2)化療藥物和栓塞對肝臟局部微環境和免疫產生影響;(3)化療藥物通過血液循環或動-靜脈分流到達體循環。HBeAg陽性、高HBV DNA載量以及多次TACE治療是HBV相關HCC患者HBV再激活的獨立危險因素[56-57]。109例HBV DNA<2000 IU/mL的HBV相關HCC患者,23例(21.1%)TACE術后出現HBV再激活,其中HBeAg陽性患者再激活率為55.6%,HBeAg陰性患者為18%(P=0.019)[56]。研究認為,對于可檢出HBV DNA且HBeAg陽性的患者,TACE治療可引起HBV再激活,需要提前/及時抗病毒治療。98例基線HBV DNA<2 IU/mL的HBV相關HCC患者前瞻性對照研究發現,ETV抗病毒組(51例)HBV再激活率為5.9%,明顯低于未抗病毒組(47例)的23.4%(P<0.05)。與HBV無激活組相比,HBV再激活組TACE治療后5 d ALT、總膽紅素水平明顯升高(P<0.05)。多因素分析顯示,HBeAg陽性、腫瘤數目超過3個、未抗病毒治療是HBV再激活的關鍵因素[57]。因此,對于HBV相關HCC,即便基線HBV DNA低于檢測下限,仍需積極進行抗病毒治療。
接受TACE治療的HBV相關HCC患者,無論病毒載量如何,只要HBsAg可測出,都應給予積極抗病毒治療,同時需綜合考慮患者肝功能狀況和肝硬化程度。對肝功能Child-Pugh A級、肝硬化程度較輕的患者,可在TACE治療的同時進行抗病毒治療;對肝功能Child-Pugh B級、肝硬化程度較重的患者,建議給予改善肝功能、抗病毒治療1~2周再行TACE治療。抗病毒治療首選一線NUCs,原則上終身服藥,切忌隨意停藥、換藥。需加強HBV相關HCC患者TACE治療后抗病毒治療管理,及時發現HBV再激活,以保護患者肝功能,減少經化療栓塞治療后的肝硬化失代償事件發生率,減少HCC復發及多源性生長的風險,最終提高患者的總體生存率。
肝移植是HBV相關HCC的根治性治療手段。一項Meta分析評估了基于給予NUCs方案的肝移植受者的臨床結局,并探討了不同的預防方案,共納入25項研究(n=2327),HBV復發率為1.01%(95%CI:0.53%~1.59%);HBV病毒血癥或丁型肝炎病毒重疊感染對HBV復發無顯著影響(P=0.23及0.71)。一線NUCs與乙型肝炎免疫球蛋白(HBIG)無限期聯合治療的復發率低于一線NUCs單藥治療(P<0.001),與一線NUCs聯合有限療程HBIG的復發率相似(P=0.48)。研究認為,有效的NUCs抗病毒治療提供了令人滿意的對HBV抗病毒預防作用,并改善了肝移植受者的長期預后;一線NUCs與HBIG的有限組合是終身雙重治療的替代方案[58-59]。同時,如移植后出現CHB復發,應密切監測HCC復發[60]。
1.3.2 IFN在HBV相關HCC三級預防中的作用 IFNα是較強的免疫調節劑,既具有抗病毒作用,又具有抗腫瘤作用[56,61],因而被推薦用于HCC的綜合治療手段之一[4-5]。
Meta分析[62]證實IFN在HCC系統性治療中的意義,但并非所有HBV相關HCC患者均可通過應用IFN類而獲益,只有HCC確診時,病灶小于3 cm者可經過附加的IFN類治療減少HCC復發率(RR=0.50;95%CI:0.35~0.72;P<0.001)。系統性回顧分析[63]結果則認為,IFN類聯合TACE使得患者明顯獲益,但手術切除后應用IFN類并未明顯減少復發率和病死率。228例HBV相關HCC患者經手術切除病灶后,再序貫采用TACE(126例)或TACE聯合IFN(102例)[64],結果表明聯合組較單用TACE組OS明顯延長(36.3個月 vs 24.5個月,P<0.05);聯合組3年和5年的復發率亦顯著低于單用TACE組(P<0.05)。Meta分析[65]對HBV/HCV相關HCC患者輔助應用PEG-IFN的效果進行總結分析發現,PEG-IFN明顯提高3年和5年RFS,3年、5年HR分別為0.80(95%CI:0.64~0.99;P=0.04)和0.82(95%CI:0.67~0.99;P=0.04);對于經過根治性手術治療的患者,應用PEG-IFN者5年OS明顯長于未應用PEG-IFN者(HR=0.67;95%CI:0.47~0.97;P=0.03)。前瞻性隨機對照研究[66]探討了PEG-IFN聯合ETV對RFS和OS的影響,結果表明,手術切除/RFA術后即應用PEG-IFN聯合ETV較1年后聯合治療或單用NUCs有更好的療效,2年和8年的RFS更長,8年的OS更高(P值均<0.05);術后早期聯合治療組如在48周時HBsAg下降大于1500 IU/mL則具有更低的復發率和病死率。
多項回顧性研究、Meta分析和少數前瞻性研究認為,HBV相關HCC患者綜合治療時輔助應用IFN類可提高患者的生存率,減少HCC早期和晚期的復發,提高患者的OS,但PEG-IFN只能應用于代償期HBV相關HCC患者,需要掌握好適應證,并積極應對不良反應。將PEG-IFN與高效高耐藥屏障NUCs合理聯用,有助于提高OS或降低復發,尚需進一步積累前瞻性隊列研究證據積累。
推薦意見6:HBV相關HCC患者只要HBsAg陽性,無論HBV DNA是否可檢測出,均應立即給予一線NUCs抗病毒治療(1A)。無PEG-IFN應用禁忌證的患者,術后可應用PEG-IFN聯合NUCs治療(2A),聯合治療可提升OS。
推薦意見7:對肝功能Child-Pugh A級、肝硬化程度較輕的患者,進行TACE治療的同時應積極抗病毒治療(1A)。對肝功能Child-Pugh B級、肝硬化程度較重的患者,應根據患者肝功能狀態、腫瘤負荷程度給予改善肝功能、抗病毒治療1~2周再行TACE治療(2A)。對于手術、放療、系統性化療、靶向治療的HBV相關性HCC患者,參照本推薦意見執行。
推薦意見8:TACE治療前基線期HBsAg陰性但抗-HBc陽性HCC患者,不建議進行預防性抗病毒治療(2A)。發生HBV再激活應立即給予抗病毒治療。對HBsAg陰性但抗-HBc陽性且接受較大強度TACE的HBV再激活高危的患者,必須嚴密隨訪監測,以盡早發現HBV再激活并進行抗病毒治療(1A)。
推薦意見9:對于HBV相關HCC采用肝移植治療的患者,建議在肝移植前盡早開始應用一線NUCs進行抗病毒治療(1A)。
2 HCV相關HCC
HCV感染在HCC發生發展中起重要作用,慢性HCV感染將增加患者罹患HCC的風險。近年來,抗HCV治療已進入直接抗病毒藥物(direct antiviral agent,DAAs)時代,無IFN的泛基因型方案目前被認為是HCV抗病毒治療首選[67]。由此,必然帶來HCV相關HCC預防、診治及臨床管理策略的變遷和更新[68]。隨著DAAs在我國陸續進入醫保,藥物可及性顯著增加;隨之,相關臨床實踐中的重要問題亟待解決,這不但影響醫生與患者治療策略抉擇,也關系到疾病的轉歸與預后。自DAAs上市以來,其與HCC發生、發展以及轉歸預后之間的爭論引人關注。隨著臨床及基礎研究推進,數據質量的提高,本共識就此進行了更新,旨在提高臨床醫生對DAAs在HCC患者中應用的認識,帶動HCV相關臨床實踐進步。
2.1 流行病學及危險因素 據WHO統計,2019年全球約有5800萬HCV感染者,約29萬人死于HCV相關疾病,主要為肝硬化和HCC。全球HCV的流行存在地域性差異,流行率為0.5%~2.3%[69]。用2006年的血清進行調查發現,我國HCV抗體陽性率為0.43%[70]。2015年進行的一項基于模型的研究發現,我國約有980萬慢性HCV感染者,感染人數居全球首位[71]。
HCV感染是HCC發生、發展和復發的主要危險因素之一,2018年數據分析顯示,21%HCC新發病例及死亡病例歸因于HCV感染[6,72-73]。HCV感染者發生HCC的相對風險為未感染者的15~20倍[74-78]。HCV相關HCC多發生在肝硬化基礎上,非硬化患者(硬化前階段)HCC年發生率為0.68%[79],而在HCV相關肝硬化患者中,HCC平均年發病率為1%~4%,亞太地區可達7%[80]。
HCV感染者發生HCC的危險因素包括與人類免疫缺陷病毒(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HIV) 或HBV合并感染、HCV基因1b型、高病毒載量、男性、高齡、糖尿病、肥胖、長期飲酒、吸煙、黃曲霉毒素B1暴露史等[75,81-85]。
2.2 HCV相關HCC二級預防中的抗病毒治療
2.2.1 IFN抗病毒治療對HCV相關HCC的影響 在DAAs上市之前的IFN時代,PEG-IFNα聯合利巴韋林方案(PEG-IFNα+RBV,PR)是全球HCV感染者抗病毒治療的首選方案[67],其中RBV不僅可以顯著改善患者對PEG-IFN的應答,還可預防HCV復發[86-89]。PR方案的持續病毒學應答(sustained virological response,SVR)率在我國丙型肝炎患者中為53%~88%[90-100],可降低HCV相關肝炎和肝硬化患者HCC的發生率[101-105]。
在疾病的不同階段,在以IFN為基礎的治療方案中,與未實現SVR的患者相比,實現SVR后能夠降低70%~79%的HCC發生率[106-108]。另外,高齡、合并糖尿病以及飲酒、肥胖等因素都是IFN抗病毒治療過程中發生HCC的風險因素[107,109]。
丙型肝炎具有較易慢性化且癥狀不典型等特點,眾多患者初診HCV感染時即已處于肝硬化階段,限制了IFN的應用。另外,IFN存在不良反應多、成本高、療效欠佳、用藥不便等問題。隨著各種DAAs的上市,其優越的抗病毒療效,較低的不良反應,我國醫保政策帶動下不斷增加的藥物可及性等,徹底改變了HCV抗病毒治療策略,IFN已不再作為HCV感染的一線治療。
推薦意見10:建議選用DAAs作為治療HCV感染的一線藥物,不再建議應用含有IFN的治療方案(1A)。
2.2.2 DAAs治療對HCV相關HCC的影響
2.2.2.1 DAAs治療對HCV相關HCC發生率的影響 DAAs治療可有效清除HCV,獲得SVR,但DAAs對HCV相關HCC的影響早期爭議較大。有研究[110]認為,DAAs治療可能有潛在提高HCC發生率的風險。但后續大規模系統綜述[111]顯示,與未接受抗病毒治療的人群[3.080/100人年(95%CI: 1.535~5.158)]相比,DAAs治療可明顯降低HCC的發病風險[1.269/100人年(95%CI:1.124~1.424)](P<0.001)。
患者接受DAAs治療或IFN治療后,進展為HCC的風險是相似的。一項Meta分析[112]顯示,在IFN治療組,HCC發生率為1.14/100人年(95%CI:0.86~1.52),DAAs組為2.96/100人年 (95%CI:1.76~4.96)。但在DAAs治療組中,肝硬化和門靜脈高壓患者的比例高于IFN治療組,對患者人群差異進行調整后,兩組間未見顯著差異。
為進一步明確不同DAAs治療方案對HCC發生風險的影響,對33 137例接受不同DAAs治療方案的患者分析后發現,帕利瑞韋(paritaprevir)/利托那韋(ritonavir)/奧比他韋(ombitasvir)/達塞布韋(dasabuvir)(ProD)方案、索磷布韋(sofosbuvir)單藥、索磷布韋/西咪匹韋(simeprevir)以及雷迪帕韋(ledipasvir)/索磷布韋治療組,其HCC發生率分別為0.95%(82/6289)、1.91% (143/4356)、2.47%(168/3210) 和1.26%(348/19282),經基線校正后顯示,不同DAAs方案治療后HCC發生率無明顯差異[113]。常用DAAs種類及用法詳見附錄1[67,114]。
2.2.2.2 DAAs治療后發生HCC的危險因素
2.2.2.2.1 DAAs治療是否獲得SVR對HCC發生風險的影響
DAAs能夠使大多數HCV感染者實現病毒清除,獲得SVR,但仍有少部分患者(1%~15%)達不到這一目標。治療失敗通常與治療后復發、治療中病毒學突破及HCV產生耐藥相關,DAAs治療后是否獲得SVR對HCC的發生有顯著影響[115]。Meta分析[116]顯示,在獲得SVR和未獲得SVR人群中,HCC發生率分別為2.1/100人年(95%CI:1.4~3.4)和9.1/100人年(95%CI:5.4~15.3);與非應答者相比,DAAs治療獲得SVR后可使HCC發生風險下降78%(P<0.01)。SVR可使非肝硬化患者發生HCC的風險降低70%~80%,還可使不同階段的肝硬化患者發生HCC的風險降低50%~78%[117]。
2.2.2.2.2 肝硬化對DAAs治療后HCC發生率的影響 不同階段HCV相關肝硬化人群中,Child-Pugh A級治療后獲得SVR者HCC發生率為41/1952(2.1%),未獲得SVR者為5/83(6.6%);Child-Pugh B級治療后獲得SVR者,HCC發生率為15/189(7.8%),未獲得SVR者為3/25(12.4%)[118]。一項納入62 354例患者的研究[119]顯示,治療失敗的肝硬化人群中,HCC發生率最高(3.25/100人年);在獲得SVR的肝硬化人群、治療失敗的非肝硬化人群及獲得SVR的非肝硬化人群中,HCC的發生率分別為1.97/100人年、0.87/100人年和0.24/100人年。多項大規模研究[119-120]顯示,經DAAs治療后,HCV相關肝硬化人群獲得SVR的概率為93%~95.2%,發生HCC的概率為3.8%~6.0%。
2.2.2.2.3 影響DAAs治療后HCC發生風險的其他因素 既往無HCC病史的慢性HCV感染者,經治療獲得SVR后的HCC發生率為1.3%(0.9%~7.4%);既往有HCC病史的患者經DAAs治療獲得SVR后,其HCC復發率仍高達29.6%(17.1%~71.6%)[121-127]。既往有HCC病史者,在DAAs治療期間和治療結束后,均應警惕HCC復發。
其他DAAs治療后發生HCC的因素還與性別、年齡、飲酒以及糖尿病等有關,其中男性、高齡、長期飲酒者及糖尿病患者發生HCC的危險相對較高[118,122,128]。
2.2.2.3 DAAs治療后仍需監測HCC的發生 DAAs治療獲得SVR的患者,在治療結束后仍有進展為HCC的風險。已獲得SVR的肝硬化患者每年發生HCC的概率為1.39%[70]。現有證據[71]表明,對DAAs治療后的患者進行HCC監測有利于降低病死率。凡具有HCC高危風險因素的慢性HCV感染者,無論DAAs治療后是否獲得SVR,均建議至少每隔3~6個月檢查一次肝臟超聲和血清AFP等腫瘤標志物。
推薦意見11:DAAs治療后獲得SVR可顯著降低HCV相關HCC的發生風險。對既往有肝硬化或有HCC病史的慢性HCV感染者,無論是否獲得SVR,均應進行HCC監測,推薦肝臟超聲聯合血清AFP檢查,至少每隔3~6個月1次(1A)。
2.3 HCV與HIV或HBV合并感染
2.3.1 HCV-HIV合并感染 全球范圍內,約有230萬HCV-HIV共感染者,在HIV感染者中,HCV合并感染的全球流行率為6.2%[129],我國Meta分析的流行率為24.7%(95%CI:19.3~30.5)[130]。HCV-HIV合并感染被認為是 HCV相關肝病(如肝纖維化或終末期肝病)進展的危險因素[67,131-132],即使應用抗逆轉錄病毒治療(antiretroviral treatment,ART)實現HIV病毒學抑制后,患者死亡風險仍較高[133]。相比于HCV單獨感染,關于HCV-HIV共感染對HCC發生風險的影響尚存爭議[134-140]。自2014年以來,HCV-HIV合并感染者被WHO列為優先治療人群[134]。與HCV單一感染相比,HCV-HIV合并感染人群的DAAs治療方案相同且應答率相似[67,141-144]。
2.3.2 HCV-HBV合并感染 約1%~15%的HCV感染者伴隨HBV感染[145-146],亞洲國家更為常見[122]。2016年,全國多中心調查顯示,我國HCV感染者中HBsAg陽性率為4.11%[147]。HCV與HBV兩種嗜肝病毒的合并感染更易導致肝硬化、肝臟失代償或HCC[148-151],對HCC發生風險具有疊加效應[150]。HCV-HBV合并感染時,HCV通常占主導地位,HBV DNA多處于低復制水平或低于檢測值[67,142,145]。DAAs有效抑制HCV后,HBV再激活現象已成為重要臨床事件[122,152]。對即將接受DAAs治療的患者應開展有關HBV感染證據的篩查,明確是否存在HBsAg陽性或單純抗-HBc陽性[153]的HBV感染,并在DAAs治療期間進行管理。考慮到HBsAg陽性患者的安全性,建議在DAAs治療之前對HBV進行預防性治療,直到DAAs治療結束后3個月[67,134,142,154]。對于單純抗-HBc陽性的HBV感染者,盡管HBV再激活的可能性較低[155],在DAAs治療期間仍需監測ALT、HBsAg及HBV DNA水平,必要時開始抗HBV治療[122,156-157]。HCV-HBV合并感染者與HCV單一感染者的DAAs治療方案相同[67,142,154],少數研究提示其SVR率未受影響[156,158]。
推薦意見12:所有擬接受DAAs治療的HCV感染者,需在治療前篩查是否存在HBV感染,并根據病史決定是否需要篩查HIV(1A)。
推薦意見13:HCV-HIV或HCV-HBV合并感染者,DAAs治療方案與HCV單一感染相同且療效相當,具體藥物詳見附錄1。對于同時符合HBV抗病毒治療標準的患者,可給予相應的HBV抗病毒治療,可選擇ETV、TDF、TAF或TMF等一線治療藥物(1A)。
推薦意見14:如HBsAg陽性但HBV DNA檢測不出,建議在DAAs治療開始前對HBV進行預防性治療,至少持續到DAAs治療結束3個月后。對于單項抗-HBc陽性而HBV DNA陰性的HCV感染者,需監測氨基ALT、HBsAg及HBV DNA水平,必要時應及時啟動抗HBV治療(1B)。
2.4 HCV相關HCC三級預防中的抗病毒治療
由于大多數臨床試驗未納入HCC患者,有關DAAs治療HCV相關HCC獲得SVR以及HCC復發風險的數據主要來自回顧性隊列和真實世界研究。多數研究表明,與未發生HCC或已發生HCC后但接受了肝移植的HCV感染者相比,現患HCC的HCV感染者應用DAAs治療后的SVR率相對較低[159-161]。在接受不含IFN的索磷布韋方案治療后,總SVR12高達93%,而HCC患者的SVR12僅為82%[162]。在一項納入421例HCV相關肝硬化患者的研究[163]中,33%病例具有活動性HCC或HCC病史。DAAs治療后,不合并HCC的肝硬化患者SVR為88%,而合并HCC為79%,兩組數據存在統計學差異。在未獲得SVR的HCC患者中,93%存在活動性腫瘤。多變量分析顯示,活動性腫瘤是DAAs治療失敗的危險因素。HCC緩解后,DAAs療效類似于不伴HCC患者[164]。
對于發現時即為HCV相關HCC的患者,HCC根治性治療(包括外科手術、局部消融、肝移植及立體放療等)后再行DAAs治療,可提高SVR,同時,HCC復發風險降低,總體生存率提高[165]。Meta分析[166]顯示,與未行抗病毒治療相比,接受DAAs治療能夠降低60%的HCC復發風險(OR=0.4;95%CI:0.26~0.61)。對來自美國及亞洲多中心的1676例HCV相關HCC患者進行回顧性分析,其中1239例患者未接受抗病毒治療,437例患者接受DAAs治療后獲得SVR;結果表明,接受 DAAs治療獲得SVR患者,5年生存率顯著提高(87.78% vs 66.05%,P<0.001);獲得SVR可降低63% 5年全因病死率及66%肝臟相關病死率[167],接受DAAs治療能夠使HCV相關HCC患者獲益。
2.4.1 接受HCC根治性治療的HCV相關HCC患者的抗病毒治療
2.4.1.1 DAAs對接受手術切除及消融治療的HCV相關HCC患者肝癌復發的影響 雖然IFN可降低HCV相關HCC行外科手術切除后的復發率和病死率[168-170],但由于副作用等原因,HCC患者行外科手術后接受IFN治療的比例不足10%(213/2237)[171],DAAs的出現為這類人群的治療提供了新方法。然而,早期3項研究[123,172-173]發現,經過DAAs治療后有相當高比例的患者出現HCC復發,引發廣泛關注及爭議。肝內HCC復發一般分為早期(1~2年以內)復發和非早期(2年以上)復發。早期復發通常是原發癌的微觀轉移或先前治療過的癌灶局部復發。非早期復發歸因于潛在肝硬化導致的多中心致癌過程[174]。有研究[175]認為,HCV的清除可以改善肝功能并延長HCC患者的生存時間,雖然也可以降低HCC的復發率,但降低的比例并不樂觀。其可能原因為DAAs無法抑制已經形成的癌前病變發展為惡性腫瘤,因此無法降低HCC的早期復發率。在DAAs治療的起始時期已經有潛在的HCC發生,造成DAAs治療后HCC的早期復發率較高這一假象[123,176]。
越來越多的研究證實,DAAs不會加速HCC外科切除術后的復發甚至可以降低HCC復發率。歐洲一項納入47例患者平均隨訪時間為21.5個月的研究[177]表明,DAAs治療可以降低HCC復發風險(HR=0.894;95%CI:0.827~0.965;P=0.004)。一項回顧性隊列研究[178]顯示,外科切除術后接受DAAs治療的患者和未經治療的患者HCC復發的中位時間分別為17.4個月和10.1個月,同時兩組間HCC復發率存在顯著差異(73.3% vs 47.8%)。與未治療相比,DAAs治療組和IFN治療組5年累計HCC復發率基本一致,分別為54.2%和45.1%(P=0.54)[121]。
局部消融是HCC根治性治療常用的方法。迄今,只有一項回顧性研究單獨納入接受消融治療后給予DAA治療的HCV相關HCC患者。該研究共納入926例接受RFA治療后的HCV相關HCC患者,分為DAAs治療組(27例)、IFN治療組(38例)及不行抗病毒治療組(861例),這三組的1年和2年的HCC累計復發率分別為21.1% vs 26.3% vs 30.5%和29.8% vs 52.9% vs 61.0%[179]。該研究提示,RFA治療后,DAA治療的復發風險不高于IFN組和未行抗病毒治療組。
來自北美的一項793例HCV相關HCC患者回顧性隊列研究[180]納入107例RFA治療后接受DAAs治療的患者,157例RFA治療后未接受抗病毒治療。結果顯示,DAAs治療與HCC復發(HR=0.92;95%CI:0.59~1.44)或早期HCC復發(HR=0.99;95%CI:0.54~1.81)無關,且還可以顯著降低死亡風險。對177例經包括RFA(81例)治療后HCV相關HCC患者進行分析表明,接受DAA治療的HCV相關HCC患者HCC復發率顯著降低(HR=0.353;95%CI:0.191~0.651)[125]。
DAAs治療可降低HCC根治性治療后的死亡風險,提高總體生存率。包括31個國家的多中心隊列研究證實,DAAs治療可降低HCC患者全因死亡率。其中接受DAAs治療的患者941人年(接受RFA 138例)中,死亡43例;未接受DAAs治療的患者526.6人年(接受RFA治療130例)中,死亡103例(粗率比0.23;95%CI:0.16~0.33)。在逆概率加權分析中,DAAs治療與死亡風險顯著降低相關(HR=0.54;95%CI:0.33~0.90)[165]。
2.4.1.2 手術切除及局部消融治療的HCV相關HCC患者接受DAAs治療的時機 美國胃腸病學會建議HCC行肝切除或消融治療后完全緩解的患者需接受DAAs治療,治療時間可在術后4~6個月后。延遲DAAs治療可以延長現有微小HCC克隆的免疫監視時間,還可以創造更長的時間以驗證HCC是否完全緩解,從而最大限度地減少錯誤分類的機會[117]。一項納入1820例HCV相關HCC患者(接受局部消融515例)的Meta分析[181]提示,至少在腫瘤完全緩解后6個月開始DAAs治療。德國肝癌聯盟也建議,HCV相關HCC患者接受根治性治療后最早術后6個月接受DAAs治療[182]。目前,僅有一項研究單獨探討接受RFA的HCV相關性HCC患者DAAs治療時機,研究發現,HCC行RFA治療與接受DAAs治療的間隔時間是抗病毒治療后HCC復發的唯一預測因子(OR=0.3;95%CI:0.03~0.64;P=0.01)[183]。
2.4.1.3 手術切除或局部消融治療的HCV相關HCC患者DAAs治療方案的選擇 對于術后肝功能尚可(MELD評分<18~20分)的HCV相關代償期HCC肝切除術后患者,應行DAAs治療,治療方案可參考中國《丙型肝炎防治指南(2019年版)》[68]實施;如術后肝臟失代償或術前曾有肝臟失代償病史,建議給予不含蛋白酶抑制劑的DAAs治療方案。
推薦意見15:手術切除及局部消融等根治性治療的HCV相關HCC患者接受DAAs治療可降低腫瘤復發風險,降低死亡風險,提高總體生存率。在HCV相關HCC根治性治療后4~6個月腫瘤無復發,可開始DAAs治療(2B)。
推薦意見16:對于HCC根治性治療后肝功能尚可(MELD評分<20分)的代償期患者,可行DAAs治療,可選擇泛基因型方案或基因特異型方案;如肝臟失代償(MELD評分≥20分)或治療前曾有肝臟失代償病史,建議給予不含蛋白酶抑制劑的治療方案,可首選泛基因型DAAs[如索磷布韋(Sofosbuvir)聯合維帕他韋(Velpatasvir)等](2B)。具體用藥及用法詳見附錄1~3。
2.4.2 接受肝移植的HCV相關HCC患者的抗病毒治療
2.4.2.1 DAAs治療肝癌復發的影響 關于DAAs在接受肝移植的HCV相關HCC患者中的療效,尤其是有關HCC復發風險的研究較少,存在爭議。一項回顧性研究[184]納入了81例接受肝移植的HCV相關HCC患者,其中18例患者移植前接受了DAAs治療。與未接受DAAs治療的患者(6/63,9.5%)相比,移植前接受DAAs治療的患者其HCC復發風險(5/18,27.8%)呈現更高趨勢,且在DAAs治療組復發的5例患者中均觀察到腫瘤肝外轉移。雖因樣本量過小,此結果無統計學意義(P=0.06),但仍引起了廣泛關注。隨后,Donato等[185]納入35例接受移植前DAAs治療的HCC患者,在移植術后20個月的隨訪時間內,HCC復發率僅為8.5%(3/35),認為移植前行DAAs治療不會增加術后HCC復發的風險。兩項研究之間的結果差異可能來源于更大的樣本量(35 vs 18)及更高的SVR率(94% vs 50%)。法國一項多中心前瞻性研究[186]分析了314例在移植后接受DAAs治療的HCV相關HCC患者,其12周SVR率為96.8%。肝移植后中位隨訪時間為70.3個月,共觀察到7例HCC復發,復發率僅為2.2%。該項結果提示,肝移植后給予DAAs治療,可獲得較高的SVR率及較低的HCC復發率。
Gorgen等[187]進行了一項回顧性多中心研究,該研究納入875例HCV相關HCC肝移植患者,分為移植前DAAs治療組(121例)、移植前IFN治療組(112例)、移植后DAAs治療組(395例)、移植后IFN治療組(105例)、未接受抗病毒治療組(142例)。中位隨訪時間分別為2.1年、2.9年、4.5年、7.8年和2.7年。分析結果顯示移植前DAAs治療組、移植前IFN治療組、未行抗病毒治療組HCC復發率分別為 6.6%、15.2%、28.2%(P<0.001)。5年無復發生存率分別為93.4%、84.8%、73.9%(P<0.001)。移植后DAAs治療組、移植后IFN治療組和未行抗病毒治療組的HCC復發率分別為6.3%、11.4%、282%。經過多變量回歸分析提示,無論移植前或移植后,應用抗病毒治療均可減少HCC復發風險。
2.4.2.2 DAAs治療的時機 國際肝移植學會關于肝移植候選人中丙型肝炎管理的共識聲明(2017年)[188],推薦移植等待名單中的HCV相關代償期肝硬化合并HCC患者,可術前給予DAAs抗病毒治療;HCV相關失代償期肝硬化合并HCC患者,若在短時間內(3~6個月)不接受肝移植,應進行抗病毒治療。反之,則建議將抗病毒治療推遲到移植術后。歐洲肝病學會關于丙型肝炎治療建議(2018年)[105]則指出,HCV相關HCC患者,若無合并肝硬化或處于代償期肝硬化,移植前行抗病毒治療可減少移植后HCV復發及移植術后并發癥的風險,而移植后行抗病毒治療獲得SVR的可能性更高。美國胃腸病學會的DAAs治療慢性丙型肝炎與HCC臨床專家共識(2019)推薦指出,HCC的存在與DAAs治療后獲得較低的SVR相關。接受肝移植的HCC患者的DAAs治療時機應綜合考慮中位等待時間、是否使用HCV陽性器官以及肝功能異常的程度。相比移植后DAAs治療,移植前用藥具有改善肝功能[189-190]、預防移植后HCV復發[191]、避免移植后可能出現的藥物相互作用等優勢,而其可能存在HCC復發率升高、SVR率降低等弊端,但尚缺乏充足的證據。
2.4.2.3 DAAs治療方案的選擇 對于治療方案的選擇,應綜合考慮患者移植時間、肝功能、HCV基因型、供受體HCV感染情況、合并用藥等多個因素。
基于國內外指南[67,105],若患者于移植前行DAAs治療,且為無肝硬化或代償期肝硬化,首先推薦泛基因型方案索磷布韋/維帕他韋 (Sofosbuvir/Velpatasvir)或格卡瑞韋/派侖他韋(Glecaprevir/Pibrentasvir),或適合HCV-1、4、5、6基因型的索磷布韋/雷迪帕韋(Sofosbuvir/Ledipasvir),治療時間為12周。當患者為失代償期肝硬化時,推薦索磷布韋/維帕他韋+利巴韋林(Sofosbuvir/Velpatasvir+RBV,泛基因型)或索磷布韋/雷迪帕韋+利巴韋林(Sofosbuvir/Ledipasvir+RBV, 1、4、5、6基因型)方案治療12周。若有RBV禁忌證或無法耐受時,可僅使用索磷布韋/維帕他韋 (Sofosbuvir/Velpatasvir)或索磷布韋/雷迪帕韋(Sofosbuvir/Ledipasvir),但需將療程延長至24周。
若患者于移植術后行DAAs治療,需關注供受體HCV感染情況。對于HCV RNA陽性的受體,無論供體HCV RNA陽性或陰性,術后均應重新測定HCV基因型以指導抗病毒治療,方案同上。對于HCV RNA陰性的受體,若接受抗HCV陽性但HCV RNA陰性的供體,術后檢測HCV RNA陽性,需按上述方案抗病毒治療。若接受HCV RNA陽性的供體,其移植后早期和嚴重疾病的風險暫未知,建議術后重新測定基因型,按上述方案早期抗病毒治療[188]。
推薦意見17:對于肝功能尚可(MELD評分<20分)、等待移植時間較長的HCC患者,可考慮于移植前行DAAs治療。對于肝功能不佳(MELD評分≥20分)、等待移植時間較短的HCC患者,可將DAAs治療推遲至移植術后。治療方案的選擇需根據移植時間、肝功能、HCV基因型、供受體HCV感染情況、合并用藥等因素綜合考慮(2B)。
2.4.3 接受TACE治療的HCV相關HCC患者抗病毒治療 一項病例對照研究[192]探究了DAAs治療對71例(26例接受過TACE治療)治療后處于完全緩解狀態的HCV相關HCC患者的復發情況,結果表明,DAAs對于HCV相關HCC患者的肝癌復發沒有影響(41% vs 35%,P=0.790 4)。DAAs治療HCV不會加速HCC復發,但對早期復發沒有預防作用。
來自北美的隊列研究[180]中包括793例(360例接受過TACE治療)HCV相關HCC患者,其中304例(107例接受過TACE 治療)接受DAAs治療,489例(253例接受過TACE治療)未接受抗病毒治療。結果提示,DAAs治療與HCC復發(HR=0.90;95%CI:0.70~1.16)或早期HCC復發(HR=0.96;95%CI:0.70~1.34)無關。同年該團隊[165]在加拿大開展了另一項包括接受手術、TACE等治療的797例(358例接受過TACE治療,56例接受過立體放療等其他治療)HCV相關HCC患者的隊列研究,結果表明,DAAs治療與顯著降低的死亡風險相關(HR=0.54;95%CI:0.33~0.90),且這種相關性因DAAs治療后是否達到SVR而不同;DAAs治療后能夠降低取得SVR患者的死亡風險(HR=0.29;95%CI:0.18~0.47),但不能降低非SVR患者的死亡風險(HR=1.13;95%CI:0.55~2.33)。一項回顧性隊列研究[193]納入425例接受TACE治療的HCV相關HCC的患者,與使用IFN和未進行抗病毒治療相比,DAAs治療能夠降低腫瘤進展風險(HR=0.630;95%CI:0.411~0.966)及死亡風險(P=0.042)。另一項對97例接受TACE或放療的HCC患者進行的回顧性隊列研究[194](94例接受過TACE治療)表明,接受抗HCV治療可提高行HCC治療后達到完全緩解狀態的患者的OS(HR=0.244;95%CI:0.075~0.788)。在早期行TACE的HCV相關HCC患者中,接受DAAs治療與未行HCV抗病毒治療相比,HCC復發率降低,RFS延長(18.6% vs 72.7%,P=0.002;44個月 vs 11.5個月,P=0.002)[195]。
推薦意見18:接受TACE治療的HCV相關HCC患者,給予DAAs抗病毒治療可以降低死亡風險,提高OS;降低已經獲得完全緩解患者的 HCC復發風險(2B)。
2.4.4 HCV相關晚期HCC患者的抗病毒治療 美國肝病學會[196]建議HCV感染的成年人,除了那些預期壽命短且無法治愈的患者,均應給予抗病毒治療;晚期HCV相關HCC患者,如非預期生存期短且無法補救,應進行DAAs抗病毒治療。目前,有關DAAs治療在HCC免疫治療及靶向治療患者中的應用數據有限,未來依據研究推進情況將進一步補充及更新。
在發生HCC之前治療HCV是最佳策略,即HCV相關HCC二級預防證據較之現有三級證據更有利于達成共識。對于已發生HCC、并可進行根治性治療的HCV感染者,將DAAs治療時機推遲到抗腫瘤治療使得HCC完全緩解后進行,可能會提高SVR率。對于已列入肝移植名單的HCC患者,DAA治療的時機應根據具體情況來確定,并結合所在地區的中位等待時間、HCV陽性器官的可用性和肝功能障礙的程度。在中晚期HCC患者中,SVR相對較低,與早期HCC患者相比,HCC相關死亡率的風險較高。目前還沒有足夠的數據來評估DAA治療在這些患者中的獲益及成本效益。對于活動性HCC患者是否給予DAAs治療,應綜合考慮腫瘤負荷、HCC治療獲得完全應答的可能性、肝功能障礙程度、總體預期壽命以及患者的治療意愿等。
DAAs治療在HCC三級預防中的應用尚有諸多問題有待明確。但毋庸置疑,DAAs的成功治療可減輕肝纖維化、降低門靜脈高壓和改善肝功能,而上述變化通常是HCC完全緩解和未治療的HCV感染者死亡的主要驅動因素。盡管目前支撐證據數據質量有待提高,但對于大多數HCC患者,DAAs治療的受益通常超過了潛在缺點,這為其在此類患者中的應用提供了依據。

附錄1 丙型肝炎DAAs的分類[67,114]

附錄2 初治或PRS經治的無肝硬化HCV感染者治療方案[67]
共識起草小組成員:牛俊奇(吉林大學第一醫院),江家驥(福建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葉勝龍(復旦大學附屬中山醫院,海軍軍醫大學東方肝膽外科醫院),董菁(福建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高沿航(吉林大學第一醫院),劉嶸(復旦大學附屬中山醫院),周偉平(海軍軍醫大學東方肝膽外科醫院),黃罡(海軍軍醫大學東方肝膽外科醫院),曾昭沖(復旦大學附屬中山醫院),于樂成(東部戰區總醫院)
執筆人:董菁(福建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高沿航(吉林大學第一醫院),劉嶸(復旦大學附屬中山醫院),黃罡(海軍軍醫大學東方肝膽外科醫院)
編寫組專家(按姓氏筆畫排序):于樂成(東部戰區總醫院),馬雄(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附屬仁濟醫院),萬謨彬(海軍軍醫大學附屬長海醫院),牛俊奇(吉林大學第一醫院),王伽伯(解放軍總醫院第五醫學中心),王炳元(中國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葉勝龍(復旦大學附屬中山醫院,海軍軍醫大學東方肝膽外科醫院),孫劍(南方醫科大學南方醫院),莊輝(北京大學醫學部),任紅(重慶醫科大學附屬第二醫院),江家驥(福建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劉景豐(福建醫科大學孟超肝膽醫院),劉嶸(復旦大學附屬中山醫院),華海清(東部戰區總醫院全軍腫瘤中心),朱康順(廣州醫科大學附屬第二醫院 ),陳成偉(海軍軍醫大學九〇五醫院),陳敏山(中山大學腫瘤防治中心),陳煜(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佑安醫院),張大志(重慶醫科大學附屬第二醫院),張德智(吉林大學第一醫院),楊震(山東第一醫科大學附屬省立醫院),范建高(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附屬新華醫院),周偉平(海軍軍醫大學東方肝膽外科醫院),鄭琦(福建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段鐘平(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佑安醫院),南月敏(河北醫科大學第三醫院),侯金林(南方醫科大學南方醫院),趙景民(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三〇二醫院),莢衛東(中國科學技術大學附屬第一醫院),胡鵬(重慶醫科大學附屬第二醫院),賈繼東(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友誼醫院),徐小元(北京大學第一醫院),唐紅(四川大學華西醫院),高沿航(吉林大學第一醫院),郭武華(福建醫科大學孟超肝膽醫院),謝雯(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地壇醫院),黃罡(海軍軍醫大學東方肝膽外科醫院),曾昭沖(復旦大學附屬中山醫院),曾爭(北京大學第一醫院),董菁(福建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溫曉玉(吉林大學第一醫院),鄢和新(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附屬仁濟醫院)>

附錄3 初治或PRS經治的代償期肝硬化HCV感染者治療方案[67]
利益沖突聲明:牛俊奇曾經擔任BMS、GSK、Gliead、默沙東、諾華、艾伯維、羅氏、凱因科技、豪森、圣和、東陽光、歌里等企業的新藥臨床注冊研究,企業臨時顧問或衛星會講者。江家驥曾經擔任過GSK、諾華、Roche、歌禮、Janssen的臨時顧問,曾經或目前仍為BMS、GSK、Bayer、Novartis、Gilead、Roche、MSD、特寶等公司的講者。葉勝龍曾參與Bayer、Sanofi公司新藥臨床試驗及AstraZeneca、BMS、GSK、Merck、Novartis、Pfizer、SciClone等公司咨詢,均與本項目無利益沖突。其他共識起草小組成員與本共識制定相關的企業及個人均無利益沖突。
志謝:特別感謝莊輝院士對本版共識提出的建設性及指導性意見和建議。感謝中華醫學會肝病學分會肝癌學組第3屆和第4屆全體委員完成函審以及對本版共識提出的寶貴意見和建議,提出意見和建議的專家均列入了討論專家名單。感謝蘭州大學世界衛生組織指南實施與知識轉化合作中心陳耀龍教授在指南編寫方法上給予指導。
感謝吉林大學第一醫院圖書館倫志軍研究員在文獻檢索方面給予指導。吉林大學第一醫院博士和碩士研究生:張明媛,高修竹,劉旭,劉麗莉,馬鶴銘,王暢,湛夢茹,劉宇維,朱琦,朱倩,任天弈,李臘梅,李杰,馬振華,趙天業參加了文獻檢索,趙天業提供了文獻檢索和方法學的輔導,在此也特別致謝。
華夏肝臟病學聯盟和《臨床肝膽病雜志》編輯部提供了少量資金贊助。多次討論會議是在華夏肝臟病學聯盟舉辦的學術會議期間進行或以網絡會議方式舉行。正大天晴藥業集團在最初兩次討論中給數位專家提供了差旅費,后期根據指南編寫原則,退出了贊助。編寫人員均無勞務費用。
本共識已在國際實踐指南注冊平臺注冊,注冊號:IPGRP-2021CN269。

參考文獻見二維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