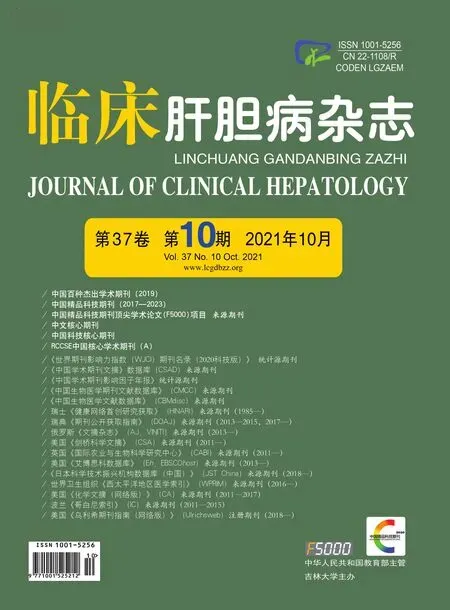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肝纖維化進展中胃腸激素的變化水平
朱滬敏, 劉旭東, 黃 露, 李品樺, 吳鐵雄, 龐華珍
1 廣西中醫藥大學 研究生學院, 南寧 530000;2 廣西中醫藥大學附屬瑞康醫院 肝病科, 南寧 530000
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NAFLD)是全球慢性肝病的首要原因[1]。據報道,我國NAFLD的患病率為15%~30%[2],并且呈現逐年上升趨勢。NAFLD在臨床上可分為單純性脂肪肝(NASFL)、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NASH)、脂肪性肝纖維化和肝硬化[3]。肝纖維化是以細胞外基質過度沉積為特征表現的病理性組織修復過程,是各種慢性肝病向肝硬化發展的關鍵步驟[4]。本研究旨在觀察NAFLD肝纖維化進展對血清膽囊收縮素(CCK)、二胺氧化酶(DAO)、D-乳酸(D-LA)、胃泌素17(G-17)、脂多糖(LPS)、胃動素(MTL)水平的影響,以期對肝纖維化進展導致的終末期肝病及消化系統相關并發癥監測提供參考。
1 資料與方法
1.1 研究對象 選取2018年10月—2020年6月在廣西中醫藥大學附屬瑞康醫院門診就診及病房住院治療的NAFLD患者326例。納入標準:(1)符合《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防治指南(2018年更新版)》[5]的診斷標準;(2)年齡18~75歲;(3)合并其他疾病,但在觀察期間不影響病例觀察者。排除標準:(1)飲酒史>5年,折合乙醇量男性≥40 g/d,女性≥20 g/d;(2)病毒性肝炎、自身免疫性肝炎、藥物性肝炎、原發性硬化性膽管炎等患者;(3)孕產婦或哺乳期婦女;(4)合并心、腦、腎等重要臟器嚴重疾病患者以及明確診斷的糖尿病患者;(5)有重要數據遺失、資料不全者。
1.2 研究方法
1.2.1 資料的獲取 收集患者的性別、年齡、就診日期、就診號、是否有重大慢性病或家族遺傳病史。
1.2.2 血清學指標 早晨空腹抽取靜脈血,應用美國RXL全自動生化分析儀檢測生化指標,如TBil、DBil、IBil、總蛋白(TP)、Alb、Glb、ALT、AST、ALP、GGT;使用ELISA試劑盒進行酶聯免疫吸附試驗法測定CCK、DAO、D-LA、G-17、LPS、MTL水平。
1.2.3 無創纖維化指標 無創肝纖維化指標檢測應用FibroTouch測定(FT-C型,無錫海斯凱爾醫學技術有限公司),獲得肝臟硬度值(LSM),單位以kPa表示。操作前囑患者取合適體位,暴露右側第5~10肋間部位。操作時由一名經過專業培訓且經驗豐富的主治醫師使用B超探頭(3.5 mHz)二維成像,避開肝內相關組織,定位在右側腋前線或腋中線第7、8、9肋間,而后使用標配動態寬頻探頭(2.5 mHz),使之與皮膚垂直,觀察壓力指示器的變化,當其顯示為綠色,顯示屏上M波形強度一致,表現為分布均勻、A波形呈線性時開始檢測。當四分位間距(IQR)與中位數的比值(IQR/med)<10%時表示此次檢測數據有效,記錄此次數值并進行下一次測量,要求成功測量次數在10次以上。
1.2.4 分組情況 根據FibroTouch的診斷標準分為5組,分別為F0~1組(LSM<7.3 kPa)、F2組(7.3 kPa≤LSM<9.7 kPa)、F2~3組(9.7 kPa≤LSM<12.4 kPa)、F3~4組(12.4 kPa≤LSM<17.5 kPa)、F4組(LSM≥17.5 kPa)。另根據有無肝纖維化分為無肝纖維化組(A組,LSM<7.3 kPa)、肝纖維化組(B組,LSM≥7.3 kPa)。
1.3 倫理學審查 本研究方案經由廣西中醫藥大學附屬瑞康醫院倫理委員會審批,批號:KY2018-004。

2 結果
2.1 一般資料 326例NAFLD患者中男225例,女101例,年齡18~74歲,平均(46.45±11.87)歲,中位年齡47(37~55)歲。F0~1組(n=161)、F2組(n=89)、F2~3組(n=46)、F3~4組(n=16)、F4組(n=14) 5組間ALT、AST、ALP、GGT、CCK比較,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值均<0.05)(表1)。
2.2 A組與B組間肝功能指標、胃腸激素指標比較 A組161例中男104例,女57例,年齡20~72歲,中位年齡46.0(37.5~53.5)歲;B組165例中男121例,女44例,年齡18~74歲,中位年齡48(37~56)歲。兩組間肝功能指標ALT、AST、GGT以及胃腸激素指標CCK、LPS比較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值均<0.05),其他指標組間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值均>0.05)(表2)。
2.3 LSM值與肝功能指標相關性分析 Spearman相關性分析結果表明,LSM值與DBil、ALT、AST、ALP、GGT呈顯著正相關(r值分別為0.128、0.266、0.225、0.137、0.213,P值分別為0.021、<0.001、<0.001、0.013、<0.001)。
3 討論
NAFLD合并晚期肝纖維化增加了肝臟特異性發病率和總體病死率[6],日益成為危害人類健康的全球問題。肝臟是人體最大的消化器官,與胃腸功能關系密切,慢性肝病常出現消化道癥狀[7]。近年來,探索肝纖維化進展對胃腸功能的影響成為研究熱點,為改善慢性肝病預后及減少消化系統并發癥提供理論指導。

表1 5組間肝功能及胃腸激素指標比較

表2 兩組間肝功能指標、胃腸激素指標比較
本研究發現LSM值與DBil、ALT、AST、ALP、GGT具有相關性,并且隨著肝纖維化程度加重,患者血清ALT、AST、GGT水平亦升高,提示肝纖維化進展伴隨肝功能損傷。相關文獻[8-9]報道,NAFLD患者肝纖維化進展與血清ALT、AST、GGT水平升高有關,與本研究結果一致。
本研究結果顯示,隨著肝纖維化程度加重,患者血清G-17、MTL、DAO、D-LA水平無明顯變化,差異無顯著性;血清CCK、LPS水平出現明顯變化,提示肝纖維化進展可能影響膽囊收縮及胃腸功能。胃泌素具有促進胃酸分泌,調節胃蠕動的作用。G-17是胃泌素主要分泌激素之一[10],從肝臟和腎臟代謝,且與慢性肝病胃黏膜病變有關。柴朝會等[11]采用放射免疫法測定肝硬化無靜脈曲張組血清胃泌素含量基本正常。此文獻報道與本研究結果一致。MTL可調節消化間期的胃腸運動,并與胃腸功能障礙性疾病發病有關[12]。脂肪肝患者通常存在膽汁代謝異常,胃黏膜經過膽汁刺激促進MTL的釋放[13]。秦俊等[14]研究發現,肝硬化患者血中MTL水平較正常對照組升高。本研究未得出類似結論。DAO與D-LA作為腸道黏膜損傷標志物,反映腸道黏膜屏障功能[15-16]。金希團隊[17]在動物實驗中觀察到NASH模型組大鼠血漿DAO和D-LA水平較健康對照組顯著升高。本研究結果提示,不同肝纖維化水平對促進胃酸分泌、調節胃腸動力及反映腸道黏膜損傷的激素無明顯影響。可能與本研究納入的觀察對象中重度肝纖維化人數較少有關,中晚期肝纖維化至肝硬化階段血清G-17、MTL、DAO和D-LA水平的變化有待進一步探討。
本研究發現,血清CCK水平隨肝纖維化早期呈上升趨勢,進展至中晚期呈下降趨勢,但總體來看仍然呈上升趨勢,提示肝纖維化進展可能影響胃腸功能。已經有研究[18-19]證實,NAFLD肝纖維化進展增加了胃食管反流和結腸憩室的發病風險。CCK具有調節腸道運動,促進膽囊收縮及胰腺分泌等作用[20]。慢性肝病通常存在膽汁排泄異常。有文獻[21]報道,脂肪肝患者膽囊收縮率及膽囊排空率下降。Keith等[22]發現,肝硬化患者發生胃排空障礙與CCK水平上升有關,與本研究結果一致。另外有研究[23]證實,CCK參與抑制攝食,導致體質量下降,間接降低了NAFLD的發病風險,提示這可能與肝纖維化進展,CCK應激性升高,負性拮抗脂肪肝有關。
NAFLD存在腸道菌群失調,使LPS產生增多,誘導炎癥反應,造成肝損傷[24]。Cani等[25]在動物實驗中觀察到,人為誘導的NAFLD鼠模型存在血清LPS水平升高現象。有臨床研究[26]觀察到肝硬化患者血清LPS水平顯著升高。本研究發現,血清LPS水平在肝纖維化早中期呈下降趨勢,進展至肝纖維化晚期甚至肝硬化階段,呈上升趨勢。本研究結果與以往的的報道存在差異,究其原因,可能與本研究納入的樣本量分布不均有關。然而,已經有細胞實驗證實了LPS在低濃度、短時間刺激肝星狀細胞活化的效果比高濃度、長時間更好[27-28]。目前尚未見類似結果的臨床研究報道。該結果為進一步探討肝纖維化進展過程中體內LPS水平的具體變化提供一定的理論依據。
綜上所述,通過對肝功能指標和胃腸激素指標的檢測與觀察,發現不同程度肝纖維化的NAFLD患者體內存在血清CCK、LPS水平紊亂,紊亂程度與肝臟硬度可能有關。因此,在臨床診療中,要關注NAFLD肝纖維化患者膽囊收縮功能及胃腸功能的改變。
利益沖突聲明:本研究不存在研究者、倫理委員會成員、受試者監護人以及與公開研究成果有關的利益沖突。
作者貢獻聲明:朱滬敏負責課題設計,資料分析,撰寫論文;黃露、李品樺、吳鐵雄、龐華珍參與收集數據,修改論文;劉旭東負責擬定寫作思路,指導撰寫文章并最后定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