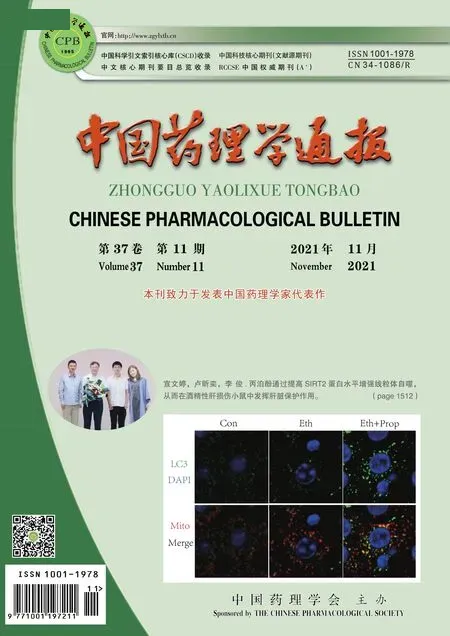基于網絡藥理學牛磺石膽酸抗炎作用及機制
王妙然,李 月,張蕓綺,藺曉菁,鐘 瑩,陳春秀,周 永,肖曉秋,李繼斌
(1.重慶醫科大學營養與食品衛生學教研室,2.重慶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重大代謝性疾病轉化醫學重慶市重點實驗室,重慶 400016;3.重慶市巴南區人民醫院臨床營養科,重慶 401320)
動物膽汁及其結石是一種沿用數千年的傳統中藥原料,可用于治療肝膽疾病、驚厥、創傷和皮膚潰瘍、感染性疾病等。其主要成分包括膽汁酸、膽色素、膽固醇、磷脂及抗氧化物(如維生素E,褪黑素,谷胱甘肽等)。膽汁酸是膽汁的主要成分,由膽固醇在肝臟中合成,儲存于膽囊,并隨進食活動分泌到腸道。除了能促進脂類和脂溶性維生素吸收,還可作為調節代謝、炎癥和免疫功能的生物信號分子[1-2]。牛膽汁和牛膽結石(牛黃)因其來源豐富而被廣泛使用。牛膽汁中包含的膽汁酸主要有TCA、TDCA、TCDCA、TLCA、GCA、GDCA、GCDCA、GLCA、ACA等[3]。其中,牛磺石膽酸(taurolithocholic acid,TLCA)是由CDCA衍生而來的一種典型的次級膽汁酸,也存在于人類膽汁中,具有抑制炎癥反應的作用[4],但其具體機制尚未完全明確。近年來,網絡藥理學方法越來越多地用于中藥復方或單體成分作用靶點的分析預測[5],具有系統性解釋藥物治療疾病作用機制的優點。因此,本文利用網絡藥理學來研究TLCA的抗炎作用及機制。
1 資料與方法
1.1 TLCA分子結構與作用靶標獲取查詢PubChem數據庫(https://www.ncbi.nlm.nih.gov/home/chemicals/)并下載TLCA的3D分子結構。將文件導入PharmMapper Service數據庫(http://www.lilabecust.cn/pharmmapper/)和SWISS數據庫(http://swisstargetprediction.ch/)獲得TLCA潛在作用靶點,利用UniProt數據庫的Retrieve/ID Mapping功能,將靶點UniProt ID轉換為Gene Symbol。
1.2 炎癥靶點篩選在GeneCards數據庫中(https://www.genecards.org/)檢索獲取炎癥相關基因,分別與TLCA作用靶點進行匹配,得到共同靶點。
1.3 構建蛋白互作網絡圖將TLCA炎癥靶點基因導入STRING數據庫(https://string.db.org/),獲取靶點蛋白-蛋白相互作用關系圖(PPI),設置combined score>0.4,將結果導入Cytoscape軟件,構建TLCA炎癥靶點可視化PPI網絡圖。
1.4 GO功能富集和KEGG通路分析運行R軟件進行GO功能富集分析(gene ontology)和KEGG通路富集分析(Kyoto Encyclopedia of Genes and Genomes)并輸出注釋結果。
1.5 分子對接在NCBI數據庫查找TGR5氨基酸序列并輸入SWISS-MODEL數據庫(http://swissmodel.expasy.org/)對蛋白結構進行同源建模。利用AutoDock軟件對TLCA與TGR5進行分子對接分析。
2 材料與方法
2.1 實驗材料與試劑
2.1.1材料 小鼠RAW264.7巨噬細胞由重慶醫科大學附屬第二醫院龔建平教授課題組惠贈。
2.1.2試劑 高糖DMEM培養基(貨號:C11995500BT)購自Gibco公司。胎牛血清(貨號:04-005-1A)購自BI公司。TLCA(貨號:700252P)及LPS(貨號:L2630)購自Sigma公司。IFN-γ(貨號:HY-P7071)購自MCE公司。PBS(貨號:AR1155)購自博士德公司。青-鏈霉素溶液(貨號:C0222)、RIPA裂解液(貨號:P0013C)、BCA蛋白濃度測定試劑盒(貨號:P0010)、彩色預染蛋白分子量標準液(貨號:P0068)和Western一抗稀釋液(貨號:P0023A)均購自碧云天公司。辣根素過氧化物酶標記山羊抗兔IgG(貨號:98164)、辣根過氧化物酶標記山羊抗小鼠IgG(貨號:91196)購自CST公司。TRIzol總RNA提取試劑盒(貨號:9109),反轉錄試劑盒(貨號:RR047A)、SYBR Green(貨號:RR820A)購自TaKaRa公司。引物由生工生物工程(上海)股份有限公司設計合成。CD86抗體(貨號:sc-28347)購自Santa公司,P65(貨號:8242)、p-P65(貨號:3033)、IκBα(貨號:4818)、p-IκBα(貨號:2859)、β-actin抗體(貨號:3700S)購自CST公司。Western blot檢測試劑盒購于advansta(貨號:190720-33)。FITC標記的山羊抗小鼠IgG(H+L)購自ZSGB-BIO (貨號:ZF-0312)。
2.1.3儀器 細胞培養箱、酶標儀(美國Thermo公司),正置熒光顯微鏡(德國Leica公司),定量PCR儀、電泳儀(美國Bio-Rad公司),凝膠/發光圖像分析系統(法國Vilber Lourmat公司)。
2.2 方法
2.2.1細胞培養及處理 RAW264.7細胞在含10% FBS、1%青-鏈霉素溶液的DMEM高糖培養基中于37 ℃、5% CO2孵箱中培養,待細胞融合至80%左右,按每孔2.0×108L-1個接種于6孔板,培養過夜后,分別給予TLCA(30 μmol·L-1)、LPS(100 μg·L-1)和IFN-γ(20 μg·L-1)、TLCA聯合LPS及IFN-γ進行干預,24 h后提取細胞總RNA和總蛋白。
2.2.2RT-qPCR 按TRIzol RNA提取試劑盒說明書提取細胞總RNA。取1μg總RNA經反轉錄獲得cDNA。以GAPDH為內參進行實時熒光定量PCR,根據2-ΔΔCt計算目的基因相對表達量,見Tab 1。

2.2.3 免疫熒光將RAW264.7細胞按每孔5×107L-1個接種于12孔板過夜,分別給予TLCA(30 μmol·L-1)、LPS(100 μg·L-1)和IFN-γ(20 μg·L-1)、TLCA聯合LPS及IFN-γ處理24 h。棄培養液,取出爬片,PBS洗3遍后用多聚甲醛固定15 min,山羊血清封閉30 min,4 ℃孵育一抗過夜,孵育熒光二抗,DAPI染胞核后于熒光顯微鏡下觀察并保存圖片,用ImageJ軟件計算熒光強度。
2.2.4Western blot 提取各組細胞總蛋白,用BCA試劑盒測定蛋白濃度。蛋白變性處理后進行電泳,轉膜,封閉及抗體TGR5(1 ∶1 000)、P65(1 ∶1 000)、p-P65(1 ∶1 000)、IκBα(1 ∶1 000)、p-IκBα(1 ∶1 000)、β-actin(1 ∶10 000)孵育。辣根素過氧化物酶標記二抗孵育后,ECL化學發光法顯影,計算目的蛋白表達水平。

3 結果
3.1 TLCA作用靶點篩選將PharmMapper和SWISS數據庫的TLCA 作用靶點與GeneCards得到的炎癥相關基因進行比對,篩選出87個TLCA抗炎潛在作用靶點。
利用STRING數據庫,去除離散點后,得到81個靶點蛋白的相互作用(PPI)關系圖,其中包括GPBAR1等,再用Cytoscape軟件進行可視化處理后篩選得到其核心靶點為SRC、EGFR、MAPK3、PIK3CA、JAK2、IL10、MMP2、KDR和ESR1。
3.2 GO功能富集分析和KEGG通路分析GO結果表明,這些靶點被富集到1 506個生物學過程,與炎癥反應調節、白細胞遷移、細菌分子響應、固有免疫調節等生物學過程密切相關;在細胞組分方面,富集最多的包括:細胞膜脂筏、膜微結構域、膜區;在分子功能中,主要起作用的是蛋白酪氨酸激酶活性、絲氨酸/蘇氨酸激酶活性(Fig 1)。

Fig 1 GO classification enrichment analysis
KEGG結果顯示, 與81個潛在靶點基因顯著相關(P≤0.05)的通路有124條,排名靠前的信號通路為: PI3K-Akt信號通路、人類巨細胞病毒感染、腫瘤蛋白多糖等(Fig 2)。

Fig 2 KEGG pathway analysis
3.3 分子對接鑒于PPI網絡圖顯示GPBAR1蛋白(G protein-coupled bile acid receptor 1,即TGR5)為TLCA靶點之一,GO分析也提示靶點基因功能主要富集在“脂筏、微結構域、膜區”,說明TLCA的抗炎作用與細胞膜上的分子高度相關。TGR5是一種G蛋白偶聯膜受體,作為一種較晚發現的膽汁酸受體,可能是介導TLCA調節炎癥反應的關鍵。因此,本研究選擇TGR5作為關鍵靶點,利用AutoDock軟件,進行分子對接分析。結果顯示TLCA與TGR5對接分數為-9.0,結合活性較強。此外,運用Pymol軟件分析結合部位發現,TLCA結合于TGR5蛋白靠近中心部位,結合位置較穩固(Fig 3)。

Fig 3 Molecular docking of TLCA and TGR5
3.4 TLCA抑制RAW 264.7細胞M1型極化經LPS和IFN-γ處理的RAW 264.7細胞出現M1型極化特征,包括體積變大、形態不規則、伸出偽足,胞質顏色變淡;而聯合TLCA處理后,M1型RAW 264.7細胞數量減少。相應地,LPS和IFN-γ處理顯著上調M1型極化相關炎癥因子IL-1β、IL-6、TNF-α、iNOS的mRNA表達水平(P<0.01),抗炎介質IL-10和M2型標志物Arg1表達也有升高(P<0.01)。聯合TLCA處理后,IL-6、TNF-α、iNOS的mRNA表達明顯下降(P<0.05),但對IL-10、Arg1表達無顯著降低作用(Fig 4)。

Fig 4 Effects of TLCA on expression of IL-1β, TNF-α, iNOS, IL-6, IL-10 and Arg1 induced by LPS and IFN-γ n=6)
免疫熒光結果表明,M1型極化細胞標志物CD86在LPS和IFN-γ處理后表達明顯增加(P<0.01);而TLCA可降低CD86表達(P<0.01,Fig 5)。

Fig 5 CD86 immunofluorescence
3.5 TLCA抑制RAW264.7細胞NF-κB通路Western blot結果顯示,RAW 264.7細胞在給予TLCA處理后,TGR5蛋白表達水平明顯上升(Fig 6)。LPS及IFN-γ處理組細胞p-P65和p-IκBα蛋白表達增加(P<0.05),P65蛋白表達不變,IκBα表達下降,提示NF-κB信號通路被激活。而聯合TLCA處理時,p-P65、p-IκBα蛋白表達下降,P65蛋白表達不變,IκBα表達升高(P<0.05,Fig 6)。

4 討論
炎癥是多種代謝性疾病發生發展的重要機制,慢性炎癥以分泌促炎細胞因子的巨噬細胞積聚為主要特征,被認為是腫瘤、胰島素抵抗、肥胖等疾病的重要變化,其病理生理機制復雜多樣。其中,炎癥因子在多種疾病中發揮作用,如:COVID-19、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動脈粥樣硬化等。當病毒感染和/或繼發感染觸發的免疫反應過量釋放細胞因子,會導致組織細胞“炎癥風暴”[6],表現為全身性高炎癥水平和多器官衰竭,增加患者死亡率。
本研究通過網絡藥理學分析篩出TLCA發揮抗炎作用的靶基因有87個,其核心靶基因包括SRC、EGFR、MAPK3、PIK3CA、JAK2、IL-10、MMP2、KDR和ESR1。其中SRC、EGFR、MAPK3/ERK1、ESR1、MMP2與腫瘤發生、血管生成、轉移和炎癥反應密切相關[7-9]。IL-10作為一種重要的抗炎因子可經多條信號通路參與炎癥調節。PIK3CA是PI3K的一個亞基,參與眾多細胞生物學過程,包括葡萄糖轉運、癌癥發生和炎癥反應。GO分析和KEGG注釋結果表明TLCA大多數抗炎靶點富集于PI3K信號通路。“細胞成分”富集分析排名前3位分別為“脂筏、微結構域、膜區”,說明TLCA抗炎作用與分布于細胞膜的分子高度相關。
膽汁酸主要通過FXR核受體和TGR5膜受體調控一系列生理活動。TGR5又稱GPBAR1,分布于膽囊、肝、骨骼肌和棕色脂肪組織,巨噬細胞表達最為豐富[10]。配體與TGR5結合后,可通過多條激酶通路,如PKA、AKT、SRC激酶、Rho激酶、mTORC1和ERK1/2,進而參與葡萄糖穩態、能量代謝和巨噬細胞介導的炎癥調節[11-14]。膽汁酸是最主要的內源性配體,其中石膽酸、去氧膽酸、鵝去氧膽酸和膽酸都是有效激活劑[15]。TLCA作為一種結合次級膽汁酸,是TGR5的天然強效激動劑,EC50為300 nmol·L-1[11]。在本研究中,分子對接分析也證實TLCA與TGR5分子具有較高的結合活性。
巨噬細胞在炎癥反應中居重要地位,已有研究提示TGR5可通過多條途徑降低巨噬細胞介導的炎癥反應[16-17]。在本研究中,我們選擇LPS和IFN-γ誘導的RAW264.7細胞驗證TLCA抗炎作用。RAW264.7細胞具有高度異質性,在不同信號刺激下發生不同的表型變化。LPS和/或IFN-γ介導的經典激活中,巨噬細胞向促炎表型(M1亞型)極化,TNF-α、IL-6和IL-1β等炎性細胞因子分泌增多;而IL-4則誘導抗炎表型(M2亞型)極化,產生IL-10等抗炎細胞因子[18]。本研究發現,LPS和IFN-γ處理可誘導RAW 264.7細胞M1型極化,炎癥因子表達水平上升。同時,p-P65、p-IκBα蛋白表達升高,提示與巨噬細胞NF-κB通路被激活有關。在給予TLCA處理之后,M1型標志物表達下降,NF-κB信號通路被抑制,但對M2極化無明顯降低作用。
綜上所述,本研究通過網絡藥理學篩選了TLCA抗炎癥的作用靶點,構建了藥物-靶點-疾病相互作用網絡,預測了其多靶點機制。其中,膜受體TGR5作為TLCA的關鍵靶點是其抗炎作用重要環節。在LPS和IFN-γ誘導的RAW264.7細胞炎癥模型中, TLCA可通過抑制NF-κB信號通路發揮抗炎作用。此外,本研究結果為分析TLCA其他潛在抗炎機制以及開發潛在抗炎藥物提供了新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