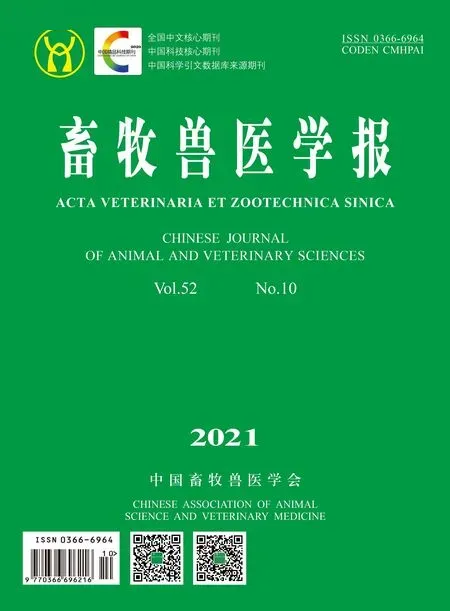牛環曲病毒研究進展
趙 龍,李 昊,湯 承,2,岳 華,2*
(1. 西南民族大學畜牧獸醫學院,成都 610041; 2.動物醫學四川省高校重點實驗室,成都 610041)
牛環曲病毒(bovine torovirus, BToV)主要感染牛的消化道和呼吸道,具有雙重組織嗜性。該病毒已被證實為一種重要的牛腹瀉病原,并且有可能致呼吸道疾病[1-4]。該病毒于1982年在美國首次報道,命名為“Breda”病毒[5]。1993年,國際病毒分類委員會將該病毒列入套氏病毒目、冠狀病毒科、環曲病毒屬[6]。2018年,國際病毒分類委員會重新將該病毒列為套式病毒目(Nidovirales)托巴套氏病毒科(Tobaniviridae)環曲病毒亞科(Torovirinae)環曲病毒屬 (Torovirus)的成員[7]。
迄今為止,BToV已在全球17個國家檢出,其危害受到越來越廣泛的重視[3-5,8-17]。根據BToV的HE基因序列特征可將其劃分為3個基因型(基因Ⅰ~Ⅲ型)[14,18],當前世界各國主要流行的是Ⅱ型和Ⅲ型[11,14,19-20]。本實驗室最近證明了BToV在國內牛群中的存在[11,21],檢測到的毒株為Ⅱ型和Ⅲ型。該病毒在國內屬于新發牛腹瀉病原,本文就BToV的生物學特性、流行概況、所致疾病的臨床癥狀與病理變化、檢測方法等進行綜述,以期為BToV的研究提供參考。
1 BToV的生物學特性
1.1 基因組結構及蛋白
BToV的基因組為線性單股正鏈RNA[22],目前GenBank中共有6條BToV基因組序列,它們長度為28 297~28 475 bp,基因組3′端為多聚A尾,5′端非編碼區之后為復制酶基因,此基因包括 2 個大的重疊開放閱讀框ORF1a和ORF1b,分別編碼聚合蛋白pp1a和pp1b[22-23]。復制酶基因的下游為4 個小的開放閱讀框,分別編碼4種結構蛋白:纖突蛋白(S)、膜蛋白(M)、血凝素酯酶蛋白(HE)、核衣殼蛋白(N)[22-23]。近年來有學者在ORF1a的5′端鑒定出1個新的編碼序列(圖1),編碼1個由258個氨基酸組成的蛋白質(30K),目前還沒有關于該蛋白功能的報道[24]。

圖1 牛環曲病毒(Breda 1)基因組結構示意Fig.1 Diagram of BToV (Breda 1) genome
1.1.1 纖突蛋白S基因編碼的纖突蛋白(S蛋白)存在一個“類胰蛋白酶”裂解位點(1 003~1 007 aa),可將S蛋白裂解為S1和S2兩個亞基[25-26]。與冠狀病毒類似,目前認為BToV的S1亞基負責與宿主細胞表面的受體結合,S2亞基則介導病毒與宿主細胞的膜融合,在病毒的感染過程中起著重要作用[7,27]。該蛋白還具有N端信號序列,一個假定的C端跨膜錨定結構域和兩個七肽重復結構域,并且該蛋白是誘導機體產生中和抗體的重要抗原,與病毒的致病性、組織嗜性和宿主范圍密切相關[23,26,28]。
目前GenBank中共有25條完整BToVS基因,長度為4 752~4 755 bp,編碼1 583~1 584個氨基酸,核苷酸相似性和氨基酸相似性分別為90.7%~99.9%和89.8%~99.9%。基于完整S基因氨基酸序列的遺傳進化樹表明,國內毒株在進化樹上聚為2個不同的分支,分別與日本毒株和土耳其毒株的親緣關系最近,表明國內BToV毒株具有遺傳多樣性(圖2)[13,11]。值得注意的是,其中一個分支上的7個毒株均為S基因重組毒株,重組區域位于S1亞基[21],重組毒株分別來自四川、西藏、河南,表明這種重組毒株已經在國內存在流行,鑒于S1亞基在與宿主受體結合方面起著重要作用,這種重組毒株的生物學特性值得進一步研究。
1.1.2 血凝素酯酶蛋白HE基因編碼的血凝素酯酶蛋白具有凝集素結構域(R)、酯酶結構域(E)、膜近端結構域(MP)三個結構域[18,29]。在病毒感染的初期,BToV的HE蛋白幫助病毒實現與7,9-di-O-acetylated Sias和9-mono-O-acetylated Sia兩種唾液酸的可逆性結合,從而逃避宿主的免疫作用[18,29]。這種具有受體破壞酶活性的結構蛋白還在A群β冠狀病毒、C型流感病毒、傳染性鮭魚貧血病毒這3類病毒中發現[30-32]。環曲病毒和A群β冠狀病毒的HE蛋白以及C型流感病毒的HEF蛋白三者具有30%的序列相似性,并且認為環曲病毒和冠狀病毒的HE蛋白起源于同一祖先[29]。該蛋白與病毒的毒力改變、組織嗜性改變、和跨種間傳播密切相關[30-32],在病毒的感染與進化中起著重要作用[29]。
目前,GenBank中BToVHE基因共有39條,長度為1 251~1 260 bp,編碼416~419個氨基酸,核苷酸相似性和氨基酸相似性分別為71.8%~100%和71.0%~100%,基于完整HE基因的遺傳進化樹顯示,國內Ⅱ型毒株聚為2個不同的分支,分別與荷蘭、土耳其毒株親緣關系最近,顯示出國內基因Ⅱ型毒株具有遺傳多樣性(圖3)。而國內Ⅲ型毒株聚為一支,與土耳其Ⅲ型毒株親緣關系最近,表明Ⅲ型毒株在國內具有獨特的遺傳進化趨勢(圖3)。

▲和■分別表示我國牦牛源和牛源的BToV毒株Black triangle and black box represent BToV strains from yak and cattle in China, respectively圖2 完整S基因氨基酸序列最大似然法進化樹Fig.2 Phylogenetic tree based on the aa sequences of the complete S gene
BToV的HE基因與豬環曲病毒(PToV)HE基因密切相關,2003年,Smits等[14]的研究顯示,基因Ⅱ型BToV毒株是由原型(Ⅰ型)毒株與PToV在HE基因的3′端發生重組而來,而基因Ⅲ型BToV毒株可能是Ⅱ型BToV毒株與一種未知的ToV在HE基因的中間區域發生重組而來。而本實驗室近期研究表明,Ⅲ型BToV毒株可能是由Ⅰ型毒株AF076621.1和Ⅱ型毒株AB661461.1在HE基因的中間區域(105~1 083 bp)重組而來,該重組分析結果與先前報道[14]不同的原因可能是本實驗室在做重組分析時加入了GneBank中近年新登錄的BToVHE基因序列。這種通過HE基因同源重組產生新基因型毒株可能是病毒在進化過程中逃避宿主免疫的一種策略[14]。冠狀病毒的HE蛋白的氨基酸突變可能會影響病毒與受體的結合,進而改變病毒的組織嗜性,造成病毒的跨種間傳播(如HCoV-OC43毒株)[31,33-34],這提醒我們不要低估環曲病毒可能存在的跨種間傳播能力。
1.2 BToV的遺傳進化
目前,GenBank中共有6條BToV基因組序列,1條為加拿大原型毒株Breda 1[22],2條基因Ⅱ型毒株來自日本[19],其余3條均為作者實驗室近期登錄,包括2條基因Ⅱ型毒株和1條牦牛基因Ⅲ型毒株[11,21]。6條BToV基因組序列核苷酸相似性為82.0%~99.2%。牦牛BToV基因組與其余5條相比,核苷酸相似性為82%~97%,與國內奶牛源BToV基因組SC2基因組相似性最高。基于基因組的遺傳進化樹顯示,國內牦牛BToV基因組與國內奶牛BToV基因組SC1和SC2親緣關最近,表明牦牛BToV可能是由國內奶牛毒株傳播而來,但兩者也有一定的遺傳距離,可能與牦牛宿主及生活環境的獨特性有關。國內3個BToV毒株與日本BToV毒株的親緣關系較近,并且相比最早報道的原型毒株Breda 1,由于原型毒株Breda 1與PToV發生重組[19],導致目前流行的BToV基因Ⅱ型和Ⅲ型毒株與PToV的親緣關系更近 (圖4)。
BToV的進化有以下幾種表現:1) 氨基酸突變,ORF1a非常容易發生氨基酸的缺失和替換[35],同時S基因和HE基因也存在著氨基酸的突變[11,13],這些氨基酸突變可能是病毒適應宿主和環境從而發生的改變。2)基因重組,目前,GneBank中登錄的6個BToV基因組中,除最早登錄的原型毒株Breda 1以外,其余5個BToV毒株均為重組毒株,其中4個毒株重組區域位于ORF1b 3′端至HE基因的3′端[11,19],1個毒株的重組區域位于S基因[21],并且這5個重組毒株的HE基因也存在重組事件,重組形式表現為單斷點重組和區域重組[14,21]。氨基酸突變的累積和基因重組使得BToV具有豐富的遺傳多樣性,甚至進化出新的基因型毒株。分析GneBank中登錄的HE基因,目前世界各國流行的毒株均是重組后的基因Ⅱ型和Ⅲ型毒株[11,14,19-21],不同基因型毒株流行情況的改變可能與HE基因的重組有關。

▲、■、●分別表示牦牛源毒株、國內牛源BToV毒株、BToV原型毒株Breda1Black triangle, black box, and black circles represent BToV strains from yak, cattle in China, and prototype strain (Breda1), respectively圖4 環曲病毒基因組核苷酸序列最大似然法進化樹Fig.4 Phylogenetic tree based on the nucleotide sequences of the complete genome
1.3 抗原性
前期的報道顯示,BToV S蛋白功能與BCoV S蛋白類似,是感染過程中誘導機體產生中和抗體的重要蛋白[23,36],但目前暫無關于該蛋白中和抗原表位的報道。本實驗室前期研究發現部分毒株S基因S1亞基存在重組事件[21],該現象對S蛋白抗原性的影響還有待于進一步研究。
1.4 理化特性
BToV對溫度十分敏感,當溫度高于4 ℃時,BToV的傳染性在24~48 h內消失,31~43 ℃時毒力顯著降低,50 ℃可迅速滅活,但在18~25 ℃可保持形態特征和血凝素特異性至少穩定10 d[23,37]。在4 ℃保存時,則在92~185 h傳染性會有明顯的降低,2~3周后傳染性消失[23,37]。因此,BToV需保存在-20~-70 ℃,以保持病毒的穩定性和傳染性[23,37]。反復凍融或高速離心可使BoTV的S蛋白脫離從而喪失病毒的侵染力,甚至分解[23]。BToV對磷脂酶C、胰蛋白酶和糜蛋白酶不敏感,且后兩者會增強BToV的感染性,對氯仿和二乙醚敏感,處理后病毒感染性消失[23,37]。目前還沒有關于BToV的pH抗性具體信息,但馬環曲病毒(EToV)在pH 2.5~10.3處于穩定狀態[23,37]。
1.5 血凝特性
BToV可凝集大鼠和小鼠的紅細胞,不凝集人O 型血、牛、雞、豚鼠、倉鼠的紅細胞[23]。
2 流行概況
病牛和帶毒牛均是傳染源,其糞便中含有大量病毒[23]。該病毒的傳播途徑主要以糞-口傳播,但也有文獻報道該病毒在牛鼻腔拭子中檢出,表明該病毒可經呼吸道傳播[2-3,23]。目前,BToV的易感動物只有牛,包括肉牛、奶牛和牦牛。主要感染3月齡以內犢牛,但也有導致成年奶牛發生腹瀉的報道[2]。
2.1 國外流行情況
目前,已在中國、美國、日本、南非、荷蘭、德國、土耳其、巴西等 17個國家檢出BToV[3-5,8-17],陽性率為1.74%~43.20%。血清學檢測結果表明該病毒已經在歐美國家廣泛流行,來自荷蘭和德國的成年牛血清樣本中,BToV抗體陽性率高達94%[38],在美國,BToV抗體陽性率也高達88.5%~89.7%[23],而在英國,BToV抗體陽性率為55%[39]。分析GenBank中現有的39個BToVHE基因,目前世界各國流行的毒株主要為基因Ⅱ型和Ⅲ毒株[11,14,19-20],其中最早登錄的3個BToV毒株均為基因Ⅰ型毒株,報道于加拿大[22]、美國[26]和荷蘭(GenBank登錄號: Y10866.1);基因Ⅱ型毒株現有24個,主要報道于日本[2]、中國[11]和荷蘭[14]等國;基因Ⅲ型毒株共12個,僅在中國[21]、土耳其(GenBank登錄號:MG957145.1)和荷蘭[14]有報道。
2.2 國內流行情況
國內關于BToV檢測報道較少[11,13,21],師志海等[13]從河南地區的奶牛和肉牛中檢測到BToV,陽性率分別為4.07%和3.06%。本實驗室也從四川、陜西、遼寧奶牛中檢出BToV,陽性率為5.12%~69.56%,并且從四川陽性樣本中鑒定出基因Ⅱ型毒株[11]。本實驗室近期還在來自西藏、青海、四川藏區牦牛腹瀉樣本中檢出BToV,陽性率為3%~11.8%[21],并從西藏牦牛腹瀉樣本中鑒定出BToV基因Ⅲ型毒株。可見BToV已經在國內牛群中存在和流行,未來應進一步關注該病毒在牛腹瀉中的生物學意義。
3 所致疾病的臨床癥狀與病理變化
BToV主要引起犢牛腹瀉,也可導致成年牛腹瀉[1-2]。盡管目前還無使用BToV細胞分離株人工感染牛的報道,但使用排除其他病原的BToV陽性腹瀉糞便過濾物灌喂8日齡以內的犢牛后,24 h即出現腹瀉癥狀,觀察到綠黃軟糞或深棕色的水樣糞便,隨后腹瀉加重并伴有脫水癥狀,96 h時開始死亡。對其腸黏膜組織進行病理學檢查,發現犢牛感染BToV后空腸、回腸、盲腸等腸道黏膜均有不同程度病變,大腸部分區域壞死、部分細胞出現空泡變性、壞死,腸絨毛萎縮和融合等,因此證實該病毒是一種致牛腹瀉病原[1,23,37]。BToV也可在具有呼吸道病癥的牛呼吸道樣本中檢出[3],但其與呼吸道疾病的相關性還有待證實。
4 BToV的檢測技術
4.1 病原檢測
4.1.1 電鏡觀察 電鏡是觀察 BToV 最直接的方法,BToV 病毒粒子在電鏡下形態呈圓形或腎形等,具有多形性[23]。該病毒可使用免疫電鏡技術(IEM)進行特異性鑒定[5]。
4.1.2 PCR檢測 針對BToV的檢測主要依靠RT-PCR和Real-time RT-PCR方法。目前已報道的有6種普通RT-PCR檢測方法和4種巢式RT-PCR檢測方法[8,10-11,17,40-43],以及2種Real-time RT-PCR方法[44-45]。其中靶向S基因的檢測方法有5種[17,40-43],靶向M基因有4種[10-11,42,44],靶向N基因有3種[8,42,45]。與Real-time RT-PCR方法相比,RT-PCR方法和巢式RT-PCR的引物所擴增片段較長,既能用于檢測又能用于遺傳進化分析;但是RT-PCR方法的靈敏度低于Real-time RT-PCR方法,且不能用于定量檢測。
本實驗室前期研究發現國外報道的RT-PCR[10,42]和Real-time RT-PCR方法[45]對國內BToV毒株的檢出效果并不理想,可能是國內BToV毒株在國外檢測引物的擴增位點上具有不同程度的核苷酸突變。有研究表明,由于S基因編碼的纖突蛋白位于病毒粒子表面,容易受環境壓力影響而發生突變,不宜作為檢測靶標基因[42],而M基因和N基因的保守性更為突出,適宜作為檢測靶標基因[42]。因此,人們重新建立了靶向M基因的RT-PCR方法[11],該方法檢測結果優于國外報道的PCR方法[10,42,45],可用于檢測國內BToV毒株。
4.1.3 分離培養 前期研究表明,BToV只能在日本學者Aita等[2]篩選的特定HRT-18細胞克隆株(HRT-18 Aichi 克隆株)上進行分離培養,接種病毒后產生以細胞膨大(enlargement of cells)為特征的細胞病變,隨后細胞死亡脫落形成空斑[2,46-48],而對其他來源的HRT-18細胞以及Vero和MDBK傳代細胞不易感,無法分離培養[2]。
4.1.4 基于酶聯免疫吸附試驗的抗原檢測技術 1987年,Brown等[39]以豚鼠抗BToV血清作為一抗,牛抗BToV血清作為二抗建立了檢測BToV抗原的雙抗體夾心ELISA法;2003年Hoet等[41]將該方法進一步優化,對1999—2001年美國俄亥俄州地區259份牛糞便樣本進行檢測,BToV陽性率為9.7%。但由于BToV抗原制備困難,且糞便背景值較高,容易對檢測造成干擾,因此該檢測方法并不廣泛適用。
4.2 抗體檢測
目前,只有一種基于酶聯免疫吸附試驗的抗體檢測方法報道。1987年Brown等[39]以牛抗BToV血清為一抗,從糞便中純化得到的BToV作為抗原建立了檢測BToV抗體的競爭ELISA法;1989年Koopmans等[38]對該方法進一步優化,對1985年期間荷蘭的1 313份牛血清和德國的716份牛血清進行BToV抗體檢測,陽性率分別高達94%和90%,表明該病毒已經存在廣泛流行。但由于BToV抗原分離純化困難,該方法并未得到廣泛應用。
5 防控措施
目前,尚無針對BToV的任何疫苗,也沒有特異性的治療抗體。犢牛及時飼喂初乳可獲得母源抗體保護,有效減少發病[23]。由于病牛糞便是主要傳染源,隔離病牛,做好環境消毒是預防該病的重要措施[23]。對于病牛和脫水嚴重的牛應及時補液,調節酸堿平衡和電解質平衡,防止繼發感染[23]。
6 問題與展望
自1982年首次報道BToV以來,迄今已有38年歷史,但該病毒的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仍然薄弱[37,49]。首先,病毒的分離鑒定是病毒生物學特性和疫苗研究的基礎,進一步建立和優化BToV的分離培養體系是需要解決的問題。第二,BToV的S蛋白在病毒的感染過程中發揮重要作用,但關于S蛋白功能結構鑒定以及與宿主細胞受體的相互作用等研究還未見報道。第三,BToV與呼吸道疾病的相關性有待研究。第四,在國內仍然欠缺系統的BToV流行病學資料。因此,進一步開展上述領域的研究,對BToV的基礎生物學和應用研究有重要意義。
7 結 語
BToV在國內屬于新發現牛腹瀉病原,目前已在國內奶牛和牦牛中分別檢測到基因Ⅱ型和Ⅲ型毒株,但國內不同基因型毒株的流行情況仍不明確,相關防控措施仍比較欠缺。因此,進一步加強對國內BToV的病原生物學、流行病學、診斷和防控技術等研究對于牛腹瀉的防控具有重要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