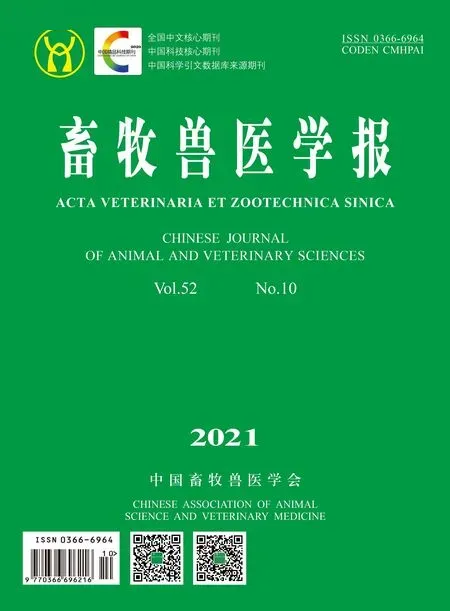A:L1 ST128型鴨源多殺性巴氏桿菌的耐藥性及毒力分析
張亞楠,李亞菲,陳汝佳,余 波,彭 珊,李 婷,蒲 齡,徐景峨*
(1. 貴州省農業科學院畜牧獸醫研究所,貴陽 550005; 2. 廣東省農業科學院農業質量標準與監測技術研究所,廣州 510640; 3. 貴州大學動物科學學院,貴陽 550025)
多殺性巴氏桿菌(Pasteurellamultocida)是革蘭陰性菌,能在世界范圍內引起多種動物疾病,如禽霍亂、豬萎縮性鼻炎、兔敗血癥和牛肺炎等[1-3],在某些情況下,還可通過動物咬傷或抓傷引起人類感染[4-5]。目前,由于缺乏有效的多血清型疫苗,抗生素仍是治療巴氏桿菌感染的首選方法[6],但隨著抗生素的不合理使用,多國出現了對包括頭孢噻呋、頭孢噻肟、頭孢曲松等第3代頭孢菌素類抗生素在內的多種抗菌藥物耐藥現象,這給抗菌藥物的使用帶來了嚴峻的挑戰[7-9]。
毒力因子是細菌入侵并在宿主體內增殖的關鍵因子,同時還具有較強的免疫原性[10]。毒力基因的豐度與細菌的致病性相關,目前已被證實與P.multocida致病性密切相關的毒力基因除莢膜(capsule)和脂多糖(lipopolysaccharide,LPS)相關基因外,還包括菌毛和黏附素(fimbriae and adhesins)、毒素(Pasteurellamultocidatoxin)、鐵調節蛋白和鐵獲取蛋白(iron regulation and iron acquisition proteins)、唾液酸代謝相關蛋白(sialic acid metabolism)、透明質酸酶(hyaluronidases)及外膜蛋白(outer membrane proteins)的毒力基因[3,11]。其中,莢膜可增強P.multocida的侵襲力和繁殖能力,由莢膜編碼基因簇編碼,該區域分為3個功能區(莢膜多糖輸出區、莢膜合成區和莢膜多糖磷脂替換區),按照結構可分為5種不同的莢膜基因型(A、B、D、E、F)[12];按照每個區域的基因數目,可分成兩大類:A、D、F型一類,10個編碼基因緊密相鄰;B和E型為另一類,15個編碼基因,在莢膜多糖輸出區分散排列[13]。LPS有黏附、侵入和抗血清的作用,其致病作用跟LPS的完整性相關[14-15]。LPS由類脂A和核心寡糖組成,根據核心寡糖外核基因在不同菌株間的差異可分為8個LPS基因型,即L1~L8[16]。此外,菌毛和黏附素在P.multocida感染致病過程中扮演著十分關鍵的作用,能黏附并定植于宿主細胞或組織,如IV型菌毛亞單位蛋白(由ptfA基因編碼)、黏附相關蛋白(包括FimA、ComE1、FhaB、Flp1、Flp2、Hsf_1、Hsf_2、TadG、TadF、TadF、RcpB等)、菌毛低分子蛋白(fimbrial low-molecular-weight protein, Flp)(由Flp操縱子基因編碼)等[11]。在P.multocida流行病學研究中,基于不同毒力基因譜檢測的毒力基因分型已發展成為一種有用的基因分型方法,因此對于鴨源P.multocida毒力基因多樣性的檢測顯得尤為重要[17]。
P.multocida分離株的感染表現出宿主偏好,如A:L1:ST129、D:L6:ST50、A:L3:ST9分別在禽類、豬、兔的感染中占優勢[3]。應用莢膜基因型、LPS基因型和多位點序列分型(multilocus sequence typing, MLST)相結合的基因分型方法將有助于臨床分離株的鑒定,為研究P.multocida的全球流行性和分子進化提供依據[17]。
本研究從貴州省出現的疑似禽霍亂的56日齡的病(死)花邊鴨組織中分離得到5株P.multocida,對分離株進行分子生物學鑒定,同時采用細菌全基因組測序技術對分離得到的P.multocida強毒株PmCW1進行測序,并對其耐藥基因及毒力基因進行分析,探究分離株的生物學、毒力及耐藥特征,對鴨霍亂的臨床用藥及疫苗研發具有一定指導意義。
1 材料與方法
1.1 主要儀器與試劑
胰蛋白胨大豆瓊脂培養基(TSA)、胰蛋白胨大豆肉湯(TSB)等購自青島海博生物生物技術有限公司;新生牛血清購自北京鼎國昌盛生物技術有限責任公司;無菌脫纖維綿羊血購自北京索萊寶科技有限公司;細菌基因組DNA提取試劑盒購自天根生化科技有限公司;DL2000 DNA Marker、Premix Taq (EXTaqversion 2.0 plus dye)等購自寶生物(大連)工程有限公司;瓊脂糖,購自Oxoid公司。普通梯度PCR儀、核酸電泳儀、凝膠成像系統,均購自Bio-Rad公司;超凈工作臺,購自蘇州凈化設備有限公司。
1.2 菌株的分離與鑒定
2020年6月,貴州省三穗縣某鴨場56日齡花邊鴨群3 000余羽,3 d內發病死亡1 185羽,疑似感染禽霍亂,從典型的臨床癥狀和剖檢癥狀的病死鴨中,隨機無菌采集5只病(死)鴨的腦和肝組織分別進行細菌的分離,觀察菌株在含有5%新生牛血清的TSA平板及鮮血瓊脂平板上的生長情況并進行菌株的純化。采用kmt1基因特異性PCR方法進行分子生物學鑒定,測序并Blast分析,以確認其多殺性。引物序列:kmt1-F(5′-ACCGACAAGCCCACTCACAACA-3′);kmt1-R(5′-ATCATCCTAACCGCCTGAAAGC-3′)。
根據Townsend等[12]報道的莢膜基因型分型方法和Harper等[16]建立的脂多糖基因型分型方法,送生工生物工程(上海)股份有限公司合成PCR引物。PCR產物經1%瓊脂糖進行凝膠電泳分析。
采用文獻[12-13]報道的腸桿菌科細菌基因間重復序列聚合酶鏈式反應(enterobacterial repetitive intergenic consensus sequence,ERIC)-PCR方法鑒定5株分離株的同源性。
1.3 多位點序列分型法(MLST)
本研究采用多宿主來源P.multocidaMLST數據庫(Multiple host MLST database)對5株分離株進行MLST分型。根據P.multocidaMLST官網(http://pubmLst.org/pmultocida_multihost)上推薦的PCR方法分別擴增7個管家基因(adk、aroA、deoD、gdhA、g6pd、mdh、pgi)。PCR產物利用1%瓊脂糖進行凝膠電泳分析,條帶大小正確的擴增產物送往生工生物工程(上海)股份有限公司利用對應的測序引物進行測序,并將序列提交至Multiple host MLST database進行MLST基因分型。
1.4 動物回歸試驗
健康未接種禽巴氏桿菌疫苗的15日齡三穗鴨24只,隨機分成6組,每組4只,公母各半。5組試驗組分別肌肉接種P.multocida分離菌懸液,0.2 mL·只-1, 濃度依次為1.1×102、1.1×103、1.1×104、1.1×105、1.1×106cfu·mL-1,對照組注射等量生理鹽水,逐日觀察動物發病及死亡情況,及時對死亡鴨進行剖檢、觀察,并進行病原菌的分離鑒定,同時采用ERIC-PCR方法鑒定攻毒前、后分離株的同源性。
1.5 藥物敏感性試驗
參照美國臨床實驗室標準協會(CLSI)標準[18],采用微量肉湯二倍稀釋法測定18種抗菌藥物的MIC值,被測試的抗菌藥物包括阿莫西林、氨芐西林、頭孢噻肟、頭孢曲松、頭孢噻呋、頭孢他啶、黏菌素、鏈霉素、慶大霉素、阿米卡星、環丙沙星、左氧氟沙星、恩諾沙星、林可霉素、紅霉素、阿奇霉素、氟苯尼考和多西環素(北京索萊寶科技有限公司,中國)。以大腸埃希菌ATCC?25922和金黃色葡萄球菌ATCC?29213作為質控菌。
1.6 全基因組測序與耐藥性、毒力性分析
用細菌基因組DNA提取試劑盒提取PmCW1基因組DNA,提取的基因組DNA樣品由北京諾禾致源基因科技有限公司進行全基因組測序。基因組測序在Nanopore ProMethation和Illumina NovaSeq PE150上進行;使用Unicycler軟件[19](https://github.com/rrwick/Unicycler)用于基因組組裝。使用GeneMarkS(Version 4.17)[20](http://topaz.gatech.edu /GeneMark/)軟件對新測序的基因組進行編碼基因預測。使用Comprehensive Antibiotic Research Database(CARD)數據庫(https://card.mcmaster.ca/)提供的Resistance Gene Identifier(RGI)軟件將PmCW1的氨基酸序列與CARD數據庫進行比對(RGI內置blastp,默認e value≤1×10-30),根據RGI的比對結果,統計注釋到數據庫的抗性基因信息。對注釋得到的PmCW1耐藥基因與其耐藥表型進行比較分析,分析其耐藥表型和耐藥性的關系。使用Diamond軟件[21],把目標物種的氨基酸序列與Virulence Factors of Pathogenic Bacteria(VFDB)數據庫(http://www.mgc.ac.cn/ VFs/)進行比對,把目標物種的基因和其相對應的毒力因子功能注釋信息結合起來,得到注釋結果。使用Easyfig[22](http://mjsull.github.io/ Easyfig/)分析PmCW1毒力相關的脂多糖核心寡糖外核、莢膜編碼基因簇及Flp操縱子基因簇與HN141014(LUCX00000000)、P1059(CM001581)、Pm70(AE004439)、ATCC1702(LUDD00000000)及HN06(CP003313)之間基因結構與同源性的差異。
2 結 果
2.1 菌株的分離鑒定
2020年6月,從5只病(死)鴨的腦和肝中均分離出較純的巴氏桿菌,同一個體不同部位分離出來的菌株算作1株,共分離得到5株巴氏桿菌。在含5%新生牛血清的TSA平板上生長良好,在鮮血平板上長成水滴狀小菌落,不溶血(圖1)。kmt1-PCR擴增結果與預期相符(圖2),測序結果與NCBI公布的kmt1基因序列比對,相似性達99%以上,確定5株均為多殺性巴氏桿菌。從ERIC-PCR的電泳結果(圖3)可以看出,本次分離得到的5株菌具有相同的擴增片段,表明菌株間同源性高,克隆傳播的可能性大。

a.含5%新生牛血清的TSA平板;b.鮮血平板a.TSA plate containing 5% newborn bovine serum; b.Blood plate圖1 鴨源巴氏桿菌在不同培養基上的菌落形態Fig.1 Colony morphology of Pasteurella from ducks on different media

M. DL2000 DNA相對分子質量標準;1~5.PmCW1~5;6~10.陰性對照M. DL2000 DNA marker; 1-5. PmCW1-5; 6-10. Negative control圖2 kmt1-PCR鑒定結果Fig.2 Results of kmt1-PCR identification

M.DL5000 DNA相對分子質量標準;1~5.PmCW1~5M.DL5000 DNA marker; 1-5.PmCW1-5 respectively圖3 5株巴氏桿菌分離株的ERIC-PCR結果Fig.3 ERIC-PCR results of five P. multocida isolates
2.2 莢膜基因型:脂多糖基因型和MLST分型
利用PCR方法對5株菌進行血清基因型鑒定,結果顯示均為A:L1型(圖4)。對5株菌分別進行7個管家基因的擴增和測序,測序結果提交至http://pubmLst.org/pmultocida_multihost,結果顯示,5株均為ST128型,圖5為MLST所用7個管家基因PCR陽性圖。
2.3 動物回歸試驗
P.multocidaPmCW1動物回歸試驗結果顯示,1.1×104、1.1×105、1.1×106這三個試驗組中鴨12 h內全部死亡,24 h內5組試驗組鴨全部死亡,對照組正常。死亡鴨剖檢觀察到全身性出血(圖6),分離鑒定結果顯示在5%新生牛血清的TSA平板均有較純的菌落生長,經菌落PCR鑒定均為P.multocida。同時,ERIC-PCR鑒定結果顯示與攻毒所用的PmCW1具有相同的擴增片段,可以判定為同一株P.multocida(圖7)。

M.DL2000 DNA相對分子質量標準;1~5.PmCW1-5;6~7(圖a)/6(圖b).陰性對照M.DL2000 DNA marker; 1-5.PmCW1-5 respectively; 6-7(Fig.a)/6(Fig.b).Negative control圖4 莢膜基因型(a)和脂多糖基因型(b)PCR結果Fig.4 PCR for Capsules genotype (a) and lipopolysaccharide genotype(b)

M.DL2000 DNA相對分子質量標準;1~7.deoD、gdhA、g6pd、adk、pgi、mdh、aroA基因陽性結果M.DL2000 DNA marker;1-7 are positive results of deoD,gdhA,g6pd,adk,pgi,mdh,aroA gene,respectively圖5 MLST所用7個管家基因PCR陽性圖Fig.5 Positive PCR results of seven housekeeping genes used in MLST
2.4 藥物敏感性試驗
由表1可見,在對5株菌進行18種抗菌藥物敏感性檢測中,阿莫西林的MIC值最高,均>128 mg·L-1; 其次為鏈霉素,MIC值為32~8 mg·L-1; 后面依次為林可霉素(MIC值均為8 mg·L-1)、 阿米卡星(MIC值為8~2 mg·L-1)、氨芐西林(MIC值為4~2 mg·L-1);對黏菌素的MIC值差異較大,MIC最大值為4 mg·L-1(PmCW1),而最小的則為<0.06 mg·L-1(PmCW5),存在至少64倍的差異;對慶大霉素的MIC值,除PmCW1為2 mg·L-1,其余均為1 mg·L-1;5株菌對其余11種 抗菌藥物的MIC值均≤0.5 mg·L-1。

表1 抗菌藥物對5株鴨源多殺性巴氏桿菌的MIC值
受試藥物的耐藥折點值判斷標準主要參考CLSI VET01-S中描述的值,CLSI VET01-S未給出的則參考歐盟委員會藥物敏感性測驗(EUCAST)標準[23]。5株菌均對氨芐西林、阿莫西林、左氧氟沙星和林可霉素4種藥物耐藥,其中PmCW1還對環丙沙星低水平耐藥。
2.5 PmCW1抗性基因的分析
通過對PmCW1基因組測序數據分析發現,該菌存在多個耐藥基因,包括2個β-內酰胺類耐藥基因(青霉素結合蛋白pbp2和pbp1a),5個四環素耐藥基因(tetA、tetB、tetT、tet34、tet35),1個磷霉素耐藥基因(murA),1個磺胺類耐藥基因(sul3),1個維吉尼亞霉素乙酰轉移酶vatB,1個甲氧芐啶耐藥基因(dfrA3),1個廣譜抗菌劑三氯生耐藥基因fabI,3個多黏菌素抗性決定區基因(PmrE、PmrC和basS)。同時檢測到9個抗生素耐藥基因簇/操縱子(CpxR、vanRE、vanRN、vanTrL、vanHA、vanHB、vanL、mecC、arlR)和18個與外排泵復合體相關的基因(mdtk、bcr-1、cmeC、cpxA、CRP、farB、hmrM、H-NS、macA、macB、MexI、MexV、msbA、msrB、opmE、patA、sav1866、TaeA),它們介導對多種抗生素耐藥。此外,還預測出4個喹諾酮耐藥決定區基因(gyrA、gyrB、parC、parE)和1個與氟喹諾酮耐藥相關基因mfd,經比對發現gyrA的80位出現突變(Ser80Gly)、parC的84位出現突變(Leu84Ser)。

a.心、肺出血;b.肝出血、壞死;c.腸道彌漫性出血a. Heart and lung bleeding; b. Liver hemorrhage and necrosis; c. Diffuse intestinal bleeding圖6 攻毒致死鴨的剖檢圖Fig.6 Necropsy diagram of ducks killed by challenge poison

M.DL5000 DNA相對分子質量標準;1.PmCW1;2~4.攻毒后分離株M.DL5000 DNA marker; 1. PmCW1; 2-4.Isolates after challenge圖7 攻毒前后分離株的ERIC-PCR結果Fig.7 ERIC-PCR results of isolates before and after challenge
2.6 PmCW1毒力基因的分析
經與VFDB數據庫比對,預測PmCW1中存在的毒力基因總數為201;根據毒力基因所屬類別名稱(即VF_name)進行歸類,毒力因子有71種;某類毒力基因的占比=(毒力基因所屬類別名稱即VF_name)÷(預測出來的毒力基因總數即201)×100%(圖8);如數量為1的即占比<1%,圖8中未將具體名稱列出。PmCW1中存在的主要是與脂寡糖/脂多糖(LOS/LPS)(galE、galU、gmhA、htrB、kdkA、kdsA、kdsB、kdtA、kpsF、lex2B、lgtF、licA、licC、lpxA、lpxB、lpxC、lpxD、lpxH、lpxK、lsgA、lsgD、lsgE、lsgF、msbA、msbB、neuA、rfaC、orfM、rfaD、rfaE、rfaF、rffG、waq、wecA、yhxB/manB等)、莢膜(capsule)(phyBA、hyaEDCB、hexDCBA、bexA、bexC、bexD等)、黏附因子(fimbriae and adhesins)(flp1-flp2-tadV-rcpCAB-tadZABCDEFG、ptfA、comEA、hofBC等)等相關基因,此外,還有鐵攝取相關蛋白基因(ccmABCEF、hgbBC、fur、hscB等)以及部分外膜蛋白基因(ompP5等),絕大多數在不同宿主來源的P.multocida中間高度保守。PmCW1中有些基因存在多個拷貝數,如脂寡糖/脂多糖相關基因rfaC存在2個拷貝、血紅素生物合成相關基因hemN存在2個拷貝等。

占比<1%的毒力因子名稱未列出The names of virulence factors with a percentage <1% are not listed圖8 PmCW1毒力決定因子Fig.8 PmCW1 virulence determining factor
2.7 P. multocida基因組局部區域比較分析
脂多糖變異區(即外部核心多糖編碼基因簇)比較基因組學分析顯示(圖9a),PmCW1(A:L1,ST128)與HN141014(A:L1,ST129)相比,它們之間基因結構一致;而與P1059(A:L3,ST8)、Pm70(F:L3,ST9)、ATCC1702(A:L2,ST156)相比,它們之間的變異區主要集中在hptE與priA基因之間,這一區間內的基因主要為糖基轉移酶編碼基因。
莢膜多糖磷脂替換區phyBA和莢膜多糖輸出區hexDCBA,在不同血清型之間高度保守,而合成區基因簇存在差異,A型由hyaEDCB基因編碼,D型由dcbEFCB基因編碼,F型由fcbEDCB基因編碼。PmCW1(A:L1,ST128)與HN141014(A:L1,ST129)、ATCC1702(A:L2,ST156)相比,各基因結構一致;與Pm70(F:L3,ST9)相比,除hyaD與fcbD的相似性為82.7%,其余各基因相似性均高于98.1%;與HN06(D:L6,ST50)相比,hyaED與dcbEF之間相似性在61.1%~50.4%,且HN06在phyBA和hyaED之間存在一個IS605/IS200家族轉座酶基因(圖9b)。
Flp操縱子由14個基因(flp1-flp2-tadV-rcpCAB-tadZABCDEFG)組成,承擔細菌的黏附功能。在本研究中分析5株巴氏桿菌Flp操縱子相似情況如圖9c所示,除Pm70(F:L3,ST9)缺失flp2基因,其余4株的Flp操縱子均是經典的14基因編碼組成。PmCW1(A:L1,ST128)的Flp操縱子與HN141014(A:L1,ST129)的各基因結構一致;與Pm70(F:L3,ST9)除了flp1基因外各基因相似性均高于82.0%;而與P1059(A:L3,ST8)、ATCC1702(A:L2,ST156)雖然基因結構一致,但基因相似性較低。

圖9 多殺性巴氏桿菌脂多糖核心寡糖外核(a)、莢膜合成區(b)及 Flp 操縱子(c)比較基因組學分析Fig.9 Comparative genomic analysis of LPS outer core biosynthesis gene clusters(a),capsular loci (b), and Flp-operons(c) among different P. multocida
3 討 論
莢膜和LPS對P.multocida的毒力和宿主特異性起著重要作用。本研究從貴州規模化鴨場分離得到5株鴨源P.multocida強毒株,經鑒定血清型(莢膜基因型:脂多糖基因型)為A:L1型,這與王林柏等[24]、Li等[25]報道的國內部分地區禽源P.multocida血清型主要為A:L1型的結果一致,也與Peng等[3]報道全球不同地區的流行情況相同,說明在全球范圍內流行的禽源P.multocida仍以A:L1型為主。需要注意的是,Ujvári等[26]、Ewers等[27]報道A:L1在貓和人分離株中最常見,Turni等[28]、Ujvári等[29]也報道過人類和各種動物物種之間存在P.multocida的共享基因型,同時還有報道[26]稱人類不是P.multocida的自然宿主,但是人類可能通過與家庭寵物或養殖場動物接觸而感染,造成不同血清型的P.multocida跨物種水平傳播到人類。
已有的流行病學調查數據表明,導致某些特定疾病的P.multocida集中于某一特定的ST型,例如有報道與出血性敗血癥相關的P.multocida多為ST122,而與禽霍亂相關P.multocida多為ST129[30-31]。這些結果意味著P.multocida的ST型與疾病之間也可能存在一定的相關性。目前無論是我國還是全球范圍內禽源P.multocida的多位點序列分型以ST129型為主,偶見ST122、ST107、ST6、ST44、ST8、ST58等[1,24,32-33]。本研究分離得到的鴨源P.multocida均為ST128型,這在禽源P.multocida中鮮有報道,提示在貴州地區鴨源P.multocida出現了不同于全國流行的ST型。
本研究中P.multocida分離株僅對氨芐西林、阿莫西林、左氧氟沙星、林可霉素和環丙沙星5種藥物耐藥,不同于陳國權等[34]、Holschbach等[7]報道的P.multocida分離株耐藥性嚴重,說明P.multocida的耐藥性受地理位置、用藥史、管理水平及環境等多方面因素影響。對食品動物上禁用抗生素(如頭孢曲松、頭孢噻肟、頭孢他啶、阿奇霉素等)的MIC值較低,說明此規模化鴨場對抗菌藥物的使用相對合理。同時結合采樣調研,說明此鴨場未亂用這些抗生素。本研究中的分離株ST型相同,但藥敏試驗結果存在差異,如不同菌株對黏菌素的MIC值存在至少64倍的差異,這可能與在動物體內不同抗生素壓力下的選擇作用有關。
PmCW1的耐藥表型與耐藥基因檢測結果基本相符,如PmCW1中僅存在2個β-內酰胺類耐藥基因(青霉素結合蛋白pbp2和pbp1a),這與PmCW1對青霉素類藥物氨芐西林和半合成青霉素類藥物阿莫西林均耐藥,而對其他4種三代頭孢菌素類藥物MIC值均<0.06 mg·L-1的結果相一致。喹諾酮耐藥決定區(QRDR)靶位基因突變通常定位于gyrA(第67-106位)或parC(第63-102位)的氨基末端結構域,gyrB和parE的突變也會導致喹諾酮類藥物耐藥,但突變頻率相對少[35]。本研究中發現PmCW1的QRDR存在突變,gyrA的80位出現突變(Ser80Gly)和parC的84位出現突變(Leu84Ser),Kong等[36]也報道過P.multocida中parC的84位突變,這可能是PmCW1對喹諾酮類藥物耐藥的原因之一。此外,還預測到1個與氟喹諾酮耐藥相關基因mfd,在空腸彎曲桿菌中mfd的過度表達提高了環丙沙星耐藥性的自發突變率,mfd對氟喹諾酮類藥物耐藥性的產生中起重要作用[37],但mfd在P.multocida中對氟喹諾酮類藥物耐藥性的作用還需要進一步驗證。
在流行病學研究中,毒力基因分型已發展成為一種有用的基因分型方法,所用基因一部分為P.multocida的廣泛特征基因,它們在不同基因型和/或不同寄主種類的菌株中具有較高的檢出率,如ptfA、fimA、hsf-2、exbB、exbD、tonB、fur、sodA、sodC、ompA、ompH、oma87和plpB等;另一部分毒力基因只在有限數量的分離株中檢測到,這主要與特定類型的疾病和/或某些寄主物種有關,例如toxA只在與進行性萎縮性鼻炎相關的菌株中發現,而tbpA只在牛和羊源的分離株中發現[17]。本研究中預測到參與編碼PmCW1的毒力基因有201個,除莢膜、LPS和Flp相關基因外,還有IV型菌毛基因(ptfA、comE、hofB、hofC、vfr)、鐵攝取相關蛋白(ccmABCEF、hgbBC、fur、hscB等)以及部分外膜蛋白(ompP5等)等重要毒力基因。IV型菌毛基因ptfA已經在莢膜A型、B型和D型菌株中被發現[38],ptfA和comE編碼的假定蛋白與菌毛幫助P.multocida黏附到宿主細胞上面,這與在其他細菌中發現的黏附素結構相似[39];ccmABCDEF操縱子,編碼參與血紅素翻譯后附著的蛋白質,在大腸桿菌中也有發現[40];fur編碼鐵攝取調節因子Fur,與在胸膜肺炎放線桿菌中發現的相似[41];這些毒力基因的存在、缺失或豐度可能受到寄主、地理位置或環境因素的影響,對P.multocida毒力的增強、減弱具有一定的作用。
通過局部比較基因組學分析顯示,強毒株PmCW1在脂多糖變異區和莢膜合成區的基因簇與A:L1型P.multocida各基因結構一致,說明PmCW1具有典型的A:L1型P.multocida的特征。脂多糖變異區(即外部核心多糖編碼基因簇)常位于兩個保守基因fpg和priA之間[42],而在本研究中,L1型與其他兩種LSP型(L2、L3型)菌株間差異區縮小,主要集中在hptE和priA之間,這種差異可能是引起P.multocida菌體脂多糖血清型不同的原因[43]。值得注意的是rpmE基因在不同菌株間相似性高于90%,且在hptE和priA之間隨機排列。對莢膜合成區進行比較,發現A型與D型的各基因結構及相似性差異大,而A型與F型的差異非常小,這可能與P.multocida分離株感染的宿主偏好性有關,如A型和F型常引起禽類的感染,D型在豬的感染中占優勢[3]。Flp操縱子通常由14個基因編碼,但也存在部分基因缺失的情況[44],如禽源弱毒株Pm70(F:L3,ST9)的Flp操縱子缺失flp2基因;PmCW1具有經典的14基因編碼,與其余4株A型P.multocida之間基因結構相同,但相似性存在差異。本研究系統分析了鴨源A:L1,ST128型P.multocida強毒株PmCW1的耐藥性及毒力特征,為貴州地區鴨霍亂的臨床用藥及疫苗研發提供理論依據。
4 結 論
通過對臨床疑似鴨霍亂的病原菌進行系統研究,發現在鴨源P.multocida鮮有報道的ST128型PmCW1,且為強毒株。PmCW1攜帶多種耐藥基因(pbp2、pbp1a、tetA、tetB、tetT、tet34、tet35、sul3以及dfrA3)介導對青霉素類、四環素類、磺胺類以及甲氧芐啶等藥物耐藥;此外,還存在耐藥基因簇/操縱子和外排泵復合體相關的基因,可介導P.multocida對多種抗生素耐藥。PmCW1具有典型的A:L1型P.multocida的特征,毒力基因主要是脂寡糖/脂多糖(LOS/LPS)、莢膜、黏附因子等相關編碼基因;此外,還檢測到還有IV型菌毛基因(ptfA、comE、hofB、hofC、vfr)、鐵攝取相關蛋白(ccmABCEF、hgbBC、fur、hscB等)以及部分外膜蛋白(ompP5等)等重要毒力基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