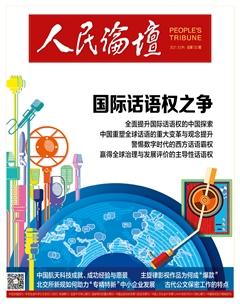城市人才流動新動向新特征與新動能
袁方成
【關鍵詞】城市 人才流動 人口 地方政府 高質量發展 【中圖分類號】C912.81 【文獻標識碼】A
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提出,要“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城市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增長極,具備較完善的基礎設施支撐體系與強大的內需潛力,是構建國內大循環的前沿區域。人才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第一資源,是人力資源中能力、素質較高的勞動者,在推進城市治理更新、驅動區域產業創新、激活新發展格局、推動高質量發展中具引擎作用。
城市人才流動聚集的方位脈絡,對打造高質量發展的新發展格局具有重要影響。自2010年《國家中長期人才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提出以來,“人才強國”正式成為我國國家戰略目標之一。伴隨2016年《中共中央關于深化人才發展體制機制改革的意見》的出臺,不少地方自主性引才聚才政策不斷創新,其中多數強調要著力吸納45歲以下、學歷在本科或專科以上的高、專、精、缺人才,旨在以“人才新政”提升優質人才聚集力、增強城市競爭力。“人才新政”在引才聚能過程中作用顯著,但也存在如“重單次補貼,輕薪酬預期”的結構失衡問題,“重學歷輕應用、重理輕文”的行為主體角色錯位問題,制度規范滯后、政策效用單一等競爭性、壁壘性問題。2019年底,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關于促進勞動力和人才社會性流動體制機制改革的意見》,為城市人才流動提供新的政策指引,強調構建合理、公正、暢通、有序的社會性流動格局,破除妨礙勞動力、人才社會性流動的體制機制弊端,既要以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為主體構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格局,拓寬人才城市間流動空間;也要為基層人才、技術技能人才拓展社會性流動空間。在“十四五”時期,需注重在大局視野下深化推進城市人才工作良序開展。
立足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系統把握我國城市人才流動的新趨勢新動向、新局勢新動能、新階段新路徑,有助于明晰我國城市發展與人才流動的基本關系與重點走向,推進創新驅動發展戰略,面向“城才”政策短板弱項,為實現城市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注入新興變革動力。
城市人才流動的新動向和新特征:聚合中開全域
2021年是“十四五”規劃的開局之年,我國城市經濟社會發展也同步進入新階段。面向新起點,城市人才流動趨勢承上啟下,總體呈現“跨域多核加速集聚、青年群體化身主角、行業跨界拓土納新”的格局特征,在聚合中實現人才流動方向的“邊際擴展”。
第一,因勢利導,跨域多核加速集聚。人口流動情況是人才流動的宏觀鏡像,集中反映了人才跨域流動的一般性規律——跨域多中心流動成為新趨勢。2021年5月,我國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以下簡稱“七普”)主要數據發布。數據顯示,我國人口總量為141178萬人,其中,東部地區人口接近總人口數量的四分之一,為39.93%;中部地區與西部地區各占比25.83%、27.12%,東北地區人口占比不足一成(見圖1)。與2010年相比,東部地區人口所占比重上升2.15個百分點,人口向經濟發達區域、城市群進一步集聚。
圖1 2020年“七普”區域人口數量占比統計

根據2010年、2019年《中國城市建設統計年鑒》中的城區人口數據清單,以我國的現行城市規模標準進行區分統計,可觀察到,與《國家中長期人才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始發年份相比,2019年我國城區人口數量體現由中小城市向大城市及以上規模城市“加速集中靠攏”趨勢。城區人口超過100萬的大城市數量同比增長23個,屬同期增幅最高(見表1)。其中,除一線城市外,成都、西安、鄭州、杭州、重慶、長沙、武漢、佛山、蘇州等新一線城市成為我國流動人口“大面積落地”的多所新巢,人口增量與增幅較為龐大(見表2)。
表1 2010年、2019年各等級城市人口數量變化

表2 2010年、2020年全國人口普查數據

人才流動在人口流動的一般性規律下,同步呈現兩大現實態勢:
一是加速向重點都市圈與城市群靠攏匯流。2017年-2020年人才跨域求職數據顯示,60%以上人才流向五大城市群(見圖2)。其中,長三角、珠三角、成渝地區人才凈流入占比分別為 6.4%、3.8%、0.1%,兩大“三角”地區成為人才流入的集中區域。京津冀、長江中游地區人才整體“凈流出”,占比分別0.7%、1.2%。
圖2 “五大城市群”人才流動數據(2017年-202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