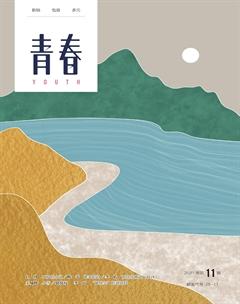網文如何書寫現實?
當下,網絡文學的現實化轉向是網絡文學發展的一個突出現象。但網絡文學書寫現實,是否意味著網絡文學對傳統文學現實主義寫作的回歸?網絡文學在表達現實方面,是否有屬于自己的,并且極為重要的特征?
驍騎校是較早嘗試都市現實題材并獲得成功的作家。他的《橙紅年代》爆紅,《匹夫的逆襲》乃都市題材口碑之作,《長樂里:盛世如我愿》是2020年度中國作協網絡文學影響力上榜作品。這也是對他現實題材創作的肯定。驍騎校的創作不乏網文元素,穿越、異能、金手指、主角光環,他的作品創造了現代都市的幻想空間,但同時,我們知道“橙紅宇宙”不是無本之木,它具有物質性——甚至這種“物質性”較之諸多傳統文學更具體、更現實。即使驍騎校添加了諸多理想化的想象,這種想象也毋寧說是對于現實的心靈再現。按照驍騎校的文本,我們在徐州考察了作品中出現的地名和區域,尋找到美好理想的現實根基。在驍騎校所繪制的文學地圖上,一切物象依然真實而鮮活。
鐵渣街與黃花小區
《匹夫的逆襲》里有一個地方叫“鐵渣街”,小說中有這樣的描寫:“這里是近江市的東南角,十年前還是農村田地,近年來城市擴大規模,房地產業大發展,農田變成了小區,原來的村莊變成了亂搭亂建藏污納垢的城中村,到處是出租屋和洗頭房,路燈桿上貼滿野廣告,空中電線交織如同亂麻。”這個名字源自日本動漫《銃夢》,也取材于驍騎校在徐州時的家。
鐵渣街有跡可循。在徐州云龍區玄武路31號,有一條街叫“鐵貨街”,由于種種原因至今仍未拆遷,保留著幾十年前的樣貌。現在鐵貨街里基本上都是出租房,很多人在這里做小本生意,巷道里堆滿了貨物和垃圾,陽光很難照射到窄小陰暗的屋子里,日子并不好過。鐵貨街在幾十年前屬于城鄉接合部,街的北面就是黃河,每到下雨天,由于排水系統以及排水措施不到位,巷道里面會積滿水,水線有時能達到人的膝蓋位置。從部分石階上的青苔以及水痕可以窺見這里在斑駁歲月中延續不斷的生命力。
《匹夫的逆襲》第三卷第六十五章“百姓兇猛”中提到,“手下們沖上去猛踹防盜門,這扇門是那種簡陋的鐵欄桿防盜門,用膨脹螺絲固定在磚混的墻壁上,七八十年代的老房子早已年久失修,兩下就踹開了,暴徒們一擁而入”。這里所描寫的鐵欄桿防盜網與鐵貨街現存的防盜門如出一轍。鐵貨街原來是山東、河南以及安徽一帶由于黃河泛濫被逼離家而來的逃難者的聚集地,他們無法進城,只能在這扎堆過活,搭起大棚,以販賣鐵器為生。很多鐵器都是日本人退出徐州之后留下來的廢銅爛鐵,由這些難民加工之后生產出來的,其中大部分被用來制作防盜門窗。這里人人都要養家糊口,沒有本事的人只能以偷竊為生,現在鐵貨街原址依舊保留了很多銹跡斑斑的防盜門窗,鐵貨街附近也有以制作防盜門窗為生的小商販。
鐵貨街的門面有兩種,一種是上文提到的做防盜門窗的,另一種就是掛紅燈的。那時候的鐵貨街生活著一群沒有經濟來源的未婚女性,只能通過一些特殊渠道來養活自己。驍騎校的小說里多次提到此類現象,比如《匹夫的逆襲》第一卷第二十七章“十元休閑”:“結了賬,兩人走在鐵渣街的夜路上,普通店鋪都關門上板了,只剩下‘夫妻保健和‘十元休閑的招牌亮著曖昧的紅燈。”他將這里的混亂與復雜書寫得淋漓盡致,這是無奈,也是人性的倔強。
第四卷第四十五章“刀仔”里有這樣一段:“區政府一幫領導分析認為,重中之重在于城鄉接合部的鐵渣街,這里向來是城管執法的難點,流動攤販多,占道經營嚴重,而且盡是外來人口,潑婦刁民,不服管教,執法難度很大,不下猛藥不行。劉飛市長是個眼里不揉沙子的人,視察調研,從不按照下面人預定的路線進行,想玩虛的只會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所以必須全面鋪開,不留死角,搞一次聲勢浩大的綜合治理,預先把不安定因素都解決掉。”其中,“城鄉接合部”“流動攤販”“占道經營”“外來人口”等都與鐵貨街的歷史面貌相符合。
其實在鐵貨街的南面不遠處就是金谷里,從前著名的一條娛樂街區,現在改名為“新生里”,在徐州市云龍區黃河西路112號。這里已經拆遷了一半,但仍然保留了一小部分原貌。金谷里曾是國民黨統治時期建立的軍妓所,從外圍能看到一座高塔,那是監視妓女以及外來人員的瞭望臺,至今仍保存得很好。金谷里的老房子基本上都有一截露在外面的水管,這里很早就通了自來水,但是并沒有下水道,需要用水管把廢水排到室外。
驍騎校曾經提到過這樣一個故事:一個修鞋的,有一天在這里撿了一個跑來的瘋女人當老婆。他聽到時覺得很震驚,但當時這種事情在鐵貨街和金谷里時有發生。
金谷里的外圍有很多商販,大型貨車上堆滿了貨物,每輛貨車上都貼著各種各樣的物流廣告,是一個小型的配貨站,這又與《匹夫的逆襲》第七卷第三十章“送貨”里“鐵渣街緊挨著四環路,路邊有許多配貨站,向全省二級經銷商發貨就靠這些價廉方便的配貨站,雖然速度和安全性比不上正規物流,勝在價格便宜”這一段不謀而合。
文中,男主人公劉漢東的家位于一個叫“黃花小區”的地方。該小區現已不可考,唯一名字相近的便是“火花小區”,在徐州泉山區火花街道188號。火花小區幾年前已經拆遷,現地名為“火花街道辦事處”。
不過,我們在《匹夫的逆襲》第四卷第四十五章“刀仔”看到有關“火花辦事處”的描述:“星期天中午,火花辦事處城管中隊開始在鐵渣街整頓,三十名城管隊員在數名派出所民警協同下從北頭到南頭拉網式清理,后面跟著兩輛白色長安面包車和一輛車門上噴著行政執法字樣的卡車,遇到不配合的,城管們也不打也不罵,一群人上去圍起來,雙目注視,直到對方配合,攝像機全程拍攝。”這里提到了“火花辦事處”,也就是現在的“火花街道辦”;第八卷第八章“胃出血”里:“‘我還真有幾個問題想問大家,你們有住花火村、鐵渣街的嗎?” 這里提到的“花火村”其實就是“火花村”,在十幾年前,確實是叫“花火村”,后來更名為“火花村”。據徐州民俗研究專家李世明老師所說,火花小區在20世紀50年代是個農村合作社,起名“火花”是因為人民群眾就像火花一樣,聚集在一起變成了燎原之火。后來改為街道辦,依舊沿用了“火花”這個名字。
其實從現實的徐州地理來看,鐵貨街與火花街道辦相距較遠,鐵貨街也沒有像鐵渣街那樣被拆遷變成園地,顯然,作品中的鐵渣街與黃花小區應該是作者對自己的記憶和經歷加工改造后的結果。鐵渣街的故事已經隨著小說的完結而落幕,但是那些從小說中走出來的人還在為生計發愁,鐵貨街的故事還在繼續。
108號
驍騎校的許多小說多次提到一個特殊地點——“108號”,《橙紅年代》里劉子光住的大雜院叫108號,《匹夫的逆襲》里劉漢東和火穎他們也住在鐵渣街108號。每一個彩蛋都有一個特別的寓意,作者年輕時住過的大院,當時的門牌號碼就是“108號”。
徐州很多路都有108號,但是最符合條件的就是西安北路的108號。這里以前是棚戶區,屬于農村地帶,到處都是破破爛爛的小平房。西安北路算是一條比較新的路,是改革開放以后才建設的,20多年過去了,西安北路發生了很大變化,108號已經不復存在,到76號就截止了。76號往前走就是銅沛路,是連接銅山區和沛縣的一條路。
除了“市中心”“棚戶區”“城鄉交界處”幾個點之外,“第四監獄”也可以驗證108號的存在。驍騎校的小說里多次出現過對于監獄生活的描寫,這些描寫都非常真實具體,真實到很多讀者都懷疑作者是否有過相關的經歷。實際上,在西安北路和銅沛路交界處的東北面不超過300米就是江蘇省第四監獄,這是省內唯一一個建在市中心的監獄。國民黨時期用于關押政治犯,后來用于關押重刑犯。《橙紅年代》第二季第二十七章“邂逅女主播”:“短暫的會面之后,王文君戴著手銬押上囚車,送往省第四監獄服刑,等待他的將是一年半的改造生活”,這里的“省第四監獄”也就直指徐州的第四監獄。
站在西安北路的十字路口,可以看到監獄灰色的高墻以及綿延的鐵絲網。除了第四監獄,其他省內監獄都是在深山老林里,一般人員無法接觸。據當地居民說,第四監獄雖然是一個重刑犯監獄,但是里面實施人性化管理,設備也是很好的,犯人甚至可以上網,這又與《匹夫的逆襲》后記里“劉漢東在江東省第一監獄服刑,條件不錯,還能上網”相符合。從這個方面來講,驍騎校二十歲左右應該就是居住在西安北路108號的棚戶區里,好奇的年輕人也許經常會從第四監獄外路過,有時候也能從別人那里打聽到有關第四監獄的軼事。可惜的是,這個記載作者一部分人生的108號已經被拆除改建,西安北路的歷史也止步于76號了。
微山縣韓莊鎮
藍浣溪是《匹夫的逆襲》中一個十分重要的角色,她出身底層,看似柔弱,實則最難攻克。她的人生,風雨泥濘,倍加難行,但就算陋衣赤腳,她也不曾放棄,更能代表匹夫的逆襲精神。這一角色并不是憑空誕生,而是生長于韓莊的世情百態之中。從韓莊當地的種種故事中,驍騎校想象了這一人物,他幻想“藍浣溪”是一個有學識、有膽量的聰明女孩,能夠憑自己的努力考上好大學,卻被那個年代某些不法分子的惡意所摧毀,盡管如此,藍浣溪依舊堅強地活著,她愛憎分明,機智果敢,最終越過風雨,綻放最耀眼的光芒。
如今的韓莊和20多年前相比,變化并不大,矮小的房屋歪歪扭扭地立在道路兩旁。雖然遠處建起了現代化的房屋,但是韓莊的那種氣息依舊沒變。
2003年左右,驍騎校曾經到過這里的一個電廠,據考察,應該是微山縣華潤微山湖電廠,1956年建立,2007年廢棄,現已炸毀,但是電廠原址還保留著,現在是貨運中轉站。電廠內部荒草叢生,瓦片和玻璃碎片散落在草地里,遠處的辦公處非常破敗,上面有紅油漆寫的“危樓”以及“禁止入內”。原來的廠房已經不見了,只有水塔還孤零零地佇立著。雖然電廠已經不在了,但是在《匹夫的逆襲》和《橙紅年代》中依舊保留了許多關于電廠的描述,作者將這些有關于電廠的記憶運用到文章里,比如《橙紅年代》第十季第四十章“暑假回家”中有關于電廠知識的運用:“電話程控交換機壞了,移動通訊機房也被炸毀,通訊要靠無線電和衛星電話,發電廠被炸毀,核心部件需要從歐洲進口才行,修好起碼是幾個月后,就算修好也不能投入使用,因為全國的汽油柴油儲備所剩無幾,別說發電了,就連汽車都加不到油了。”
韓莊的電廠是真實存在的,卻不曾出現過一個那樣耀眼的“藍浣溪”,驍騎校就把在韓莊那些光怪陸離的故事里出現過的無數個“藍浣溪”們,合成一個,永遠記錄在紙上。
銅山區工地
驍騎校18歲左右在徐州一個建筑工地當農民工,他在《好人平安》里提到過這些經歷,雖然他認為他在人生最應該驕傲的年齡就跌入谷底,但這些也是他人生的歷練。他和傅平安都跌入過相同的谷底,但是兩人都沒有放棄。傅平安這樣一個角色其實就是以驍騎校自己為原型建立起來的。傅平安在當兵歸來之后,經歷了一次次人生低潮,但是壓得越狠他反彈得越高。驍騎校表示,好人一生平安,有這樣一個由頭,也有這樣一個寓意。
這個工地是“風華園”,徐州以前的一個標桿項目,據說43號樓的鋼筋就是驍騎校穿的。
《好人平安》第三十三章“老李”里提到老李的兒子在“淮門工業職業技術學院”讀書,老李和傅平安從工地去往這個學校時大概有30里路,這個學校應該就是現在的徐州工業職業技術學院,于1964年創辦,位于徐州市鼓樓區,從這里到風華園小區也差不多是30里。并且原文中一直說的“淮門新區”,也與十幾年前的“銅山新區”相符合。風華園小區附近充斥著現代城市的氣息,很難看出小說中描繪的以前的樣貌,再不見坑坑洼洼的泥地與漫天飛揚的塵土,雖然有一種歷史已逝的落寞感,但是那些故事都給這個看似普通的小區帶來了別具一格的意義。
四十多年,徐州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但是驍騎校文筆中的空間感和煙火氣依舊能讓人在看到這些地方的第一眼就回味出小說中的內容。尤其是那些還沒有被拆毀的老街巷,站在那狹窄矮小的屋檐下,陽光從縫隙里漏下來,仿佛就置身于小說中,能看見那些奮斗的青年,看見那些無奈的女人,看見這世間百態。
而這些人、這些事是可以經過讀者的二次加工的,現實向的網絡文學給予讀者更多的共鳴,同時留下更多的體驗空間,讀者完全可以根據自己的現實經驗再去創造出一個屬于自己的鐵渣街,這就是網絡文學“現實取向”的力量。未來幻想性的網絡文學也許依舊會呈現蓬勃發展的趨勢,但是一切文學的根基都是“現實”,現實能夠使網絡文學在文學性與真實性之間達到一個平衡,使之既可陽春白雪,又可下里巴人。沿著驍騎校的作品,我們重新走過他所描繪的地方,發現作家的文學地理,并不只局限在文字中,它就是有形的和無形的“現實”。
作者簡介
張夢霓,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學生。
責任編輯 孫海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