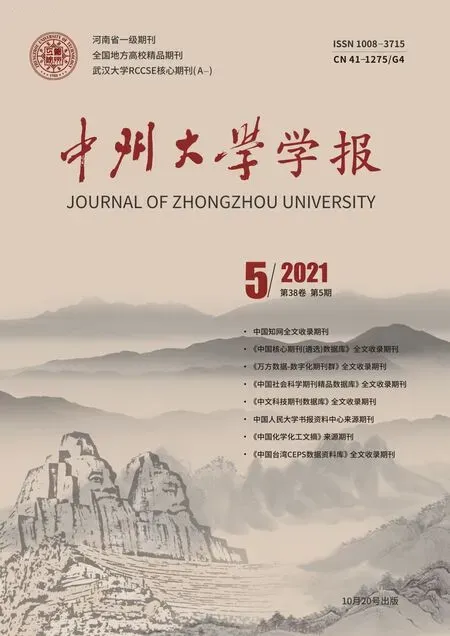河南省農村留守女童的積極發展、學校適應與成長困境調查分析
程紹珍,張小麗
(1.鄭州大學 教育學院,河南 鄭州 450001; 2.黃河科技學院 社會性別/兒童研究中心,河南 鄭州 450063; 3.鄭州財稅金融職業學院,河南 鄭州 450001)
史無前例的城鄉人口流動催生出規模龐大的“農村留守兒童”群體。據中國社科院調查報告統計顯示,2017年16 歲以下義務教育階段農村留守兒童數量達5000多萬。他們在成長過程中,雖然共同面臨父母缺席和支持性資源的缺失等不利的留守環境,但其積極發展和社會適應狀況存在多元性、差異性的特點,以及留守階段與未來發展狀況相關性,以上問題已經引起學者的關注[1]。
農村留守兒童指父母雙方或單方流動到其他地區,孩子留在戶籍所在地由代理監護人管理或自我照顧的18周歲以下的未成年人[2],目前學界對留守兒童發展研究正在從重視“留守問題”調查向促進積極發展、良好社會適應轉型。積極青少年發展觀( positive youth development,PYD) 是利特(litle)于1993年首次提出。2002年之后又經埃克勒(Ecceles,2002)、羅斯(Roth,2003)與勒納(Lemer,2004)對其完善。積極青少年發展觀強調青少年自身蘊含的發展潛力和良好環境在個體發展中的重要作用,主張“培育”而非“管理”,是個體和組織促進青少年能力提高的原理、方法和推動青少年積極發展的實踐活動。近年來國內研究者開始關注積極青少年發展的品質研究[3-5],提出了“積極心理健康教育”的概念。目前我國學者在吸取國內外積極心理學營養的基礎上,嘗試融入中國傳統文化優秀元素,緊扣積極青少年發展時代精神,提出中國文化背景下積極青少年發展的結構、內涵[6]、理論、干預實踐[7-8]。初步構建了具有中國文化特色的青少年發展促進體系。
對于青少年,良好的學校適應對身心健康、積極發展至關重要, 學校是青少年除家庭之外的主要活動場所,學校適應是其成長的一項重要發展任務[9]。部分研究發現,留守兒童在學校適應和心理適應上均存在一定的困難和問題,傾向于發現留守兒童的“問題”,得到了有關留守兒童這一群體的諸多“消極”結果[10]。但另一部分研究發現留守兒童即使在諸多風險因素環境下也能得到較好的發展,表現出生活自理、助人行為[11]、自強不息、茁壯成長的積極態勢[12]。
此外,課題組從性別的維度尤其是女童的視角考察農村留守女童生存環境、發展狀況和學校適應,發現相對于男童,農村女童更容易被父母留在家中,她們比留守男童承擔更多的家務勞動、照料責任和農活負擔;留守男童和留守女童在學校適應和心理適應上均存差異性,一項探討青少年在學校適應方面表現的差異性和青少年積極發展不同類型的研究發現,女生的積極品格得分顯著高于男生,女生的整體發展水平相比男生更高;一項初中生學校適應相關研究發現,男生的外顯問題、學習問題和內隱問題水平高于女生, 而適應能力水平明顯低于女生[13]。這些研究提示,留守兒童群體內存在積極發展及其適應狀況的異質性,哪些因素引起差異性及不同的學校適應,這也是本研究試圖考察的問題。為此,課題組于2019年4月到2020年10月,對洛陽、周口、潢川留守兒童進行調查,探討農村留守兒童積極發展特點及其與學校適應的關系。
一、調查對象
本次調查采用隨機抽樣和整群抽樣相結合的方法,在河南省洛陽、周口、潢川4個鄉鎮隨機抽取7所學校15個班級663名學生進行問卷調查。刪除廢卷33份,最終有效問卷份630名兒童,其中留守兒童381名(男生209人,女生172人);平均年齡(M):12.63歲,留守兒童均差(SD):1.83歲。
二、研究工具
(一)一般情況調查問卷
問卷內容包括性別、年齡、是否獨生子女、留守與非留守、父母親受教育程度、家庭月收入、監護人情況、假期承擔家務勞動狀況等。
(二)中國積極青少年發展量表(C-PYD)
采用郭海英、藺秀云、林丹華等編制共118題,包括品格、能力、聯結和自我價值4個分量表。本文采用積極青少年發展——品格分量表,包括“愛、志、信、毅”四個量表,總計42個項目。“愛”分量表共20個項目(如“如果同學有困難,我會主動幫助他”),“志”分量表共9個項目(如“我在學習上很刻苦”),“信”分量表共7個項目(如“我是個言行一致的人”),“毅”分量表共6個項目(如“目標已確定,即使遇到障礙我也不輕言放棄”)。在總樣本中,品格量表總體及四個分量表的信度指標范圍為 0.83~0.96,以往的研究顯示該量表具有良好的信效度。量表的結構與內涵融入了我國傳統文化中的優秀元素。
(三)學校適應狀況采用中國積極青少年發展量表(C-PYD)——能力量表
包括“學業能力、社會情緒能力和生活能力”三個量表,共26個項目。學業能力分量表共12個項目(如“我總是喜歡嘗試用不同的方法解決學習上的問題”),社會情緒能力分量表共9個項目(如“我知道如何交到更多的朋友”),生活能力分量表共5個項目(如“對我而言,做好個人衛生,如洗漱、洗衣服等,是一件容易的事”)。在總樣本中,能力量表總體及三個分量表的信度指標范圍為0.72~0.95,以往的研究顯示該量表具有良好的信效度。
(四)數據統計分析
全部資料收集后,采用SPSS17.0數據庫集中錄入,使用一般描述性統計、t檢驗、相關分析和回歸分析對數據進行分析處理。
三、調查結果
(一)留守兒童與非留守兒童的優秀品格發展狀況
首先,以積極青少年發展傳統優秀品格各維度得分為因變量,留守兒童與非留守兒童為自變量,分別進行獨立樣本t檢驗和方差分析。研究結果顯示,農村留守兒童與非留守兒童在友愛善良、有志進取、誠信自律、樂觀堅毅等中華民族傳統的優秀品格方面沒有顯著的差異。結果見表1。

表1 留守兒童與非留守兒童優秀品格發展的差異性分析
(二)留守女童與留守男童在積極發展水平、學校適應能力狀況
以積極青少年發展各維度得分為因變量,社會性別為自變量,分別進行獨立樣本t檢驗和方差分析。研究結果顯示留守兒童積極發展水平總分和5個維度得分上均存在著一定的性別差異。表現為: 留守女童的品格和適應能力得分顯著高于男生;在有志進取、誠信自律、樂觀堅毅、社會情緒與生活適應能力得分高于留守男童。女生的整體積極發展水平相比男生要好。結果見表2。

表2 留守女童與留守男童積極發展水平、學校適應能力的差異性分析
(三)留守男、女童承擔家務勞動狀況
假期女童比男童承擔了較多的家務和田地勞動。研究對381名留守兒童(男女留守兒童分別為209人、172人)假期承擔農活家務勞動情況顯示,男生幫父母干農活做家務、做自己事情分別為110人、99人;女生幫父母干農活做家務、做自己事情分別為109人、63人,留守男童幫父母干農活做家務人數占留守男童人數的52.6%,做自己事情人數占47.3%;留守女童幫父母干農活做家務人數占留守女童人數63.4%,做自己事情占36.6%;留守女童幫父母干農活做家務比留守男童高出10.8個百分點。
四、相關討論和啟示
(一)農村留守兒童與非留守兒童積極發展的基本現狀
農村留守兒童與非留守兒童同樣具有友愛善良、勤奮刻苦、誠信自律、樂觀堅毅等中華民族傳統的優秀品質,這一結果與國內葉枝、趙國祥等學者來自北京、遼寧、河南研究發現青少年積極發展水平整體處于中等偏上水平的發展趨勢結果相一致。顯示大部分留守兒童雖然面臨父母缺席、城鄉分離等不利的留守環境,但是依然有積極、良好的社會適應能力。 顯示不利的諸多風險生態環境,同樣可以進一步激發潛能和自身積極的品質,他們具有積極成長和發展的愿望和固有能力,可以成為自我發展的主導者。依據此類研究結果可以認為,過分夸大留守兒童存在的問題,給他們貼上“問題兒童”的標簽是不恰當的。要建立“減少問題”與“促進積極發展”雙管齊下的留守兒童關愛新思路。
(二)留守女童與留守男童積極發展品格水平、學校適應狀況
葉枝、趙國祥等研究發現,青少年的積極發展水平存在著一定的性別和年紀差異。具體表現為女生的品格得分顯著高于男生。本次調查驗證了以往學者的研究結論,留守兒童積極發展水平存在著一定的性別差異。表現為: 留守女童的品格、學校適應能力得分高于留守男童; 女生的整體積極發展水平比男生好。可能的原因一是社會宏觀環境的改變,形成促進留守女童積極發展的外界環境。近年來,中國在深入貫徹落實男女平等基本國策、破除傳統觀念方面取得了突破性進展。2011 年,國務院頒布了《中國婦女發展綱要(2011—2020年)》,在婦女與教育領域逐步落實“教育性別平等原則”。相關統計數據顯示,小學教育和接受中等教育女孩的在校率提高,鄉村女童生存和發展環境有所改善,提高了農村女童教育、發展的機會和能力[14]。其次, 農村家庭對女孩子教育投資趨于增長的態勢,相關調查發現,“養兒防老”的傳統理念趨于瓦解;家庭中的女兒成年后在照顧父母、親情支持中扮演更為積極的角色,客觀上影響了父母,舍得為女兒的教育投資,使其在積極健康發展中發揮作用并從中平等獲益。
此外,已有研究顯示個體可能也在自身的發展中扮演了重要的行動者角色[15]。獲得積極發展的留守女童能更珍惜和有效地調控身邊多重社會資源和情境資源,發揮自身優勢、克服環境制約,促進自身積極發展,為進一步獲得適應性成長奠定基礎,從而建構自身的生命歷程,也是很有意義的研究議題。
本研究顯示,留守女童學校適應能力得分高于留守男童。與以往研究認為男生比女生表現出更多行為問題的結果一致[16],可能與性別的生物學因素相關,男孩子更容易調皮、沖動、多動,特別是中小學階段的男生成熟相對較晚,對自我行為的約束和控制能力較低,缺失堅毅專注、勤奮進取精神,父母外出打工使他們更容易出現問題行為、適應問題,一些調查已指出,父母外出打工對留守男孩的學習成績造成的不利影響更大[17]。此外,可能的原因是來自傳統男女角色的刻板印象,遵從“男兒有淚不輕彈”等傳統的男孩則傾向于對壓力閉口不言,可能導致其缺乏同他人甚至家人的交流分享,不容易建立社會支持網絡。
(三)留守女童承擔家務勞動狀況及成長困境
全國范圍內對農民工輸出多樣本調查發現,父母外出打工以后,留守女孩、特別是貧困地區女童,要承擔更多的家務、農業和看護弟妹勞動,更少時間參加體育或其他娛樂活動,對留守男孩卻幾乎沒有影響[18]。 放學以后,男孩更傾向于出去玩,一些留守男孩在校外游蕩、迷戀網絡游戲,甚至涉足“幫派”[19]。還有研究發現,外出打工的父母擔心留守男孩的種種“不利處境”,傾向于將兒子帶到打工城市,以便更好地管教和照顧[20]。在對留守兒童團體活動分享交流中,更多的女孩坦言,爸爸媽媽外出打工,地里農活、弟妹的看護和大部分家務勞動是在爺爺奶奶的支配下由女孩承擔,祖輩監護對留守男孩形成“管護”空檔,對留守女童也難以提供社會支持,留守女童依然面臨突出的成長困境。上述情況本身也透視出家務勞動依舊被視為女性的責任,而非兩性共同承擔。 在傳統性別角色分工模式和父權制色彩濃厚的中國農村,盡管傳統性別規制一度面臨“解傳統化”的挑戰,但留守婦女,包括留守女童承擔更多家務勞動的格局在短時間內很難發生徹底改變,仍會在人口流動、家庭拆分模式中得到延續。
有研究對義務教育階段后留守兒童的職業發展、生活狀況的追蹤研究,覺察到在兒童留守階段中留守兒童性別勞動分化,即留守女孩必須承擔一系列再生產勞動,留守男孩則很少參與勞動經歷,會提前形塑了性別化的勞動習慣和勞動態度,表現新生代農民工在勞動習慣、勞動紀律等方面巨大的性別分化,現有研究認為新生代農民工已不具備其父輩在艱辛年代里鑄就的勤勞敬業、堅韌隱忍的勞動品質,以頻繁地更換工作和逆反行為表達對單調勞動、嚴苛管理、勞資矛盾、利益糾紛的強烈憤懣和利益訴求[21]。 并且其中很大一部分有留守經歷。相關研究成果和本文的實證發現也許可以為探討留守經歷對兒童成長發展的影響提供一個合理解釋。如埃爾德的生命歷程理論所述,個體的生命歷程嵌入了其所經歷的事件之中,同時也被這些事件塑造著。再如美國心理學家埃里克森 (Erik.H.Erikson) 認為,個體在成長的不同階段,如果不能成功地解決周圍環境所提出的特定社會要求,將會給其未來的社會化過程留下隱患。從生命動態歷程觀察會發現,相當一部分留守兒童的留守階段,可能影響他們未來社會化適應的能力,主體都出現了某種程度的斷裂或背離。如果他們對曾經的經歷不能建立起合理的認知,可能導致其成年后面臨融入社會的困難。因此探討不同經歷、不同因素對兒童成長發展的影響是很有意義的研究議題。
四、結論
留守男童、留守女童與非留守兒童在友愛善良、勤奮刻苦、誠信自律、樂觀堅毅等中華民族傳統的優秀品格方面沒有顯著的差異;留守女童的品格、學校適應、整體積極發展水平相比男生要好;假期女童比男童承擔了更多的家務和農田勞動。在教育和培養過程中,關注農村留守兒童積極發展,要突破傳統性別角色界限,倡導家庭性別平等并惠及女童。關注留守男童的積極發展,不斷提升他們的積極發展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