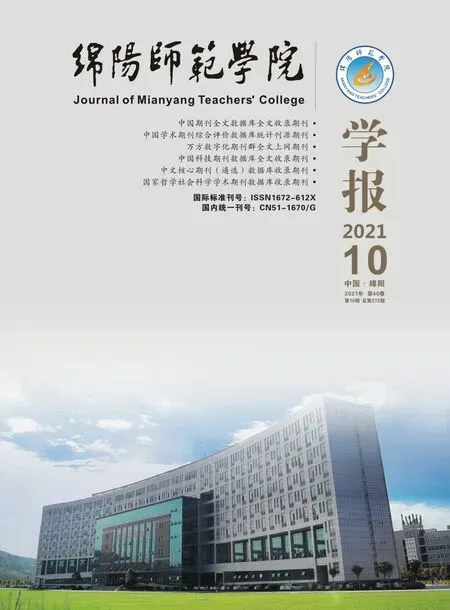論宋詩的中醫元素與構思心理
——從“詩脾”說開去
成天驕
(西南大學文學院,重慶 400715)
陳寅恪先生指出:“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年之演進,造極于趙宋之世。”[1]277作為傳統文化不可或缺的一方面,宋代中醫學獲得全面的發展,中央政府頒布248條與醫學相關的政令,社會中下層士大夫同樣對中醫理論的學習及運用投入了大量的熱情[2]。在如此社會熱潮的推動下,中醫學得以突破單純的醫療領域,將影響深入到社會生活中的各個方面。有關中醫與古典文學間的雙向互動早已受到學界關注,研究涉及各個層面。如王毓紅《中國古代文學批評與中醫——以〈文心雕龍〉〈黃帝內經〉為例》[3]從理論的角度探討二者之間的同源與異質;蔡德龍《醫文一家——文學與中醫的雙向互動》[4]則在文人思想、創作手法、文體結構等范圍內考察中醫和文學是如何相互影響的。可惜的是,在眾多觀照層面中,有關詩歌語詞構成邏輯與中醫之間的聯系卻從未被納入視野,這為筆者的研究留下了空間。
“詩脾”是宋詩用詞,經筆者對《全宋詩》進行統計,發現共存在32首涉“詩脾”詩,而在唐詩中這一詞匯卻并未得到使用。“詩脾”一詞并非突然生成,而是中醫學思維對文學的影響在一定積累后于詩歌中的表現。“詩脾”的形成過程及使用語境表現了漢語詞匯形成發展的思維模式及文化場域內部的相互影響,具有代表性,同時又體現出宋代中醫大發展潮流下對文學領域的滲透,具有典型性。“詩脾”因其深厚的文化內涵,得以成為一個文化負載詞,顯現出文學內部的發展變革動力源自社會場域的各個側面,理解其內涵能夠幫助加深理解宋代醫學與文學之間的相互影響。
站在文學本位的角度進行考量,“詩脾”釋義為“詩思”。在古典詩論中,詩歌創作的構思心理歷來都是討論的重要部分,如劉勰《文心雕龍》中的《神思》篇專門討論構思在文學創作中占據的位置,認為“文之思也,其神遠矣”[5]246。現代學界同樣重視對傳統詩歌思維過程的考察,如周裕鍇先生在《宋代詩學通論》[6]中探究宋人在詩歌創作過程中的思維模式。然而筆者在眾多的研究中,卻并未見將“詩脾”一詞在表達與解釋詩歌構思心理方面的作用納入視野。與其說“詩脾”一詞在宋代才開始大量出現,毋寧說對它的使用可以作為宋詩獨特構思風格下的一例實用表征。從理解宋代詩學的角度考慮,“詩脾”具備文學意義上的獨特闡釋空間。
一、醫文互動影響下的構詞心理
(一)形成過程:從“詩人脾”到“詩脾”
《全唐詩》中雖無“詩脾”一詞的用例,但在詩歌中將“詩”與“脾”這兩個概念相聯系,卻是源自唐人貫休《古意九首·其四》:“乾坤有清氣,散入詩人脾。”[7]24“詩人脾”作為偏正短語,由“詩人”與“脾”兩個部分組成,其中“詩人”為修飾中心詞“脾”的定語,結合全詩“詩人脾”釋為“詩人的脾臟”。經筆者統計,在《全宋詩》中共有四處用例,分別為方岳《豆苗》中“晚菘早韭各一時,非時不到詩人脾”①,連文鳳《參寥泉》中“寒泉不浸詩人脾,漫乞山僧潑春茗”,高登《偕學子游都嶠》中“()氣知多少,凄入詩人脾”,吳潛《謝惠計院分餉新茶》中“不惟散滿詩人脾,還入靈根茁苕穎”,均與貫休句同義,釋作“詩人的脾臟”。值得一提的是,綜觀以上用例可發現,“詩人脾”在整句中的成分均作賓語,將其分別作為“到”“浸”“入”“散滿”等動詞的賓語,可以明顯看出詩意所要強調的是“詩人脾”的場所性質。
與“詩人脾”相比,“詩脾”無論在使用頻次還是涵義上都有所增加。從數量統計上來看,《全宋詩》中“詩脾”的使用量是“詩人脾”的九倍之多。在語義上,盡管同為偏義短語,一字之差卻造成了意蘊的含混。“詩人脾”中“詩人”作為修飾定語,其涵義是固定且明晰的,作為中心詞的“脾”指人的脾臟。絕大部分情況下,“詩脾”之釋義與“詩人脾”相同,甚至在整個語句上也可看出直接用自貫休句,如朱熹《題清虛庵來月軒》“離緒幾多無著處,不堪清氣入詩脾”,蕭立之《贈周材叔能畫號蒼厓》“閉門磐礴天耆定,往往清氣流詩脾”。也有雖用法不同,卻仍可作“詩人脾”解,如林稹《冷泉》“一泓清可沁詩脾,冷暖年來只自知”,胡仲弓《為續雲賦》“折芳歸藝圃,剩馥入詩脾”。然而對“詩脾”的解釋絕不局限于此,楊萬里《仲良見和再和謝焉四首·其一》:“未惜詩脾苦,端令鬼膽寒。吾才三鼓竭,君思九江寬。”“詩脾”在這里與后文作者的才、思相聯系,被明確賦予了文學上的闡釋空間,顯然不能僅僅以“詩人的脾臟”作解。“詩脾”與“鬼膽”對仗,指詩人作詩的思維。整句意為“不惜詩人的思慮之苦,寫出來的詩能夠讓鬼膽寒”,如此方能與后文“吾才”“君思”相對應,“詩脾”在這里指的是詩歌創作的構思過程。
然而從實例來看,“詩思”仍不能解釋全部用例,如歐陽澈《春日書事》“暖力著人添醉圣,韶華入眼逼詩脾”,“詩人的脾臟”在此已顯然不通,但“詩思”同樣欠缺意味,美好的風光進入詩人的眼底不僅僅可引起詩人之思,更直接引發的應是詩人心底的情感。“詩脾”在此解釋為“詩情”似乎更加合適。不論是思還是情,作為句中成分,“詩脾”的作用不再僅僅是動作發生的場所,而更強調其具備的功能性,而這種功能又與人體精神領域的思維、情感掛鉤。脾臟作為人體器官,與心臟、肝臟、肺臟、腎臟共同構成人體最重要的五個器官,即“五臟”,是具體實在的物質存在。而在“詩脾”的構詞與使用過程中,脾臟的功能不僅與人的精神發生了聯系,甚至本身都可作為思維、情感的抽象存在。想要完善“詩脾”的解釋以及弄清“詩脾”這一構詞產生的緣由,首先還是需要回到“詩人脾”的起源,必須闡明脾臟作為身體的內臟器官,是如何與人的精神發生聯系,進而進入詩歌領域的。
(二)含義重構:詩脾、詩思與詩情
《黃帝內經》云,“心藏神,肺藏魄,肝藏魂,脾藏意,腎藏志”[8]57,“中央生濕……在藏為脾……在志為思”[8]20。脾藏意與脾主思的概念源自《黃帝內經》,屬于傳統中醫的重要理論。“‘脾藏意主思’既是‘五神藏’理論的核心概念, 也是情志學說的重要組成部分。”[9]傳統中醫認為,人的意與思均是人體物質器官的后天產物。《靈樞·本神》曰:“所以任物者謂之心,心有所憶謂之意,意之所存謂之志,因志而存變謂之思,因思而遠慮謂之慮,因慮而處物謂之智。”[10]150思維活動源于物質器官的生成。從生理的角度來說,脾臟對人的精神也確實存在一定的影響效果,營養物質被吸收進體內后,通過脾胃的作用轉化為水谷精微、津液等養分,并通過脾胃的“升清”運輸至頭部,對其供應營養,以保持人體正常的思維運轉[11]。在這樣的中醫思維下,脾臟成為統攝意與思的器官,生理上的異常則會影響到思維精神層面。脾臟的功能如果受到損害,則會影響精神,導致神思恍惚、健忘、抑郁、癡呆、癲癇等病狀[12]113-130。
意與思均產生于脾藏,卻具備不同的內涵所指。根據現代中醫心理學研究,脾所藏之“意”的具體內涵為人的記憶、思維功能,皆屬于認知心理學的范疇;而“脾主思”中的“思”,則是人之喜、怒、憂、思、恐等情緒,屬于情緒心理學的范疇[9]。從語言文字學的角度來說,“思”在情緒上之含義偏向于“憂”,可釋為憂愁、憂傷。《爾雅·釋詁》曰:“傷、憂,思也。”[13]79然而“憂”只是人類情緒中的一部分,“脾主思”的情緒內涵不僅局限于“憂”,還具備更廣泛的所指。雖然脾之“思”在基本的感情色彩上更偏向于“憂愁”,然而在感情生發的功用上,相較于其他情緒而言,“思”具備更基礎的地位。七情中的其他六種情緒都是通過思慮而產生,“肯定、積極的刺激通過思則會表現出來喜;否定、消極的刺激通過思慮后則表現出來悲或怒等”[14]。因而從更基礎的層面來說,對“脾主思”的闡釋應不僅局限在脾臟對人“憂”感的控制上,可以說在復雜的人類心理中,脾臟的功能作用是整個情緒變化產生的基礎。
“詩脾”的兩重涵義與“脾藏意主思”分別相對應,首先是“脾藏意”所導向的詩歌構思的環節,即詩歌創作的理性思維過程;其次是“脾主思”機制產生的引發詩歌創作的各類情緒情感;最后在形而下的意義上,詩脾即引發詩思、詩情的脾臟器官。綜上所述,“詩脾”一詞具備三重涵義:一是詩人之脾臟,即感情及思維生發的場所;二是詩思,指詩歌創作的構思;三是詩情,為引發詩歌創作的心理情感。
中醫學為脾臟與人類思維心理層面的結合提供了理論基礎,而整個中華傳統文化場域內的醫文互動現象成為“詩脾”構詞產生的大前提。中醫學與文學不僅在產生基礎上具備同源性,還存在思維方式上的同質性,顯現出中華傳統文化中文理與醫理的統一性。“中醫學在本質是哲學化的醫學,在中醫理論體系的形成和發展中,氣一元論、陰陽學說和五行學說等哲學思想起到了構建框架的關鍵作用。”[15]5對兩個領域分別進行歷時性的考察可見,從語詞構成到理論批評,在各個層面上都可看到二者之間的互動。在文學領域,“脾”在三國時期繁欽的《繁休伯與魏文帝箋》中最早出現在詩歌“棲入肝脾,哀感頑艷”[16]565當中,同時期還有甄皇后的《塘上行》“想見君顏色,感結傷心脾”[17]406,憂思之情會傷害到心肝脾等器官。到了唐代盧仝的《與馬異結交詩》“唯有一片心脾骨”[18]4383中,情感已經突破了單純的“憂”義,代指交友雙方之間真摯的友情,具備了更復雜的內涵。晉皇甫謐的《針灸甲乙經》在體裁上確認了詩歌與脾臟之間的關系:“脾氣盛則夢歌樂。”[19]162在古典詩歌理論中,詩、樂、舞本就是三位一體之關系,脾臟會影響人的情感與思維,進而與詩歌創作發生關聯。在這樣的文化心理認同下,“脾”得以與“詩人”相結合,“詩人脾”成為詩人創作思維過程與情感生發階段的場所。而“詩人脾”到“詩脾”的轉變,則是對這種場所的側重轉移到對本身思維及情感生發功能的強調。
(三)脾臟獨勝:五臟的不同內涵
值得一提的是,除心、脾之外的其他三個臟器卻極少有此構詞,經筆者檢索《全宋詩》,肝臟僅《木犀·其三》“清逼詩肝巧斫鎪”、《度劍有日高永康以詩送行次韻》“春風迸詩肝”、《謝崔象之示詩稿》“獨落詩人肝”3例,肺臟僅《李監餉四物各以一絕答之·土瓜》“久覺相如詩肺渴”1例,腎臟則無此構詞,唯一特殊的是“詩心”共29例。
與肝、肺、腎相比,“詩脾”的大量存在具備較強的特殊性與典型性,存在某種催生其產生的內部規律。在“心藏神,肺藏魄,肝藏魂,脾藏意,腎藏志”[8]13的理論中,肺、肝、腎的功能同樣涉及形而上的層面,而產生入詩結果不同的原因則是其所對應的具體精神層面內涵的差異。“‘魄’多指那些與身俱來的,本能的,較低級的心理活動;而‘魂’相對于‘魄’多指那些非本能的,較高級的心理活動……‘志’的含義較多,大致相當于現代心理學的意志、記憶、情緒、情感。”[20]42-43與脾臟相比,肺與肝所主導的心理活動層次相對較低,還未進入可以進行文學思維的階段。而腎所主之“志”又太過復雜,在古人對詩歌的認識當中,“志”是具備多重含義所指的概念,早就脫離了單純的詩歌構思階段。“詩言志”,“志”最主要代表詩歌中所蘊含的政治、倫理方面的內容,同時也可以用于詩人私人情感的表達。因此,如果用“志”或腎來代指詩思、詩情,則容易產生歧義,也不符合古人對“志”的普遍認識,在對“詩腎”的選擇上,醫學思維讓位于文學本位的認識。
而相對較為特殊的“詩心”一詞,從使用數量上來說幾乎不輸“詩脾”,甚至從整個中國古典詩歌的范圍來看,“詩心”的使用頻率要遠遠高于僅在宋代作為流行詞匯的“詩脾”。從語詞釋義來說,“心”在古典文學中代指情感與思維較為常見,“詩脾”較之更為偏澀。然而“詩脾”的使用語境相較“詩心”具備一定的特質,可以明顯看出是特殊創作思維下的產物,這也是導致“詩脾”在宋代不遜于“詩心”的原因,以下筆者將對之進行論述。
二、“詩脾”的使用語境及其文化哲學意義
與“詩脾”在詩歌表達中內涵的復雜性相似,宋人對其的使用語境同樣顯現出一定的特殊性與典型性。作為文化負載詞,“詩脾”一詞具備深厚的文化意涵,而在宋代詩學與中醫理論背景的觀照下,這種特殊性同樣呈現出民族集體文化的充分積淀,證明了文化負載詞所具備的強大承載力。一體兩面,在特殊條件下對“詩脾”進行反復的使用正好強化與鞏固了宋人本身對自我詩學理論的實踐與認同,而對于當今學界來說,探討“詩脾”用法的特殊性也在幫助理解宋詩內涵與特質的過程中起到了以小見大的作用。
(一)脾與水——中醫功能認識影響下的特殊語境
筆者通過對《全宋詩》檢索出的32處用例進行歸納,將“詩脾”的使用語境分為以下幾大類:
1.與飲品(酒、茶、湯)相關
(1)《似仁澤宗芑》:“涼生開酒量,香妙醒詩脾。”
(2)《中秋雨》:“舉杯吞寒光,流入詩脾肝。”
(3)《春日書事》:“暖力著人添醉圣,韶華入眼逼詩脾。”
(4)《次韻章太博遷匠丞不入·其三》:“解頤鼎鼎得匡來,凈洗詩脾萬古埃。何以報君青玉案,誰其醑我紫霞杯。”
(5)《蒼玉洞分韻得淺字》:“聊持一樽酒,陟此云外巘。流香入詩脾,汲影漱清淺。”
(6)《夏日陪楊邦基、彭思禹訪德莊烹茶分韻得嘉字》:“閉門積雨蘚封徑……山童解烹蟹眼湯,先生自試鷹爪芽。清香玉乳沃詩脾,抨紙落筆驚龍蛇。”
2.與風、雨、霜、雪相關
(1)《柳軒雪夜》:“但覺詩脾兩清絕,可勞騷客賦招魂。”
(2)《武康主簿吳挽詩》:“風花搖切夢,梅雪照詩脾。”
(3)《茶·其三》:“才看云腳如絲動,便覺詩脾作雪清。”
(4)《謝林簿遺廬阜茶芽·其一》:“磚爐石銚自烹吃,清落詩脾作雪花。”
(5)《游濂溪》:“雪我酒腸霜詩脾,此身疑在神仙境。”
(6)《春雪》:“一轉陽和回土脈,十分清氣入詩脾。”
(7)《僧惠澄從余學詩》:“急喚清風下佳樹,盡吹塵土出詩脾。”
(8)《汪發疆中見遺佳篇筆勢高妙且從仆求詩以歸輒為此數句》:“落落湖邊松,瀏瀏松下風。泠然入君懷,蕭颯詩脾中。”
3.與河流、湖泊相關
(1)《擬上舍寒江動碧虛詩》:“江遠澄無底,秋深分外寒……詩脾覓句難。”
(2)《行藏》:“千古常經川上水,莫將閑氣動詩脾。”
(3)《仲良見和再和謝焉》:“未惜詩脾苦,端令鬼膽寒。吾才三鼓竭,君思九江寬。”
(4)《送龍孝梅過上海及見郊外巨室》:“五茸三泖在指頭,收攬萬象歸詩脾。”
(5)《冷泉》:“一泓清可沁詩脾,冷暖年來只自知。”
(6)《葛井涵秋》:“寒波清冽不受暑,主人愛取沁詩脾。”
4.與月相關
(1)《云關觀月》:“夜半衰翁猶獨坐,清光吸盡入詩脾。”
(2)《八月十四夜對月》:“片月耿層空,清氣入詩脾。”
(3)《題清虛庵來月軒》:“夜吟唯覺月來遲,正憶先生獨坐時。離緒幾多無著處,不堪清氣入詩脾。”
(4)《跋劉敏叔畫楊誠齋先生探梅圖二首·其一》:“壽骨勁如霜后雪,詩脾寫出月中梅。”
5.與氣味相關
(1)《十日菊為子昂壽》:“誰云清香減,清香在詩脾。”
(2)《為續蕓賦》:“折芳歸藝圃,剩馥入詩脾。”
6.其他
(1)《世之詠物者采春花而落秋實余欲矯其失作冬果十詠·其六·椑》:“長卿消病久,清冷慰詩脾。”
(2)《出山追述所見》:“清秋非但入詩脾,挽向溪山深處去。”
(3)《贈醫官吳將使》:“江湖未遇醫治手,煩向詩脾謾一針。”
(4)《次韻弟觀到蔡峰莊》:“未宜回首林丘舊,剩把詩脾厭翠微。”
(5)《玉梁道中雜詠·其一》:“塵坌不可奈,飄然入林坰。稍覺道心勝,漸至詩脾清。”
(6)《贈周材叔能畫號蒼崖》:“閉門磐礴天耆定,往往清氣流詩脾。”
其中河流湖泊為水,風、雨、霜、雪均由水經過物理變化而成,可看作水的另一種形態,飲品為液態,因此這三類又可共同劃歸為與水相關的使用語境,最終可得表1:

表1 “詩脾”使用語境表
由表1可見,“詩脾”在使用時與水相聯系占據了相當大的比重,由此可以發現“詩脾”使用語境的特異性,即通常被放置于與水或水性物質有關的語境中。換言之,在宋人的詩歌構思及文化思維中,“詩脾”與水之間具備相關性。而要對之進行解釋,同樣需要進入廣闊的文化場中探究。
中醫學認為脾主運化、統血與升清。“脾主運化”指脾臟負責人體內液態物質的代謝、消化與吸收。“《素問·經脈別論》云:‘食氣入胃,散靜于肝……飲入于胃,游溢精氣,上輸于脾,脾氣散精,上歸于肺。通調水道,下輸膀胱。水津四布,五經并行……’。《素問·厥論》曰:‘脾主為胃行其津液。’明確指出脾氣散精,運化精微和輸布津液。”[21]“脾主統血”則是因為脾臟會影響到血液的運行,人體內的血液正常循環全依賴脾氣的調控[22]。作為體液的一部分,血液無疑可視為人體內水液的重要組成。從某方面來說,“脾主統血”與“脾主運化”具備一定功能上的重合,因而從功能指向上觀之,人的脾臟天然與水存在關聯。最終這樣的中醫文化心理影響到詩歌創作層面,受醫理啟發的詩人們將二者相聯系,創作出具備獨特審美性的詩篇。
(二)脾與氣——傳統哲學思維影響下的特殊語境
“詩脾”的另一特殊使用語境是與“氣”相聯系,其直接來源為貫休句,而宋詩中的使用方式也多與之相似,如“往往清氣流詩脾”“莫將閑氣動詩脾”。值得一提的是,從“氣”本身涵義來說,諸多用例又可視為對“脾與氣”的變體。段玉裁《說文解字注》:“氣、氣,古今字。自以氣為云氣字,乃又作餼為廩氣字矣。氣本云氣,引伸為凡氣之稱。”“氣”有“云氣”“氣象”“節氣”等義[23]32。《朱子語類》中,氣所構成的復合詞可以分為理學概念、天地間的自然概念、人的生理功能征兆、人的精神狀態及詩文風格、人的性格情感及品格等方面[24]。從這一角度來說,與“水”相關的使用語境均可視作“氣”的變體,氣味類語境如“誰云清香減,清香在詩脾”也同樣如此。
“詩脾”與“氣”的大量使用源自中華傳統哲學中的“氣”思想。作為中華傳統哲學中的一個重要概念,在古人“同源同構互感”②的思維模式下,“氣”成功進入到醫學、文學領域。在中醫的理論體系中,“氣”是人體的根本元素,掌控人的生老病死[3]53。《釋名》曰:“脾,裨也,在胃下,脾助胃氣,主化水谷。”[25]28脾臟的第三大功能“脾主升清”正顯現出脾臟與人體之“氣”的關聯。“脾胃……在氣化功能方面互相配合。脾主生清氣,胃主降濁氣。”[26]45脾臟所“升清”的正是人體內的清氣。而“脾主運化”理論同樣與“氣”有關,脾胃不僅將所吸收的物質轉化為營養,還負責通過“脾氣”將其運輸到身體各處[26]。水谷精微與“氣”一起通過脾臟在人體內運化傳輸。
文學領域中的“氣”同樣常見,自曹丕首次在《典論·論文》中提出文氣論后,“氣”成為文學中的重要概念,涉及文學創作的各個方面。宋代理學興起,理學家們對“氣”及文學與“氣”關系的認識極大影響到詩歌創作。在哲學思維的影響下,對“氣”的闡釋在兩個領域內顯現出活躍的醫文互動。“韓愈曾說:‘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對此,曾國藩從‘胃氣’學說闡述說:‘大抵文字雖極剛勁,然須有寬博深懇之意寓于其中,使其神氣有余于筆墨之外。正如岐黃家論脈,必有胃氣相似,即所謂藹如者也。’”[4]56對“氣”的運用突破了學科界限,在這樣的文化場中,真正重要的不是“氣”在醫學或文學中的含義具體所指,而是醫生或學者在各自領域內對“氣”進行使用的文化現象,并使“氣”的概念在這樣的使用中發生闡釋的交互。從“乾坤有清氣,散入詩人脾”開始,將“氣”與“詩脾”相聯系在構思心理上源自對脾臟與“氣”之相關性的認識,而又恰好契合詩歌理論中對“氣”概念的偏好,最終造成了這一特殊使用語境的大量出現。
三、“詩脾”蘊含的宋詩構思心理
“詩脾”的特殊釋義與使用語境背后所呈現的是古人內蘊深厚的深層文化心理。需要強調的是,對詩歌語詞的研究最終仍要回歸到文學本位中去,在這樣的立場下,宋人對詩歌的體悟起到關鍵作用,對“詩脾”的闡釋與使用的特殊語境反映出宋人獨特的詩學思維。作為詩學實踐,“詩脾”同樣從反面形塑與鞏固了宋人的詩歌創作觀。當“詩脾”作“詩思”解時,指詩歌創作的構思過程。作為藝術思維的重要構成,宋人對詩歌的構思具備深厚的體認,并在對“詩脾”的具體使用語境中暗含了這種認識。
(一)觀物:物我交融
詩人對世界的觀察或者說詩人對世界的審美觀照是詩歌構思發生的前提與基礎。對“物”與“我”之間的統一與融洽的追求一直是中國傳統哲學的核心內容,如《莊子·齊物論》“天地與我并生,萬物與我為一”[27]88、董仲舒“天人合一”思想等。宋人對自我與宇宙關系的體認同樣追求“在靜穆的觀照中將自己的生命與宇宙生命打成一片,從萬物的生機中獲得一份生命的欣悅”[6]318。在藝術創作時認為藝術家與審美對象需要高度融合,如蘇軾《書晁補之所藏與可畫竹三首》:“與可畫竹時,見竹不見人。豈獨不見人,嗒然遺其身。其身與竹化,無窮出清新。莊周世無有,誰知此凝神。”[28]3160當忘卻自我,將注意力完全投射到所畫之竹上時,最終得以達到“身與竹化”的理想狀態。“詩脾”的使用語境顯現了宋人在詩歌構思時實現物我交融的努力。如“才看云腳如絲動,便覺詩脾作雪清”,作者的詩思如同雪一般無比澄澈,如同鏡子般,將外物映照在內心,物我之間的交流毫無阻礙。“物我交融”在與“氣”有關的使用語境中最為明顯,“片月耿層空,清氣入詩脾”中的“氣”既可看作自然界的抽象顯化,又可視為人體內的物質存在,詩人和自然通過“氣”化為一體,“氣”得以成為溝通主客體的橋梁。
值得一提的是,對“詩脾”的使用可以成為中西方文論之間比較的一個觀察維度。本體的情緒被投射到客體上,主客體間的不斷交互充滿了生機與能動性,而這種審美機制正是西方文學理論中的“移情”。朱光潛先生認為,移情是人將所觀察到的無生命物看成有生命的東西,并與之發生情感上的共鳴[29]584。關于中西古代文論中的移情現象之相似與異質,學界已有大量研究,“移情”的審美發生機制恰恰符合宋詩對“物我融合”的追求。在審美移情中, 物與我之間的絕對界限被打破,二者之間互相交融,最終成為統一體[30]。同時在對審美主體的要求上,傳統古典文論與西方“移情”說都追求“在審美過程中,首先要求主體排除一切功利目的對客體進行凝神關照”[30]99。如《文心雕龍·神思》:“貴在虛靜,疏淪五藏,澡雪精神。”[5]247宋人葛立方云:“詩之有思,卒然遇之而莫遏,有物敗之則失之矣。”[31]500強調在觀照外物時保持自身澄明的心境,采取幾乎類似禪定式的靜觀態度。在這一方面,“詩脾”與“水”有關的使用語境幾乎可以看作《神思》篇的變形,如“一泓清可沁詩脾,冷暖年來只自知”“寒波清冽不受暑,主人愛取沁詩脾”,與“澡雪精神”相似,詩人之“脾”被純凈之水洗滌后自然喪失“機心”,進而達到了澄澈無暇的境界。
(二)感興:物興我情
當詩人對世界的關照處于“以我觀物”狀態時,在構思上也自然會偏向表達情緒對外部世界的感應,此時情感成為關注的中心。“在中國古代詩學體系中,‘感興’是創作論的核心范疇,同時也最能集中地體現中華美學的民族特色。”[32]《文心雕龍·物色》:“詩人感物,聯類不窮,流連萬象之際,沉吟視聽之區。”[5]410宋人同樣重視“感興”這一詩歌構思的發生機制,楊萬里《答建康府大軍庫監門徐達書》:“我初無意于作是詩,而是物、是事適然觸乎我。”[33]2841蘇軾《南行前集敘》:“山川之秀美,風俗之樸陋,賢人君子之遺跡,凡與耳目之所接者,雜然有觸于中而發于詠嘆。”[34]323在對“詩脾”的使用過程中宋人顯現出對“感興”詩思模式的強調,如“涼生開酒量,香妙醒詩脾”“千古常經川上水,莫將閑氣動詩脾”,詩人因外物而“動”,產生了詩歌創作的情緒,對“詩脾”一詞的使用正顯現了宋人對“感興”的偏好。
值得注意的是,宋人的“感興”論相較前代具備更多的內涵,特別強調創作者的主導地位。恰如周裕鍇先生所說:“詩人并非被動地依賴外物的感發,詩人主體的精神人格在感物中起主導作用。”[6]326如楊萬里《應齋雜著序》:“至其詩,皆感物而發,觸興而作,使古今百家、景物萬象皆不能役我而役于我。”[33]3340“詩脾”的使用語境同樣體現了這種主體意識,具體在于多將其與“入”“歸”“在”等動詞搭配使用,如“一轉陽和回土脈,十分清氣入詩脾”“五茸三泖在指頭,收攬萬象歸詩脾”,感于外物產生的情緒最終要歸入“詩脾”受詩人的掌控。
(三)妙悟:詩出天然
當詩人產生創作的情感后,需要創作靈感的幫助才能最終形成作品,而宋人對這種靈感的認識則偏向于“妙悟”,正如嚴羽《滄浪詩話》指出:“詩道亦在妙悟。”[35]12關于妙悟的認識,陳伯海認為:“總之,‘妙悟’的特點在于不憑藉理性的思考而能夠對詩歌形象內容的情趣韻味作直接的領會與把握,這種心理活動和能力便構成了詩歌創作的原動力。”[36]172而施惟達則表述為:“詩歌的審美藝術思維……是‘不涉理路’。…‘不涉理路’指出了妙悟活動不假推理、憑借直覺的特點。”[36]172總之,宋人認為妙悟的產生并不是苦心搜冥的產物,而是出于天然,“詩本無形在窈冥,網絡天地運吟情。有時忽得驚人句,費盡心機做不成”[37]。通過妙悟產生的詩歌才最貼合自然,達到類似姜夔提出的“自然高妙”的境界。
“宋人既認為詩的本質為宇宙的邏輯同構,因此總是相信有一種名叫‘詩’的東西,蘊于天地混茫之間,藏于寂寞杳冥之境。”[6]328在宋人的哲學思維中,妙悟是“詩”由無形之態轉為口中吟詠、寫于筆墨的形而下狀態的途徑。將詩歌的本質視作無形之物、獲得詩歌的途徑視作無所用意的結果的思維模式恰與“詩脾”的用法相似。天地之“氣”同樣無形無質,詩歌可視作“氣”的形態之一,“清氣”浸潤人之“詩脾”和妙悟的產生一樣,并不是詩人能夠通過辛苦搜冥、主動追求得到的,而是完全出自天地自然的生發,這正是詩歌妙悟的結果。
四、結語
文學是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然而中華人民對本民族文化的體認卻并不僅僅局限于文學領域,在文學之外還有更廣闊的文化場。在當下提倡發展傳統文化的新時期,如何從宏觀把握文化的立場上去進行文學研究,以幫助國民加深對傳統文化的認同,是崇高而又艱巨的使命。“詩脾”一詞的特殊內蘊及與宋人詩思的關系歷來受到忽視,其釋義詩思與詩情源自中醫學對脾臟“脾藏意主思”的醫理認識,而其使用語境往往與“水”和“氣”相關則在更廣泛的意義上符合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心理。其構詞產生心理與使用的具體語境,是脾臟構詞數量相對于其他四個臟器得以勝出的原因,同時顯現出中華傳統文化場內部的學科互動。最后在詩歌創作的構思中,對其深入分析有助于理解宋人詩歌創作的思維模式,進而加深對宋詩獨特風格的體認。
注釋:
① 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全宋詩》,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除特殊注明外,本文所引宋詩均源于此版,不再出注。
② 葛兆光把這種中國古代思維稱作“同源同構互感”,意思是說,“在古代中國人的意識里,自然也罷,人類也罷,社會也罷,它們的來源都是相似的,它們的生成軌跡與內在結構是相似的,由于這種相似性,自然界(天地萬物)、人類(四肢五臟氣血骨肉)、社會(君臣百姓)的各個對稱點都有一種神秘的互相關聯與感應關系”。葛兆光,《眾妙之門——北極與太一、道、太極》,《中國文化》,1990年,第6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