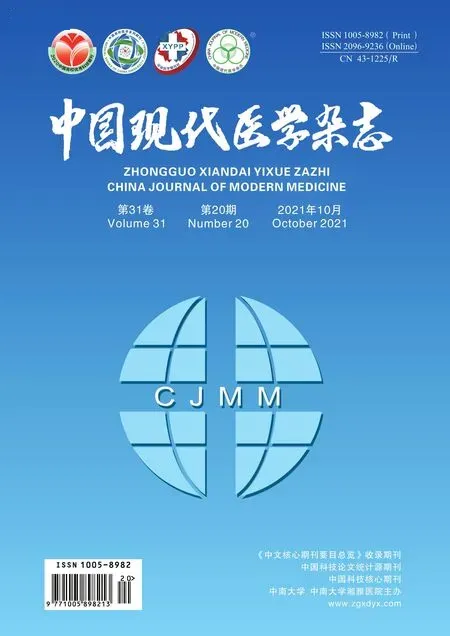新型高光面抗生素骨水泥間隔器治療髖關節假體周圍感染的早期療效分析*
鐘達,谷四全,雷鵬飛,高發維,王成功,蘇士龍,涂皓城,齊軍
(中南大學湘雅醫院骨科,湖南長沙410008)
髖關節假體周圍感染(periprosthetic joint infection, PJI)是骨科最常見的疾病之一,文獻報道髖關節置換術后PJI 發生率為1%~2%[1-4]。PJI 治療的最終目標是有效根除感染,重建功能性、無痛、穩定的關節[2]。目前治療方法主要有抗生素治療、保留假體的清創術、一期或二期翻修、關節融合及截肢術等[5-10]。其中,使用抗生素骨水泥間隔器的二期翻修術被認為是目前最有效的方法,其遠期成功率近90%[2,7,11]。
DUNCAN 等[12]首先報道負載抗生素丙烯酸水泥假體在全髖關節置換術(total hip arthroplasty, THA)后PJI 二期翻修中的成功應用,髖關節抗生素骨水泥間隔器的作用在于局部緩釋抗生素、維持髖關節周圍軟組織張力、提供一定的關節活動度、利于二期翻修手術等[12-14]。經過數十年的發展,目前有多種髖關節間隔器應用于髖關節二期翻修,如非活動關節面型、活動關節面型、自制型、模具制作型,商品化型、術前預制型等,每種髖關節間隔器因其設計方法不同,均存在一定的并發癥[15-17],如髖臼磨損、間隔器斷裂及脫位、髖關節疼痛、關節活動度差等[18-21]。目前尚無一種公認最優的髖關節間隔器[2,21]。
本研究對傳統髖關節間隔器進行改進,采用人工股骨頭假體的雙極頭金屬外杯,術中制作一種新型高光面抗生素骨水泥間隔器,并應用于PJI的二期翻修,旨在改善患者曠置期間的關節功能、疼痛及生活質量等,并獲得更好的二期髖關節翻修效果。本研究回顧分析患者病歷資料,探討高光面抗生素骨水泥間隔器應用于PJI 二期翻修的早期臨床療效與優勢,以及使用高光面抗生素骨水泥間隔器行一期曠置術的技術要點。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選取2018年8月—2019年12月在中南大學湘雅醫院診斷為髖關節置換術后假體周圍感染的15 例患者。其中,男性8 例,女性7 例;年齡31~63 歲。12 例患者明確了致病菌,其中6 例為金黃色葡萄球菌感染,4 例為表皮葡萄球菌感染,2 例為溶血性葡萄球菌感染;3 例未培養出病原菌。15 例患者術前常規行骨盆正位、髖關節側位及雙下肢全長站立正位、CT 掃描及三維重建評估髖關節及下肢情況。15 例患者術前站立位雙下肢長度差(2.41±0.83)cm。術前Harris 髖關節評分(43.41±3.11)分、髖關節傷殘和骨關節炎(hip disability and osteoarthritis outcome score, HOOS)評分(253.62±10.47)分。本研究經醫院醫學倫理委員會批準,所有患者簽署知情同意書。
1.2 診斷、納入及排除標準
1.2.1 MSIS 假體周圍感染診斷標準主要標準:①2 次從病變關節采集的組織或關節液標本中培養出同一病原體;②存在與假體相通的竇道。次要標準:①紅細胞沉降率(erythrocyte sedimentation rate,ESR)升高> 30 mm/h 和C 反應蛋白(C-reaction protein, CRP)升高> 10 mg/L;②關節液白細胞計數升高> 3 000 個/μl 或白細胞酯酶測試(++);③關節液中性粒細胞百分比(PMN%)升高>80%;④假體周圍組織的病理學分析在5 個高倍鏡視野(×400)下發現中性粒細胞> 5 個/高倍鏡視野;⑤假體周圍組織或關節液標本中1 次培養分離出微生物。滿足主要標準中的1 項或3 項次要標準可診斷[22]。
1.2.2 納入標準①根據美國骨與肌肉感染病學會(Musculoskeletal Infection Society, MSIS)的定義診斷為髖關節置換術后假體周圍感染[22];②采用高光面抗生素骨水泥間隔器進行一期曠置術并完成髖關節二期翻修。
1.2.3 排除標準①嚴重的免疫缺陷、心肺功能嚴重受限等不耐受任何手術;②影像學、實驗室檢查結果和臨床資料不全者;③伴有影響二期翻修術側運動和感覺功能的疾病,如下肢偏癱、小兒麻痹癥等;④患者依從性差,不理解或不能配合。
1.3 手術方法
1.3.1 高光面抗生素骨水泥間隔器的術中制作將1 g 萬古霉素與40 g 骨水泥混勻,待抗生素骨水泥成面團期,將其部分放入金屬外杯(DePuy 雙極頭外杯,鈷鉻鉬合金)中,部分包裹于克氏針作為間隔器股骨柄,外杯及股骨柄大小參考原有假體或磨銼型號。將間隔器股骨柄置入金屬外杯過程中逐漸去除多余骨水泥,磨去碎屑,制備成合適大小和前傾、外展角的骨水泥間隔器(見圖1A、B)。
1.3.2 一期曠置患者側臥位,全身麻醉或神經阻滯麻醉后沿后外側切口逐層顯露髖關節,取出髖臼假體、人工股骨頭和股骨柄。銳性方法切取部分炎癥組織送病理學檢查和細菌培養,使用大小合適的髖臼銼磨去約2 mm 髖臼骨質,刮匙反復刮除髓腔內炎癥病灶,使用合適大小髓腔銼處理創面直至滲血良好,徹底清除炎癥和壞死組織后用生理鹽水、絡合碘鹽水、過氧化氫溶液交替連續沖洗傷口10~15 min,生理鹽水沖凈傷口,放置混有萬古霉素的高光面抗生素骨水泥間隔器(見圖1C、D)。術畢留置負壓引流管一根,逐層縫合傷口。

圖1 高光面抗生素骨水泥間隔器及一期曠置
1.3.3 曠置期間曠置期間進行4~6 周抗感染治療[23],靜脈使用敏感抗生素治療(對培養陰性者經驗性給予萬古霉素聯合左氧氟沙星)2~3 周,口服敏感抗生素制劑或利福平和左氧氟沙星2~3 周;每4 周至少復查血常規、CRP、ESR,觀察時間約12 周,曠置期間患者可正常活動患肢及扶拐行走。待傷口愈合、CRP 和ESR 基本恢復正常,無臨床感染癥狀時,行二期髖關節翻修術。
1.3.4 二期翻修患者側臥位,全身麻醉或神經阻滯麻醉后沿髖關節后外側切口逐層分離,直至顯露高光面骨水泥間隔器并將其取出(見圖1E、F)。術中取高光面抗生素骨水泥間隔器周圍增生軟組織送病理檢查,徹底清除增生組織,生理鹽水沖洗手術區域,植入髖關節假體,重建髖關節,逐層縫合傷口(見圖2)。術后1 d、3 d、1 周復查血常規、CRP、ESR 等炎癥指標,常規使用抗生素2~3 d 預防感染,根據患者麻醉后復蘇情況、疼痛及下肢肌力評估,術后第1 天可離床助行器輔助行走。

圖2 典型病例
1.4 隨訪
15 例患者曠置術前及術后1 個月、二期翻修術前及末次隨訪均行血常規、ESR 和CRP 等炎癥指標檢測和Harris 髖關節評分、HOOS 評分,統計術中出血量、手術時間、雙下肢長度差及術后并發癥。
1.5 統計學方法
數據分析采用SPSS 25.0 統計軟件。計量資料以均數±標準差(±s)表示,比較用隨機區組設計的方差分析,兩兩比較用Bonferroni 法。P<0.05 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患者術后情況
本組15 例患者均完成一期曠置與二期翻修術,并得到隨訪,隨訪11~27 個月,平均(17.13±5.03)個月。一期曠置術手術時間(119.93±8.61)min,術中出血量(565.33±278.69)ml, 曠置觀察期(3.79±1.07)個月,曠置期間無間隔器脫位、斷裂等并發癥。15 例患者于二期翻修前復查炎癥指標,均達到感染控制標準。二期翻修手術過程順利,所有間隔器均易于移除,手術時間(108.47±14.93)min,術中出血量(480.00±117.72)ml,術中銳性方法取間隔器周圍增生組織行病理檢查未見炎癥細胞浸潤,培養未發現病原菌,未見明顯新增髖臼缺損。1 例患者二期翻修術后1 個月脫位,行閉合復位后功能良好,15 例患者均無感染復發。
2.2 手術前后Harris髖關節評分變化
15 例患者曠置術前及曠置術后1 個月、二期翻修術前及末次隨訪Harris 髖關節評分總分比較,經方差分析,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曠置術前Harris 髖關節評分總分較低(P<0.05)。手術前后疼痛、關節功能的Harris 髖關節評分比較,經方差分析,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且兩兩比較均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手術前后髖關節活動度及畸形的Harris 髖關節評分比較,經方差分析,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末次隨訪髖關節活動度及畸形的Harris 髖關節評分較曠置術前提高(P<0.05)。末次隨訪髖關節功能獲優(Harris>90分)8例,良(Harris 80~89分)7例,優良率為100%。見表1。
表1 手術前后Harris髖關節評分比較 (n=15,分,±s)

表1 手術前后Harris髖關節評分比較 (n=15,分,±s)
注:①與二期翻修術前比較,P<0.05;②與曠置術后1個月比較,P<0.05;③與曠置術前比較,P<0.05。
時間曠置術前曠置術后1個月二期翻修術前末次隨訪F 值P 值總分43.41±3.11①②58.30±4.57①③76.85±6.89②③89.47±3.60①②③341.145 0.000疼痛22.00±4.14①②28.00±4.14①③35.33±5.16②③41.87±2.07①②③94.308 0.000關節功能15.80±2.96①②23.47±2.95①③34.00±1.93②③39.13±1.64①②③288.179 0.000髖關節活動度2.87±0.61①3.23±0.46 3.65±0.16③4.47±0.52①②③33.431 0.000畸形2.73±0.80①②3.60±0.51③3.87±0.35③4.00±0.00③20.082 0.000
2.3 手術前后HOOS評分變化
15 例患者曠置術前及曠置術后1 個月、二期翻修術前及末次隨訪HOOS 評分總分比較,經方差分析,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曠置術前HOOS評分總分較低(P<0.05)。手術前后疼痛HOOS 評分比較,經方差分析,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且兩兩比較均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手術前后癥狀、日常活動能力、運動和娛樂、生活質量的HOOS 評分比較,經方差分析,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末次隨訪時HOOS 評分較曠置術前及二期翻修術前提高(P<0.05)。見表2。
表2 手術前后HOOS評分比較 (n=15,分,±s)

表2 手術前后HOOS評分比較 (n=15,分,±s)
注:①與二期翻修術前比較,P<0.05;②與曠置術后1個月比較,P<0.05;③與曠置術前比較,P<0.05。
時間曠置術前曠置術后1個月二期翻修術前末次隨訪F 值P 值總分253.62±10.47①②260.30±7.52①③339.45±14.75②③380.78±8.40①②③1357.432 0.000癥狀62.07±2.94①62.47±3.11①80.60±4.47②③86.80±2.08①②③264.584 0.000疼痛58.00±4.74①②63.52±3.99①③82.23±2.65②③89.13±1.54①②③488.699 0.000日常活動能力64.64±3.86①64.63±2.79①73.90±8.82②③83.33±5.07①②③44.425 0.000運動和娛樂38.53±4.67①38.47±3.16①41.87±3.69②③54.90±3.09①②③84.064 0.000生活質量30.38±2.35①31.22±2.50①60.85±6.08②③66.62±2.55①②③485.986 0.000
2.4 手術前后雙下肢長度差變化
15 例患者曠置術后、二期翻修術后雙下肢長度差分別由術前(2.41±0.83)cm 減少至(1.20±0.30)cm和(0.63±0.13)cm,經方差分析,差異有統計學意義(F=47.442,P=0.000)。
3 討論
3.1 二期翻修使用髖關節間隔器的現狀
髖關節置換后假體周圍感染是THA 術后初次翻修的三大主要原因之一,其治療仍是骨科醫生面臨的棘手問題[24]。目前臨床上有多種治療方法,其中,二期翻修被認為是治療慢性髖關節假體周圍感染的金標準[17,25-26],也有研究報道二期翻修在原發性髖關節感染伴有活動性、竇道等近期感染復發征象或其他手術導致的髖關節感染中取得良好的臨床效果[5,12,27]。
然而,二期翻修術目前尚有爭議,曠置間期由數天到數年不等,曠置期間使用的間隔器種類多樣,但仍存在一些并發癥[2,28]。非活動關節面型的髖關節間隔器雖然能有效緩釋抗生素抗感染,但存在關節活動度有限的問題[21,25];活動關節面型髖關節間隔器臨床應用較多,其能有效緩釋抗生素,并為一階段曠置手術患者提供更好的功能活動[13,29],但目前臨床上使用的此類間隔器仍存在脫位、斷裂、骨量丟失、摩擦產生骨水泥顆粒等相關并發癥[25,30-31]。
3.2 高光面抗生素骨水泥間隔器的療效及優勢
高光面抗生素骨水泥間隔器采用人工股骨頭假體的雙極頭金屬外杯覆于髖關節間隔器的頭部外側,相較其他髖關節間隔器可獲得更加光滑的髖關節活動界面,很大程度上解決了間隔器關節面粗糙的問題,從而改善患者曠置期間關節功能。一方面,高光面髖關節間隔器可通過增加患者過渡期的髖關節活動度,從而改善髖關節功能和提高患者的生活質量,本組病例曠置期間Harris 髖關節功能評分、關節活動度評分較術前均得到明顯改善,二期翻修術前HOOS 生活質量評分明顯提升。另一方面,高光面髖關節間隔器通過提升關節活動界面的光滑度,減少患者活動時產生的摩擦傷,從而減輕患者過渡期疼痛。本組病例曠置術后疼痛的Harris 髖關節評分及HOOS 評分較曠置術前均得到明顯提高。其次,高光面髖關節間隔器通過減少接觸界面摩擦產生的骨量丟失,可更好地保留患者髖關節骨量,為二期翻修手術提供更好的骨質基礎,減小巨大骨缺損帶來的二期翻修手術難度。
在感染控制方面,細菌在人工關節假體表面形成生物膜是其抵御抗生素、不易清除的主要原因之一[32-33]。在細菌生物膜形成的影響因素中,除了細菌本身的生物學特性外,生物材料的種類和植入物表面的化學結構、表面粗糙度、親水性等物理特性也會影響細菌在植入物表面的黏附、增殖和生物膜的形成[33-34]。KOSEKI 等[35]一項關于葡萄球菌在不同植入材料上形成生物膜的體外研究表明,培養6 h 后鈷鉻鉬合金的生物膜覆蓋率明顯低于鈦合金、純鈦和不銹鋼,細菌很難在鉻鉬合金表面上形成生物膜。其次,更粗糙的表面可為細菌黏附、繁殖和生物膜的形成提供更廣闊的區域,而高光面抗生素骨水泥間隔器采用高拋光的鑄造鈷鉻鉬合金雙極頭外杯,一定程度上材料表面不易形成細菌生物膜。另外,在徹底清創的條件下,術后靜脈輸入敏感抗生素及聯合口服敏感抗生素制劑或左氧氟沙星與利福平,可增強抗菌效果及避免產生耐藥菌[10]。本組病例顯示感染根除效果良好,曠置觀察期(3.79±1.07)個月時達到感染控制標準,平均隨訪時間(17.13±5.03)個月未發現感染復發患者。
3.3 使用高光面抗生素骨水泥間隔器行曠置術的技術要點
使用高光面雙極頭金屬外杯獲得更加光滑的關節活動界面是高光面抗生素骨水泥間隔器與傳統間隔器的主要區別。為了達到更加良好的曠置期髖關節功能,間隔器的制作參照患者原有假體大小或磨銼型號,具有合適的前傾與外展角度。因此,一期曠置手術時使用大小合適的髖臼銼去除約2 mm 髖臼骨質,髓腔銼去除股骨髓腔內炎癥病灶,在除去細菌附著界面并形成新鮮創面的同時,可為間隔器的制作提供一定參考。其次,最大程度清除炎癥組織、可疑感染組織、瘢痕增生及細菌附著界面,仍是一期曠置手術成功的關鍵所在。
綜上所述,髖關節高光面抗生素骨水泥間隔器制備過程簡便,可在有效根除感染的同時,為患者在曠置期間提供良好的關節活動功能、減輕疼痛、提高生活質量、保留骨量,為二期翻修創造良好條件。但本研究觀察的樣本量小,隨訪觀察主要針對早期療效,以后將進一步進行更大樣本、隨機對照的遠期療效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