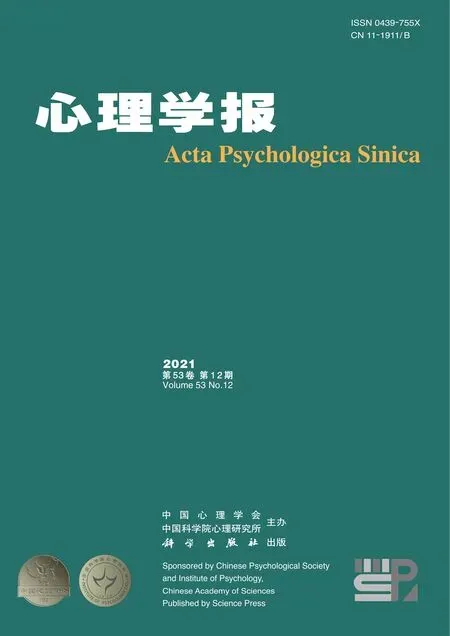身體的意義:生成論視域下的情緒理論*
葉浩生 蘇佳佳 蘇得權
身體的意義:生成論視域下的情緒理論
葉浩生蘇佳佳蘇得權
(廣州大學心理與腦科學研究中心, 廣州 510006) (浙江師范大學教師教育學院, 金華 321004)
生成論的情緒學說從“意義建構”的視角看待情緒的動力作用, 主張情緒與認知相互交織, 與有機體適應環境的身體活動密切聯系。情緒是身體的情緒, 身體是情緒體驗中的身體。身體在情緒體驗中扮演著構成性角色。根據這一觀點, 情緒是一種積極的行動傾向, 是在理解環境意義基礎上的具身行動。情緒并非發生于有機體頭顱內, 而是產生于大腦、身體和環境的互動與耦合之中。由于認知與情緒在生成論的視域下統一在有機體意義建構的活動之中, 因而認知的4E屬性也必然反映到情緒上, 使得情緒和情感也具有了具身、嵌入、延展和生成特征。情緒的生成理論為了解情緒, 進而理解意識的本質提供了一個新視角。
情緒, 生成論, 意義建構, 具身認知
1 引言
情緒是一種復雜的意識體驗。在心理學的歷史發展進程中, 許多心理學家對情緒作出了解釋, 提出了各式各樣的情緒理論(Reisenzein, 2019)。其中, 詹姆斯?蘭格的情緒理論和認知的情緒理論分別代表了情緒理論的對立兩極: 詹姆斯?蘭格的理論聚焦于情緒的生理成分, 情緒被視為身體變化的主觀感受, 而認知理論則視情緒主要由特定情境的認知評估構成, 生理感受僅僅是認知評估的副產品。處于兩極之間的還有其他一些折衷觀點(Barlassina & Newen, 2014)。
此外, 盡管情緒理論取得了明顯進展, 但是情緒的研究者們仍然遭受著“笛卡爾式焦慮”的困擾。笛卡爾確立了“心物”或“心身”二元實在論。依照這種觀點, 情緒和情感體驗作為一種內部 “精神品質” 既與物質性的身體相區別, 也與外在客觀世界相分離(O’Shiel, 2019)。無論是詹姆斯?蘭格式的情緒身體感受理論, 還是與其對立的認知評估觀點, 都主張情緒或情感發生于有機體的內部, “情緒、心境和動機狀態(如欲望、需要、疲憊和疼痛等), 皆被視為有機體的一種狀態, 有機體處于這種狀態中。學者們可能在什么成分構成了情感狀態方面存在分歧, 但是無論它包括了什么成分, 通常情況下, 這些狀態或過程都依然處于有機體內部” (Colombetti, 2017 p.445), 人際世界和環境成分似乎在情緒和情感的形成中扮演著微乎其微的角色, 并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
近年來, 情緒的生成取向(enactive approach)開始嶄露頭角(Glas, 2020)。生成取向從“意義建構” (sense-making)的視角看待情緒的動力作用, 主張情緒與認知相互交織, 與有機體適應環境的身體活動密切聯系。根據這一觀點, 情緒并非發生于有機體頭顱內, 而是產生于大腦、身體和環境的互動與耦合(Sánchez, 2019)。有機體以身體的方式作用于環境, 身體在情緒形成中扮演了關鍵角色。“情緒的生成理論”為了解情緒的本質提供了一個新視角。
“生成論(enactivism)是心靈哲學和認知科學的一種新發展。它一般依照主體與物理環境的自然互動來定義認知…” (Dierckxsens, 2020, p.100)。“生成” (enaction)這一術語是認知科學家瓦雷拉、湯普森和羅西在1991年出版的《具身心智:認知科學與人類經驗》一書中提出來的。這些學者不滿主流認知主義范式, 嘗試以現象學、進化生物學、動力系統論和東方智慧來填補認知科學與人類真實經驗之間存在的裂隙。這些學者主張, 認知并非是發生于有機體頭顱內的被動信息加工, 而是“有機體與環境互動過程中的具身和嵌入(embodied and embedded)活動。為了正確理解認知, 他們認為, 我們應當承認, 認知活動是身體化的有機體在具體和特殊的環境中‘做’出來的, 不同的身體和不同的環境會導致不同的經驗…知覺與行動密不可分, 知覺是一種行動, 而不是一種對世界的內部表征, 認知是從事活動的有機體理解世界的身體行動” (de Haan, 2020, p.7)。
生成論是廣義具身認知思潮的一個分支。正如Meloni和Reynolds (2020)指出的那樣: “具身認知與生成論的關系類似于種與屬的關系” (p.4)。遺憾的是, 就像具身認知已經分化為許多不同取向一樣, 認知科學的生成論也演化出不同進路, 其中, 至少有三種生成論范式格外引人注目, 即自創生生成論(autopoietic enactivism)、感覺?運動生成論(sensorimotor enactivism)和激進生成論(radical enactivism) (Ward et al., 2017)。在這三種形式的生成論中, 由于自創生的生成論勢力最強、影響最廣, 對情緒理論的沖擊也最大, 因此, 在后面相關論述中, 將主要以自創生生成論為基礎, 兼顧其他兩種形式的生成論觀點。
2 情緒與意義
無疑, “意義建構” (sense-making)是自創生生成論最富有特色的概念(Reybrouck, 2021)。“意義建構”是認知的最基本標志(Villalobos & Palacios, 2021), 同時, 意義建構又與情緒緊密聯系, “生命有機體的意義建構不僅是認知的, 同時也是情感的” (Colombetti, 2017, p.446), 有機體并非被動地從感官獲得環境賦予的信息, 然后形成關于外部世界的內部心理表征, 并從中抽取環境的意義。相反, 有機體通過身體行動積極地作用于環境, 以既是認知的, 又是情感的方式與環境形成關聯, 建構一個有利于自身生存的意義世界。因此, 有機體并非被動表征世界, 而是根據生存需要建構一個意義世界, 意義建構是生命有機體具身行動的根本特征。但是為了準確理解什么是“意義建構”, 必須首先把握什么是“自治”。
2.1 自治(autonomy)與意義建構
“自治”是生成論的核心概念之一。“自治”的早期范型是“自創生” (autopoiesis) (Maturana & Varela, 1980)。“自創生”源自生物學概念, 它的含義是“自我生產” (self-production)。“自創生”的一個簡化定義是:“一個系統若是自創生的, 則(i)這個系統必須有一層半透邊界; (ii)這個邊界必須由發生于邊界內的反應網絡生產出來; (iii)這個反應網絡必須包含再生產此系統成分的反應” (湯普森, 2013, p.85)。
自創生的典型范例是活細胞。所有的細胞都有一個半透膜。由于這個半透膜的存在, 在細胞內部與外部環境之間就建立了一個邊界。但是這個邊界的存在并不意味著細胞是封閉的, 相反, 它要保持生命活力, 在結構上必須是熱力學開放的, 這意味著在半透膜邊界內部, 包含有一個新陳代謝網絡, 與環境進行著持續的物質和能量交換, 以便保持活細胞的生命力。新陳代謝網絡決定了有哪些成分可通過細胞膜進入并參與了細胞內部的活動, 而另一些成分作為廢棄物被代謝掉。這個新陳代謝網絡有雙重功能, 一方面, 它能夠更新其自身的成分, 包括構成邊界的成分, 另一方面, 如果沒有半透膜所提供的邊界容量, 新陳代謝網絡將分解在周圍的物質中。這就是說, 細胞內的新陳代謝過程一方面決定了這些邊界, 而新陳代謝過程自身又也正是因為這個邊界才能持續存在。因此, 抽象地說, 細胞包含了自我生產的循環過程。在這個意義上, 細胞在組織上是操作閉合的, 即細胞的存在既是它的原因, 也是它的結果, 原因和結果合為一體。細胞是一個通過自身不斷生產自身的互動網絡組織, 組成細胞的各種成分相互作用, 制造出半滲透的膜, 使自身形成區別于其他物質的一個獨立單位。它不斷生產著自身, 維持自身作為獨立的生命體, 并使自身區別于非生命體。細胞自己生成自己。身體免疫系統、神經系統等都具有自創生的特征。
以細胞為代表的“自創生系統”為基礎, 生成論的倡導者們試圖在“自創生”的基礎上將“生命”描述為“自治”系統, 即所有的生命都是一個“自我決定”的系統。依照自創生生成論的創始人之一di Paolo (2009)的觀點: “一個自治系統可定義為這樣一種系統, 它由一些過程組成, 這些過程彼此依賴、互動, 在不穩定的條件下積極主動地產生和維持著系統的同一性” (p.15)。自治系統的典型特征是, 它并沒有一個“中樞”, 管控著系統中的其他部分。相反, 系統的結構和行為是其各組成部分相互影響的結果。對于一個系統來說, 如果它是自治的, 則必須滿足三個條件: (1)組成該系統的成分遞歸性地(recursively)相互依賴, 形成了整體的網絡結構; (2)無論存在于什么領域, 都構成一個整體單位, 使自身區別于其他單位; (3)系統的行為給自己界定了一個與世界互動的領域。換言之, 自治系統的特點是系統內各成分相互依賴、相互影響、相互決定, 不存在一個“中樞”支配和決定著系統內部的其他成分。自治系統的這一特征使它明顯區別于認知主義的信息加工系統。在認知的信息加工系統中, 總是存在一個中樞執行功能, 對系統內的其他成分起著監控、操縱和支配作用。自治不同于“他治”。自治就是自我決定(self-determined)。自治系統的行為規范源于維持自身的需要, 而他治系統的行為規則是由系統外部的其他因素規定的, 如認知的信息加工系統就是一個他治系統。信息加工的規則不是認知過程本身具有的, 而是系統外部的“他者”制定的。用生成論的術語來說, 有機體的行動既界定了自身,也界定了一個“認知域” (Villalobos & Ward, 2015)。
自治系統的運作方式遵循意義建構的原則。一個生物體為了適應環境, 必須不斷地進行自我調節。有些生存條件是有利的, 可促進有機體的生存和生長; 另外一些條件可能是不利的, 甚至是有害的, 可導致對有機體的傷害, 有機體必須采取“趨利避害”的行為方式, 才能生存和生長。這種趨利避害的自我調節就是一種對環境條件的認知評估, 體現了認知的特點。更為重要的是, 有機體通過對環境的認知評估, 獲得了環境的意義: 避開那些有害條件, 趨向那些有利條件, 認知評估就是一個“意義建構”的過程。它使得本來中性的物理化學環境變成了一個對有機體生存具有至關重要性的意義世界。有機體的環境不再是中性的、漠然的、毫無情感的, 而是有著吸引或排斥力的、富有情感色彩的意義世界(Umwelt)。
2.2 意義建構(sense-making)與情緒
意義建構是自治系統的互動和關系一面。自治并非意味著與世隔絕, 為了在不穩定的環境條件下維持自身的同一性, 有機體必須與環境實現熱力學交換, 獲得生存所需的資源。與環境的互動就是一種意義建構的過程。意義建構過程是認知性質的, 因為它給有機體確立了一個認識世界的視角, 由這個視角出發, 進行觀察, 世界就具有了意義。同時, 這一意義建構過程又是情緒的和情感的, 因為有機體不再以中性的眼光看待環境。在這個環境中, 有些條件是有機體在乎的, 有些條件是不在乎的; 有些是有機體偏愛的, 有些是有機體厭惡的。“意義建構不僅是認知的, 也是一種情感現象。就像我們看到的那樣, 意義建構是意義世界的生成。意義世界并不僅僅是有機體與之互動、分化出自身的物理環境…意義世界是從有機體視角所看到的世界。通過意義建構, 物理世界被轉換為有機體的意義世界。面對這個意義世界, 有機體不再, 也不能采取漠然的態度。從概念上講, 意義世界是與有機體關聯的世界, 它以一種重要意義觸動、碰撞和影響著有機體” (Colombetti, 2018, p.574)。
意義建構的這一特征使得生成論的情緒學說從一開始就視情緒和認知為一體化存在: 一方面, 心智, 包括認知, 從其根源上就與情緒和情感關聯, 情感體驗彌漫在整個認識過程中, 與認知融合成緊密聯系的整體; 另一方面, 情緒具有意向性(intentionality), 指向一定對象, 這說明情緒和情感具有認識特征。“情感并非心智的一個獨立部分, 僅僅與心智的其他非情感部分產生互動; 如果我們從心智中‘拿走’情感, 剩下來的就不再是心智” (Colombetti, 2017, p.448)。
生成(enaction)意味著“行動” (action), 意義建構就是一種具身的行動過程。對于認知主義來說, 情緒是一種認知評估: 有機體首先被動地吸納環境信息, 然后形成情境的認知表征。在表征的基礎上產生意義, 進而導致情緒的內部感受。這一過程是被動的、靜態的, 不涉及任何身體行動。但是對于生成論來說, 情緒是動力性質的, 它伴隨行動而產生, 同時又促進了行動。情緒意向性地指向特定的目標或事件, 促使我們追求或躲避某個對象。因此, 情緒是一種積極的行動傾向, 是在意義建構的基礎上, 即在理解環境意義基礎上的身體行動, 而不是一種被動的內部心理狀態, “生成論者通常把心理現象理解為在構成上與‘能動性’(agency)緊密相連…情緒也不例外, 從根本上說, 它是一種有機體對環境中突出價值特征的積極趨向和追求” (Slaby et al., 2013, p.37)。
因此, 意義建構過程涉及了效價和意義, 從而與情緒和情感融為一體。有機體的意義建構并非發生在一個“中性”或“中立”的物理環境之中。依賴于不同的身體構造、不同的能力和需求, 環境的不同部分對有機體展現出不同的價值和意義。換句話說, 有機體對環境的依賴性意味著環境中的某些方面對有機體的生存和發展具有情感價值, 有機體為這些方面所吸引; 而另外一些方面沒有價值, 為有機體躲避或排斥。有機體必須“搞清楚” (make sense of)這些價值, 建構一個有利于生存和發展的意義環境。這樣一來, 意義建構就不再是有機體的一種不帶感情色彩的、超然的努力: 有機體受到環境的“感染” (affect)。所以意義建構具有價值的敏感性。這種價值敏感性就體現了意義建構的情感特點。
2.3 自治系統、意義建構與情緒
從生成論的視角來看, 情緒是“自治”的生命有機體參與和理解周遭環境的行動傾向, 是意義建構的具身表現方式。從這一角度理解情緒, 則情緒并不僅僅是一種內部心理狀態, 而是包含了認知評估、生理激活、動機傾向、運動表現和身體感受等諸多復雜成分的“混合體” (amalgam)。盡管情緒并非像傳統認知主義情緒理論所描繪的那樣, 僅僅包含認知評估的成分, 但是由于意義建構的選擇性特征, 情緒必然與認知評估緊密聯系在一起。之所以如此, 是因為從本質上來說, 情緒是像我們這樣具有心智存在的“在乎和關心”。這種“在乎和關心”使得這個世界有了情感色彩, 讓我們擺脫了對世界的“漠然”, 有了愛、恨、情、仇。這樣一來, 意義建構就不僅是認知的, 而且是情緒和情感的。認知和情緒在意義建構中不再是孤立的元素, 而是水乳交融的整體, 同時認知和情緒共同表現為一種具身的行動傾向中。
3 身體與情緒
與認知主義明顯不同的是, 生成論把身體置于情緒學說的中心地位。它反對認知主義的情緒觀。根據這一觀點, 情緒是一個發生于“頭顱”內的中樞事件, 生理激活、行動傾向和動作表現等身體事件僅僅是認知評估的副產品, 是伴隨認知過程而發生的一種生理感受。這種感受僅僅是一種“伴隨物”, 對于情緒形成并沒有特別貢獻。對于一個“具有”心智的個體來說, 重要的是認知和思維, 而認知和思維是一種理智的、概念的和抽象的精神過程, 與承載這一過程的身體鮮有聯系。因此, 在傳統情緒理論中, 占支配地位的情緒學說要么忽略身體, 要么把認知評估與身體事件相隔離, 認為理解情境的意義是認知的特權, 是理性思維的工作, 身體僅僅扮演著一種傳輸信息、執行操作的角色。
3.1 認知的情緒理論
對于身體的認識論意義的忽略早在笛卡爾時代就開始了。笛卡爾從理性思維出發, 預設了心智與身體的二元對立, 主張思維是心智的功能, 與物理性的身體無關。換言之, 在認識的起源上, 身體沒有任何意義。在《靈魂的激情》一書中, 笛卡爾認識到情緒涉及到身與心兩個方面, 但是卻視身體影響僅僅是一種“生理騷動”, 其作用無怪乎就是告訴心智身體的目前狀態, 并不能導致任何適應性行為(Descartes, 1988)。情緒在笛卡爾那里, 似乎就是一種身體感受, 包括饑渴、疲勞、心跳等等。這些生理變化并不足以導致適合情境的理智反應, 只有心智的介入才能導致適當行為的發生。當代主流情緒理論大多提出類似的主張, 認為情境的認知評估對于適當行為的發生是絕對必要的, 認知的主要工作就是監控、評估和調節身體動作, 以便使每一個行動都源自理性, 而不是源自身體化的激情。
當代主流情緒理論在強調理智作用方面, 甚至比笛卡爾走得更遠, 其觀點更為極端。從一方面來說, 盡管笛卡爾忽略身體的認識論意義, 但是笛卡爾的確賦予伴隨情緒的某些身體變化以應激性地調節行為的能力, 而某些當代的情緒理論家卻完全否認身體變化對于情緒的作用, 認為身體事件僅僅是伴隨情緒發生的偶然副產品。從這樣一種觀點來看, 情緒是理性判斷的產物, 完全隸屬于認知范疇。沙赫特與辛格的情緒二因素說就典型地體現了這種觀念(Dror, 2017)。從另一方面來說, 當代某些情緒理論承認了伴隨情緒發生的身體事件的作用, 但是卻從強調認知的立場出發, 假定這些身體事件必須得到認知的“解釋”, 才能為主體所覺察。換言之, 主體只有在認知評估的框架下才能確定情緒的性質和體驗。笛卡爾假定了在激情條件下的身體騷動與心智之間的直接關系, 但是他并不認為身體騷動需要得到心智的解釋才能導致特定的情緒體驗。他主張一旦與心智過程產生聯系, 許多身體事件就可以直接誘發特定的情緒體驗。在這里, 一個解釋性的心智完全是多余的。
但是當代情緒認知理論在認知評估與身體的關系上, 卻把強調重心完全置于認知評估方面。從二元論立場出發, 情緒認知理論把認知評估歸結為理智的、心理的, 屬于精神范疇, 而身體感受和其他身體事件則被歸結為肉體的、生理的, 屬于物理化學范疇。兩者之間無論從性質和功能方面, 都是斷裂的。具體來說, 在認知評估與身體的關系方面, 大致存在著三種主張: 首先, 身體“間接地”影響情緒的形成。根據這一觀點, 為了產生特定情緒體驗, 身體事件必須得到認知的解釋。只有經過了認知評估, 身體事件才能在情緒中發揮影響。因此, 身體影響是間接的。前述沙赫特和辛格的情緒學說就屬于這種觀點; 其次, 身體事件是認知評估的“副產品”。身體事件從因果關系上并不能導致任何情緒體驗。伴隨情緒而發生的心跳、面部表情和動作反應等身體事件僅僅是認知評估的結果。上世紀80年代, 心理學家Lyons (1980)提出了“情緒因果評估理論” (causal-evaluative theory of emotion)。根據這一理論, 情境中某一對象的知覺導致了對情境的一組信念, 使得個體對情境與自身的關系有了一定認識。這些認識反過來又導致某種需要和愿望, 進而誘發某種行為。換言之, 認知評估與個體需要一起導致了特定的生理變化, 這些生理變化的主觀記錄就是情緒。在這里, 生理變化等身體事件似乎在情緒形成中發揮了作用。但是, 深入分析揭示出, 身體的作用是極其有限的, 它們不過是之前認識過程的結果和副產品。身體并沒有在情緒形成中發揮主導作用。第三, 認知評估和身體可以“相互作用”。依據這種觀點, 認知評估、生理喚醒和行為反應都是獨立的功能“模塊” (modular), 盡管相互之間存在著互動關系, 但是它們從神經機制上講是分離的和獨特的, 分別在情緒形成中扮演不同角色。在Scherer (2000)的情緒“組件過程模型” (component process model)中, 認知系統主管評估, 監控內外環境的反饋信號, 決定這些信號對有機體的意義; 自主神經系統負責體內調節, 為行動提供能量資源; 運動系統涉及了情緒的外在表現; 動機系統則負責行動的準備和執行。所有這些系統都參與到情緒形成中, 各司其職, 分工合作。盡管這一觀點在一定程度上接納了身體的作用, 但是認知評估仍然處在主導地位, 身體仍然處在被決定、被監控、被解釋的邊緣位置。
總而言之, 上述三種觀點都忽略了身體的意義建構角色, 而把意義的產生歸結為認知評估的功勞, 從而否認了身體在情緒體驗中的主導意義。之所以形成如此極端的態度, 與反對早期情緒的身體感受理論有關。
3.2 生成情緒理論
在20世紀初期, 詹姆斯?蘭格的情緒理論曾經主張, 所謂情緒就是身體變化的主觀感受, 肌肉、心臟和血液循環系統等身體因素都對情緒有重要作用。具體地說, 我們并非因為恐懼而顫抖, 而是因為顫抖才恐懼。在情緒形成過程中, 身體變化在先, 情緒反應在后, 不同的身體事件導致不同的情緒體驗(James, 1884)。詹姆斯?蘭格的情緒理論承認了身體的作用, 但這一觀點存在的問題是:第一, 無法解釋情緒的意向性, 即情緒的對象指向性; 其次, 忽略了環境的影響, 似乎情緒僅僅是體內因素的結果; 最后, 割裂了認知與身體事件的關系, 顧此失彼, 導致眾多爭議。
“如果要獲得情緒基本要義的適當表述, 似乎有必要拒絕在純粹認知理論與純粹身體感受理論之間做出錯誤選擇。明顯的事實是, 我們真正需要的是這樣一種理論, 它既考慮情緒中的復雜認知狀態, 又視身體感受為情緒的主要構成成分…” (Hutto, 2012, p.177)。生成論的情緒學說恰恰兼顧了認知與身體雙方的影響, 以完整有機體的意義建構活動解釋情緒和情感的基本性質, 突出強調了身體在情緒體驗中的意義與作用。
從生成論的角度來看, 所謂“身體” (body), 并非生理學和醫學意義上的軀體, 而是指“活的身體” (the lived body)。現象學創始人胡塞爾曾經提出, 存在著兩種對身體的理解, 一是作為客體的身體(K?rper), 即軀體。這個身體是物理性質的, 是認識和反思的對象; 二是作為主體的身體(leib), 這是產生認識和體驗的身體。這個身體是前反思中的身體, 是現象的身體, 是認識的主體(?berg et al., 2015), 相當于梅洛?龐蒂的“身體?主體(body-subject)”。這個身體是情緒體驗發生的背景和后臺。一切情緒體驗皆以身體這個背景為基礎。換句話說, 情緒體驗的主體是“活的身體”: 是身體在思考, 是身體在認識, 在認識和思考的同時, 是身體在產生著相應的感受和體驗。所以, 情緒體驗并非一種“無身” (disembodied)的精神狀態。有誰見過沒有身體反應的“恐懼”或“憤怒”?情緒恰恰體現在腺體分泌、肌肉僵直和劇烈心跳中。因此, 情緒是身體的情緒, 身體是情緒體驗中的身體。兩者水乳交融, 渾然一體。
身體與情緒體驗水乳交融的狀態決定了身體在情緒體驗中扮演著構成性(constitutive)角色, 而不僅僅是因果性角色。詹姆斯?蘭格理論之所以不能完滿解釋情緒的性質, 就是因為這一理論完全從因果關系上解釋身體對情緒的作用, 從而把身體事件與情緒體驗割裂開來, 導致了一種笛卡爾式二元論觀點。但是生成論與此不同。生成論認為“活的身體及其相應的神經生物因素在情緒體驗中扮演了構成性的, 而不僅僅是因果性角色…身體感受在意義產生過程中發揮了關鍵作用, 認知評估與身體化過程構成性地相互依賴” (Maiese, 2014, p.231)。
當我們說身體在情緒體驗中扮演了構成性角色時, 其中心含義是指包括各種身體感受、生理變化和行為反應等在內的身體事件是完整情緒體驗的組成部分。這些身體事件并非僅僅從因果方面貢獻給情緒體驗, 而且完整的情緒體驗中包含了這些身體成分: 激烈的心跳、急促的呼吸、扭曲的面孔、緊張的肌肉、刺痛的皮膚和出汗的手心等都是情緒體驗中不可缺少的成分。正是在這些身體事件中, 我們被“感染”、被“震撼”、被“觸動”; 或者讓我們“歡欣鼓舞”, 或者讓我們“心驚肉跳”, 或者讓我們“目瞪口呆”。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 我們說, 情緒是“具身的”, 情緒體驗從構成方面來說依賴于有生命的身體, 身體在情緒體驗中扮演了關鍵角色。
認知評估也離不開身體。生成論主張, 情緒和情感并非心智的一個獨立成分。完整的心智既包含了理性的、認知的成分, 也包含了非理性的、情緒的成分。這些成分構成性地相互依賴, 共同組成完整心智的整體。生命有機體的一個典型特征是, 它通過具身的行動建構一個意義世界, 以維持自身的同一性。這一意義建構過程既是認知的, 也是情緒的。說它是認知的, 因為它確立了有機體活動的一個視角, 從這個視角看世界, 世界就不再是中性的物理世界, 而是意義的生存世界; 說它是情感的, 也是因為從這個視角出發, 這個世界就變成了它“在乎的”、“關心的”和“有價值的”, 也會因此而被“感動”、被“沖擊”, 產生一定的身體感受和體驗。從這一角度來看, 人的認知仍然是情感的一種形態, 是理解自身和世界的一種活動方式。所以, 認知過程從根本上來說, 與情緒和情感緊密聯系在一起, 情緒和情感彌漫性地存在于認知過程中, 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任何嘗試分開兩者的企圖, 都是注定不能成功的。多年來, 人工智能研究之所以進展緩慢, 就是因為以二元論的觀點看待認知與情感, 總是試圖割裂認知與情感的聯系, 把認知局限在理智的、邏輯的范疇, 排斥了認知的情感成分。由此得到的只能是一個“人工”智能, 而不是“人的”智能(Yan et al., 2021)。
3.3 小結
認知的情感屬性決定了情緒的認知評估是一個與身體相互聯系的過程。情緒的認知理論主張, 在情緒體驗中, 最重要的是認知評估和解釋等理智過程, 情緒體驗依賴于這些認知成分。情緒的生成理論并不否認認知評估的作用。它強調的是在認知和身體事件之間并沒有涇渭分明的界限。情緒體驗既不是認知評估的伴隨物, 也不是解釋和判斷的副產品。相反, 認知評估因其固有的情緒和情感成分而成為一種身體化的意義建構方式。例如, 依照傳統認知理論, 如果你發現你的配偶有一個情人, 那么你的嫉妒之情完全是因為對這一事件的認知評估而引起, 而你的震驚, 哭泣、哽咽和粗魯的身體動作僅僅是嫉妒心理的副產品或伴隨物。它們似乎對嫉妒本身無足輕重, 重要的是對這一事件的認識, 是認識引發了嫉妒。但是生成論的解釋是, 你的震驚、哭泣、哽咽和粗魯的身體動作都是你對這一事件的身體化理解, 是認知評估的構成成分。正是因為這些身體變化, 你才對這一事件有了切身感受, 才那么“刻骨銘心”。所以, 認知評估既是理智的, 也是身體的。你的僵直的身體動作, 撕心裂肺的呼喊、扭曲的面部肌肉都是一種對情境的身體化理解。生理上的這些變化是認知評估的物理實現方式(Stein, 2020)。在這個意義上看, “生成論”的認知不同于傳統的“認知”。傳統的“認知”是沒有身體的“認知”, 或者說是“純認知”; 而是而生成論的“認知”是身體的認知, 即“知情一體”, 認知、情緒、身體三者氤氳旖旎、難分難解, 不存在涇渭分明的界限。
4 從4E認知到4E情緒
4E認知(embodied, embedded, extended and enactive cognition), 即具身的、嵌入的、延展的和生成的認知是廣義生成論的另一個名稱。這幾種認知研究分別代表著生成論陣營中的不同取向, 它們在“一個統一的頭銜下一起反對那種內部主義的、以大腦為中心的認知主義觀點” (Newen et al., 2018, p.4)。由于認知與情緒在生成論的視域下統一在有機體意義建構的活動之中, 因而認知的4E屬性也必然反映到情緒上, 使得情緒和情感也具有了具身、嵌入、延展和生成特征。
4.1 情緒的具身性
情緒與認知一樣, 基于身體, 源于身體。身體構造、活動和狀態決定了情緒體驗的性質和質量。早期詹姆斯等人的情緒身體感受理論已經論證了身體的意義, 可是這些早期理論視身體事件為因果性質的, 并不認為身體事件是情緒體驗的構成成分, 但是“具身情緒理論揭示出: 情緒表達、情緒知覺、情緒加工和理解都與個體的生理喚醒緊密聯系在一起” (Wu et al., 2020, p.2)。換言之, 身體感受、生理激活、行為傾向都是完整情緒體驗的有機組成成分。神經藥物學的研究表明, 多巴胺、血清素、去甲腎上腺素等具有提升心境、改善抑郁情緒的功能。服用這類藥物可以改變抑郁癥患者的情緒體驗。這說明情緒體驗中包含了這些生理成分(Jenkins et al., 2016)。
心理學和神經科學的一系列研究也證實了情緒體驗與身體的密切聯系。早在上世紀80年代, 心理學家Riskind (1984)就發現, 當被試以頹廢姿勢坐在椅子上時, 更多回憶起消極情緒事件; 而那些昂首挺胸坐姿的被試則更多回憶起積極情緒事件, 不同的坐姿引發不同的情緒回憶。坐姿似乎“隱含”在情緒體驗中。Havas等人(2010)發現, 向皺眉的肌肉注射肉毒素(Botox)會損害被試對消極語義內容的理解, 肉毒素不僅麻痹了皺眉的肌肉, 而且“麻痹”了被試體驗相關情緒內容的能力。這表明, 在理解與皺眉相關的情緒內容時, 被試通常會微微皺眉。皺眉構成了理解情緒內容的必要成分。另一方面, 根據Wollmer等人(2012)的一項隨機對照試驗, 在這些皺眉肌肉中注射肉毒素可以顯著改善患者的抑郁癥狀。顯然, 對自己和語義內容的負面情緒評價是由相應的面部肌肉活動支持的。Garfinkel等人(2014)的研究發現, 當心跳加速時, 被試更容易識別到恐怖刺激, 更易喚起恐懼情緒。“這些事實說明, 我們是一種呼吸的、有血有肉并伴隨有心跳的生物, 這部分地可以解釋為什么我們會體驗到這類情緒狀態” (Gallagher, 2017, p.152)。
情緒體驗不僅為各種身體事件所引起, 而且身體事件是情緒體驗中不可缺少的成分。從生成論的視角來看, 身體并非一個從第三者角度看到的客體, 也并非僅僅是情緒體驗產生的“生理基礎”, 而是包括情緒體驗在內的各種心智過程賴以發生的主體。一方面, 一個人感知自己的身體并能以一種客觀的方式看待它(body-as-object), 另一方面, 感知者就是身體, 因此, 身體以一種具身的方式感知、體驗和行動(body-as-subject)。一個人既有身體又同時是身體。正是這個作為主體的身體產生著各種情緒體驗。沒有這個身體, 一切情緒體驗都失去了根基。情緒的具身性就是身體的主體性。各種身體事件從主體的角度形成了情緒體驗。在這個意義上, 我們說, 情緒并非一種可以離身的精神現象, 而是一種具身的經驗。
4.2 情緒的嵌入性
情緒的具身性指的是情緒體驗對于身體的依賴性, 而情緒的嵌入性則指情緒對情境的依賴性。作為一個具身的主體, 我們并非生活在真空中, 而是存在于世界之中, 與情境中的人、物和事件處于不斷的交互之中。傳統認知主義把情緒視為發生于頭顱中的內部心理事件, 情境不過是情緒的額外因果變量。在認知主義那里, 情境的角色被還原為一組刺激。這些刺激以線性因果的方式導致個體的情緒體驗。生成論則認為, 情緒和情感并不依賴于體內動力, 而是依賴于我們與這個世界的互動, 與情境有著密切關聯。“人類并沒有獨立于他人的心境和情緒。情緒是‘在世存在’的方式。它在前反思的基礎上, 讓我們與他人保持一致; 表明了我們的關系、興趣和沖突的目前狀態…” (Fuchs, 2013, p.225)。情緒產生于環境、扎根于環境。例如, 當我們情緒不佳時, “換一個環境”可能就會導致情緒的改善。這說明情緒是嵌入環境的。當環境變化時, 情緒體驗也隨之發生改變。
文化心理學的研究表明, 情緒和情感的表現風格與社會文化生活有著緊密聯系。不同的社會文化習俗造就了不同的情感表達方式。Oishi等人(2004)研究發現, 日本等東亞國家的人, 在心境形成方面, 更多源于朋友、親戚、同事和配偶等社會關系和社會情境, 因為這些國家屬于集體主義社會, 更注重人際關系。與此形成顯明對照的是, 北美和西歐等國家的人, 在心境形成的原因方面, 更多與個人有關, 因為這些國家從屬于個體主義社會, 人們更關注個人自我價值的實現。另外一些研究也證實了情緒與社會文化情境的緊密聯系。例如, 北美和西歐等個體主義國家的人更看重積極、昂奮、外向的情感狀態, 而東亞集體主義國家的人更推崇平靜、沉穩、內斂的情感表現(Tsai et al., 2006)。
傳統認知主義并不否認情緒對情境的依賴性, 也認為我們的情感生活會隨環境改變而發生變化。但是生成論強調的是, 人類可以通過改變環境而造就不同的情感體驗, 從而使得情緒更深地扎根于情境。例如, 通過改變房間內家具的擺放, 讓我們產生舒服的情感體驗; 通過移除房間內有關某人的一切物品, 減輕我們同這個人分離的痛苦。在這里, 我們通過改變環境, 積極地“架構” (scaffold)情感體驗, 也就是日常所說的創造一種“情感氛圍”, 從而導致內在體驗和行為方式的改變。情緒調節策略就建筑在這種改變環境、架構體驗的基礎上。這也說明情緒調節策略是嵌入環境的, 各種環境因素構成了情緒調節的有機組成部分。
4.3 情緒的延展性
生成論強調, 心智并非完全發生于頭顱之內。認知過程橫跨了大腦、身體和環境。認知超越了皮膚的界限, 包含了支撐認知的外部資源。在這個意義上, 認知是“延展的”。因為“在某種條件下, 身體行動和環境資源可以算作認知過程的構成部分” (Kiverstein, 2018, p.19)。現在的問題是, 情緒同認知一樣具有延展屬性嗎?如果答案是肯定的, 那么, 情緒的延展屬性具有什么特點呢?
作為一種心智形式, 情緒和情感同樣超越了頭顱的界限, 延伸到身體與環境。情緒的延展性表現在兩個方面: 第一, 大腦本身并不足以產生情感體驗, 大腦內的神經活動并不能完滿解釋情緒的產生。相反, 身體的其他部分在生物、生理、形態和運動學細節方面對情感體驗的實現做出了重要貢獻。因此, 情緒超越了大腦, 延展到身體的非神經部分。例如, 研究發現, 較之帶著太陽鏡的被試, 那些被陽光映射誘發的、無意識皺眉的被試報告了更多憤怒和攻擊體驗(Marzoli et al., 2013)。這說明面部肌肉的激活參與了憤怒體驗的實現。第二, 除了上述情緒的身體延展外, 情緒體驗還表現出環境的延展性, 而且環境的延展性可能更能體現情緒的延展特征。環境的延展性指的是情緒直接超越了個體的生物疆界, 與環境中的人、物和事件形成緊密聯系, 那些本來外在于個體的環境因素構成了情緒體驗的有機組成部分。例如, 對于一個喪失親人的個體來說, 其悲傷的情緒體驗不僅存在于內心, 而且存在于靈堂、哀樂、親友的哭泣、葬禮儀式、悼念的話語等等。這些環境事件加強著個體的悲傷體驗, 形成“情感氛圍” (Brinkmann & Kofod, 2018)。
因此, 悲傷的情感體驗并不是個體內部發生的事件, 而是“延展”到環境中的其他人和物, 使得環境染上濃重的情感色彩。此外, 情緒的環境延展性還表現在集體情緒的形成方面。個體本身本來沒有什么特殊的情感, 但是在特定的群體中, 群體的互動造成了一種情感氛圍, 處于這個氛圍中的每個個體都分享著共同的情感體驗, 甚至會導致某種過激行為, 所謂“暴民心理”指的就是這樣一種狀態。在這種狀態中, 情感體驗并不是個人的, 而是集體的。情緒體驗跨越了個體, 延展到群體的每一個成員。
4.4 情緒的生成性
在談到認知的生成屬性時, Krueger (2021)指出: “盡管認知的生成論取向在特征和范圍上存在著差異, 但是所有的生成論都分享著幾個核心主張: 第一, 認知與行動緊密聯系, 其次, 認知過程由大于腦內的各種過程組成…” (p.365)。這一論斷不僅適用于認知, 同樣適用于情緒。情緒的生成性就是指情緒并非是發生在大腦中的被動心理反應, 而是一種“行動”, “生成” (enaction)本身包含著“行動” (action)。從詞根意義上講, “生成”就是“使…行動”。認知是一種行動, 認知與行動密不可分: “為了行動我們必須知覺, 為了知覺我們必須行動” (Gibson, 1979, p. 223); “知覺存在于知覺引導的行動, 認知結構出自循環的感知運動模式, 它能夠使得行動被知覺地引導” (Varela et al., 2010, p.139)。情緒同樣如此, 情緒和情感不是一種被動反應, 而是一種“做” (doing)的過程, 其目的是為了有效行動。
從生成論的角度來看, 情緒和情感是意義建構的一種身體行動方式。情感體驗不是一種知覺狀態, 而是一種行動傾向。它給我們傳達意義, 讓我們在意義建構過程中采納一種更具有適應性的智慧行為。各種情緒類型, 如恐懼、憤怒、慚愧和羞恥等都是一種行為反應模式。這些身體反應之所以在進化進程中保存下來, 是因為它們可以讓有機體為不同的行動做好準備。面對危險的事物, 我們產生恐懼, 準備逃離; 面對令人難堪的羞辱, 我們憤怒且準備毆擊; 面對錯誤, 我們內疚, 且準備道歉。情緒“觸動” (move)我們, 讓我們“趨利避害”。英文“”來源于拉丁語“”, 意思是走出去(to move out)。因此, 情緒是動力性質的, 情緒體驗中包含著動機成分。它是一種積極的、意向性的努力和追求。換言之, 它促使我們采取行動。在這個意義上, 情緒是“做”出來的, 表現為一種行動傾向。
情緒的生成屬性在情緒調節中表現得最為明顯。前文已經指出, 情緒并不是對環境刺激的被動反應, 而是作用于環境的行動傾向。人類高于其他動物之處就在于可通過身體行動去影響自身的情緒體驗。這種情緒調節策略在日常生活中隨處可見: 疲勞的時候來杯咖啡, 醒目提神; 緊張的時候小酌幾杯, 讓自己放松; 痛苦的時候吃塊巧克力, 讓自己體驗一點甜蜜。海洛因成癮者之所以難以戒斷, 就在于吸食海洛因后飄飄然的舒適感。許多人精心設計房間裝修, 去獲得一種美學效果, 以便影響自己的心境。這類情緒體驗都是“做”出來, 是我們的身體行動“生成的” (enacted)。
5 討論
在心理學發展史上, 情緒理論一直沉淪于身體感受論與認知論的爭吵中。以詹姆斯?蘭格理論為代表的身體感受理論強調了生理激活、行為反應等身體事件對情緒的塑造, 卻忽視了情緒的意向性。認知理論站在相反的立場上, 強調理性評估的作用, 主張情緒的形成乃認知判斷的結果, 身體反應僅僅是認知過程的伴隨物或副產品, 忽略了情緒的體驗特征。具身認知興起以后, 身體對認知的塑造作用開始得到強調, 但是具身認知似乎更關注“認知”。在具身認知的框架下, 認知過程似乎就是“冷冰冰的”理性過程, 缺乏情感的“溫暖”。生成論則在強調身體塑造作用的基礎上, 以“意義建構”統攝認知和情感, 把認知和情感統一在有機體追尋意義的身體活動中, 從而為情緒研究開辟了一個新視角, 并為重新認知意識的本質提供了一個新思路。
5.1 意識的本質:生命與心智連續性命題
在最近幾十年里, 有關意識本質的探討不再是一個純思辨的哲學問題, 而是成為從自然科學角度探索的實證問題。物理、化學、生物、心理和神經科學的學者從各自的領域出發, 對意識問題進行不懈的探索, 集中表現為探討大腦的神經生物學過程如何引起意識狀態, 似乎意識就是大腦的神經生物學屬性, 意識事件似乎就是大腦的神經事件。但是生成情緒學說把身體置于情緒體驗的中心, 并且把情緒嵌入到周遭環境中, 主張情緒體驗產生于大腦、身體和環境的互動耦合之中, 強調了認知和情緒統一在有機體意義建構的身體活動中。這啟示我們, 意識并非發生于頭顱中的神經生物學事件, 意識、身體和環境是緊密聯系的整體。如果我們僅僅從大腦內部尋找意識體驗的神經機制, 就無法真正認識意識的本質。
行為主義從方法論上否認的意識的存在, 認知革命恢復了意識研究的合法地位。但是傳統的認知科學所談的“意識”, 更側重于“他治”視閾下的“純意識”、“純認知”, 并沒有解決意義生成難題。意識似乎就是一種被動的“表征”或機械的“符號加工”。但是生成論從“意義建構”的視角重新認識意識, 提出“生命與心智具有深刻連續性”命題, 即生命的基本生物現象與心智的高級認知現象之間本來是強連續性的。這一觀點有力駁斥了笛卡爾的二元論觀點。自笛卡爾以來, 意識與物質、身體與心理、認知與情緒之間形成了一條難以逾越的“認知鴻溝”。如果這條鴻溝存在, 那么生命的“生物之花”如何釀出“意識之酒”?生成論則為人們重新認識意識的本質提供了有益啟示。與皮亞杰的發生認識論如出一轍。皮亞杰的建構主義把認知的發展與兒童的身體動作結合起來, 強調了身體動作內化的建構過程。而生成論從生命心智演化的視角出發, 以“意義建構”為基, 提出了“自治”的概念, 將自創生與生物適應性合二為一, 使得笛卡爾的二元論變為一種真正的“身心一元論”, 生命蘊含著心智, 心智也蘊含著生命。在這個意義上, 生命就是認知過程, 認知過程就是生命過程, 生命蘊含了意義生成。
最重要的是, 生成論的情緒學說, 提出了創新性的觀點, “自治”是通過“情緒”這一具身行動方式來進行意義建構的, 為理解意識的本質帶來了新視角, 即理解“意識”的本質不能僅從“認知”出發, 更要從“情緒”出發, 同時更要從“認知與情緒一體化”出發。
5.2 認知的本質:知情一體
從生成論的視角來看, 人類的意識生活并非僅包含認知和思維。只關注心智的認識方面而忽略心智的體驗方面并不能完整地描述人類的條件, 因為人類從一開始就不是純粹的理性動物, 而是情感動物和動機動物, 他們不僅會思考, 而且會感受、體驗、評估、關心、需要和奮斗。將認知、情感和動機作為三個基本的、不可化約的心理能力的劃分, 是19世紀心理學從哲學中繼承下來的, 目前仍然是主流認知科學的核心觀點。實際上, 人作為一種生物自治系統, 不斷追尋著有利于自身生存的意義環境。意義建構是生物體的基本特征。在意義建構過程中, 我們選擇那些對生存具有意義的條件, 規避那些有害的條件。這個過程既是認知的, 又是情感的。因為我們選擇的, 正是我們在乎和關心的, 其中認知成分和情感成分如此緊密地交織在一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以至于不得不進行一個綜合分析。
認知主義視人為一個信息加工裝置, 而信息加工是一種中樞過程, 發生在頭顱之內。這個過程與身體無關。身體接受刺激、執行反應, 進行新陳代謝, 為大腦提供營養, 在認識世界方面沒有任何意義。這一觀點貫徹到情緒理論中, 身體對情緒的影響就被減少到最低限度。盡管從表面上看, 認知理論并沒有完全拋棄身體, 身體作為情緒的“生理基礎”也受到足夠的重視。在某些認知的情緒理論中, 身體事件也是情感過程的組成成分, 但是, 情緒基本上是一種頭顱內的事件, 其中最關鍵的是認知的作用, 身體事件只有得到思維判斷的“認可”才能間接地對情緒產生影響。但是生成論把情緒和情感從“頭顱”內拉了出來, 放到頭顱之外的身體上, 嵌入到周遭環境中。情緒和情感不再是發生在頭顱之中的內部事件, 而是超越了頭顱、身體和環境, 成為一種關系性存在。
5.3 情緒的本質:4E方法論
需要指出的是, 生成論, 特別是自創生的生成論在方法論方面也面臨著“內在主義” (internalism)和“唯心論” (idealism)的指控。批評者指出, “自治”和“意義建構”都源于一種生物學概念。生成論把理論重心放在生物自治的個體身上, 強調有機體的自我生產、自創生, 建構一個屬于自身的意義世界。無論是在認知方面, 還是在情緒方面, 這都是一個孤獨有機體適應環境的活動。在這個意義上, 它忽略了心智的環境根植性, 此外, 自創生生成論強調“生成”, 認為有機體的世界不是一種客觀存在, 而是自治的有機體通過意義建構“生成的”, 或者是有機體的活動所“導致的” (bring forth)。這在某種意義上否認了客觀世界的存在, 因而是一種唯心主義觀點(de Jesus, 2016)。
但是, 從前述關于情緒的闡述中, 我們可以看出, 生成論在強調帶有個體色彩的自治和意義建構的同時, 并沒有把情緒和認知等心理過程完全放在有機體的內部。正如Gallagher (2019)指出的那樣: “自治概念最好看作是關系性的, 而不是視為人性中預先給定的特征” (p.805)。
在論述情緒的4E特征時, 生成論反復強調, 情緒體驗并非是一種發生在大腦頭顱中的內部心理事件。相反, 情緒和情感超越了個體的生物疆界(皮膚), 橫跨了大腦、身體和環境。情緒體驗是互動的產物, 產生于有機體作用于環境的活動之中。因此, “生成論并非是內在主義的, 從生成論觀點來看, 有許多事例都表明, 外在于有機體的一些過程應該被視為心理過程的載體。因此我們可以說, 生成的心智同樣是‘延展的’ …這不僅表現在認知方面, 而且也表現在情感方面…這挑戰了情感的傳統內在主義觀點” (Colombetti, 2017, p.446)。
6 結語
生成論對情感體驗的探討是否代表了心理學發展史上的“第四次革命”?上世紀初, 行為主義以客觀范式取代意識研究的心理主義范式, 把研究的焦點從意識轉到外周行為和周遭環境, 被稱之為“行為主義革命”。上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 認知心理學的興起把心理學家注意的焦點重新轉到有機體的內部, 探討認知的內在機制, 實現了心理學的“認知革命”。但是在認知革命的框架下, 人類意識生活似乎就是認識。知覺、記憶和思維等認知過程成為心理生活的全部。即使是80年代后興起的具身認知似乎也更關心“認知”, 所探討的主要是身體對認知的塑造。情緒和情感在心智生活中的作用并沒有得到應有重視。這種狀況最終導致了所謂的“情感革命” (affective revolution)。許多心理學家開始關注情緒的作用, 掀起了情緒研究的熱潮。這是心理學的“范式”轉換, 可視為心理學的又一次“革命”。但是情感革命是在認知框架下進行的, 情緒的認知理論占據了主流。這一理論把情緒和認知割裂開來, 關注情緒的認知加工機制, 忽視情緒的主觀體驗。生成論則以現象學為武器, 從第一人稱的體驗出發, 把情緒的科學研究與人類真實生活經驗結合了起來, 實現了情緒研究的又一次“范式轉換”。這是否是心理學的又一次“革命”呢?
致謝:在修改的過程中, 復旦大學哲學博士后朱林蕃先生為本文提出許多寶貴修改意見, 在此謹致謝意!
Barlassina, L., & Newen, A. (2014). The role of bodily perception in emotion: In defense of an impure somatic theory.,(3), 637?678.
Brinkmann, S., & Kofod, E. H. (2018). Grief as an extended emotion.(2), 160?173.
Colombetti, G. (2017). Enactive affectivity, extended.,(3), 445?455.
Colombetti, G. (2018). Enacting affectivity. In A. Newen, L. de Bruin, & S. Gallagher (Eds.),(pp.571?588).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de Haan, S. (2020). An enactive approach to psychiatry.,(1), 3?25.
de Jesus, P. (2016). From enactive phenomenology to biosemiotic enactivism.(2), 130?146.
Descartes, R. (1988). The Passions of the Soul. In J. Cottingham, R. Stoothoff, & D. Murdoch (Ed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Dierckxsens, G. (2020). Enactive cognition and the other: Enactivism and Levinas meet halfway.(1), 100?120.
di Paolo, E. A. (2009). Extended life., 9–21.
Dror, O. E. (2017). Deconstructing the “two factors”: The historical origins of the Schachter–Singer theory of emotions., 9(1), 7?16.
Fuchs, T. (2013). Depression, intercorporeality, and interaffectivity.(7?8), 219?238.
Gallagher, S. (2017).Oxford University Press.
Gallagher, S. (2019). Precis: Enactivist interventions.(3), 803?806.
Garfinkel, S. N., Minati, L., Gray, M. A., Seth, A. K., Dolan, R. J., & Critchley, H. D. (2014). Fear from the heart: Sensitivity to fear stimuli depends on individual heartbeat.(19), 6573?6582.
Gibson, J. (1979).Boston: Houghton Mifflin.
Glas, G. (2020). An enactive approach to anxiety and anxiety disorders.,(1), 35?50.
Havas, D. A., Glenberg, A. M., Gutowski, K. A., Lucarelli, M. J., & Davidson, R. J.(2010). Cosmetic use of Botulinum Toxin-A affects processing of emotional language.(7), 895–900. doi: 10.1177/0956797610374742
Hutto, D. D. (2012). Truly enactive emotion.(2), 176?181.
James, W. (1884). What is an emotion?(34), 188?205.
Jenkins, T., Nguyen, J., Polglaze, K., & Bertrand, P. (2016). Influence of tryptophan and serotonin on mood and cognition with a possible role of the gut-brain axis.(1), 56.
Kiverstein, J. (2018). Extended cognition. In A. Newen, L. de Bruin, & S. Gallagher (Eds.),(pp.19?40).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Krueger, J. (2021). Enactivism, other minds, and mental disorders., 365–389. https://doi.org/10.1007/ s11229-019-02133-9
Lyons, W. (1980).. Cambrige UK: Cambrige University Press.
Maiese, M. (2014). Body and emotion. In L. Shapiro (Ed),Routledge, Taylor & Francis Group.
Marzoli, D., Custodero, M., Pagliara, A., & Tommasi, L. (2013). Sun-induced frowning fosters aggressive feelings.(8), 1513–1521. doi:10.1080/ 02699931.2013.801338
Maturana, H., & Varela, F. (1980).. Dordecht: D. Reidel Publishing Co.
Meloni, M., & Reynolds, J. (2020). Thinking embodiment with genetics: Epigenetics and postgenomic biology in embodied cognition and enactivism., 1?24.
Newen, A., de Bruin, L., & Gallagher, S. (Eds). (2018)..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berg, G. K., Normann, B., & Gallagher, S. (2015). Embodied-enactive clinical reasoning in physical therapy.(4), 244?252.
Oishi, S., Diener, E., Napa Scollon, C., & Biswas-Diener, R. (2004). Cross-situational consistency of affective experiences across cultures.(3), 460–472
O’Shiel, D. (2019). Understanding dualism through emotion: Descartes, Spinoza, Sartre.,(54), 728?749
Reisenzein, R. (2019). Cognition and emotion: A plea for theory.,(1), 109?118.
Reybrouck, M. (2021).. Routledge.
Riskind, J. H. (1984). They stoop to conquer: Guiding and self-regulatory functions of physical posture after success and failure.(3), 479–493. doi: 10.1037/0022-3514.47.3.479
Sánchez, C. V. (2019). The oscillating body: An enactive approach to the embodiment of emotions.,(54), 712?727.
Scherer, K. R. (2000). Emotions as episodes of subsystems synchronization driven by nonlinear appraisal processes. In M. D. Lewis & I. Granic (Eds.),(pp. 70?99).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laby, J., Paskaleva, A., & Stephan, A. (2013). Enactive emotion and impaired agency in depression.(7-8), 33?55.
Stein, D. J. (2020). Cognitive embodiment and anxiety disorders.,(1), 53? 55.
Thompson, E. (2013).(translated into Chinese by Li Hengwei et al.). China: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湯普森. (2013).(李恒威等譯). 浙江大學出版社.]
Tsai, J. L., Knutson, B., & Fung, H. H. (2006). Cultural variation in affect valuation.(2), 288–307.
Varela, F. J., Rosch, E., & Thompson, E. (2010).(translated into Chinese by Li Hengwei et al.). China: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瓦雷拉, 羅西, 湯普森. (2010). 具身心智: 認知科學與人類經驗. 李恒威等譯. 杭州: 浙江大學出版社]
Villalobos, M., & Palacios, S. (2021). Autopoietic theory, enactivism, and their incommensurable marks of the cognitive.(1), 71?87.
Villalobos, M., & Ward, D. (2015). Living systems: Autonomy, autopoiesis and enaction.(2), 225?239.
Ward, D., Silverman, D., & Villalobos, M. (2017). Introduction: The varieties of enactivism.,(3), 365?375.
Wollmer, M. A., de Boer, C., Kalak, N., Beck, J., G?tz, T., Schmidt, T., … Kruger, T. H. C. (2012). Facing depression with botulinum toxin: A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5), 574–581. doi: 10.1016/j.jpsychires.2012.01.027
Wu, L., Huang, R., Wang, W., Selvaraj, J. N., Wei, L., Yang, W., & Chen, J. (2020). Embodied emotion regulation: The influence of implicit emotional compatibility on creative thinking.doi: 10.3389/fpsyg. 2020.01822.
Yan, F., Iliyasu, A. M., & Hirota, K. (2021). Emotion space modelling for social robots.,, 104178.
The meaning of the body: Enactive approach to emotion
YE Haosheng, SU Jiajia, SU Dequan
(Research Center of Psychology & Brain Science, Guangzhou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006, China) (School of Teacher Education, 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 Jinhua 321004, China)
Emotion can be considered as one of the most complex conscious experience phenomena. This is mirrored by the variety of the differing and often opposing emotion theories in psychology. For many years, emotion theory has been characterized by a dichotomy between the mind and the body. Enactive approach to emotion, however, tends to treat emotion as a sense-making process by which the physiochemical environment is transformed into an— a world that is meaningful for us. Emotion and cognition are interwoven in this process and closely related to the physical activities of the organism that help the organism adapt to the environment. When correctly understood, sense-making is neither passive information absorption nor active mental projection. Instead, our sense-making depends both on what is offered by the environment and on our morp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bodily action. Emotions are the emotions of our body, and the body refers to the lived body in the emotional experience. The lived body plays a constitutive role in the formation of emotion. According to enactivism, emotion is an active action tendency, which means that living beings are autonomous agents who actively make sense of their environmental conditions and bring forth or enact their emotional experiences. Emotions do not occur in the organism’s skull, but arise from the interaction and coupling of the brain, body, and environment. Therefore, emotions are simultaneously mental-physical and bodily cognitive, not in the familiar sense of being made up of separate-but-coexisting bodily and cognitive constituents, but instead in the sense that they blend with each other to achieve complete harmony and convey meaning and personal significance as bodily meaning or significance. Since cognition and emotion are unified in the activity of sense-making of the organism in the enactive theory of emotion, the 4E attributes of cognition, namely, embodied, embedded, extended, and enacted, must also be reflected in emotion and affective life: (1) Emotion is embodied, which means the body is not just a means of expressing our feelings and emotions; it is the particular shape and nature of our body that makes our affective life a meaningful experience. (2) Emotion is embedded. By virtue of being embodied, our emotive life is also automatically embedded or situated in an environment. Emotions are rooted in the environment and form a whole that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environment. (3) Emotion is extended, which means that the brain itself is not capable of producing emotional experiences, and the neural activity in the brain cannot fully explain the formation of emotions. On the contrary, other parts of the body contribute significantly to the realization of emotional experience in terms of biological, physiological, morphological, and kinematic details. Emotions, therefore, extend beyond the brain to the non-neural parts of the body. (4) Emotion is enacted. Emotional experience is not a state of perception, but a tendency to act. It conveys meaning to us and allows us to adopt more adaptive intelligent behavior in the process of sense-making. Therefore, emotions are dynamic in nature, and emotional experience includes a motivational component. It is an active, intentional effort. In this sense, emotions entail “doing” and manifest themselves as a tendency to act. The enactive approach to emotion offers a new paradigm for the psychology of emotion, thereby opening up a new perspective for emotion research.
emotion, enactivism, sense-making, embodied cognition
B84-069
2021-03-16
國家社科基金后期資助重點項目“身體運動與心理發展研究” (20FTYA002)
蘇佳佳, E-mail: sujiajia0929@163.com; 蘇得權, E-mail: sudequan617@sina.com
情緒在這里是一個總括性術語, 指的是意識經驗中的非認知方面, 包含各種體驗和感受, 也多少包含著一些行為動力成分。它既包括短暫的、指向明確的具體情緒, 如憤怒、喜悅、悲傷和痛苦等, 也包括持久的、迷漫性的、對象不明確的主觀體驗, 如焦慮、抑郁和心境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