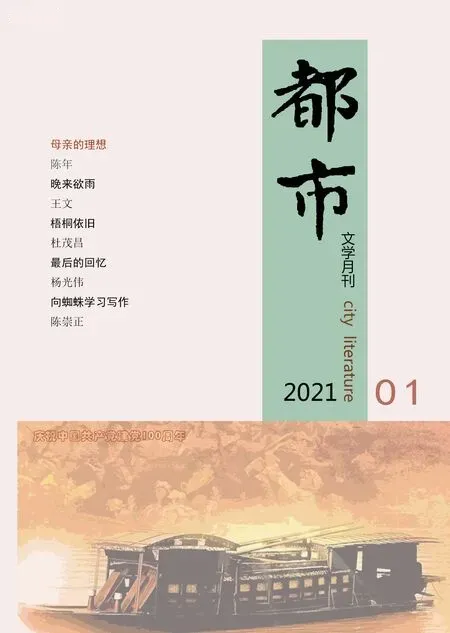母親的理想
陳年
看韓國電影《寄生蟲》,當看到沒有工作的基宇一家在半地下室里為比薩店折包裝紙盒時,李劼不由想起自己的母親。想起她凌晨坐在小板凳上包小餛飩的樣子:左手拈起一張餛飩皮,右手拿一塊舌形的小木板往面皮子上抹一點肉餡,手心里一團一攥,四方的面皮就變成一朵含苞欲放的花。
母親一直希望自己成為一個出色的女人。憑著她的聰明和勤勞讓全家人過上幸福的好日子。從二十七歲到四十七歲,這個樸素的愿望伴隨著她走過人生中最好的時光。
李劼是在香港回歸那年的二月出生的,聽母親說那一年春節時,每個單位都發了串串燈,大街上的建筑物上、樹上也掛滿了一閃一閃的彩燈,說是家家掛燈戶戶披紅歡迎香港回到祖國母親的懷抱。然而二月十九日(農歷正月十三)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去世,街頭所有的彩燈彩旗都撤了下來。這是國家重大事件留給普通老百姓的記憶。
這一年二月,他們的小家也發生了一件大事,父親拿到了新房的鑰匙。沒有錢裝修,他自己弄點涂料刷了刷房,又到五金店買了一張白鐵皮,自己動手包了包門皮,上面用銅釘鑲出一個金燦燦的“福”字圖案。大門是一個家的臉面,所以花在上面的錢和心思就多些。母親對門很滿意,那時還沒有高端的防盜門,礦區人流行用白鐵皮包門,一扇銀光閃閃的門暗示主人的身份地位。三月份的時候他們抱著剛剛滿月的李劼歡天喜地地搬到了新家。對普通老百姓來說,分房子搬新家更值得紀念。
福禍相伴,住進新房子的第二年,二十七歲的母親離開了她工作十年的單位。她下崗了,從此成了一名無業人員。母親不甘心淪落為沒有收入的家庭婦女,而且家里的經濟狀況也不允許她成為全職太太。當初為了買房,剛剛結婚一年的他們和親朋好友借了大量的外債,誰家也沒有閑錢擱著,各家有各家的困難,為了信譽,他們必須盡快把錢還給人家。母親心急如焚,天天出去找工作,可煤礦上根本沒有多少工作崗位適合女工。
為了重新找到工作,她厚著臉皮求一位隊長,想得到一份農場的工作。農場是為了安置下崗工人新成立的一個單位,主要工作是開荒種地,養豬,養兔,養雞。工作條件并不好,每個月只能拿百分之七十工資。但是失業的女工們已經有點饑不擇食,只要有工作可干她們不怕吃苦,也不怕受累。當然把工作當作救命稻草的人家都是窮工人。
隊長是父親的熟人,以前兩家關系還不錯,不同的是隊長思想積極、要求進步,他寫得一手好表揚稿,礦上的廣播站天天念他的稿子。憑借稿子,隊長脫離生產一線進入機關,再進入領導層。煤礦地界小,隊長也算是領導人物。
母親被安排在蔬菜大棚工作,她是一位理想主義者,剛開始滿腦子都是浪漫的畫面,外面天寒地凍白雪茫茫,大棚里面綠油油的菜蔬生機勃勃地生長著。紅色的西紅柿、紫色的茄子、綠色的小青菜……恬靜安然的農耕田園生活是她一直向往的。
母親工作沒多久就離開了農場,好像是剛剛領到了一個月的工資。母親用那筆錢給她買了一個巨大的布娃娃。娃娃的腰間有一個小機關是聲控喇叭,隔空拍一拍手,娃娃會叫爸爸,再拍一下,叫媽媽。布娃娃一直陪伴著她長大,直到李劼的個子一點點超過它。她七歲時終于可以輕松地抱著布娃娃出門找別的小朋友玩耍了。不過這時布娃娃已經被蹂躪得面目全非,頑劣的她把娃娃的眼睫毛拔光了,卷曲的黃頭發也被修剪得七長八短,還用油筆在臉上畫了許多藍色的圓圈。藏在里面的喇叭早壞掉被扣出來丟了。一種習慣吧,過年時母親把娃娃肚子里的人造棉掏出來,外殼洗干凈掛在陽臺上,冷不丁看去,晃晃蕩蕩就像掛著一張人皮。有一回她也學著母親的樣子給它洗澡,把娃娃開膛破肚。母親回來怎么縫也縫不好,她不得不丟掉了這個親密伙伴。
這么詳細地講述一個布娃娃,是因為布娃娃和母親的工作有間接的關系,買布娃娃的錢是母親最后一次領工資。她那么珍惜布娃娃,也是對體制的一種懷念。離開農場后母親再也沒有進入任何一家單位,她和國有煤礦完全沒有關系了。布娃娃讓母親丟掉重回國企的幻想,破釜沉舟成為一個自由職業者。
李劼曾讀過母親當年的一篇小說,小說不長,只有幾千字。母親曾經是一位文學青年,她還組織過文學社團,據說文學社最鼎盛時有三百多名社員。這些文學社員遍布礦區各行各業,有機關干部、有老師、有煤礦工人、有售票員、有農民輪換工、有小商小販,這些人因為共同的愛好而走到一起。他們中最出色的一位還被推薦到魯迅文學院上學。母親也算有點文學天賦,她的作品在省里的刊物發表過,那是唯一一次,后來無論她怎么努力,都沒有再把文字變成鉛字。
小說的題目叫《禮物》,漫天的大雪,溫暖潮濕的大棚,綠油油的菜蔬,在鋪墊好浪漫的環境后一個穿著紅大衣的女人出現了。因為寒冷,她的蘋果肌被風雪染成可愛的櫻色。她已經工作了一段時間,為了表示感謝,她準備給隊長送一件禮物——一個精心挑選的剃須刀。外來貨,是從香港那邊夾帶過來的。女人的哥哥在廣州工作,她托哥哥買的。這件禮物本來是準備送她丈夫的,現在被拿來送給另外一個關系自己命運的男人。物盡所用,既然是禮物就應該發揮出它最大的價值,這個男人可以幫她找到工作。對于他們這樣的家庭來說,工作是一件天大的事。的確,送男領導刮胡刀有些曖昧的意思,但她也許就是需要利用這一層的曖昧。
女人帶著禮物去找隊長,公事私事都有,公事是黃瓜秧該轉棚了,私事是她想轉到另一個蔬菜大棚,小青菜的管理要輕松些,黃瓜棚的勞動強度太大了。
隊長笑瞇瞇地聽完女人的要求,伸出的一只手先是無聲無息地放在女人的肩上,很快就試探著向下移動,并像蛇一樣慢慢滑入女人的領口,他的另一只手則緊緊地摟著她的腰,他的身體從她身后一點點靠過來,近得讓她能感到一種可怕的堅硬。忽然,隊長把她的肩膀掰過來,并把舌頭伸進她嘴里強吻了她。女人完全被嚇傻了,身體的姿勢極端別扭,卻又感覺無法動彈,完全僵在那里,像一截木頭。她一點也不懂得配合,隊長可能有些掃興,接下來并沒有對她實施進一步的侵犯,就把她放走了。據她對這個好色男人的了解,他并不缺女人,他的手下有近百名女工,為了得到一份輕閑點的工作,很多女工爭著往他懷里撲,有時甚至還會明里暗里爭風吃醋,這一點讓他變得更加倨傲,甚至開始挑挑揀揀起來。女人明知他有這個嗜好,卻依然選擇一個人去送剃須刀。因為她一直以為自己是安全的,不是說兔子不吃窩邊草嘛。
女人從辦公室出來后,一路在哭,她當時不是不能反抗,而是不愿意反抗,她逆來順受還是希望留住那份工作,最起碼能拿到那個月的工資。她想用最小的犧牲保住工作,一份穩定的收入對她的家庭太重要了。
回到家里女人一次次的刷牙,她遭到了羞辱侵害,卻不能把這件事告訴任何人。女人知道有些話能說,有些話一輩子也不能,如果說了那會毀了一個女人的名譽。沒有哪個男人能忍受自己的妻子遭受其他男人的侵害。
女人沒有把自己當成一件禮物送出去,那么她的工作自然保不住了。
現在,母親還有一天刷四五次牙的習慣,有時候正看著一部電視劇,她站起來就去刷牙。父親說,你媽有潔癖,和你當醫生的姥姥有關。醫生們大都有潔癖。一天洗無數次手,還用小刷子仔細地刷指甲縫。
讀母親的小說,讓李劼長時間沉浸在悲哀中。為母親生活的那個年代。“下崗”這個詞對于95 后的李劼來說是陌生的。為了了解母親下崗的原因,她特意在網上搜索了1998 年時世界、中國究竟發生什么大事,怎么一下子會有那么多的失業者。
1998 年,發生了亞洲金融危機,危機的起源發生在泰國,當時泰國經濟疲軟,外匯儲備不多,還欠著大量的外債。泰國的這個特殊情況被金融大鱷索羅斯盯上,他先是借一大筆泰銖,把泰銖換成美元,當泰銖貶值后再買回泰銖給人還回去。泰銖最后貶值了60%,泰國的股市也狂跌70%,泰國老百姓蜂擁到銀行擠兌,先后擠垮了56 家銀行。泰國的很多企業破產,大量工人因此失業。亞洲金融危機對國內的經濟影響也是巨大的,尤其老國企,大都背負沉重包袱,這場風暴成了壓垮駱駝的最后一根稻草。
在《中國統計年鑒》的記載中,當年原有國有企業職工1.1 億人,集體企業職工4000 萬人,1998 年經歷下崗潮后,國有企業職工人數則為5200 萬,集體工減為1000 多萬,這減少的7000 多萬人大部分都有一段或長或短的下崗或失業的經歷。以一家三口計算,受到直接影響的人群超過2.1 億,間接影響的人數就更多。而母親就是這7000 多萬人中的一員。
現在從經濟發展的大局來看當年的下崗政策,也是一個時代艱難的抉擇,國家和小家一樣,日子困難時,只能讓他們自謀出路。與其困在工廠里,不如讓他們出去各顯其能自己找飯吃去。后來在這批下崗工人中涌現出了一大批煤老板、企業家、地產大亨,但更多的還是一些普通人。他們其實連農民工都不如,農民還有自己的一畝三分地,在城里撐不下去,回家種地,最起碼吃飯沒有問題。下崗工人卻什么也沒有,他們只能握著一雙空拳打天下。
70 后的母親沒怎么讀過書,她讀完初中便不上學了。這也注定了她沒有多少上升的空間和資本。沒有大學文憑,也就沒有通往上層社會的敲門磚。李劼曾問過母親,怎么連個高中都不讀?是不是學習特爛?一天也混不下去?
她承認有點不懷好意,誰讓母親一天到晚總是逼她學習。記憶里母親對她說過最多的話就是,學習去。一個天天讓別人學習的人,自己卻只有初中文化,是不是有些諷刺。果然母親的臉一下紅到耳朵根,她支支吾吾地說,他們礦上的孩子那時都不上高中,全國大趨勢,經歷過十年“文革”,國家急缺人才,大中專院校便從初中招生,成績好的學生都考中專。考上中專就有了工作,還讀什么高中,簡直是浪費。對于普通的工人家庭,孩子有一份穩定的工作就是最好的結局。
和母親比起來父親似乎好一些,讀了一年職高,可并沒拿到高中畢業證。兩個初中畢業生相當于半文盲吧,兩個人又沒有什么深厚的家庭背景,這種家庭的結合可想他們要面對的困難有多大。知識改變命運,這句話對他們這種身份的人來說簡直就是一道魔咒。
丟了農場的工作讓母親很受打擊。憂心忡忡的她決心自救,她失業前是一位水質化驗員,學的是細菌檢驗,四處碰壁后,母親買來了一堆培育蘑菇的書,在家里學著種蘑菇。沒有實驗室,她在廁所的一角用塑料布搭起一個小棚子,自己用廢紙箱做了接種箱,在箱子上裝了一塊玻璃,開了兩個可以伸進手的圓洞。配置了工作用的酒精燈、試管接種針等等。有一回她剛用酒精給兩手消過毒,點酒精燈時著火了。幸好李劼父親在家,要不差點引起火災。經過多次失敗她從日常食用的平菇中成功地提取培育出食用菌種,雪白的菌絲長滿培養試管,毛茸茸的像一團棉花。有了菌種就成功了一半,接著她又培養繁殖出第二代菌種。母親野心勃勃要建一個蘑菇場,成為一名農場主。這時附近村里的一個親戚正好有一個蔬菜大棚轉讓,母親便通過關系承包了下來,對這份新工作她充滿信心。
種蘑菇首先要解決生產原料問題,棉籽皮產量高是最好的原料,可是北方種棉花的地方很少,長途運輸的成本太高不合算。還有一種用鋸末,但要楊樹、柳樹的,楊樹、柳樹木質軟,不宜做家具,原料也少。剩下的就是玉米芯,出菇率不高,但原料容易找到。母親回鄉下大量收購玉米芯,玉米芯收上來還要用鋼磨磨成花生米大小的顆粒,這樣才能利于菌種的生長。李劼父親有工作要上班,人手不夠,母親便招了一個女工,是鄉下的親戚,叫李劼母親表姐。女人嘴甜,為了表示親近,把“表”字除掉了,喊母親姐,喊父親姐夫。母親呢,搖身一變成了老板,雖然手下只有一個工人。
好看的姨為了逗李劼開心,特意從鄉下帶了兩只小兔子,兔子養在菇場,李劼有空就去喂兔子。兔子愛吃“奶奶草”,一種開黃花,根莖有白色奶汁的草。小兔子的嘴巴一刻不停地蠕動,每天吃很多很多的“奶奶草”。父親總是開玩笑說,要吃紅燒兔子肉,李劼哭著不讓他吃小兔兔,這時姨便跑過來哄她。
玉米芯按比例加入糠皮、白糖、石灰,經巴氏發酵滅菌后接入菌種制成一個個小枕頭樣的菌包,成千上萬個菌包疊摞起來,像電影里擺在陣地的沙包。母親就是指揮打仗的那個將軍。菌包擺在通風不見光的大棚里面慢慢生長,有時則長出黃色綠色的雜菌,這些受了污染的菌包要及時挑出來,要不整個菇場就完蛋了。菌房里還要定時消毒,用稀釋過的敵敵畏噴灑。經過一個月的等待,當袋子里長滿白色的菌絲時,就要出蘑菇了。出菇時期溫度、濕度的把控是關鍵,李劼父親夜里便睡在菇房,隔幾個小時起來給蘑菇噴水。姨不舍得在外面花錢租房,也住菇房。為此母親還給她加了一點工資,并許諾蘑菇大量上市以后,再加一點。
功夫不負有心人,種出第一批蘑菇時,母親高興得手舞足蹈,在她眼里那些蘑菇就是一張張長在菌袋上的鈔票。一批菌包管理好的話能出菇三到四茬,她覺得挖到了聚寶盆,錢會源源不斷長出來。李劼隱約還能記著蘑菇場的一些事,一朵朵白花盛開在培養袋上,母親把白花摘下來放在塑料筐子里。很奇怪李劼記憶里一直是白花,而不是蘑菇。
母親和父親打架,她的鼻子流血了,地上有一個綠盆子,母親洗臉,里面的水是紅色的。這些場景一直留在李劼記憶里,有一回說起當年種蘑菇的事,母親驚訝李劼那么早就記事了。
父親對母親動手后,漂亮的姨帶著兔子離開了李劼家。父親惱羞成怒也不來菇場幫忙。李劼父母和礦區其他家庭的父母一樣,時不時會吵架,控制不好情緒就會動手。除了菇場那一次,后來還有很多次,當然父親手下還是有分寸的,并沒有把母親打得鼻青臉腫見不了人。說起來他們都是要臉面的人。窮人的臉皮更薄,扯不得。一扯就壞了。
姨走后,所有的活只能母親一個人干。接下來,母親病了,咳嗽、胸悶、低燒,開始以為是感冒,吃了很多感冒膠囊,VC銀翹片,都不管事。父親還算有良心,回來照顧菇場,不久他也病了,和母親一樣的癥狀。后來到了省里的大醫院檢查才知道他們得的是孢子過敏癥,也就是說,看不見的蘑菇孢子進入了他們的肺。身體的原因使他們不得不停止了這個發家致富的好夢。
母親又一次失業,“工作”成為她心里的一道隱疾。
母親曾有過一段在北京短暫的打工經歷,她當年文學社的朋友邀請她去做書,每天的工作就是在電腦上把別人的作品復制粘貼成一部面目全非的新作品。母親失望而歸。
網上流行過一個段子,說是失敗的老鳥生了一個叫作希望的蛋在窩里。那個蛋就是李劼。她成為母親沖出去的一發子彈。母親把她的理想完全寄托在女兒的身上。母親對李劼的學習要求特別嚴格,兩歲時就能識得幾百個字,五歲時成為一年級的小學生。全班年紀最小,個子最矮,別人輕輕推一把她都能摔個跟頭。母親特別在意她的考試成績。她沒有為別的事打過李劼,但考不好一定沒有好果子吃。李劼成為一個內心憂郁的孩子。
李劼上學后,母親騰出手準備大干一番。她這回吸取以前的經驗,沒有投入太多的本錢。她用一千塊錢做活動經費,開了一家自行車配件店。店面很小,只有三個平方米。這一排小房子,原來是人們放柴炭的地方,因為臨街,有人動心思在墻肚子上安了門窗,開成了門面房。一家這樣做,后面的鄰居都學著開了店鋪。這種小店極其簡陋,連一個柜臺都放不下,父親在墻上釘了幾層隔板,上面放著各種配件。家里的小書架也出自父親的手,滿滿當當地擺著各種書,他們特別舍得給李劼買書。而她卻對另一個架上的東西感興趣。李劼下學后去店里玩,便認識了閘把、閘線、輻絲、腳蹬、單支、雙支、前叉、內胎外胎等等。她記性好,說一次價錢就記住了。但母親從來不讓李劼充當小售貨員。
店里沒有暖氣,冬天時要自己生火爐,母親的手背都是裂開的血口子。公共廁所在五百米外,為了少上廁所,她從來都不敢喝水。那個自行車配件店開了三年。生意一直不好,為了招攬顧客,他們在店外擺了兩只打氣筒,免費使用。有的人用完,不好意思會丟幾個鋼镚,有的會笑一笑,拍拍口袋說一聲沒零錢。大多數人都是停下來打氣,打完跨上車子就走了。如果有人讓母親幫著給自行車打氣,她也不會拒絕,彎著腰撅著屁股,兩手用力一下一下抽拉著氣筒。她想的是和氣生財,也許某一天人家就會來店里買一根內胎。
李劼讀三年級時,母親忽然關掉了配件店。關掉的原因是她讀高年級了,怕同學們知道了他們是修自行車的,而瞧不起她。
配件店關閉后,母親很快又開了一家話吧。從電信局申請了四個電話號碼,屋子里安了隔板,一個小格子間里放一部電話,長途3 毛,短途1 毛。還有電話卡,有20 塊的,有30 塊的,比直接打電話便宜一些。話吧開了不久手機開始流行,來話吧打電話的人越來越少。
五年級時,很多家長把孩子往城里的學校轉。母親開始認為只要孩子學習好,在哪兒上學都一樣。有一回她到學校為李劼開家長會,老師給家長們念了兩篇作文,并說那是班里最好的作文。但這幾篇作文她都在作文書上讀過。她每個月都要進城為李劼買一些課外讀物,順便在地攤上給自己買幾本盜版小說。盜版書便宜,十塊錢三本。
那次家長會后,母親決定給她轉學。要想進城里上學,必須本人有房子,還是學區房,這是母親第一次聽說學區房。他們手里沒錢買房,母親聽從別人的建議想了一個迂回的辦法,花錢托關系把李劼一個人的戶口遷到姑姑家的戶口上,姑姑的房子在城里是學區房,且還是重點初中。時間不等人,遷戶口的工夫,學校有了新政策,光個人有城里的學區戶口還不行,還要直系親屬關系,也就是說必須是自己父母的戶口也在城里的學區。母親一聽就涼了,折騰了半天,李劼還是不能在城里上學。
為了能讓李劼進城,母親也是豁出去了,她和父親一合計,決定在城里買房,買不了大的買小的,買不了樓房買平房,只要是學區房就行。父親騎一輛破自行車在城里轉悠,還真讓他問到了一套,老舊小區,頂樓,面積也不大,只有50 多平方米。要價12 萬。母親去看了房,除了價錢別的都滿意。房主一分錢不降,母親咬咬牙還是決定買了。他們開始挨家挨戶地借錢。這幾年他們雖然沒閑著,但真沒掙著錢。把正在經營的話吧盤出去又借了九萬多,才買下了城里的房子。那些借錢人的名字母親記在一個小本子,天天愁得睡不著。不久母親病了,輸液吃藥折騰了一個多月,后來還是父親了解她,他把記賬的小本子藏了起來,母親的病奇跡般地好起來。
好事多磨,當時房主說要半年后才給騰房,他們的新房還沒裝修好。父親一口答應。半年后孩子正好升六年級并不耽誤上學。中間又有點插曲,半年的時間,房子漲價了,見錢起意,房東便不想賣給他們了。兔子急了也咬人,母親發揮了礦區人粗獷豪放的優點,把房東的祖宗八代臭罵一頓。而父親摩拳擦掌準備揍得他滿地找牙。一文一武,兩個人合作得不錯,房東終于搬走了。
經過戰斗,房子雖然被奪了回來,卻誤了開學時間,李劼半路插班進去,不得不又花了一筆錢。安頓下女兒的學校,母親和父親權衡再三開了一家早點店,賣小餛飩。他們手里沒有多少錢,餛飩店投入少,只要交一筆房租就行了。小區里住戶自己改建的門面房還不算太貴。他們到二手市場買了幾張桌子,再買了兩口鍋一摞碗,幾包一次性筷子就開張了。墻外面掛一塊小牌子——餛飩館。
母親的小餛飩一直是家里招牌飯,有親戚來了,母親便包一頓餛飩吃,好吃還省錢。母親的手藝是和奶奶學的,也算是家傳。蝦皮、冬菜、紫菜、香菜、蔥末、熟芝麻、蛋皮絲放在碗底,用滾燙的雞骨頭湯一沖,激出調料的香味,再把煮好的餛飩倒進碗里去,上桌前灑一點白胡椒粉,點幾滴香油。餛飩鮮就鮮在那一碗湯里嘛。
人生地不熟,城里人是瞧不起外來戶的,這種歧視也沒有惡意,有點像你無意中侵入了人家的領地,天天在眼前晃來晃去,主人當然沒有好臉色。剛開始餛飩賣得不好,他們家頓頓都是吃剩餛飩,煮著蒸著煎著拌著,東西好吃也架不住天天吃,吃得她和父親看到餛飩就躲,寧愿吃白水煮掛面。母親一個人吃,一邊吃一邊還琢磨到底哪兒不對。她一次一次調配湯料、餡料,但還是沒有人光顧。后來,她靈機一動,把賣剩下的餛飩免費送給周圍的鄰居品嘗。吃人的嘴軟,城里人也一樣,天天吃免費餛飩也不好意思,小店里客人慢慢多起來。那些熱心的吃客還會張著油汪汪的大嘴不斷提意見給母親,母親根據他們的要求改變湯的配方。
母親開始買了肉自己手工剁餡,后來樓下的鄰居有意見,不得不買了絞肉機,母親總說味道上差一點。純手工打的肉餡更香。餛飩皮薄,母親從不偷懶,總是要一碗一碗地單煮,這樣的煮出來的皮子勁道有彈性。開水大火,餛飩剛進鍋時像一朵朵的白蓮花在水里徐徐盛開,最多煮一分鐘就要出鍋,多煮幾秒,皮子已經煮老,餛飩也不能保持原來花朵的樣子。母親講究入嘴的東西既要好吃還要好看。
小本買賣,雇不起服務員,小店只有母親一個人忙活,包餛飩,煮餛飩,端飯,洗碗,收拾桌子,收錢,忙得像一只陀螺。為了不影響李劼的學習,他們家的餛飩只賣一早上,上午十點收攤后母親還能給下學回家的李劼做中午飯。
餛飩都是現包現煮,母親沒有幫手,便天天凌晨四點起來先包一部分餛飩出來。李劼有時起來上廁所看到廚房的小窗亮著,推門進去,燈光下的母親和案板上的小餛飩一樣散發著一圈柔軟的光。那一只只餛飩,如一群鳥,撲閃著翅膀,準備沖向天空。包一個餛飩不到5 秒,母親每天大概要包一千多個,重復一千多次動作。她把時間卡得剛剛好,包到規定的數目時,天光大亮,出攤的時間也到了。
小學畢業李劼數學、英語考了100,語文96,母親高興得比賣了100 碗餛飩都開心。
人緣好,買賣才好。母親的臉上常年掛著一臉的笑,大姐、大哥、小妹,叔叔、嬸嬸、爺爺、奶奶不離嘴。一天到晚總是笑,她臉上皺紋卻越來越多。李劼看不得母親的笑,那是一種沒有底線的笑,對誰都笑,哪怕是顧客帶著的一只狗呢,母親也要問候一下。有一回她撈了一只餛飩討好狗,被狗的主人一頓訓,人家的狗很名貴,是吃狗糧的,不能隨便吃別人給的東西。母親訕訕地不知該怎么辦,餛飩已經吞進狗肚子,不可能掏出來。她給狗主人不停地道歉,以后再聽話可愛的小狗,她也不敢喂人家了。
他們家的小餛飩后來成為小區的招牌,有的人從很遠的地方趕來就為吃一碗餛飩。也有人勸母親把店面開大一點,她都以沒有人手忙不過來拒絕了。李劼知道母親手里沒錢,擴大店面就得招工投資,而她掙的錢,都被她拿來交了學費、書費、補課費,尤其是一對一的家教費。說白了,餛飩是小買賣,這個手藝只能養家糊口,不能發家致富。
李劼讀高三那年,他們一家已經進城七年,也算是在城里站住了腳跟。她在市一中上學,但成績并不好,一模考試六門課的總分數是452。母親黑著臉說,這個分數只能考一所普通的二本學校。這肯定是班主任老師告訴她的,這所學校一直保持著考完試開家長會的傳統,也就是給家長一個交代,你的孩子這段時間學得咋樣,用三位數總結一下。天地良心,其實她已經很努力地學習了,一天差不多有十多個小時泡在學校里,屁股都快長痔瘡了。可是成績就是漲不起來。她也下了點功夫,比方晚上十二點以后睡,可是第二天早上瞌睡得厲害,又把熬夜的那幾個小時補回去了。回憶起那段時光,李劼覺得在人才濟濟的一中上學時是她最受打擊的三年,這讓她嚴重地懷疑自己的智商。
可想而知,她第一年高考落榜了。那一年因為道路拆遷改造,母親的餛飩小店沒了。母親一個人關著門在陽臺上哭。她的哭聲低低的,似乎是怕他們聽到。
母親再一次失業。
母親就像一只打不死的小強,沒有了店面,她又弄了一輛二手三輪車,在小區門口的空地賣小餛飩。她早早起來騎著三輪車,把做飯的家什拉出來,把桌子凳子擺好,把巨大的遮陽傘撐起來。做露天生意最怕的是老天不照顧,剛剛還是萬里無云的晴天,一會兒就下起雨刮起風。她不得不把擺好的小吃攤收起來。
因為做的是熟人的買賣,沒有房租,她賣得便比別人便宜些。當年一碗餛飩1元,后來漲到5 元,5 元以后,無論成本怎么漲,再也沒有漲過價。母親說,再漲,那些老主顧就不來了。
李劼補習一年,考上了重點大學。母親看到貿大的錄取通知書時,笑成了一朵花。貿大的旁邊是魯迅文學院,兩所學校之間僅僅隔了一條文學路。魯院是文學的圣殿,傳說在那里讀書的作家們養著一只可以談文學的藝術貓,夜里貓和作家們一起暢游在文學的大海上。母親雖然不寫小說了,但她和一些寫小說的朋友還聯系著。那位從魯院畢業后的朋友,在北京發展得不錯,還成了知名作家。母親講這些時眼睛里有一種光,那光大概也可以叫作文學吧。
憑李劼的成績,她本可以讀中山或南開的新聞系的,可是因為母親一再暗示想去魯院文學院看看,她在最后幾分鐘里,把第一志愿改成了貿大。主要是李劼那一刻心軟了,她低頭時看到母親的白頭發,像一朵白菊花盛開在頭頂。
沒想到母親這么快就老了。她讀高中時母親好像還沒有白頭發,四年下來,竟白了大半,平時全靠染發劑遮著。
這些年她把和母親對著干當作快樂,凡是母親認為對的,李劼必定唱反調。一想到馬上就要逃出母親的手心遠走高飛了,在人生的大事上權且聽她一回,全當可憐她那顆慈母心。李劼也有自己的小九九,她知道從往年的成績看,她考貿大根本沒有戲。可是那年風云突變,炙手可熱的貿大錄取分數降了5 分,就這5 分把李劼這只小妖收了進去。
去貿大報到完,母親急急地把她和父親帶到了魯迅文學院。她結結巴巴地對門衛說了三次那位文學朋友的名字,一再強調他當年在魯院讀過書。而門衛根本不關心這些,只是潦草地登記了一下他們的身份證就放他們進去了。原來只要拿著身份證,魯迅文學院是任何人都可以進來參觀的。母親分明有些失望,訕訕地收起證件,帶著他們步入這個文學的圣殿。
母親像一個朝拜的圣徒,一邊走一邊辨認著院子里的那些塑像分別是哪位著名作家,還如數家珍地講著他們寫過什么作品,有過什么經歷。父親插嘴說:“小劼,晚上吃烤鴨吧。北京的烤鴨出名。”母親滿臉通紅一句話也說不出。當然,母親在魯院也沒有遇到那只傳說中可以談文學的貓。
在去烤鴨店的路上,母親小聲對李劼說,你是我最好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