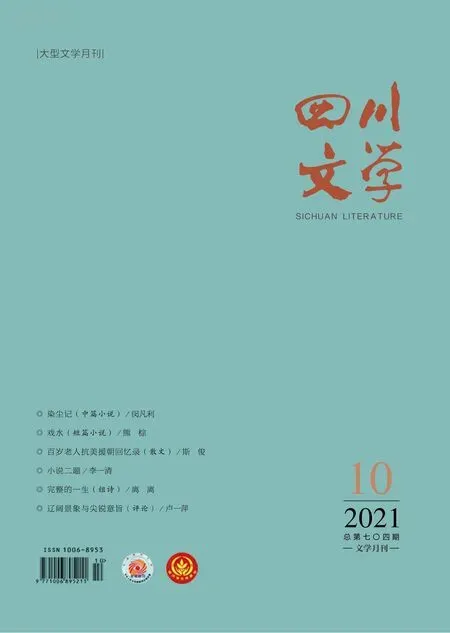九十步
□ 文/楊一父
一
九十步——不知道的,還以為是一段距離,其實是一個村莊的名字。為什么叫九十步?從哪里到哪里是九十步?到底是九十步還是九石步、九十鋪?這是個問題。
東出龍尾峽,九十村靜靜依附在右邊山崖之上。邊陲的村莊大多如此,要么臥在周遭看似隱秘內部實則開闊的平臺;要么窮盡溪流就是村莊;要么依山而居,三五戶、十多戶人家蘑菇一般長在山腰的密林之間。九十步山下是龍尾峽,地勢險要,溝深林密,夏秋遇上惡劣天氣,時有隆隆濤聲震耳欲聾;山后壁立萬仞,一道山梁東西走向,橫亙在村子背后,梁上林木茂密,偶有野物出沒。深山藏人家。要不是夕陽下那一縷炊煙或是幾聲狗吠,你怎么也不會相信山崖之上居然還住著一個村的莊戶人家。先人選擇這樣的地勢繁衍生息,自有他們的道理。是為了躲避匪患,還是為了耕種方便?總之,第一個來這里的人住下之后,另外的人也跟著就來了。來了就不走了。村民好比竹林,竹生筍,筍生竹,連成一片,村子就形成了。
棄車,循山路而上。多年前村民就是由這條羊腸山路進出的。出門下坡,進入龍尾峽,沿龍尾峽走幾里路就進了城,進城辦事或是看病,原路返回,走到思經橋,抽一支煙,歇口氣,又弓著身子一步一步往山上攀爬。大人小孩對山路上的植物熟視無睹,花開花落,一棵小樹慢慢成長,不經意間已長成大樹。從它旁邊走過的小孩變成了老人,之后又變成故人,再之后,又一撥兒孩子重復著上一輩的日子。2000年之后,村子通了公路,到九十步可以從東邊的蘇家村進入,也可以從南邊的藏漁路進入,都是平整的水泥路。有了水泥路,山路就廢棄了,幾乎沒人行走。路邊雜草叢生,有零星的野花孤獨地開放。一種叫不出名的植物結出圓圓的果實,果皮閃亮,滾動昨夜的露水。那些圓圓的果實,有紅的,有藍的,高高舉過枝頭,使勁兒昭示著自己的存在。
樹林忽然向后一閃,村口到了。事實上這已不是村口,公路通車后村口改在了路口。之前的村口已被林木育閉,一片荒蕪。人家有的遷走,有的把房改建在了公路邊。一路往前,遠遠看見一片遺棄的宅基,是九十步新興寺遺址。尚有殘碑為證。碑上記載有與新興寺相關的文字,年代久遠,字跡模糊。從殘存的碑文推斷,寺廟大約建于(或復建于)清康熙二十八年。寺有三殿,規模不算小,據說香火極盛,有遠近的香客前來朝拜,只可惜廟宇不復存焉。大殿遺址前有一對殘存的石獅,左邊的石獅腳踩石球,睜著大大的眼睛,威儀屹立,另一只雌獅則半身埋在地下,僅露出獅頭,眼睛也是睜得大大的。石獅雕刻精美,造型生動,足見當年的工匠水平很不一般。據村民講,新興寺前的石獅享受千年香火,竟然活化成仙。雙獅幻化成人形,下得山去,過著人間恩愛的日子。石獅一去數載,不思回歸。之后某一年,一個月黑風高的夜晚,新興寺突然燃起大火,古剎付之一炬。上天得知,將寺廟失火歸罪于石獅擅離職守,遂將石獅打回原形,在此蹲守。如今,即便寺宇不在,一對石獅仍堅守如初,連眼睛也不敢眨一下。廟跡中軸線上有一排青石砌成的石階直通最后一殿。石階寬一米左右,均是青石鋪就,歲月痕跡清晰可見。石階不多不少,剛好九十步。難道,九十步的秘密就藏在這里?廟的一側,石階之前,有一巨石,三間房子大小。巨石臥在寺前便是佛緣。于是,新興寺住持在巨石上鑿了石步,人們從石步進出寺廟。奇怪的是,石步不多不少,剛好九步。九石步?難道,這個石頭也藏著村子的秘密?又據本土作家李存剛考證,這個地處川藏茶馬古道旁的小村落曾經有過繁華的過往。在茶馬互市興盛時期,大大小小的鋪面開塞了整個村子,買賣茶葉的、食宿的、販賣日用雜貨的,一家接著一家。總之,那時就是一個規模不小的集市,有心人統計過集市上鋪面的數目,不多不少,恰好是九十家,村子于是被叫作九十鋪。九十步是不是九十鋪的讀音訛化而來?這也不是不可能,步和鋪傳著傳著就混淆不清了。然而,一條古道橫貫整個村子卻是事實,九十村曾是茶馬古道驛站也確有其事。看來之前曾有過集市,商鋪一家接一家也不是虛構的。那究竟是九十步、九石步,還是九十鋪?三個說法到底哪一個是此村名字真正的緣起?村里老人們含糊其詞。關于村名的來歷至今仍然沒有定論。我覺得三種說法也都有道理。一開始我認為這個問題很有必要搞清楚,可真正走進村子,才覺得這似乎又是一個沒有必要搞清楚的問題。村子無論叫九十還是九石,是步還是鋪,又有什么關系呢?作為一個有故事的村莊,名字的緣起留給人們去追問,之后止不住猜想,這,不正是村莊故事往下延續最好的理由之一嗎?
二
把村名的緣起擱在一邊,我們踏上村子里的古道。古道舊時被稱為官道。意思是官家茶運專用通道。這條道比其他地方的古道要寬得多、平得多,從石階和石墻的規模和工藝可以看出,像是官家專門劃撥銀子刻意修鑿的。境內甘溪坡、竹崗山、長河壩山坡上的古道比起這段官道來,更顯狹窄、險要,有的地方人背著茶包只能面朝山壁側身而過,大多路段的石步要么自然形成,要么是背夫們自己簡易搭砌,粗糙而原始。這是山道和官道的區別,就像鄉村道路和城市道路的區別一樣。村子往東便是蘇家,蘇家村下坡再往東就是始陽。始陽是曾經的商貿繁華之地,舊時很多商號茶號就設在始陽古鎮上。其時龍尾峽不通人煙,官家的茶葉從始陽出發,到破磷左拐上坡,經蘇家一路過來,穿過九十管道,下坡,沉入谷底,沿著龍尾峽懸崖陡壁上的棧道,一路向西,到達縣城,再向西,出碉門,之后踏上崇山峻嶺之中漫漫的山路。官道九十村段全長約6公里、寬1.5米,有規則的條石路面,道路兩側有護墻,春夏時節,山溪暴漲,護墻可將溪水引入灌溉溝,保證山下的良田不被沖毀,也方便灌溉。一路上有多處歇腳石,長長的一排或是單獨的一處,背夫將背夾子往上一靠,茶包子就穩穩當當的了。背夫或吃煙,或擦汗,或聊天,或唱山歌,直到掌拐一聲吆喝,又上路了。官道上有一段石階,古樸滄桑,卻完好如初。石階由紅砂條石砌成,兩側有方條石固定。寬1米多,長100余米,數了數,180步(180步,是90的2倍,難道這里也藏著秘密?)。石階上拐子刻出的大大小小石窩子清晰可見。拐子窩圓滑、平整,最深的有10厘米。在一塊厚厚的石板上,有個石印子,足有30厘米,狀如一只鞋,剛好容一只腳踩在里面,叫“凹腳蹬”。背夫的腳一次次地踩在上面,日積月累竟然踩出了如此石印,真是一件不簡單的事情。石印讓人想到少林功夫里的練功石,那得有多么深厚的功力,得流多少血汗,才能在石頭上留下這樣深的印記。這些拐子窩和腳印,仿佛一首凝固的歌譜刻在古道上,只要輕輕敲響其中一個音符,背夫的歲月就會從古道上醒來。再敲,茶馬古道的輝煌樂章就會在崇山峻嶺之間回響。又仿佛如一幅長卷上的印章,浩瀚的茶馬古道史詩由成千上萬的背夫一個腳印一個腳印,一拐子,一拐子繪就。而這些印記,就是背二哥們用血和汗水烙印在長卷上的印章,悲壯、深入,鮮活而奪目。上完石階的平臺上,矗立一碑。碑上刻的是“重修新興寺路梯蹬碑記”。文字依稀可猜古道歷史:“賜進士第中憲大夫陜西按察使古洪萊山楊仲瓊撰”“夾江儒學貢士會江高岳書”“主盟招討使昭勇將軍XX高繼光”“嘉靖二十一年歲次壬寅秋八月”。古道的石階是誰人主持鋪就的呢?從碑文看,應是明朝天全土司高繼光修建。這就對了,稱這段路為官道是有依據的。不過,在九十村又流傳著一個傳說。說是地主劉范氏捐建的。傳說她有一個兒子,幾代單傳。一年,兒子被土匪搶上山。劉范氏托人疏通關節,找到山寨王,用等同于兒子體重的白銀贖回兒子。不料兒子因受驚過度,回家后臥病不起,不久便夭折辭世。喪子之痛讓劉范氏覺得錢財無用,便使出家中金銀,組織當地村民修建了古道。劉范氏生卒不詳,只能估摸是清末時期人。大約在民國17年,劉范氏家突發大火,莊園付之一炬,盛極一時的家族也從此沒落,偌大的房基如今成了一片石墻圍著的菜園。推開柴扉,一片綠茵難掩蕭瑟之氣,曾經的富貴淹沒在歲月的苔蘚之下。傳說也許是后來的事情,石碑無言,已經說明了一切。
三
村莊還有另一道風景——石墻石院石房子。近些年,村里大多數人家都對房屋進行了不同程度的改造,尤其是村子通公路之后,二層、三層的小樓不斷地冒了出來,白晃晃的外墻,暗紅色的琉璃瓦掩映在青峰之下,一派欣欣向榮的景象。只有村西頭的幾間老屋還頑強地證明著村莊的過往。老屋被石板鑲砌的圍墻圍著,墻柱高兩米左右,四方抹楞有凹槽;墻柱之間,條石從低到高依次鑲嵌于凹槽內。龍門口也是條石搭就的。推門進去,院壩一色石板鋪就,院角有石槽做成的花臺,花臺里有幾朵小花懨懨欲睡。另一角有一棵老梨樹,樹冠濃密,枝條伸出了墻外。正房的板壁也是石板鑲嵌而成的,一排三間,褐紅色,陽光下散發出古老的神韻。房檐下掛著幾掛金色的玉米,是去年秋天掛上去的。一位老人坐在大門口的石凳上,陽光在他溝壑縱橫的臉上泛著古銅的色澤。一苞老玉米在老人手中不停轉動,一顆顆透亮的玉米粒兒掉進雙腿之間的簸箕里。我們的到來并未打擾到老人。老人側耳聽了聽動靜,嘴角蠕動了幾下,想要說什么卻又閉口不言。老人平靜安詳,繼續抹著手中的玉米。陽光、石屋、玉米掛、老人,構成一幅古畫。這讓我想起山下破磷村的石頭寨,那里之前也全是這種風格的民居。一點也不難推測,在很久很久以前,山上的蘇家,九十和山下的破磷連成一片,都是石頭寨的領地。烽火歲月,山上山下相互照應,抵御了一次又一次外敵入侵,確保了家族的安好和子孫的繁衍。
村莊雖然有了公路,也建了不少新房,然而,村莊的落寞和寂然卻是無法避免的。就像這幾間老屋。“村里越來越多的村人選擇了背井離鄉,村子里只剩下不多的老人和孩子,房屋空了,田地里空了,道路空了……整個九十,差不多就是座空了的村子”(《九十》李存剛)。楊賢強是我本家兄弟,是村子里20世紀90年代考出去的大學生,大學畢業之后在成都開辦了公司,經營四面八方的山貨,當然也包括九十村的。各地的竹筍、蜂蜜、鹿耳韭等生態原料,經他創意和加工,并成功進入各大超市,竟成了都市人的搶手貨,生意自然越來越好。楊賢強在成都定居了,之后將父母也接到了成都。九十的老屋日漸頹廢,不忍直視。年頭歲尾的,除非老人執意要回來看看,給祖墳燒幾張紙錢,一家人這才又回到九十村。打掃老屋,生爐做飯,卻總覺怎么也不如往日。幾日之后又關門閉戶去了成都。開始幾年老人還常回來,后來也就逐漸稀疏起來,也許,有朝一日他們還會回來的。有幾次楊賢強回天全也住城里,忙完事情一溜煙就回成都了。我想給他聊聊九十村,聊聊從楊家坪搬遷至九十的父輩,話到嘴邊卻又咽了回去。類似楊賢強者,九十村出去創業的人還有幾位,即便不如楊賢強功成名就,也大多在九十之外購了房,成了家,不想再回來。偶爾有年輕后生在外打工或是讀書回來,村子里晃動幾個青春朝氣的身影,可不久又恢復了往日的寧靜。
路口,一條石板小徑伸向竹木相間的林蔭。小徑幽靜,且彌漫著花香。走進林蔭小徑,茶花夾道。仿佛小徑盡頭住著神仙。穿過小徑,豁然開朗,一個石板嵌砌的院壩平整規則,院壩上方是一處老房基——這是吳家老宅,從基石和宅基規模可以看出,多年之前吳家大院恢宏氣象,非比尋常。老房基上立著一間破敗磚木房,獨一間,無依無靠,讓人疑心被風吹倒。聽到我們講話,門吱呀一聲開了,走出一位老人。老人叫吳永軍,是縣上某企業的退休職工,70多歲。吳家大院人丁興旺,后人紛紛成為干部或企業職工,先后搬離了九十步。老房子也一間一間拆走,最后就留下我們見到的房基。至于這間磚木房,從木料和做工看得出來,大抵是老人退休回鄉之后才建的。老人回到老家,除了喝酒打牌,終日無所事事,便在房基周圍遍種茶花,房前屋后大大小小,少說也有500株茶花,樹齡有的幾歲,有的十幾歲,胸徑有幾厘米的,有達十多厘米的。茶花開得正盛,有的才打骨朵,有的剛剛綻放,有的開得芬芳馥郁,一朵朵一樹樹在枝葉間怒放。屋后有一棵大茶花樹,枝繁葉茂,冠幅幾近十米,花樹舉著數百朵艷麗的茶花,如一團火。老人說,種茶花全是因為喜歡。如果要賣,也只賣懂花的人。老人與茶花一定有著秘而不宣的故事,否則,怎么會一個人在老屋與茶花為伴呢?花間一壺酒,幾度夕陽紅。好快意的人生。我突然想,茶花在九十村開得如此艷麗,要是村子里每個院落、每條道路都遍種茶花,那該是怎樣一番景致。
吳家老宅的前面是一片茶園。從村東頭一直綿延至村西邊。千畝茶園滾動著層層綠波。春茶已經開始采摘,茶壟之間,茶農舞動雙手,仿佛在演奏春天的樂曲。指尖翻動,一顆顆嫩芽被卷進了腰間的茶簍。一位老人見到我們,揮手打著招呼。是老支書任連輝。老人一邊摘茶,一邊向我們講述茶園的歷史。老支書說,這片茶園形成多不容易,之前大家猶豫觀望,由村上黨員干部帶頭,后來種茶的人就越來越多。十幾年了才形成這樣的規模。老支書還說,兒女們都離開了九十,可這么好的茶園怎能被撂荒呢,所以,他和老伴就留守在老屋里,守住這一方茶園。老人突然話鋒一轉,問現任支書,鎮上不是要來我們茶園搞一個春茶采摘體驗活動嗎?嗯,好,好,這樣就能吸引更多的人來九十了。老支書希望大家一起努力把九十的茶葉做好,發展鄉村旅游,讓九十再度熱鬧起來,重現昔日的熱鬧。老支書說的重現熱鬧場景,或許是指昔日茶馬驛站的興盛和繁華,老支書的愿望也許正是大家的愿望。
2015年,九十村熱鬧了半年之久。因為九十官道是茶馬古道天全段極有代表性的一段。蘆山“4·20”地震之后,縣上爭取了重建資金,啟動了官道修復項目,以期發掘整理文化資源,保護文物,形成文化旅游景點。見天幾十個工人整日在古道上施工。人們興高采烈,議論紛紛,都以為修復了官道,肯定能引來游客,村子也就熱鬧了。古道倒是修葺完成了——官道修舊如舊,殘碑重立階前,還建有路亭,題寫匾額楹聯。古道蒼蒼,山路茫茫,竹影婆娑,亭榭掩映,頗有幾分意蘊。蜀西才俊李南洋《重修九十步村官道遺址記》贊曰:
余于高處細觀,實可謂恢宏一道也。設若時侵首夏,日映余春,露泣修篁,風清隧澗,松蘿云氣,藤蔦星懸,可以陶瑩心靈,澄清耳目。又若秋冬兩時,浮涼于彤闈,凝清陰于碧沼,池潔鏡而冰春……更兼修復之后,雙碑鎮于首尾,三亭落于林蔭,遙臨一衣帶水,回望傘伴群,不由徒生感嘆,勝地淹留,何必華胥之國,蕭然物外,不假園圃之阿。
站在九十的茶園,耳畔縈繞老支書任連輝的話語。九十,也許在不久的將來,真會有變成“九十鋪”的那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