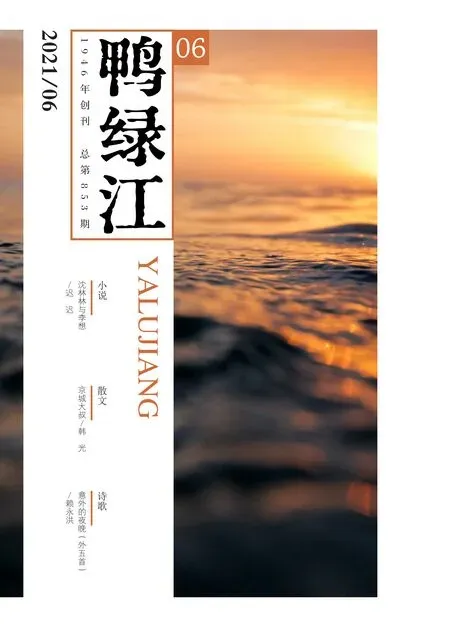陋室墨染書香濃
彭小平
愛好閱讀文學類書籍,是兒時養(yǎng)成的習慣。那時,書籍猶如家里的柴米油鹽一樣匱乏;那時,讀書就像沒有吃上一頓飽飯般的饑餓。
小鎮(zhèn)的書店里,書的種類單一,即使有自己想要的書,也無錢購買。那時候買一本書將用去三四個雞蛋換來的錢。有時,在場鎮(zhèn)的路邊,看到一截報紙,撿起來便如饑似渴地閱讀,無論是新聞還是文藝副刊,都會在閱讀中忘掉少年的饑餓與穿著破舊衣服帶來的煩惱,獨自欣喜若狂。
1978年,生活突然發(fā)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書店里的書籍種類逐漸豐富,仿佛見到泰戈爾仰天謳吟“我站在深冬的風里,等著你的愛,即使得不到你的愛,我的那份等待也是甜蜜的”,讀到托爾斯泰“幸福的家庭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卻各有各的不幸”,領略李商隱“蓬山此去無多路,青鳥殷勤為探看”的相思,感受李清照“輕解羅裳,獨上蘭舟”的離愁。讀著讀著,我的思緒卻不知不覺地漂泊到了懷春的季節(jié)。
20世紀80年代初,一個夏季逢場天的中午,我趕集后在返回途中的竹林里乘涼,認識了聞名鄉(xiāng)里的鄉(xiāng)村作家兼通訊員鐘正偉。通過鐘正偉,我認識了作家、巨石鄉(xiāng)干部王方才。由這兩位才子引薦,我又結識了揮執(zhí)教鞭的作家、安平鎮(zhèn)初中語文老師胡濤和詩人、大河堰村小學教師杜碩彥。
最初接觸他們時,心總是撲通亂跳,身體顫顫巍巍。爾后的交往中,由于愛好、觀念和價值取向相類,得到了他們的關愛,從而拉近了與之相處的距離,漸漸產生彼此融為一體的思想共鳴,甚而有了抵達至對方心靈的無隙交誼。
當生命的腳步走到投入社會的門口時,眼前生活困頓、事業(yè)渺茫,未來一片漆黑。他們是照見我靈魂的燈塔,能洞悉我藏在心底最深處的秘密。走動得最頻繁的是我與王方才和鐘正偉三人。
為了思維不至于在貧瘠的紅坡禿嶺、褐黃土地上荒蕪,我便時常到他們倆家里去,論古道今,談天說地,徹夜不愿入睡。
孤獨的時候總是那么蒼白,寂寥的日子總是那么無奈。當身心處于這種狀況時,我就與他們相約一起去趕集,我們邊走邊談,關不住的話匣子能通暢心結,有道不盡的重復話,最終依依作別。
漸漸地,他們把我當成比骨肉同胞還親的兄弟,我在享受著與他們在一起的幸福時光的同時,還恣意撒嬌和縱情放肆原本的性格。
他倆的家,與許多農村的住宅一樣,樸素而簡潔;他倆的家,與其他農戶(王方才的家也住農村)不一樣的特點是有一間簡陋的書房,書籍畫報、紙墨筆硯樣樣俱全。而他倆相異的是,王方才家有竹笛,鐘正偉家有口琴。
那時大家都不太富裕,但是,只要我們相聚在一起,再窮的家都顯得格外奢華。相比之下,鐘正偉比王方才的家境要差一些。然而,每當我們相約到鐘正偉家里時,與到王方才家一樣,都是格外歡喜的。
記得那是一個秋季,我邀王方才到鐘正偉家,忙樂了鐘正偉一家人。鐘媽媽用糧食把屋外院壩里的雞引進屋里,捉住便宰殺,輕快麻利的動作非常感人。嫂子猶如一家主男,個頭較大力氣也不小,閑庭信步似的用石磨推豆腐。鐘正偉托鄰居幫他去鄉(xiāng)場打酒、割肉、買調料,他那小小年紀的兒子則在自留地里摘蔬菜。
我們仨圍坐在其書房里,慢悠悠地喝茶,含化心中的郁結;慢悠悠地剝著新鮮的花生米,咀嚼勞動的甘甜;慢悠悠地老生常談,暢想人生的邊際。在那長談中發(fā)散的思維十分離奇,跳躍性的話語跨越天南海北。在長談中,我們暢想著美好的未來,除卻了憂愁與倦疲。
用餐時間到了,喝酒,舉杯豪飲,爾后酩酊大醉。結果,三人同床共枕,打著呼嚕,酣然在夢里游弋。
他們與我人生旅程中遇到的浩若燦爛星星的摯友一樣,給了我人生的重要熏陶,讓我有了睥睨云卷云舒的淡定從容,有了看待功名利祿寵辱不驚的倜儻灑脫。
后來,我們各自為了想要的生活,在不同的人生軌跡上踽踽前行,聚少離多,甚至未曾謀面已經年。然而,心,常用鴻雁傳書,牽隨著記憶,在鄉(xiāng)間田埂小路上幽幽徘徊;情,用網絡傳遞青春夢想,在城市的一隅冉冉泛起,感受苦痛快樂交織的人生。
他們時常提醒我做事穩(wěn)重,遇事沉著,修為淡定,人生從容。他們的每一句話對我來說都是金玉良言,每當品味、享受這些話,都覺得醍醐灌頂。他們激勵我無論何時何地,無論什么境況,都要耕讀不輟。我常獨自感激涕零,在炎熱的夏天或寒風凜冽的冬日,攜縷縷書香,溯流而上,暢飲知識的瓊釀,享受明媚陽光照耀抑或風霜雨雪洗滌下的舒暢快意。
借此,我謹將本文傳遞給我尊友、敬友、畏友的您,讀好書,交摯友,抒真情,未知您能否感受到人生炎熱中的一抹清新的陰涼和冬寒料峭的時日中一襲暖陽的溫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