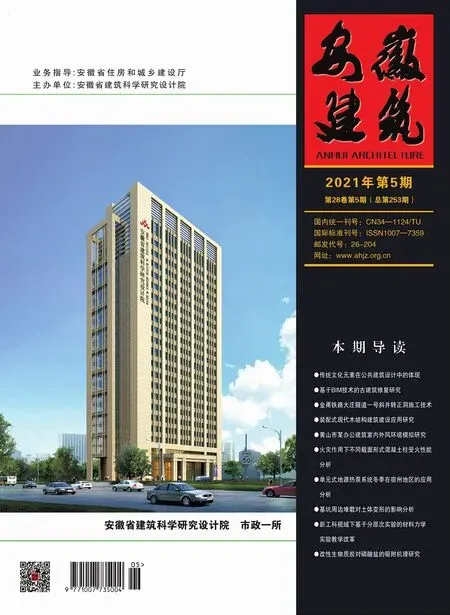江南古典園林造園手法在現代建筑環境設計中的傳承與創新
——以貝聿銘設計的蘇州博物館新館為例
趙二保 (吉首大學美術學院,湖南 張家界 427000)
1 貝聿銘建筑環境設計風格概述
貝聿銘作為一位美籍華人,中西交替的經歷對其建筑環境設計風格的形成起著決定性作用。早期的貝聿銘受現代主義建筑師路德維希·密斯·凡德羅(Ludwig Mies Van der Rohe)的影響,秉承“少即是多”的極簡主義設計理念,重點傾向于設計具有社會意義且兼具美感和低造價的高層城市住宅。60年代,趨向柯布西耶的雕塑性手法。如艾弗森藝術博物館和美國國家大氣研究中心,注重建筑造型的幾何化。中期,在對功能與形式的關系處理時,突出表現以三角形為主的建筑幾何性,從單一的幾何形體到豐富多變的組合體,形式更趨多樣。如法國盧浮宮玻璃金字塔,將現代主義的幾何性、空間性、簡潔性發揮到了極致。后期,開始將地域文化的裝飾符號抽象化地運用到作品中,使其與周邊環境更趨融合,即建筑融合自然的空間觀念,因此雕塑性的特質也有所減弱。如日本美秀美術館,注重當地環境和傳統建筑文化相呼應。同時,日本美秀美術館與蘇州博物館在環境的延續和對傳統文化的理解上有著密切的關系。
在他看來,藝術和庭院是分不開的,中國傳統園林的形象應在庭院空間的處理中得到延續,將傳統建筑的舊有元素與當地的語言和辭藻結合在一起,創造出融合傳統與現代的建筑風格。此作品播下了貝聿銘發展現代化中國建筑的種子,用他的方式打開真正的中國建筑的大門。
2 蘇州博物館的建筑空間環境
蘇州博物館新館基址處在一個有著兩千五百年歷史,充滿著詩意與人文氣息的蘇州老城區,木質的屋舍和磚砌的瓦房成為該地區的傳統建筑文化符號。在基址周邊,北靠世界文化遺產拙政園,東臨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忠王府,環境的因素對貝聿銘的設計造成極大壓力,在他看來新館必須展現傳統風貌,但也不能一成不變,通過添加新元素,使新館變得更加現代化。因此在新館的設計上提出了“不高、不大、不突出”原則,力求通過對江南傳統古典園林造園手法的借鑒,將其運用到新館的整體布局、建筑與庭院設計中,使整體融入歷史街區,為老城區增添新活力,在和諧中尋找建筑的現代之路。
2.1 整體布局
新館最大特色是吸取江南傳統造園手法,將疊石、理水、樹木及周圍環境的成景借景條件作為重要因素進行考慮。師法自然,靈活多變,充滿意趣。
在整體布局上,利用水面作為周邊古建筑風格的延伸,建筑環繞水面,形成一種向心、內聚的格局,使人感到開朗寧靜;中軸對稱的三路布局與東邊忠王府格局相互映襯,十分和諧。傳統江南院落式布局在現代幾何造型中體現了錯落有致的空間關系。
在建筑布局上,延續江南傳統園林建筑單體形象融于群體序列的特點,通過院落來聯系各功能不同的建筑,各活動單元既相對獨立,又依其性而得其所。主體建筑以粉墻黛瓦的形式“隱藏”于環境,通過尺度相似的不同空間序列的轉換,又使單體建筑顯示出獨立性格。
2.2 建筑
新館的主體建筑在整體上延續了蘇州傳統園林建筑灰磚白墻的建筑風格。在屋頂材質的選用上,摒棄當地傳統的磚瓦屋頂,選擇遇水可變色的“中國黑”花崗巖,創新地在結構上有所變化,視覺上進行切換,加之鋼和玻璃的使用,對采光性有了很大改進。在尺度上參照蘇州傳統園林建筑約6m的高度,嚴格進行高度約束,將多余功能分區移至地下部分。在建筑造型上,新館屋頂與傳統建筑瓦頂二比一的比例相一致。同時出于對建筑耐用程度的考慮,在較為脆弱的粉墻墻角部分,采用石材包裹以進行保護。
在傳承傳統民居形式的同時,通過貝氏語言的運用,使新館產生新的設計理念和審美傾向。從日本美秀美術館開始,貝聿銘的建筑有著豐富的幾何化語言、綜合安排的幾何形狀、地域文化中提取的幾何形狀等,但基礎都是最基本的幾何形體。在新館建筑的設計中,以有著穩定、剛直、簡潔、抽象、有力度等特點的三角形為母題,將建筑空間的幾何形發揮到了極致。
在建造工藝上,貝聿銘對場館各部位施工的精準程度十分注重。包括天窗木紋金屬遮光條的調光測試、樓梯的背面設計、水池的控水量、泰山石、松、竹子的選擇、室內的點線對齊、收邊工藝等都十分考究,從工程和藝術兩個角度考慮,揚長避短,將材料優勢發揮到極致,體現了工業時代的精確。
2.3 庭院
2.3.1 筑山
在江南古典園林中,為追求中國山水畫的詩情畫意,通常以太湖石來堆疊假山。正如計成在《園冶》一書中對“峭壁山”營造手法的描述:所謂峭壁山,乃是依靠墻壁鑲嵌掇疊而成,以白色的墻壁為畫紙,用石頭來作畫,掇疊時根據石頭的紋理,用繪畫的皴法,仿效古人繪畫的筆意,再植以黃山的松柏、古雅的梅花、秀美的修竹,透過圓窗盡收眼底,仿佛在鏡中神游一般。古代石匠在對太湖石外形的處理上,先根據原石的可塑性進行初步造型,再將其置于湖中,待到十年到二十年后再由他的后代收回。這時的石頭經過湖水沖刷的天然侵蝕,變得紋理縱橫、形態奇巧。
貝聿銘在蘇州博物館新館的假山營造中,傳承了江南古典園林中“以壁為紙,以石為繪”的筑山手法,同時受上述的時間重要性的影響,選用精心挑選的石塊,按照天然石的輪廓切割出來,通過燃燒巖石,使毫無特點的石塊產生陰影般效果,參照米芾山水畫的意境在拙政園的白墻前成排放置,有著“天門中斷楚江開”的壯闊氣勢,而非選用傳統園林中的太湖石。一是出于風格的考慮,太湖石“瘦、透、漏、皺”的特點與精確、優雅、簡約、抽象的建筑風格不匹配;二是在貝聿銘看來,古人在太湖石的運用上已達到出神入化的地步,自己將很難再超越古人。而采用現代工藝最終營造出的現代抽象式風格的效果,則很好地呼應了現代風格的場館建筑。其次,為營造假山的“隱喻”感,拋棄了傳統江南古典園林游人穿梭體驗的考慮,而是通過用水阻隔人與石來保護石景的尺度感和整體氣氛。
2.3.2 理水
園無水而不活。經過千百年的造園實踐,理水已如血液般成為江南古典園林造園必不可少的要素。傳統江南古典園林造園中,通常以水面形態為基礎,在水處理上遵循以曲輔方,似方若曲的法則。如江南四大名園之一的留園,在以山水為主的中部空間,其間架基礎則是由近似方形的水池構成,外形如舫的涵碧山房和明瑟樓出挑的平臺將原本呆板的方形破為曲尺形,由小蓬萊與濠濮亭所在之半島及其間連接之曲橋,再次將水面破分。以此形成的復合型水面使得中部庭院頓生曲意之趣。
蘇州博物館新館室外庭院理水正是傳承其江南古典園林水景的曲方理法。整個庭院以深度約一米的靜態水池為中心,在保持水面整體方形的基礎上,通過大廳主體建筑北面的親水平臺、八角亭以及人工硬質駁岸來柔化池岸,增加曲意,豐富其變化。連接東西場館的折橋對水面的劃分,使水面更趨豐富多彩。貝聿銘所運用的直線方形的理水手法,可理解為傳統曲方理法的創新,運用現代手法對傳統造園要素進行處理,呈現的效果更為現代,具有人工的規整與穩定的特性。平靜的水面與亭、臺、樓、沙、石、橋交相輝映,相得益彰,加之有蓮、魚、盆景以及水中浮萍的點綴等,營造出“天地無限景”的詩畫意境。
2.3.3 橋
橋在江南古典園林中具有交通通行的實用功能,連接景觀節點、點綴風景、營造情趣意境的造景功能,以及本身所具備的審美價值。蘇州古典園林中多為曲橋、拱橋,蘇州博物館新館的橋延續曲折婉轉的基因,創新地呈現出直線和折線的交叉形式,蜿蜒在庭院中心的水面,低矮的石欄使人親臨水面,有簡潔輕快之感。橋將水面一分為二,南側較為開闊的水面在主體建筑與天空的倒映下更顯寬廣,北側在圖畫式山景的烘托下則更具悠遠。在橋的材質選擇上,貝先生認為傳統橋面采用的石塊與木材不利于長久使用,因此選用鋼筋混凝土現澆的方式,同時與現代風格的整體環境也更加相符。
2.3.4 亭
有園必有亭。亭作為江南古典園林中美的符號,有方亭、圓亭、六角亭和橋亭等,在現代園林設計中同樣必不可少。在蘇州博物館新館中,亭的主體采用現代鋼架結構,雙層斜頂由玻璃覆蓋,玻璃內側鑲有木飾面金屬格柵,照明燈具置于結構柱上。亭懸于水面。北觀橋與石;東賞建筑與松梅;南與建筑大堂的親水平臺、簡潔的墻面、豐富的建筑線條互為對景;西有竹林作背景。該亭在營造園林意境的同時,也是對中國傳統造園的一種解構與重組,其本身也是一種創新形式的再現。
2.3.5 植物
在樹種選配上,延續繼承了江南古典園林在意境營造與寓意表達上對植物的要求,多選配古典樹種,如:松、竹、梅、柏、桂、杏、蓮、紫藤等。與傳統園林不同之處在于,蘇州博物館新館的植物為同現代建筑與環境相映襯,需對其進行修剪,優美曲線的樹冠設計,同白墻一起,呈現出植物工筆畫的秩序感和韻律美,亦是柔與剛的對比。
總的來看,蘇州博物館新館在地域性符號的提取上,以粉墻黛瓦為總體色調,古畫景觀圖式的庭院山水布局,假山疊石,幾何形體間相互組合,是機械的、無生機、純理性的設計,是隱喻、暗示、敘述等文化深層次的表現。因此,蘇州博物館新館并未單純的模仿與復制傳統,而是將傳統元素創新地用裝飾性的象征手法,從屬于建筑的雕塑性外表,在本質上還是現代的。
3 蘇州博物館新館引發的設計思考
3.1 對“中而新,蘇而新”的思考
在蘇州博物館新館的設計中,雖采用風格較為明顯的江南地域性符號強調整體的象征性,遵循了立足中國而創新,立足蘇州而創新的理念,但其最后呈現出的唯一性仍有待商榷。一是與日本美秀美術館的對比。在建筑的幾何外觀上,二者都采用以三角形為母題的幾何抽象坡面屋頂來表達當地傳統民居特點的手法。在光環境的營造上,蘇州博物館新館采用的將光線透過鑲有金屬貼面格柵的大面積玻璃引進室內的手法,與美秀美術館極為相似。二是與日本枯山水庭院的對比。圖畫式勾勒的蘇州博物館營造出的意境有著日本枯山水庭院的寺廟感。如蘇州博物館的置石與東福寺方丈前庭的假山,都為靜態景觀的表達,游人不可參與其中;以及宋畫齋庭院在汀步、置石、竹子等景觀要素的配置手法,與日本寺廟庭院較為相似。
3.2 對設計傳承與創新的思考
“同質化”問題嚴重是目前設計界普遍面臨的問題。在全球化盛行的當下,不僅經濟在與國際接軌,在文化上的交流也是更為頻繁,這就導致出現某些方面的盲目西化,如在城市建設中生硬的“拿來主義”。這種文化上的統一則不應是全球化所提倡的。在日后設計中,如何更好地將傳統符號融入設計語言,如何更好地體現對地域文化的尊重,在傳承中有所創新,探索出屬于中國的設計之路,這是我們應從這個作品中所思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