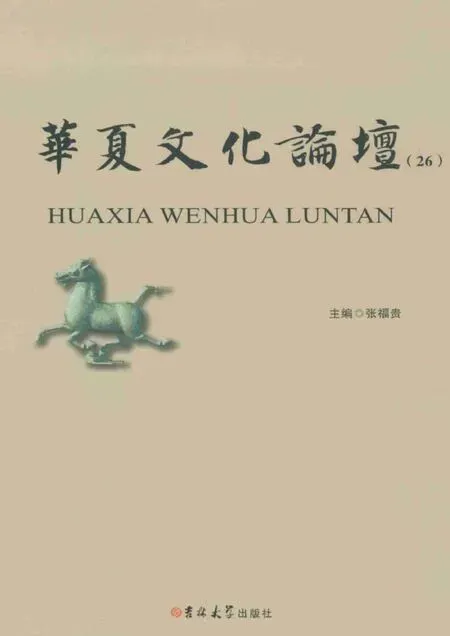論作為有機整體論踐行者的歌德
曲 寧
有機整體論是西方文藝理論發展史的重要線索之一,從柏拉圖—亞里士多德以降,途經新柏拉圖主義,一脈延續,其關于文藝的整體與部分、全體與個體、同與異、一與多、目的與手段、形式與質料之間存在不可分割的有機聯系的觀念,成為西方二元論思維模式的必要補充,因而與許多文藝價值觀的形成與理論的建構糾纏一體,發展為遍及藝術本體論、創作論、目的論等諸領域的思想潛流。到十七世紀,有機整體論忽然迎頭遭遇了機械主義的棒喝,一度幾近枯竭,但憑借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1749—1832)等人的努力,得以再次獲得發展的動力。終其一生,歌德在天才、民族文學、藝術創造的本質等問題上同樣不斷地借助有機生命觀進行思考,可以說是一位真正的有機整體論踐行者。本論即試圖對歌德一生研究、創作中的幾方面側重的梳理,探討他在文藝有機整體論史上功不可沒的地位,也試圖將這個觀念史的橫截面當作一個理論生命演進的一環來加以呈現。
一、不可分割的自然——論科學與藝術
歌德是文學史上少有的既涉足藝術創作和評論,又游獵于各種自然科學領域、并卓有建樹的多面手。他人格發展的全面性,也許只有亞里士多德能夠做比。作為科學研究者,歌德有著很健全的常識性觀念,并且有以常識來對抗理論的卓絕勇氣,而這種對抗,也許應該看成是十八世紀人文學者面對著牛頓力學為首的機械論對一切學科的鯨吞蠶食所做的最頑強的抵抗。這一點在他的色彩學研究中特別地明顯。在牛頓成功建立光學色彩學的理論體系70年后,白光是由彩光和合而成這一觀點已成為不刊之見,但是歌德這個業余色彩研究者卻拒絕承認白光的可拆分性,把這種分析的觀點看成是對自然的一種粗暴處理。靠著自己不那么合乎科學規范的實驗,更多地靠著自己長期從事繪畫研究的實際經驗,歌德得出了這樣的結論:色彩是光明和黑暗相互滲透的產物,它們不是光線在人眼中造成的被動視錯覺,而是人眼以及人的心理對光明與黑暗兩極間不同原型(赤橙黃綠青藍紫)的主動把握。20世紀以來,越來越多的學者意識到歌德的色彩學的價值,他看到客觀的光與人的主觀認知體驗之間存在著某種的和諧關系,而色彩就存在于這主客觀交互作用的整體之中。然而就當時而言,歌德對牛頓光學的挑釁卻被看作一場鬧劇,特別是當歌德用平生最大的篇幅來寫作《顏色學》這部皇皇巨著,并向愛克曼夸耀“作為一名詩人,我并沒有什么值得自豪的……但我卻是我們這個世紀里唯一懂得顏色學這門深奧科學真諦的人。在這方面我敢說,我不但有點得意,而且還有一種自覺的超越許多人的優越感”時,就惹起一片噓聲。有位英國光學家甚至認為有必要呼吁科學同仁們保護整個人類文化不受歌德這套“神秘套語”的侵蝕和破壞。
我們之所以耗費筆墨談及歌德的色彩學研究,意在指出這樣一個問題:盡管并沒有像赫爾德一樣建構起一個植物學的理論大廈,但憑借對于生命現象不可分析的整體性敏銳的覺知,歌德實際上也為他在其他領域的各種觀念奠定了一以貫之的有機論基調。
歌德看到,在他自己生命中一貫認為是不可分割的兩個部分之間,即藝術與科學之間,被人為地劃分為兩個陣營。科學自命為是對自然的理性研究者,而藝術則被認為是不那么理性的自然的模仿者。這種隔膜和劃分當然是難以令一位真正的整體論者滿意的。而機械論的科學研究方法,像我們在上文中看到的那樣,無疑就首當其沖地遭到歌德的批判和反駁。據他認為,自然與藝術同樣偉大,被同一種生命力量主導。無論科學還是藝術,都應當基于對這種整體的生命的把握。對這種無處不在的生命整體性的理解和體悟,是歌德一生跨領域探索的核心使命,它構成了歌德關于文學藝術與自然科學等各種紛雜看法的一致底色。
二、詩與真——藝術如何模仿自然
歌德對于科學和藝術界限的突破,不只體現在他依靠常識和感悟來做科學研究這一方面,而且也很好地體現在他藝術家應當成為自然的研究者這一要求上。在1789年的一篇文章中,他認為藝術,如果說是對自然的一種模仿的話,那么可以分為三個層次。第一種是停留在對現象的表面相似性上的模仿,他稱之為“對自然的簡單模仿”;一種是“虛擬”式的模仿,藝術家們對自然現象形成了某些整體性的印象或認識,于是就拋開細節,按照這種印象或認識勾勒對象的大體輪廓;最后一種是被歌德稱為具有“獨特風格”的模仿,這是最高等級的模仿,當然也是最不易為的一種模仿,因為它需要藝術“通過精確地、深刻地研究對象本身,終于達到這樣的地步,它準確地,而且越來越準確地了解了事物的特性以及它們生成的方式”,從而能夠認識和模仿各種具有典型意義的形式,才能夠形成“獨特風格”,達到藝術可能達到的最高水準。
舉例來說,一個以植物為對象的畫家不應當僅僅滿足于去描摹植物的花朵或枝葉的偶然樣態,也不應當去繪制想當然的空中花園,而應該成為博學的植物學家,“懂得從根部開始的各個部位對植物的生長發展的影響,懂得這些部位的規定以及它們之間的相互作用,他們看到并思考過葉子、花朵、結果,果實和幼芽是如何逐步發展的”,只有這樣才能創作出令人贊嘆又給人以教益的偉大作品。這里我們看到,通過對前兩個階段的超越,歌德批評了兩種流行的藝術見解。依照第一種意見,則藝術是對自然的純粹感官的復制,歌德認為如果停留在這一層面,那么就使藝術迷失在最偶然和最表面的個別事物之中。依照第二種意見,則藝術是某種“普遍性規范”的抽象表現,比如新古典主義的三一律,比如前面提及的那些“人為天才”的藝術理論,再比如藝術領域唯科學馬首是瞻的一部分觀念。
在牛頓光學蔚然成風之后,繪畫界對色彩的認識也追隨物理學亦步亦趨,甚至有些畫家指出,唯有按照彩虹七色的序列來構圖,才能夠實現畫面色彩的“和諧”。歌德對此嗤之以鼻,認為這種見解實在狹隘。他指出,這些畫家只是小里小氣地抱守著“三棱柱魔術”產生的機械順序不敢越雷池一步,在他們手里,“油畫中的色彩仍然是材料、物質、元素,并沒有通過一種真正的、天才的處理有機地納入一個和諧的整體”。在談到音樂作品時,歌德特別拒絕機械論的構成(Komposition)概念,認為把藝術作品的創作說成是“構成的”,就好像在談論用一些零件拼湊成的機器一樣,陷入了最為淺薄機械的“技藝方面的陳詞濫調”。人的藝術作品,和科學的研究對象——自然造物一樣,都是“由一種生命氣息吹噓過的”,是一個有機整體。是人的精神,而不是什么科學定律,將藝術作品的各個組成元素灌注為一個整體,真正賦予它以生命。
藝術也不可能乞靈于什么外在的先驗的格式,歌德譏諷了那些信奉新古典主義的詩人,他們“指望在任何時候都把自己的辭令和表達錘煉得跟面前的對象嚴絲合縫地相符,以便賦予它們正確的尺度,這樣的一位詩人,眼下必須背會一套現成的術語,把一定數目的字眼兒和描述詞準備停當,以便當他碰上任何形式,而需要做出適當選擇的時候,能知道如何把它們應用并排列進一種適宜的描寫中去”。這種做法照歌德看來,機械得“總像是一種鑲嵌畫之類的東西,你在其中把現成的碎片依次排好,以便最后用成千上萬塊的碎片拼湊成一幅類乎圖畫的東西”,實在令人反感。
總之藝術并不需乞靈于科學體系對世界現象的有限分類,也不應被先入為主的臆造規矩束縛手腳,但同時對自然僅僅做浮皮潦草的瞭望是不夠的,還應當真正切近地觀察與體悟。因此我們看到歌德本人親身走訪山野田園,投入大量精力從事的礦物、地質、植物學、解剖學等深入的研究,這些努力無不是為了真正了解自然的方方面面。藝術“應依靠自然,研究自然,模仿自然,并創造出與自然現象畢肖的作品來”。為了做到這一點,則詩人“應根植于他的題材,和它如膠似漆,給它注入他精神和心靈的精華,再次將它創造出來”。這段話事實上涉及到歌德對藝術本質的深刻思考。
怎樣做才是真正地了解自然呢?歌德認為對事物的理解遠遠不應停留在表面,而應準確地了解事物的特性以及它們的生成方式。歌德通過他的不盡努力最終發現的生長機制,正是使事物成為一個有機整體的那種生命力。
狄德羅《畫論》中的這段話讓歌德感觸很深:“你們把眼光投向這個弓肩駝背的男人。由于脖子前部的軟骨錯位,后面的椎骨就被壓彎,頭部向后移動,雙手移到臂關節的位置,肘部后縮,多有部位都在尋找那個適合于一個如此錯位的系統的共同的重心,而面部因此帶上一種壓抑而吃力的特征。你們若是把這個人物遮蓋起來,把他的腳給大自然看,那么她一定會毫不猶豫地回答你們:這是一個駝背的腳。”歌德評論道:“也許有人覺得上述說法太夸張,可這從最嚴格的意義上講的確是真理:有機自然的連貫性不論在健康還是疾病狀態下都超出了我們的理解力。”在狄德羅的基礎上,歌德進一步提出了自己的觀點,即大自然從來就不“正確”。因為“正確以規則為前提,而規則是人們自己依據感覺、經驗、信念、喜好所制定的。人們據此判斷的與其說是造物的內部存在,不如說是其外表現象;相反,自然變化所依據的規律則要求最嚴格的內在有機關系。……大自然致力于創造生命與存在,致力于保存和繁衍其造物,它從不理會其樣子是美是丑。一個生下來就注定美麗的形態可能會因為某一偶然原因在其某一部位受到損害,這樣就從其余部位抽走一些力量,其發育勢必由此受到影響。現在造物就不再是它所應該成為的樣子,而是它所能夠成為的樣子”。
對自然本然性而非應然性的理解,拒絕以人的有限理解來肢解自然,而是帶著最虔敬平和的心態去膜拜自然無與倫比的創造,是歌德,同時也是有機整體論在她最完滿美好的時代對機械論做出的素樸回應。
三、“原型”與“圓形”——文學藝術的創造本質
對事物具體形態所包含的全部有機力量的珍視并不意味著歌德對自然觀察的終點。事實上,歌德還試圖進一步在所有的具體形態之上總結大自然總的創造機制。這是他作為一個科學研究者而做的嘗試,同時更可以看作是作為一位自然之祭司而做的嘗試。
他對事物生長機制研究的豐碩成果體現在他的《植物形變論》(1789—1790)等在科學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論著中,而《植物形變論》的核心思想又被詩意地精煉為《植物的變形》一詩:在詩中,歌德引導人們去關注花園中植株所透射出的宇宙奧妙:在大地的孕育和神圣的光的照耀下,一顆種子中沉睡的模型蓄勢待發,根芽發育,破土而出,節節攀升,并在自然的引導下不斷尋求完美的形態。葉片滋長,彼此相似,盤繞藤蔓次第向上,直到捧出花萼、育出果實,使另一輪生命蓄勢待發:
“此刻,自然閉合那永恒之力的圓;
同時,一個嶄新的圓隨之開始,
由此,生命之鏈穿過一切時代延續,
無論整體和個體,它們都生生不息。……”(莫光華譯)
通過這樣的園中探秘,歌德呼吁人們同自然于和諧的直觀中結合,并發現更高的世界。
可以說這首詩極好地展現了歌德的宏觀有機整體觀念。在他看來,自然事物是按照一種他稱之為“原型”的模本生長的。盡管事物在它的全部演變過程中會呈現出各種形態,但卻莫不依循這種原型。這一原型類似于亞里士多德所說的形式,但是卻刨除了他那里的目的論意味。在歌德看來,這一原型與其說是先驗的有待完成的“形式”,不如說是促使包括植物在內的所有自然事物不斷發展的內在動力。舉例來說,一個畸形的形體在亞里士多德看來無疑是不完滿的、應當被鄙棄的失敗之作,但是在歌德看來,即使是這樣的造物,也依舊最充分地體現了自然的原型力量。這種力量不是別的什么,正是“有機的連貫力量”。
我們看到,在《植物的變形》一詩中,歌德特別強調了植物變化的永恒性。植物在原型的作用下完成生長的一個周期形成了一個完滿的“形變之圓”,但這并不是事情的終點,相反,這個圓又構成了孕育下一個形變過程的母體,一個新的圓的起點,這意味著自然的既成面貌并不是生命力的終局,存在一種潛在的空間可供生命力繼續提升。
在這里我們看到的是歌德給予藝術真正意義的闡釋:藝術不僅僅是對自然的復制或模仿,也不是人類無奈的生存之鏡像,它正是幫助自然按照現有的生命軌跡向上進一步升華的那種力量。這種力量不再是亞里士多德的客體理念能夠加以解釋的,它只能在一個主體論的時代被提出來。因為,是主體精神在對自然的“和諧的直觀”中,“發現了更高的世界”。甚至自然本身就是一種創造的主體精神,在《關于大自然的片段》(1782)中,歌德給予自然以人格:“她是完整的,然而總是未完成的。于是她始終能夠從事她要從事的事情。……每個人都感到,她以特有的形態出現。她隱藏于成千個名稱和術語中,然而這一切始終是同一個。”而人類自己的創造并非是對自然的造物的模仿,而正是對這種精神的模仿。在他看來,藝術創作的至高境界在于,“藝術家既能洞察到對象的深處也能洞察到他自己感情的深處,從而在他的作品中不僅能創造出輕易地就能產生表面效果的東西來,而且也能創造出可以與自然相匹敵的在精神上是有機的東西來,并且賦予他的作品這樣一種意蘊,這樣一種形式,使他的作品看起來既是自然的同時又是超自然的”。
藝術可以超越自然,“藝術家一旦把握住自然界的一個對象,這個對象就已經不再屬于自然,甚至可以說,藝術家在把握住對象的那一刻就創造出了那個對象,因為他從對象中提取出意義重大的,有典型意義的,引人入勝的東西,或者甚至給他注入了更高的價值”。就這樣把更精妙的比例、更和諧的形式、更高的特性加入表現的題材中去,制作出一個“規則,完美,非凡、圓滿的圓”,自然就在這里顯現出它最美的地方,而在通常的情況下,自然由于廣袤無垠很容易變得十分丑陋,落到無關緊要的地步。
我們看到,上述一段話和論狄德羅《畫論》的那段評論大異其趣。但是我們有理由認為,這里的表述更符合歌德對藝術本質的總體性理解。表面看去,歌德對藝術超越自然的主張已經僭越了一個造物的本分,貌似構成對自然狂妄的挑戰。實則不然,歌德對藝術的要求,正是自然對其造物的要求。畢竟歌德的自然永遠處于可待進一步完滿的上升狀態,而作為自然之子的人類善用自己從自然的母體那里得來的藝術創造力,正可以在新一環的創造之中印證自然本身的勃勃生機。
四、個體的文學、民族的文學與世界的文學
藝術是人類對現存自然的突破,是對自然生命力與創造力的理想化發揮。然而不得不看到的是,就單個藝術家來說,他們像普通的個人一樣,只是一種單獨的存在,他生活在相對狹小的空間里,自身實踐的永遠只是自然之光的一個方面。個體的局限性要求人要勇于自我突破。既然藝術要實現人類超越自身甚至超越自然的總體提升,那么每一個肩負此種責任的藝術家,就在個人成長與自我突破方面更加責無旁貸。他們要比普通人對自我的要求更加嚴苛,成為“整體的人”,須知“藝術所能達到的最高程度就是完整的人性”。
歌德所說的整體人性絕不是新古典主義那種形而上學意義上的人性之概念。他這種對整體人性的追索不是對某個天上的理式的徒然企盼,而是腳踏在大地之上對已有人格做切實可行的完善。他呼吁藝術家去做的,是盡可能地從理論和實踐上接納與自己的天性相對立的東西。輕松愉快的人要力爭嚴肅和嚴格,而嚴格的人要看到還有一種輕松愉快的人;堅強的人要招人喜歡,招人喜歡的人要表現出堅強。總之每個人看起來離他自己的天性越遠,他的天性得到的培育就越多。借由與自己的原本個性相反對的、近乎于“否定的精靈”般的因素的融合,藝術家才能夠逐漸實現人格的完整化。進而,在否定所創造的契機之上,還需要一種更為偉大的統一力量將所有“巨大的,似乎不能統一的對立在我們胸中統一起來”,因為這才是生命的本質。正如我們在《浮士德》(1797-1833)中看到的那樣,盡管靡菲斯特在作品中大展身手,但是浮士德才是真正的主角。借著靡菲斯特的襄助,浮士德——人類個體靈魂的典型,沖破一個個孤立的領域的束縛,消融理性與感性之界、跨越思想與實踐之隔、彌合歷史與當下的裂痕,把世界越來越多的層面納入到自己的胸襟之中,加以整一,最后立志投身在那人類的共同事業之中,實現了生命的徹底升華。
事實上,在實際創作中,藝術家也應當抓住對立的因素,在它們相互作用中達到更為和諧的整體。比如對立的色彩的運用,不畏懼打破“光學”的序列,而是運用互補色之間的強烈對比產生出更為強烈的整體。在文學作品中,也要將偉大的思想同對大自然的觀察、把古典的形式同民族的內容緊密結合,而后方能有真正的藝術成就。當藝術家個體的藝術臻于完善的同時,民族藝術的形成也就不遠了,因為真正的民族藝術家就當“以個人的、民族的以及傳統的手法處理他周圍的對象,并把它們溶合成一個天衣無縫的整體”。
如何確立德意志的民族文學在歌德的前半生一直是一個投入了大量精力去思考和探索的問題。歌德在發表于1895年的《文學上的無短褲主義》一文中慨嘆德國作家們整整一個世紀以來艱苦卓絕的努力與事實上的產出之間形成的反比,其中的困境在于民族文學由之生發的文化土壤的缺乏。但是歌德繼而否定了社會上流行的德國民族文學無望的悲觀論調,認為只要從這一代作家做起,著手培育年輕一代作家,就仍大有希望,而這就要求現有最優秀的作家做出全面的自我經驗之反思:盡可能地“將在他們的作品中所體現出來的他們自己的成長過程呈現給讀者”,展現哪些因素促他們成長,哪些因素則起了相反的作用。這種做法本質上在于,要挖掘出一顆德意志心靈的成長機制。因此當我們面對的是如何培育德意志民族文學這株幼苗時,我們自然應當先研究這片土壤上已有植物的成長形態,作為參照。
應當看到,歌德分明身先士卒地實踐著了自己在上面所倡導的一切。他用幾十年的時間寫作《威廉·邁斯特》,寫作《浮士德》,寫作自傳《詩與真》,這些莫不是在講述一個藝術家的成長歷程,一個民族作者的成長道路,一個德意志人的成長機制。他用自己的全部寫作經驗向德意志的文壇注入養分,孜孜不倦地改善著民族文學土壤的生態環境,以期供給下一代天才的產生。盡管在這一過程之中,他事實上就已成為那位天才,那棵偉岸的參天巨木。
在民族文學觀念的基礎之上,進入晚年的歌德憑著由自己一生的創作經驗積累下的厚重與廣博,對于文學發展的總體趨向漸漸形成了一種大膽的見解,1927年起,他開始公開呼吁各國及早認識到:“現在,民族的文學已經不是十分重要,世界文學的時代已經開始,每個人都必須為加速這個時代而努力。”人們應當突破地域民族之限,在豐富多樣的異文化中汲取全新的養分,在睦鄰關系中發現更為廣闊的世界圖景,并將文學創作納入到這一整體性圖景中來,促使世界文學的形成。世界文學觀念的提出,是歌德跳出當時相對主義文學史框架、借有機整體觀在更廣闊的領域長足探索的另一項重要成果。
結語
歌德在晚年創作了一篇名為《中篇》(1829)的中篇小說,很有寓言意味。小說以一位夫人為主線,展現了四個場景,在城堡中的交際寒暄,在市井和山間的游覽見聞,與猛獸的遭遇與搏斗,以及同吉人賽人一家的相識,沉浸在他們美妙的贊神歌詠之中。這一篇作品可以看成是對歌德一生幾個階段的詩性總結:早年的家庭教育、青年時期的游歷和自然科學的探索、中年時期的政治作為以及最終以藝術創作的方式實現對真理的探尋。歌德的人生十分豐富,他既是德語文學的培育者,又是世界文學的倡導者;他既是藝術的創作者又是科學的研習者;他既是世界的摹寫者,又是現實政治的參與者……在他那里,有機整體論已經不僅僅是一種蒼白空洞的理論,而是用一生實踐去澆灌的生命之樹,也許在全部有機整體論發展史上,歌德才給這個理論賦予了最渾整的生命形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