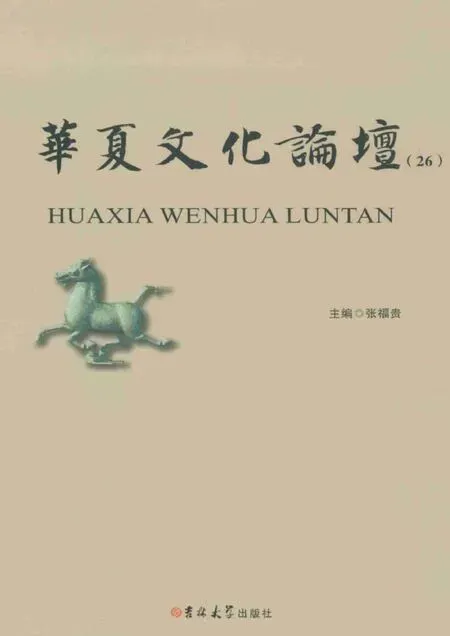“中國問題”研究的新結構
——論劉康的《馬克思主義與美學:中國馬克思主義美學家和它們的西方同行》
李 瑋
隨著世界政治格局的變動,中國問題成為當下思想界關注的重要問題。不過,研究中國的理論模式有待進一步創新。已有的中國研究的主要模式,包括“沖擊——回應”模式、“殖民——反抗”模式、“從中國發現歷史”,或是后殖民話語結構中產生的“地方性中國”“特殊論中國”等,在發揮它們各自的價值功能后,也顯現出它們的局限性。特別是,20世紀九十年代以來,“歷史終結論”引發爭議,作為應對的“主體論中國”開始引起關注,這使得“理論中國”的問題更加復雜。“什么是中國?”成為當下思想界、理論界需要進一步思考的重要問題。如何呈現中/西的對話性,而不是簡化處理為二元對立,已經成為討論“中國問題”的新思路。在這一方面,西方中心論,或是潛藏著“西方主體”的中國特殊論,或是各種中國中心論等,似乎都難免有非此即彼的傾向。對此,劉康進行了反思,他認為非此即彼的結構“隱含了平行、對立、各有其源、各自為本的本質論,自我想象成一棵傲然于世的大樹。說到底,不過是現代性思維霸權的又一種喬裝。”該結構對各自真正的“他者性”有意地漠視和壓抑,對于一個具有共生性、交錯性,悖論式的“中國”或是“西方”視而不見。
從應對冷戰語境下的中國研究,批判后殖民語境下的發散主體論,到回應中國主體論,劉康從20世紀90年代,就試圖用新的結構,來研究中國問題。他提出“世界的中國”(China of the world)的理論結構,并引用德勒茲的“塊莖”理論,重新理解中/西的關系。這種結構打破了認為中國落后于西方,或是中國超越西方,或是把中國放在西方的時間序列之外的時間處理方式,恢復中國與西方的共時性。這種共時性實現了一種空間性的折疊和對照,理論上具有“雙重反諷”的功能。劉康由是在新的地理政治空間中,在批判西方理論的同時,也重新解釋了“理論中國”。本文著重從劉康的《馬克思主義與美學——中國馬克思主義美學家和他們的西方同行》出發,分析劉康探究和思考中國馬克思主義美學和西方馬克思主義美學之間的理論旅行、創造性轉換和對照性反諷的問題。通過將中國馬克思主義美學家放到西方理論的語境下,劉康在交錯的理論譜系中發現了中國馬克思主義美學在美學再現、行為形式以及文化政治等理論領域的創造性貢獻,以及由此決定的第三世界中國現實再現的獨特性。不過,劉康的問題意識并不局限于理論內部,他更關注新的國際政治變動下中國現代性道路的選擇問題。一方面是“歷史終結論”的提出,另一方面文化革命的美學幽靈在世界領域被反復召喚,劉康對中國馬克思主義美學和西方馬克思主義美學的“雙重反諷”,開啟了對馬克思主義美學幽靈的問題的反思之路。
一、“雙重反諷”:共時的中/西結構
如果在西方的時間序列思考中國問題,那么這種思考必然帶有“西方中心論”的特點,但如果中國完全脫離西方的時間序列,這樣的理解方式也難免偏狹。20世紀50年代左右,費正清開展一系列的中國研究,他認為西方殖民給傳統中國帶來了沖擊性的挑戰,也為中國的現代化提供了機遇。費正清用“沖擊——回應”來描述近代中國的一系列的變化,在此種模式中,西方的時間性被普世化,中國被理解為等待沖擊而改變的傳統文明,中國的時間性落后于西方。八十年代,柯文對“沖擊——回應”模式進行了批判,他說該模式“使我們對十九、二十世紀的中國產生了一種以西方為中心的曲解”。柯文認為中國的諸多變化并不是對“西方挑戰”做出的回應,他主張中國研究應該離開“外在取向”轉向“內在取向”,即“從自身的情況出發,通過自身的觀點,加以認識,而不是把它看成西方歷史之實際或理論上的延續”,建立“一種植根在中國的而不是西方的歷史經驗之中的史學”。
柯文在批判西方中心論方面的努力,受到了賽義德的影響。他強調中國自發歷史的重要性,并注意中國對西方接受的復雜性,相較于抽象的中國,“從中國發現歷史”更強調區域性和地方性。受其影響,中國研究開始找尋中國內部的時間鏈條和空間結構。比如史景遷把中國現代性的發生追溯到晚明,杜贊奇將中國講述為一個類似霍米巴巴意義上的發散性民族等。不過,無論是自發現代性的目的論終點,還是“從民族國家拯救歷史”的批判對象,仍然掩藏了沒有被說出的“西方”。表面上的“中國中心”,關注中國的特殊性,實際上如酒井直樹所言,該特殊性恰恰證明了西方普遍性。將中國設定在西方時空之外,并不能說就是回歸了“中國自身”。
注意到中國面向西方殖民的另一種姿態的是“殖民——反抗”模式。在該模式中,西方與“帝國主義”等義,中國被作為一個超越西方的批判性存在。自20世紀40年至70年代末,該模式是中國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和史學家敘述中國近代、現代史的主要模式。該模式在美國漢學界亦有回應。“殖民——反抗”模式以一種反抗的邏輯簡化了“殖民西方”的復雜性。將“中國”作為超越西方的“未來”而存在,帶有浪漫化、理想化的問題。日本的中國學研究亦從西方殖民——東方反抗的邏輯出發解釋中國。溝口雄三“以中國為方法”反思日本現代化的問題。竹內好以魯迅研究為基礎提出了“近代的超克”的思想。竹內好重新恢復了東西方的張力性結構,他以魯迅闡釋為原點,為中國賦予了順應東西結構中之外的位置。與自西向東的文明推進秩序相反,竹內好以“回心”否定再否定了現代化進程,試圖建立一個以“無”為基點,進而可以激發持續否定性力量的主體,即所謂“永遠革命”。竹內好“近代的超克”的思想在近些年重塑中國主體性的思想脈絡中產生了重要影響。不過,“近代的超克”要么走向西方之外的“超克歐洲近代的大東亞”,要么走向美國后殖民意義上的主體彌散。
在時間性上,劉康改變了將中國設定為落后,或是超越,或是在西方時間序列之外的思考方式。劉康認為世界的空間和各種知識生產是塊莖(德勒茲語)之間枝杈交錯蔓生的關聯,中國在世界之內而不在之外,是交錯共生而不是非此即彼。基于塊莖式思維的“世界的中國”,有助于打破“西方總體性神話(把西方資本主義現代性作為一種總體性)”,重新恢復“充滿悖論和異質性的經驗以及多重可能性的狀態”。在《馬克思主義與美學》一書中,他將中國馬克思主義美學家與西方美學家設定為“同時代人”,從而改變了僅從中國內部思考馬克思主義美學思潮變遷,或是從影響/關聯的角度審度中國馬克思主義美學和西方馬克思主義美學關系的研究方式,對整個研究視野進行了結構化重置。該書從對西方/東方,第一世界/第三世界等二元對立模式的批判入手,剝離加在中國馬克思主義美學發展進程上的“他者”標簽。在這個思想框架中,中國研究超越“沖擊——回應”“殖民——反抗”模式,也不單純是“從中國內部發現歷史”,超越了認為馬克思就在法蘭克福,或是冷戰思維的漢學研究,從而注意到中國馬克思美學和西方馬克思美學,中國理論和西方理論之間的復雜關系。
將二十世紀重要的中國馬克思主義美學家與西方馬克思主義美學家并置,魯迅與本雅明、阿多諾在寓言性、否定美學,到瞿秋白和葛蘭西,毛澤東、葛蘭西、阿爾都塞、伊格爾頓、威廉斯,胡風與盧卡奇、巴赫金等等,他們相互對照批評。這一思路貫穿《馬克思主義與美學》全書。恢復中國和西方的共時性,不僅是為了做平行比較研究,呈現中國馬克思主義美學家和西方馬克思主義美學家的相似性和差異性,而且是為了在“對話”和“復調”中,實現對中國理論和西方理論的雙重反諷。如果說馬克思所謂“召喚死者的亡靈”,用德里達的話來說是一種時間性折疊,那么,將中國馬克思主義和西方馬克思主義、各種后學思想并置,則是一種空間折疊。中/西不再是二元對立,顯著差別,人們不得不承認它們彼此之間的相似,如此以令人不安的方式相互傳染。在中國馬克思主義美學和西方馬克思主義美學的鏡像般的關系中,人們不僅看到了理論旅行和轉換的種種奧秘,也在對照中讀出了相互反諷的意味。劉康說:“中國馬克思主義本身就是對西方馬克思主義的挑戰,是對歐洲中心論的挑戰;反過來西方馬克思主義又在中國馬克思主義身上看到了這種挑戰,同時又用來反省自身”。由此,該書創造性地揭示了歷史時間的雙重性。當本雅明所說的“雷同的空泛的時間”,將空間裹挾,構成一條目的論的線性邏輯。具有雙重性的歷史時間意味著:時間以非等質性的、非線性的方式流動,在該時間中,時間性的過去和現在,空間性的東/西呈交錯對照的姿態。“中國”的時空性也被重新結構,它不再是對照“他者”的某種本體化存在,而是一種時空疊加性的、充滿矛盾和張力的歷史化存在。理論中國不再呈東/西、中/西對峙的狀態,理論的旅行、轉換和對話由此才能發生。中國馬克思主義和西方馬克思主義各自打破了封閉的空間和絕對的時間,它們在雙重時間和空間的序列中,看到鏡像化的“自我”,看到反諷性的歷史,而不是鞏固自我想象的“他者”。
中國馬克思主義美學的“文化革命”理論和西方的“文化批評”理論本來分屬中與西,過去與現在。諸如瞿秋白和葛蘭西、毛澤東和阿爾都塞、威廉斯、胡風和巴赫金等,在現代性話語的東/西二元結構中,甚至在西方左派關于第一世界/第三世界的區隔中,難以被類比。但是,在雙重歷史時間的結構中,中國馬克思主義美學的“文化革命”理論和西方的“文化批評”相互聯系,形成一幅交錯共生的譜系。“后殖民主義的主要理論來源是馬克思主義。從安東尼奧·葛蘭西的領導權概念到愛德華·薩義德的東方主義,后殖民主義批評家一致承認它們從馬克思主義尤其是馬克思的文化理論那兒受益匪淺。”只是由于本質化的、割裂性的話語結構,我們才很難看到“中國革命在實踐中已經對馬克思主義理論做了大量的實際檢驗,也難看到中國經驗事實上駁斥了后殖民主義者關于非西方國家或‘第三世界’的美學、意識形態和心理學的種種論調。”同時,當這些理論話語在1990年代后中國思想界流行,并影響對于中國現代化道路的判斷時,劉康對于瞿秋白和葛蘭西的反思所面向的不僅是文化批評論者、后殖民話語對于世界秩序的“想象”,而且是在疊加的時空中審視新的世界政治秩序下的“中國經驗”。
二、作為一種美學再現的“現實”:修辭聯結的中/西時空
《馬克思主義與美學》一書改變了殖民或后殖民理論中對東/西,或者說中/西的定義,批判性反思中國馬克思主義美學和西方馬克思主義美學的關系,重置理論的空間性,建立一種新的地理政治,由是重新闡釋了有關“第三世界”的理論問題。
劉康對中國馬克思主義美學新的癥候式閱讀,讓他發現第三世界的“現實構建”與“美學再現”之間的復雜關系。從瞿秋白到毛澤東,劉康總結中國馬克思主義美學存在莫斯科——延安模式,該模式與整個無產階級革命對“文化”和“審美”問題的重視密切相關。在革命理論建設和革命實踐的過程中,語言、形式和審美起到了建構一個新的革命中國的作用。劉康注意到毛澤東以“民族形式”實現“中國化的”過程。其實就是一個語言問題,一個審美的同時是意識形態的形式——它將外國的、異質的普遍化的語言轉換或重構為內生的、民族語言。也就是說,馬克思主義的革命理論“旅行”到第三世界落后民族時,政治問題被著重轉換為一個美學問題。作為落后民族的中國在理解、承接和實踐馬克思主義的過程中,會試圖用“美學再現”來彌補中/西時間和空間的裂隙,來解決馬克思主義的異域性和民族性的矛盾問題。
毛澤東把審美的、文化的民族形式推崇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最終形式。這里的“形式化”和“中國化”有了對等之義。“形式”更應該被理解為是一個動詞。劉康借用約翰·奧斯汀的語言行為理論來闡釋“民族形式”中的“形式”,認為“不能僅僅將之作為是陳述句式的(再現),更應當將之看成是行為句式的(方案),既是一種宣言,同時又是一種具體的實踐。”“民族”的“形式”,也不能做“再現式”的理解。“中國化”不是一個對本民族生活、語言和特性“再現”的過程,而是一個“形式化”的選擇和創造中,訴諸身體政治的美學(情感)建構,重新發明“民族”的“行為話語”。在此話語實踐過程中,所謂“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不是如斯大林意義上社會主義理論和結構打破民族壁壘,而是通過賦予其具有情感和特殊語言風格的“民族形式”,將之由外來的、抽象的語言,轉變為具有時間和空間的“日常語言”,并創造可以被再現的“現實”。
毛澤東對于藝術和生活之間關系的論述由是獲得了新的闡釋。藝術和生活之間,并非是表現和自然的關系,而是符碼的召喚、提煉和創造,從而實現從觀念到生活的“再現”的雙向關系。劉康指出,“毛澤東把藝術作品看作是觀念形態的形式,與他對人民生活中 ‘文學藝術原料的礦藏’是‘自然形態’的界定相對應。這不是現實生活簡單、透明的再現,也不是對未經中介的現實生活的模仿。相反它是符號‘轉碼’的復雜過程,將以前的文本形式(大眾藝術和日常生活符碼的自然、粗糙形式)經過審美提煉和潤飾,再文本化為另外一種意識形態、文本形式的過程。”劉康深化了詹姆遜所謂“只有通過預先的(再次的)文本化,才能夠靠近現實”的論述。在第三世界國家的時空結構中,只有“預先的(再次的)文本化”才能夠“創造”可以被“再現”的“現實”。
用伊格爾頓的話來說,這里的符碼轉換所使用的種種“修辭”和“形式”是一種“元語言”,這種語言就是歷史唯物主義本身,“因為從根本上說,離開了那些勸說性的利益——它們通過喻說和比喻,以某種可辯駁(可篡改)的方式影射這個世界——那是無可想象的”。在伊格爾頓呼吁革命文化工作者“在改造過的‘文化’媒介范圍內大力虛構‘現實’”之前,二十世紀中葉中國馬克思主義美學家業已推陳和踐行了這一理論。通過“形式化”,中國將自身轉化為歷史唯物現實世界的一部分,由此,文學藝術“再現”的過程不是一個線性、直觀的過程,不再是未經中介的模仿,而是經由符碼轉換(一系列修辭:象征、比擬、隱喻等)的形式化,它經歷代表、表征、展現、表意或者表演的復雜機制。
《馬克思主義與美學》對上述問題進行了譜系化的分析。從瞿秋白、毛澤東到胡風,中國馬克思主義美學家對革命現實創造都持一種語言切入,對“現實”做一種“形式化”“審美化”的理解。不過他們的理論思路并不相同。胡風對“形式”的理解,較之毛澤東,更強調“搏斗”,這種“搏斗”類似于克里斯蒂娃所說的“異質對抗”。對于胡風來說,形式是作家主體性的真正的承擔者,“形式是客觀現實融合作家主體性的理性表現方式”,在胡風的主觀戰斗精神理論中,“通過把人民的希望和渴望自由從‘自在’的狀態轉化為自為,可以解決同質與抵抗的辯證關系。”同樣,胡風把這種精神的轉化與文學形式聯系在一起,他認為只有通過采取五四現實主義的新形式,才能實現人民思想的轉化和革命潛能的發掘。胡風的主體、審美經驗、現實概念是非黑格爾式的,與巴赫金的概念相近。受到巴赫金啟發的克里斯蒂娃也用“異質對抗”的觀念來解釋“主體去中心化”,“在語言中建構一個新的對象,這一對象是過程中的‘主體’通過拋棄的過程生產出來的”,與“再現系統處于斗爭狀態”。
中國馬克思主義美學家都意識到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直接再現問題上的困難性,并嘗試用多種方法解決現實再現問題。如果說胡風在主體塑造方面試圖辯證地解決馬克思主義和對象之間的矛盾性,毛澤東則是以一種領導權意義上的“代表”入手來生產新的主體和對象。劉康引用馬克思《路易·波拿馬的霧月十八》中的相關論述來思考“ 如何再現或代表農民階級的問題。”斯皮瓦克說,“被殖民化了的底層主體是無法改變的異質主體”,能夠認識和表達自身的農民(底層主體)是沒有的,農民“僅僅被標志為一種無法恢復的意識的指示物”。因此她也借助《霧月十八》來討論在階級行動過程中的“父名的意象”來討論關于底層主體意識敘述的虛假性。劉康則指出,毛澤東如何運用日常生活的文化革命將農民統一到“革命階級”中去,于是意識混亂的農民被生產為能夠被“再現”和“代表”的新主體。在這一方面,毛澤東的意識形態實踐啟發了阿爾都塞號召法國和國際工人階級通過“文化革命意識形態重建”,“再生產組織結構的物質性”。
文學藝術的“再現”和政治層面的“代表”具有同構性。再現(representation或譯為“表征”)的問題,提出它們出現在兩個不同但相互關聯的層面。一個層次是政治再現的層面。馬克思的原德文詞是Vertretung;中文詞對應是‘代表’(替身、代理、代言),第二個層次是話語或文化層面的再現(representation),德語中是‘Darstellung’,漢語中是‘再現’(再次展現、表意、表演)。政治上的代表性和話語、文化上的再現和表意密切相關,只有后者話語和文化層面上“再現”的完成,才能成就中國的政治層面的“再現”和“代表”。
由此,從文學藝術到政治代表,毛澤東將“美學再現”和“文化領導權”問題結合起來,劉康指出,“文化革命和民族形式的目的都是意識形態的、領導權的:從復制和傳播符號、形象、革命再現的意義上來說就是意識形態;從構成日常生活和文化機構的日常時間意義上來說就是領導權。”意識和物質、審美和實在、再現和現實,在中共馬克思主義美學家的文化革命理論和實踐中被辯證地統一起來,并決定了作為第三世界的中國構建的復雜性。
三、美學幽靈批判:面向新的中/西理論變動
劉康用西方的理論方法來審視中國馬克思美學,一方面是為了對照思考西方馬克思主義美學的問題,另一方面也是反思中國馬克思主義美學的發展,特別當下中國的文化問題。劉康說:“書中提到許多西方馬克思主義思想理論,跟中國做了對照和比較,目的就是把中國思想放在國際大語境中來反思,或許對我們今天對中國發展模式、中國文化價值觀的思考有些參考意義。”
在書的結尾,劉康援引了德里達的《馬克思的幽靈》,認可他在書中所說的“革命像幽靈一樣永遠不會消失”。雖然當下中國已經有了“后革命”“告別革命”等說法,但革命傳統依然存在。就像德里達認為“歷史終結”的同時,馬克思的幽靈的糾纏也必然無可擺脫。在中國,對“歷史終結”和新自由主義的批判,同樣帶來了對于中國馬克思主義美學資源的重啟,亦如重新召喚馬克思的美學幽靈。有學者這么描述“中國”和“歷史終結”之間的關系:“1989年之后盛行一時的‘歷史終結論’為80年代末社會運動提供了一個最為明確的解釋,即西方社會體制的最終勝利,中國僅僅是一個尚未終結的歷史的孤零零的例證……而從未意識到80年代末在全球范圍內發生的巨大轉變同時意味著對于新的歷史關系、新的壟斷和強制的批判和抗議。”在“歷史終結”的語境下,中國是否會成為反抗和批判新的歷史關系的“主體”?事實上,中國的確在新的歷史語境下重新召喚具有不對稱性的“美學幽靈”,在與西方馬克思主義、后殖民等文化政治理論的呼應中,討論革命中國的象征形式和情感形式,以此挑戰以西方為中心的全球化問題。
針對這一問題,《馬克思主義與美學》具有前瞻性。劉康肯定了中國馬克思主義美學的“文化革命”理論和實踐,特別是在此過程中美學所發揮的強大功能,“在批判現代性,尋找不同選擇的現代性”方面的價值。“美學可以反思式地闡明它自己在跨越歷史和地緣政治疆界的革命、現代性和現代性的不同選擇之中所起到的作用(以及廣義的文化的作用)中國現代性或現代性的不同選擇之中的美學譜系濃縮了內在于現代性之中的所有二律背反和悖論,因為它跨越了當代世界的時空界限……美學指向了尋找不同選擇的無限可能性。”正是美學打破了中/西的區隔,彌合了時空的縫隙,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由此鏡像般地相互對照。現代性及其不同選擇在美學譜系中呈現出矛盾性和多種可能性。但劉康同時指出,“文化革命”所扮演的歷史性角色遠非書齋中的符碼那么簡單,當現實成為各種修辭意義上的美學再現時,“永遠的或不斷的革命”成為一個“浮動能指”,它固然能夠實現一定意義上的大眾性反抗,但它將造成巨大的不穩定性和破壞性。
并且,雖然“中國革命通常被看作是對以西方為中心的全球化現代性而做出的地域性和民族性反應”,但是中國革命從一開始就具有全球化面向,特別是中國革命中對于文化革命的強調,它對于美學話語的強調,做出了“艱巨而自覺地努力去挑戰西方,‘去西方中心化’,也就是全球現代性的中心。”中國馬克思主義者的世界性和全球化的革命視野,不僅延續至今,而且在“歷史終結”的語境下延續著另一種歷史。它表達著對西方中心論的挑戰,以堅守特殊性的面貌出現,似乎在呼應西方馬克思主義和后學的批判性立場。劉康追本溯源,從而發現中國馬克思主義美學思路本來就和當下后殖民異曲同工。中國馬克思主義美學家對“文化革命”“領導權”問題開展思考的同時,葛蘭西在《獄中札記》也提出相同的概念和思路,并成為文化批評、后殖民等西方左派的重要資源。“賽義德與后殖民主義批評家,都以葛氏的策略為各自的種族、性別、同性戀、‘生態環保者’等分離、分裂的‘歷史板塊’(historical bloc)或小團體政治、‘微觀政治’(micropolitcs)以及 ‘認同性政治’(identity politics)來正名。”但是,劉康強調,中國馬克思主義美學的“文化革命”從來不是書齋里的“符碼”,它本來就是刀光劍影的革命實踐,它成就著宏大主體,所以即使是今天,中國馬克思主義美學的“幽靈”也并不會止步于作為一種“不對稱性”而存在,它有強烈的現實化、普世化的沖動,一如當初。
全球化進程的推進,讓世界各地的理論家都重新重視20世紀60年代作為一種批判性資源的問題。中國馬克思主義和世界馬克思主義之間的密切關系也開始浮現。重啟中國革命傳統與后學的殖民反抗話語交相輝映,似乎在形成一股合流。當下,后學旅行到中國,由強調發散主體轉變為塑造宏大主體,劉康以相互對照的“反旅行”的空間重塑,揭示了方法和結論,理論和現實之間矛盾性的裂縫。劉康反復強調:“不容 忘記的是,在 1960 年代那個特定的歷史階段,毛澤東思想對西方思想界產生了重大的‘逆向影響’(‘逆向’是指來自西方的馬克思主義以及俄國的列寧主義、斯大林主義對中國“正向”影響的回饋——來自西方的馬克思主義,后來成為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反過來又影響了西方左翼)。”在“正向影響”外增加“逆向影響”的思考,劉康試圖陳述任何一種無論中/西都不能作為孤立的本體存在,亦談不上幾種具有本質性意義的“文明”的沖撞。它們不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而且“你”“我”的主體性和對象性呈相互對照、轉換,甚至反諷、消解的關系。該結構超越了既有的非此即彼的中/西理論結構,強調新的世界格局下中/西的對照性批判。在這種對照性批判的“間性”中,我們感受到康德意義上的“世界和平”的功能性指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