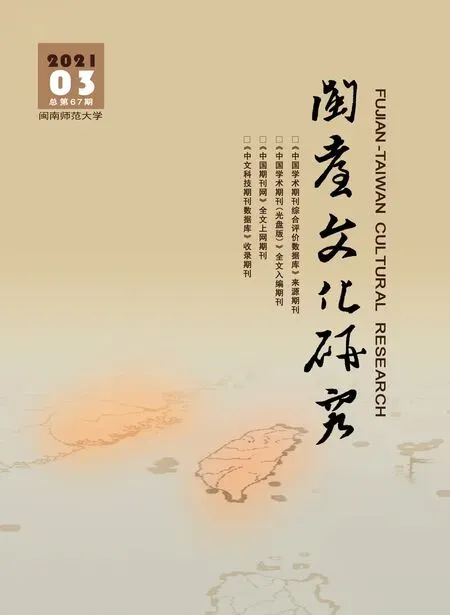施士潔詩歌中的楚辭意象論析
張 金
(南通大學文學院,江蘇南通226019)
施士潔(1856~1922),名應嘉,字沄舫,號蕓況,晚號耐公。六歲能屬對,有觸類旁通之妙。所以未冠之時,便舉秀才,十九歲赴省參加秋試,中了舉人,二十歲上京都參加春試,中了三甲進士,欽點內閣中書。施士潔其父施瓊芳早年由福建省泉州市晉江徙居臺灣,甲午戰爭臺灣被日據之后,施士潔挈家眷轉回晉江。
施士潔被稱為“閩臺詩壇盟主”,是近代臺灣詩壇的大家,和丘逢甲、許南英合稱“臺灣詩壇三巨擘”。施士潔在臺灣詩壇地位之高,成就之大,至今對臺灣及閩南文人都產生了一定的影響。連橫《臺灣詩乘》評價其道:“光緒以來,臺灣詩界群推施沄舫、丘仙根二公,各成家數。”郭麗平《施士潔的詩學思想及其文學創作》指出施士潔的孤憤精神是從屈原處繼承而來:“施士潔的孤憤精神是對屈子楚辭以來文學發憤精神的傳承。”施士潔詩歌中包含有大量與楚辭相關的內容,這些詩歌或借鑒楚辭的文學形式,或表達自身的人生感慨,或抒發內心郁結的情感。諸如《哭曾五小魯》:“小魯之死兮無端,從此俠少皆膽寒”,《盆中殘菊次坦中韻》:“美人香草今遲暮,留伴先生五柳門”。這些詩歌中蘊含著豐富的楚辭現象,體現出施士潔對楚辭的傳承與發展。由此觀之,施士潔的詩歌創作受到屈原的一定影響,他對楚辭的傳承還有許多值得探究的地方。
一、施士潔詩歌中的楚辭意象
(一)騷壇
施士潔詩歌中多次出現“騷壇”,分析其中內涵,施士潔詩歌中出現的“騷壇”多指“詩壇”。他的《□□□歸日本索詩贈別》道:“林逋鄭古兩詩人,與君鼎足騷壇時”,林逋是北宋著名隱逸詩人,鄭古是唐代詩人,以這二位詩人與友人相比,是對友人詩才的稱贊,“鼎足騷壇”在這里即指“鼎足詩壇”。再如,《墨史疊韻索和》:“騷壇我已慚盟主,吟伴君堪讬蹇修”,施士潔被譽為“閩臺詩壇盟主”,這里自謙所言“騷壇我已慚盟主”中“騷壇”自是指“詩壇”。類似的例子還有很多,《黎系叟司馬招游虎溪遇雨次系叟韻》:“領取江山雄杰意,騷壇牛耳有齊桓”與《三疊韻奉答氅丈》:“始知騷壇豪,無能出其右”,這兩句詩中的“騷壇”亦為“詩壇”義。
施士潔筆下“騷壇”所指含義并不局限于“詩壇”之內,如其詩《贈賀話義》言:“我愧能詩王介甫,騷壇拜倒賀方回”,作者稱其詩能敵王安石,但“騷壇”之成就卻在賀鑄之下。賀鑄是北宋詞人,能詩文,但尤長于詞,施士潔是詩壇盟主,但他亦作詞,在這首詩中主要表達人各有所長以激勵后輩。“騷壇”在此句詩中特指“詞壇”。
“騷壇”的“騷”最早由《離騷》處傳承而來,繼而成為以屈原《離騷》為代表的古典文學體裁的總稱。并且,隨著時代的發展,“騷”所代表的文體進一步擴大,“騷壇”逐漸演變為“詩壇”的含義。明清時期,“騷壇”就已經以“詩壇”義廣泛流傳。明代徐復祚《投梭記·折齒》曰:“他風流名士壓騷壇,烏鬼寧同仙鶴班。”清代秋瑾《讀徐寄塵小淑詩稿》中也提及:“今日騷壇逢勁敵,愿甘百拜作將軍。”“騷”字意義的一再演變,其中蘊含的是歷代文人學者對楚辭地位的肯定,以“騷壇”喻“詩壇”,甚至進一步引申為“詞壇”“文壇”,也進一步地反映出楚辭對詩、詞乃至文學界的影響之大。
(二)招隱
“招隱”一詞出自《楚辭·招隱士》,關于《招隱士》的作者,王逸《楚辭章句》云:“《招隱士》者,淮南小山之作也。”根據王逸的說法,《招隱士》是漢代淮南王劉安門客淮南小山所作。顧名思義,“招隱”即是指召喚隱逸之士,對于所招的“隱士”是誰,歷來說法不一。王逸認為《招隱士》為“閔傷屈原之作”,因此招的人是屈原。王逸云:“怪其文升天乘云,役使百神,似若仙者。雖身沉沒,名德顯聞,與隱處山澤無異,故作《招隱士》之賦,以章其志也。”但后人多質疑此說,朱熹認為此篇主旨應為召喚隱士離開山林,回歸到現實社會中來,王夫之也持同樣的觀點:“今按此篇,義盡于招隱。為淮南招致山谷潛伏之士,絕無閔屈子而章之之意。”也有學者認為此篇為思念劉安而作,金秬香在《漢代詞賦之發達》說:“小山《招隱》,何為而作也?詳其詞意,當是武帝猜忌骨肉,適淮南王安入朝,小山之徒,知饞釁已深,禍變將及,乃作此以勸王亟謀返國之作。”周建忠、賈捷注評的《楚辭》云:“此篇不論是小山之徒在當時處于政治的考慮還是純粹的情感召喚,如今已被歷史淹沒,但《招隱士》只能是淮南小山之徒因思念而召喚淮南王劉安而制。”上述三種說法各有千秋,至今學界還尚無定論。
自東晉兩漢之后,漢代掀起一股“隱士風”,諸多賦作和詩作中都有“招隱”之味。但由于社會歷史、政治環境、人文思想等的發展變化,東晉兩漢之后詩賦中“招隱”的意思已經發生了轉變,不再是《招隱士》中所表達的含義,如左思的《招隱二首》、陸機的《招隱詩》表達出了作者厭倦仕途,渴望歸隱山林的心理,張華的《招隱二首》則流露出隱以待時的隱逸思想。由此可見,東晉兩漢之時,“招隱”的內涵已從召喚隱士回歸社會轉變為提倡隱逸,吟詠隱士生活。
施士潔詩歌中共有十首提及“招隱”,在這些詩歌中,“招隱”都延續了東晉兩漢時期文人作品中所表達的含義。陶淵明作為晉代杰出的文人,其隱逸思想影響了世世代代的文人,其中也包括臺灣地區的學者,施士潔也不出其外。如《壽蔡曉滄觀察五十》:“招隱合歸陶栗里,移家剛好晉桃源”,“陶栗里”即陶淵明,栗里位于廬山溫泉北面一里許,是陶淵明的故鄉。作者在詩中表明招隱自該像陶淵明一樣,移家“晉桃源”,隱逸之后,脫離了世俗的煩惱,從而達到陶淵明筆下“桃源”那樣與世隔絕、安穩愜意的美好境界。再如《感事和壽人韻》:“歷山□欲歌招隱,眾自耕田鳥自耘”,“欲歌招隱”表現出施士潔內心動搖,其對隱逸生活心生向往,“眾自耕田鳥自耘”是作者追求的遠離世俗之后無憂無慮、自給自足的生活,這樣眾人一起耕耘且有鳥兒作陪的生活場景和陶淵明《歸園田居·其三》中所描繪的“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有異曲同工之妙。
除此之外,施士潔包含“招隱”的其他八首詩歌中也表現出其隱逸思想。如《和恕齊留別韻》:“大陸多矰繳,鴻冥不可蹤。征君拜黃憲,地主訪茅容。島市同淪落,騷壇孰折沖。桐陰吾故里,招隱愿相從”,施士潔稱贊東漢隱士黃叔度、賢人茅容的才德,實際上是以他們來勉勵自己,在政治環境險惡的情況下,詩壇也受到了沖擊,面對此等境遇,作者不免有些心灰意冷,因而萌生出歸隱回鄉的想法。這里的“招隱”即是“歸隱”之意。再如《乙卯(1855)十二月十有二日林季繩公子二十有一初度健人其獨子也以詩為壽如韻和之》:“鷺嶼別開招隱館,騷壇高筑受降城”,《叔莊吟社自癸丑至庚申八年矣花事惟菊特盛主人屬同社》:“招隱不妨朱邸客,論交無愧白衣人”,及《避地鷺門骨肉離逖數月矣歲暮始復團聚舉家乘小輪船赴梅林澳風逆浪惡不得渡晚宿吳堡感事書懷》:“依然帶發憨頭陀,來唱山中招隱歌”等,這些詩作都表現出施士潔無法忍受當時惡劣的政治和文化環境,無力改變的同時又不愿身處泥沼,在這樣矛盾痛苦的心境中難免會生出“歸隱”的念頭。
由上述可見,《招隱士》中的“招隱”一詞的本義無論是閔傷屈原、招隱士入仕還是喚淮南王劉安,都在長期的文化流傳過程中發生了演變,時至今日,“招隱”在現代人的心目中多數指置仕途于身外,歸隱山林,追求隱逸生活。這種意義的轉變始自兩漢時期,特別是受到東晉兩漢的影響,是與政治歷史環境息息相關的。
(三)香草美人
屈原在《離騷》中大量運用“香草美人”意象,將自己豐富的想象融入其中,講述了自己的身世、遭遇、理想追求、政治主張等。屈原用香草喻自己,喻他人,象征著詩人高貴的品質,例如,“扈江離與辟芷兮,紉秋蘭以為佩”中的“江離”“辟芷”和“秋蘭”都是香草,王逸《楚辭章句》注:“言己修身清潔,乃取江離、辟芷以為衣被;紉索秋蘭以為佩飾;博采眾善,以自約束也。”屈原借這三種香草來表現高潔的品質,至死不渝的高尚情操。“蘭芷變而不芳兮,荃蕙化而為茅。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為此蕭艾也”中“茅”作為惡草與芳草“荃蕙”相對,“蕭艾”作為惡草與“芳草”相對,屈原借香草向惡草的轉變表達正直的人變節之痛心和憤懣。
美人則用來比喻楚王或君子或自喻,洪興祖《楚辭補注》注“恐美人之遲暮”言:“美人,謂懷王也。人君服飾美好,故言美人也。”《離騷》中詩人多次求美人而不得則象征著屈原忠而被謗因此被君王疏遠。但屈原上下求索,不斷尋美:“和調度以自娛兮,聊浮游而求女”就是為了表現其對人格的完美追求,以求達到兩美合一的境界。“香草美人”作為楚辭中具有代表性的意象,獲得了后世許多文人的認同感,在后世的詩歌創作中,這種以草木或美人來比擬自己或君臣的方法流傳下來,成為一種常見的詩歌創作方法。
施士潔詩中多處運用“香草美人”意象,《盆中殘菊次坦公韻》:“美人香草今遲暮,留伴先生五柳門”,用“香草美人”意象指代君子。《黃恕齊孝廉逸翰樓詩集》:“野老酸辛留史筆,美人遲暮托騷懷”這里施士潔直接用“美人”指代屈原,體現出“美人”意象與屈原之間緊密的聯系,且作者將屈原與杜甫相提并論,這更是對屈原歷史文化地位的肯定。
施士潔詩中的“美人香草”在承襲屈原開創的香草美人意象用法的同時,也在此基礎上做了一定程度的引申。例如,《疊次韻答雁汀韻再答》中就多次提及“美人”“香草”:“美人在何許,癡想古夷光。試誦莘田句,吟箋草自香。好色本國風,騷人性不減。所以屈靈均,字字芷蘭擷。草幽香可憐,香幽不可掇。安得素心人,緘香寄寥闊。鬢絲禪榻間,六根此參透。彼哉物之尤,南威而鄭袖。”詩中所提及的“美人”,有兩層含義,一是指“夷光”,即西施這樣的美女;二是指像西施這樣高潔的人。這一點在屈原用“美人”意象喻己、喻人的基礎上又縮小了范圍,特指品性高尚的美女。施氏在此詩中變相化用了“香草”意象的含義,將屈原詩句里帶有香草理解為這是對品行高潔美人的追求,像“南威”“鄭袖”這樣美而不端的女子不僅不值得追求,反而會受到鄙視。在施士潔的詩歌作品中,“香草”意象的含義也從美好的德行品質發生了轉變,《疊厚奄詩來和韻書感韻》:“一門騷雅誰能友,兩世□□老更親。蘭芷孤吟遷客怨,萍逢小聚異鄉緣。”在此句中,“蘭芷”作為香草與“遷客”相對,“孤吟”賦予了其生命力,香草不再是一種修飾,而是和“美人”意象一樣,直接代指人,在這里指的是“詩人”。
香草美人意象由屈原開創,已經成為一種文學表現手法。施士潔在此基礎上,將其運用到自己的詩歌創作中,在繼承的同時也有創新,將香草美人意象的內涵包括但不限于屈原所表達的意義,通過詩句的闡釋進一步引申出更深層次的內涵。
二、施士潔詩歌中出現的楚辭意象原因分析
(一)歷史原因
楚辭意象含義的轉變很大程度上是長期的歷史文化的演變造成的。屈原創作《離騷》《九歌》《九章》之后,漢代不少文人模仿楚辭作品的體例形式,創作了一系列擬騷詩,如東方朔《七諫》、王褒《九懷》等,這些擬騷作品幾乎都是以屈原的思想作為引申的出發點,但作品所要表達的思想感情是作者自己的。由此可見,對騷體詩歌的模仿自漢代起就開始盛行。隨著屈原作品對后世的影響不斷擴大,在歷史的長期作用之下,一些最能代表屈原作品的典型意象流傳下來,且被后世詩人廣泛運用到文學創作之中,如“離騷”“香草”“美人”等。
因此,施士潔在詩歌創作的時候,繼承了歷史的傳統,借楚辭意象更含蓄更深沉地表達其內心的情感。“騷壇”“香草美人”“招隱”等詞在施士潔之前就大量被文人運用到文學作品中,早在明清之時,“騷壇”一詞在詩人的筆下已是“詩壇”義,更進一步被引申為“文壇”義。由此可見,施士潔的創作并不是單憑自身,而是在學習前人的基礎上完成的。隨著歷史不斷演變,文化的代代傳承,前人的創作方式也會被后來的學者所學習容納,使得這些楚辭意象成為更廣泛的情感的載體。因而,楚辭意象在流傳過程中出現的意義演變實質上是長期歷史演變下文學發展的必然結果。
臺灣與大陸為一體,解讀施士潔的詩歌作品,不僅發現其對大陸文化的繼承與發展,更表現出至少在日據之前,大陸與臺灣之間的文化一脈相承、同氣連枝。施士潔詩歌中出現諸多楚辭意象也是他學習、傳承中華文化,促使其發展的體現。
(二)環境因素
施士潔詩歌中包含如此多的楚辭意象,最深沉的原因之一是時代因素。中日甲午戰爭前夕,全國人民投入抗日救國陣線,施士潔也全力以赴,走上抗日第一線。并發揮他的詩的戰斗作用,寫了《同許蘊白兵部募軍感迭前韻》和《瀛南軍次再迭前韻禾同事諸子》等詩篇,藉以號召民軍前仆后繼,浴血奮戰,保家衛國。甲午中日戰爭之后,中日簽訂了不平等條約,施士潔無比痛憤怒,對代表清政府簽訂馬關條約的李鴻章做出“尚方愿賜微臣劍,先斬和戎老儈頭”(《感時示諸將和陳仲英廉訪韻》)的激烈批判。類似這樣批判現實社會、對命運作出抗爭的詩歌俯拾即是:“腐氣儒無將,哀時□□□”(《痛哭》)、“恨未喪師先失地,問誰揖盜自開門”(《別臺作》)。作者對清政府的失望,對侵略者的痛恨,對賣國賊的憎惡表現的淋漓盡致。
面對晚清政府動蕩、危機四伏的時局,自己卻無力改變的現實社會,施士潔不由得自內心深處發出悲吟:“窮途夸父猶追日,孤憤靈均欲問天。”(《和獲叟鴻雪堂詩韻時將有遼東之行酒緣燈紅感懷贈別》),盡管環境是惡劣的現實是殘酷的,但施士潔從未放棄改變現狀,他加入抗日保臺的斗爭,以期挽救故土即將淪落于他國的悲慘狀況。他正是借夸父和屈原這樣不服輸和堅持求索的精神,來表達自身對于正義的追求、對殘酷的社會現實的反抗。
施士潔中出現的楚辭意象不可避免地與當時社會環境息息相關。屈原一心為國卻忠而被謗,無法左右帝王的想法,正如施士潔抵制割臺政策卻無力改變當時的狀況,特殊的時代背景刺激了他強烈的悲憤的創作,施氏正是借楚辭意象來表達與屈原相似的情感體驗。
(三)作者個人生活際遇
施士潔創作的諸多騷體詩歌不是其一時興起之作,這是他一生的經歷及其心中郁結的情感的抒發。施士潔和其父施瓊芳二人有“父子進士”之稱,施士潔從小聰明伶俐,二十二歲就考中進士,比其父有過之而無不及。但其科舉考試并非一帆風順,其詩《禮闈聯捷》曾曰:“名場磨我總書癡,得失無端祇自知”,道出自己苦讀的辛酸。據孟建煌考察,施士潔做官之后,因官冷身貧、家中變故以及利益誘惑等諸多原因而辭官歸故里,過上了士紳的生活。離臺內渡之后,施士潔在外漂泊,生活窮困潦倒。故土難回本就幾多愁苦,妻、子先后因鼠疫而亡更是給其人生增添了數不盡的悲哀。施士潔人生坎坷如斯,其對于世事已經看淡了許多,因而其詩歌中常常表達出“歸隱”的念頭,他和他崇敬的蘇軾一樣,愛好平淡舒適的生活,對烏煙瘴氣的官場文化的排斥與不滿促使著他遠離污濁的官場而身歸故鄉。《夢蝶園限東真陽韻》:“甯靖東來故國亡,先生招隱托蒙莊”、《健人疊韻見和再疊簡菽莊鐘社主人并諸同志韻酬之》:“洞天老鶴初歸隱,浪嶼吟螀已報秋”等詩都足以表現出施士潔人生坎坷心生歸隱的內心想法。由此觀之,正是個人生活際遇、人生觀念的影響,施士潔的詩歌中才會出現諸多“招隱”類的楚辭意象。
施士潔強烈的愛國精神也是他詩歌中產生諸多楚辭意象的重要原因。這種愛國情感和屈原的家國之思一樣,都在他們詩歌創作過程中流露出來。乙未(1985)割臺,施士潔恥為異族之民,攜家眷內渡,寓居于福建省晉江西岑,先后作《感時示諸將和陳仲英廉訪韻》《痛哭》《別臺作》《和哭庵績寓臺詠懷韻》表達自己的慟哭與悲憫。《和哭庵績寓臺詠懷韻》中表達的尤為深切:“紅毛樓上空回首,十萬人家冷灶煙。天昏欲叩黯神傷,痛飲離騷吊楚湘……景陽門內人延敵,函谷關前客遁逃。舊鬼煩怨新鬼哭,故應六月慘飛霜。”施士潔先引離騷,再征杜甫,因為經歷的時代背景與歷史環境相似,故而和屈原、杜甫產生了跨時代的心理共鳴。同是熱愛家國卻痛失家國,同是留戀故土卻無法歸故土,這種同命相連之感是屈原和施士潔之間特殊的情感鏈接。這種深沉的情感凝聚在心中無處得到宣泄,只有通過詩歌表達出來,作者對流離失所的難民的同情以及沉重的愛國情感在這些詩歌中得到了充分的體現。
三、結語
施士潔詩歌中包含如此多的楚辭意象,這些意象的含義在日益發生著轉變,相較于屈原作品中的原意已經作了進一步的引申,產生了異意。楚辭意象含義的轉變不僅是文學發展的必然結果,也是世世代代的文人學習屈原、對楚辭文化傳承的結果。
從施士潔的詩歌中,我們可以體會到其追求楚辭、繼承楚辭的方面,也能夠感受到屈原強大的人格力量給予后人的激勵與鼓舞。可以說,施士潔詩歌中的這些楚辭意象是在歷史因素、時代背景以及作者人生經歷三重因素作用之下產生的。近似的人生遭際、共有的愛國主義情感,使施士潔對屈原產生了心理共鳴和身份認同,在面對外敵侵略、故土難歸的境地中受到屈原的感召,由此二者自然地聯系到了一起,故而施士潔悲憤的感情訴諸于筆端,其詩歌中大量出現楚辭意象,借以表達內心的情感。
注釋:
[1]連橫:《臺灣通史》,上海:商務印書館,2017年,第265頁。
[2]郭麗平:《施士潔的詩學思想及其文學創作》,《泉州師范學院學報》2015年第3期。
[3][4][5][6][7][8][9][18][19][21][22][23][24][30][31][32][33][34][35][36][37][38][39][40]全臺詩編輯小組撰,施懿琳主編:《全臺詩》第十二冊,臺南市:臺灣文學館,2008年,第50頁,第236頁,第183頁,第341頁,第189頁,第401頁,第233頁,第141頁,第147頁,第262頁,第310頁,第380頁,第103頁,第236頁,第259頁,第359頁,第124頁,第91頁,第93頁,第94頁,第213頁,第413頁,第293頁,第97頁。
[10](明)徐復祚著,孫京榮評注:《六十種曲評注》第一冊,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82頁。
[11]劉玉來:《秋瑾詩詞注釋》,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50頁。
[12][13][14]王逸:《楚辭章句》,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244頁。
[15]王夫之:《楚辭通釋》,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175頁。
[16]金秬香:《漢代詞賦之發達》,上海:商務印書館,1934年,第19頁。
[17][25][27][29]周建忠,賈捷:《楚辭》,南京:鳳凰出版社,2009年,第218頁,第2頁,第30頁,第30頁。
[20](晉)陶淵明著,許巍選注:《陶淵明詩選》,1984年,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第27頁。
[26]王逸:《楚辭章句》,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4頁。
[28](宋)洪興祖:楚辭補注,北京:中華書局,2018年,第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