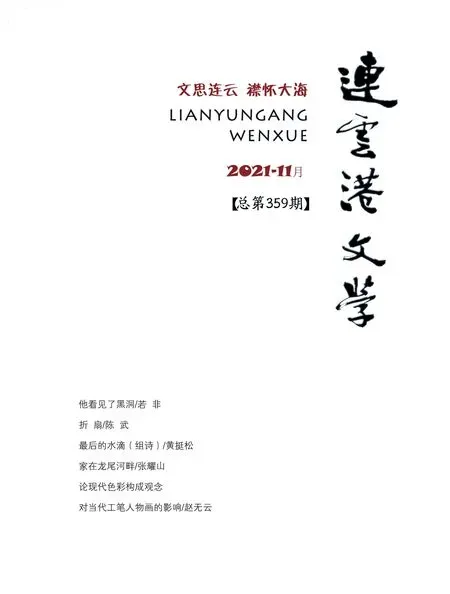家住龍尾河畔(四)
張耀山
如煙歲月
我的出生地新浦,前幾年與海州區合并,統稱為海州區,生于斯長于斯的我,忽然有點江山易主寄人籬下的感覺。這不是狹隘的我對出生地的眷念,而是覺得抹掉新浦似乎等于割裂了一段的歷史。
新浦的地名已經不存在了,再過兩代人,將會被后人遺忘,淹沒在歷史的長河里。站在對歷史的敬畏,對后人負責的立場上,我想對新浦形成的過程作簡略地回顧。
辭書上,對“浦”字除作姓氏以外,還有許多解釋,不一一敘述了。從《古海州志》對“東海諸浦”的注釋看,古海屬地區的“浦”有四個特征:一是上無源頭,二是下通海潮,三是漁舟鹽舶,四是經過人工疏浚。通俗地講,所謂“浦”是指沿海灘地上無正式源泉的、季節性向海里排洪各自獨立的小水系,后經鹽工、漁民加工,成了運鹽河道和漁船停泊的避風之處。這是我市著名的地方志專家韓世泳先生對“浦”字的權威性解讀。在沒有新的更有說服力的觀點誕生前,姑且用之。
韓世泳先生繼續深度解析:古海州沿海灘上為什么會有這些獨立的小水系呢?這是海州海岸不斷變遷的結果。據《海州志》記載,古代大海離海州城很近,明萬歷六十六年(1578 年)至清咸豐五年(1855 年)這277 年間,由于黃河全部走蘇北入海,泥沙驟增,使蘇北地區海岸線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大量泥沙淤墊,使海岸線迅速向海州古城東北方向推進。云臺山逐漸離海歸陸,出現了大片海灘。夏秋季節,洪水漫流,順勢匯集,沿著低洼處向下流淌,流入大海。由于不斷受海水的洗刷和海潮的沖淘,這些小溝越來越深,越來越寬,自然形成了上無源頭、下通海潮的小水系。隨著時間的推移,海灘變成了鹽灘,成了人們曬鹽捕魚的場所,這一條條小水系又得到了疏浚加工,便成了具有明顯特征的東海浦。隨著海岸線的不斷遷移,這些通稱“浦”的小水系的下游不斷延伸,使其保持下通海潮的功能。新浦就是在這種過程中產生的。因出現在板浦、六家浦之后,故時人稱之為新浦。要計算新浦的年齡,最多是從鹽商捐資疏浚新浦河,立了新浦口的清嘉慶三年(1798 年)起,至今也就二百來年的歷史(參見韓世泳先生2005 年出版的《新浦史話》)。至于隨著海岸變遷,新浦口逐漸移位到今天新浦老城區民主路一帶,那歷史就更短了。
由于新浦地區經歷了黃河入海,大量泥沙淤積后離海歸陸的地理變遷,所以新浦地區的地勢十分低洼,有人說,新浦最低處的海拔是負一米(未經考證)。老人說,蛙(讀如歲,海州方言,意為青蛙)子尿泡尿,足以淹倒半間屋。這是對處于低洼處居民生活的真實寫照。
洪水過后重建家園
1970 年夏天,連續多天暴雨,龍尾河兩岸變成一片汪洋,恰逢海水大潮,臨洪閘不能開閘泄洪,政府部門帶領街道干部,挨家挨戶動員災民投親靠友到海州等地勢高些的地方暫避時難。對一些家庭條件差的人家提供交通工具和適當的生活補助。雨過天晴后,當我們回到家園時,大多數人家的土坯房經過洪水的蕩滌,被夷為平地,境況慘不忍睹。還好,我家的房子,除了南山頭有點塌陷外,其他地方損失不算太大。政府借機調整,將校內的幾戶人家遷出。盡管政府補償是杯水車薪,加上原有房屋上能用的材料繼續使用,自己動手,鄰居相助,很快恢復了正常的生活秩序。
我家的新宅基地位于原址相隔三四戶人家的河邊上,因河堆地勢高,在肆虐的洪水中這兒的房屋安然無恙。建房新址是將郭姓人家的院落一分為二,這理所當然地引起郭家的不滿,四處找茬,因此從蓋房那天起,兩家就沒有安生過。那時,鄰居間的地界沒有嚴格的劃分。雖說土地所有權歸屬于國家,可是在老百姓的心目中,誰先占有誰就是這塊土地的主人,這一點被時人普遍認同,也是在祖祖輩輩地界爭端中形成的共識。對于郭家被割讓的土地而產生的怨氣,我們是可以理解的,但對方接下來采取的一些過格舉動使我們無法接受。
我家由盛而衰分為三個階段:1958 年祖父溘然離去,使家庭處境每況愈下;1964 年父親結扎,使家庭處境雪上加霜;1970 搬遷重建,使家庭處境岌岌可危。
1970 年,是我家最焦頭爛額的一年。那年我15 歲,我的小爺15 歲,兩位尚未成年的孩子卻是搬遷蓋房的主要勞動力。大家知道,房子再破尚可遮風擋雨,一旦拆了,便是一堆建筑垃圾,能再繼續使用的材料少之又少。沒有錢,沒有建筑材料,沒有足夠的勞動力等都可通過多方籌措和勤勞的雙手逐步完善,讓人無可奈何的是來自原址主人的騷擾。建筑材料不能走他家院里通過,腳手架不能搭在他家的院子里,說白了就是不讓你蓋房子。經過無數次協調,無數次交鋒,無數次妥協和讓步,在時風時雨你來我往的對峙中,房子的主體框架得以成型。新房上梁(落成)是隆重的收官儀式,要放鞭炮,撒喜糖,其隆重程度不亞于結婚。主家略備酒水,以答謝前來祝賀的親朋好友,主人討個喜歡,客人討個彩頭,皆大歡喜。
是日早上,河邊來了很多人,面孔很生,不太像前來賀喜的人,他們沖我家的房子,戳戳點點,指手畫腳,小聲嘀咕著。盡管我沒經過什么場面,直覺告訴我來者不善。時近中午,客人落座,菜已上桌,郭家老太來了,把喜慶的場子給攪黃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這是有策劃有預謀的惡意挑釁。她說我家的房子比她家的房子高出幾公分,是在欺負她家。當時人的確有這個講究,房子前高后低,使后面人家有壓制感,會帶來晦氣。
我祖父是搞建筑的,受他的影響,父親對百姓建房時的講究和忌諱也略知一二。在我家房屋動工之前父親就注意到這點,盡量不給郭家留下話柄,以免節外生枝。
在我家東山頭向東延伸到河邊的一塊空地,本應由我家使用,鄰里間也認同。郭家將垃圾、馬桶等污物傾倒于此,而且理直氣壯,這是明目張膽地欺人。父親自知勢單力薄,但又咽不下這口窩囊氣。兩家兵短相接,箭在弦上,一觸即發。
郭家與滕家,住在一排,是親姐弟關系,每家有五六個小孩,加之郭家與謝家聯姻,謝家老弟兄四人,每家有四五個男孩,這是以血緣為紐帶而形成的龐大的家族聯盟,我家處于“四面楚歌”的境地。有時,父親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選擇單刀赴會,其結局可想而知。我只能眼睜睜地看著父親被人圍毆卻無能為力。
平心而論,鄰居間的沖突,只追求在精神上占優勢,只是讓對方服氣、低頭、甘拜下風,而不是給對方以肉體上的痛苦為終極目標。
鄰居間的肢體沖突,往往有這樣三步:第一步是相互指責,并表明沖突的理由,堅守“要文斗,不要武斗”的底線,尚處于熱身階段;第二階段是在激烈的語言交鋒中,帶有臟字,出現某種侮辱對方的語言,甚至罵人,使矛盾升級,處于示威階段;第三階段,是肢體沖突,當事人雙方抱成一團,或抓在一起,相互推搡,嘴里不停謾罵,很少出現拳腳相加甚至使用器械,處于征服階段。這時,雙方都等待一個人的出現,這個人一定是雙方都認可都尊重的、說話有一定分量的人,他的出現,找個臺階,各自松手,一場沖突,就此平息。但內心的積怨卻沒有得到任何化解,只要機會成熟,“戰火”會再度燃起。
新居的東山頭有一棵樹,樹干很粗,樹冠很大,是郭家早年種下的。這棵樹長勢良好,可惜長錯了地方。它是郭家霸占這塊空地最有說服力的理據,卻像一塊石頭沉甸甸地壓在我父親的心上。在與郭家的多次摩擦中,大多是圍繞這棵樹展開的。
父親習慣于獨自一個人倚在南墻根悠閑地喝著小酒,抬眼望去樹正好被框在我家院落的大門里,這讓他十分不悅。父親熟知當年楊修自作聰明,與曹操玩起了文字游戲而招來殺身之禍的三國典故,更知道蘇小妹與老和尚之間拆字對聯的詼諧故事。“口”里加上“木”字不就是“困”嗎?他把這些年的所有不順都記恨在這“困”字上,欲將除之而后快。有一天他十分神秘地在我耳邊說,想把這棵樹給謀害了。我看了看酒杯和酒壺里的酒,心想,這點酒不至于讓他說醉話吧。他見我不解,繼續說:“等到冬天,我燒上一鍋開水或買上十幾斤鹽,然后……”然后他什么都沒說,用右手恨恨地做了一個“殺”的動作,這動作做得很嫻熟很解恨。這讓我打了個寒顫。接下來,他不說話也不喝酒,臉上露出淡淡的微笑。我太了解父親了,能精確地解讀他微笑背后所深藏的內容。他的腦海里一定出現了這樣一個場景:郭家人披麻戴孝,呼天號地,孝子賢孫們,沿著河邊,浩浩蕩蕩地向河對岸的小亂坑走去,空中撒滿了紙錢。
由于生活的困頓或者是酒精的刺激,父親經常在現實和幻想中互換角色,營造自己的精神家園,使他在煩惱和苦悶中,獲取短暫的快樂。這于我而言多少是個安慰。
第二年的春天來了,此樹依然枝繁葉茂,一派生機。我知道,父親只是說點氣話,以解心頭之恨罷了。
中國的文字,是有色彩,有溫度,有情感的。不同的人,站在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心境,對同一個字會有不同的甚至是顛覆性地解讀。多年以后我對父親說,我家的大門沒有門檻,構成的不是“困”字,而是個“閑”字。你完全可以理解為放松、自在、無拘無束。他悶悶地說,也可以理解為無聊、失落、不受待見。他就是這么一個愛鉆牛角尖、認死理的人。祖母說他是個“九頭牛都拉不回來的主兒”。
縱觀古今中外,一切的戰爭大致是圍繞土地的歸屬權而展開的,無論是八國爭雄,還是秦吞六國,無論是南千島群島還是馬爾維納斯群島。土地是政權的載體,土地所在,政權所在。國如此,家也然。
吵架、打架,是以語言相對話、以肢體相對抗而釆取的極端的交流方式。體現了當事人雙方的真實的訴求。后來我得知,被我家蓋房子的那塊地,原來很低洼,每到冬天,原地的主人,動員一家老少,將龍尾河里的淤泥一鍬一鍬地填平,一年種上兩季莊稼,這對于十幾口人的大戶人家來說,將其視為生命而全力守衛所釆取的非理性的舉動是可以理解。按時間推算,我想,兩家的老一輩皆已過世,生不帶來死不帶走的土地問題都與他們沒有半點關系。前世的紛紛擾擾,磕磕碰碰都已煙消云散。若能地下相逢當以一笑了之。
同齡的小爺
小爺比我大幾個月,小學時是同班同學,我們吃在一起住在一起,一起上學一起回家,不知內情的人誤認為我倆是親兄弟。
新浦地區有個俗語叫作“疼頭孫,慣老柔。”所謂“老弟”是上一代最小的男孩,而“頭孫”是下一代最大的男孩,一個是親生的,一個是“隔代疼”,在經濟條件拮據,物質匱乏,吃穿用需要精打細算的歲月里,老少兩代同齡人擺在祖母的面前,誰親誰疏,著實給她出了一道難題。在這兩難的抉擇中,祖母努力將一碗水端平。
我的祖母生了四個孩子,兩男兩女,我父親是長子;我母親生了四孩子,三男一女,我是老大,“長子出晚輩”。祖母生小爺的時候已經44 歲,而母親生我的時候才29 歲。由于年齡的懸殊,祖母的奶水不足,母親的乳汁需要哺育一老一小兩代人,這種現象在當時并不鮮見。記得很小的時候小爺惹我母親生氣,母親會斥責小爺,“你是吃我的奶水長大的。”這種說法在祖母的口中和家邊婦女的八卦中得到了印證。每當此時,小爺疑惑地看著他的母親再看著我的母親,其中的含義懵懂不知。祖母笑瞇瞇地看著叔嫂倆在斗嘴,神情暖暖的。
十歲之前,我留著長發,身上披戴著銀飾,一副女孩子的裝束,這是祖父定下的穿著基調,男扮女裝好養活,這種不男不女的打扮最容易引起男同學的譏笑和欺負,一位剛調來的劉姓同學不知底細,惡意挑釁我,被我和小爺合力反擊,狠狠地揍了一頓。這還沒完,放學后我們追到他家,嚇得劉姓同學的母親向我祖母救援才得以平息。在小爺看來,盡管大我幾個月,但他是長輩,有保護我的義務,“打仗父子兵”歷來如此。
小爺個頭沒有我高,比我矮兩公分,祖母說小時候抬水時小爺把我“帶杠”,被壓得不長的,此話說得或許有些道理。十幾歲的男孩就要擔當起繁重的體力勞動,龍尾河邊家家如此,無法偷懶的是抬水。“抬水”,是當時家中有孩的優勢,如今的城市和農村都難得一見的場景。路南、賈圩兩條街道,幾百戶人家,只有在通灌路兩邊有三家賣自來水的。夏天還好,洗菜洗衣服包括男孩洗澡,用的都是龍尾河水,只有吃的喝的用自來水,既省錢又省事。每到冬天,天不亮就要排隊,有時到中午才能等到一桶水。“懶人使重擔”,小爺心疼我,每次都將水桶靠他近一些,以減少我的壓力,這就是祖母口中的“帶杠”。
我和小爺是家中沒成年的勞動力,生活所迫,不得已要擔負起養家糊口的體力支出。好在小時候再苦再累都能快樂地生活著。
“曬平網”是這座城市東南邊緣特有的景觀,它是家庭富余勞動力的標志,也是家庭生活狀態的體現。龍尾河邊人家的額外收入大致源于龍尾河取之不盡的魚蝦資源,撈魚摸蝦是他們必備的生存技能。撈魚和摸蝦,季節不同捕撈的地點不同,捕撈的工具和技巧都有差異。拉蝦,多在春夏秋三季,拉魚則在冬季,聽說由于水冷,魚貼近河底便于捕撈。父親買了尼龍繩,我和小爺在家邊鄰居手把手地指導下學會了織漁網。尼龍繩結實耐用,脫水快且省力,但先期投資比麻繩要高許多。出于好奇,我和小爺迫不及待想嘗試一下新網的捕捉效果。與以往幾個人結伴而行不同,說服了祖母,備上干糧,叔侄二人半夜就悄悄出發了。
冬天的三更,月黑風高,紅砂路是考驗我倆膽量的第一個關口。
紅砂路東西走向,現在已被城區包圍,在振興花卉園的南門處被瀝青覆蓋的路基,是它當年的雄姿。一百多年前,這兒是靠近岸邊的海,受洶涌的海浪沖刷,退潮時露出一道砂脊,退海歸陸后便形成天然的道路,這條路上標志性建筑是火化廠,前邊還有大片的墳塋。因此紅砂路是“死亡”的代名詞,常有老人念叨說,我快到紅砂路啰,是說離死亡已經不遠了。這樣的環境對于半夜行走的兩個十三四歲的孩子而言,其恐怖的程度是可想而知的。
不足兩米寬的紅砂路上,有個人影向我倆迎面走來,速度不緊不慢,與我們擦肩而過時,西墜的殘月照在她的臉上,是個女的,臉色慘白,頭發上落滿了霜,目不斜視地向西慢慢地挪動著。極度的恐懼調動了男孩潛在的蠻勁,我們騎著自行車一口氣爬了四五百米的高坡,到了龍山頭一個賣茶的草篷底下,這時才后怕,我和小爺面對面地哭了起來。哭聲吵醒了賣茶水的李大奶,她安慰我倆不要害怕,說那個女孩不是鬼,是云臺農場知青,在一次撥稻秧時,被蛇嚇得神經錯亂,經常一個人深更半夜往外跑,周邊人都知道。真相絲毫沒有削弱我們的恐懼,隱隱預感到會有一天的不順。
天已經大亮,我倆騎著自行車沿著婦聯河繼續向東,路過大島山由小板折向南。在善后河的支流邊上有座麻風院,河面上有渡船。由于每天有船在兩岸行走,這兒并沒有結冰,凜冽的寒風將河面撕開一條百米口子,我們在這下網,等待豐收的喜悅。可沒走兩步,纜繩被如同玻璃一樣鋒利的冰塊給割斷了,我倆沮喪地坐在岸邊發呆。按纜繩、網和我們之間形成的角度推算,經驗告訴我,網離岸約十幾米遠,而且河水不會沒過我的頭頂,如果能抗得住寒冷,把網撈上來是有可能的。無知者無畏,我倆下水沒走幾步,徹底領略了“刺骨”的真正含義,繼續走下去可能要有沒頂之災,只得返回岸上。路過的農民看到我倆凍得瑟瑟發抖。在河邊劃摟些草,找個背風處點燃給我們烤火取暖,一陣風吹過,火燒焦了我們的眉毛和頭發。我們對視了一下,先笑后哭。如何向家人交代,回來的路上一直焦慮著。
從吃過午飯開始,祖母站在龍尾河邊向西南方向眺望著,我和小爺半夜從家中出發,她心中一直忐忑,看到我倆出現在賈圩橋上時,一塊石頭終于落地了。我把今天的經歷詳細地告訴了祖母,并表示愧疚,是打是罵任憑處置。祖母撫著我的頭說,只要人沒事,其他的都無所謂。我再次流下了眼淚。
一天之內三次流淚,一次是恐懼,一次是擔憂,一次是慶幸。
我和小爺大概源于同一個人的營養供給,體內澎湃著同樣的原始動力。從小我倆同在一個桌上吃飯,同在一個被窩睡覺,同在一個教室上課,稍長后我們一起撈魚摸蝦,一起上山撿石頭,一起蓋房子,一起糊火柴盒,幾十年來形影不離。如今已逾耳順之年,隔三岔五地在一起小聚喝酒,酒后忽略了老少之間的尊卑,產生了輩分的錯位,有點像兄弟間的鬧哄,這讓我隱隱有點罪惡感。感謝小爺的大度并不太在意我的越位行為。
第二個本命年
1979 年是我人生的第二個本命年。傳統的習俗認為,本命年是一個人不吉利的年份。“本命年犯太歲,太歲頭上坐,無喜必有禍”,故民間通常把本命年叫作“坎兒年”。這一年的遭遇印證了這一說法。我父親母親雙雙住進了醫院。我母親是醫院的常客,而父親則是“彎扁擔不折”。
正月剛過,小弟來到我的單位,說父親突然發病了,跑到家中看時,父親的病情遠比想象的嚴重得多。住院前幾天還能吃少許的飯,與人能作簡短的對話,接下來就是三十八天的昏迷,不省人事。醫生護士認為父親沒有康復的可能,出于善意,輪番做我的工作,勸我不要再白花錢,不要讓父親白受罪了,抓緊時間出院回家,料理后事。但我不忍心讓父親白白等死,堅持繼續治療。好在那時的醫療費用不高加之我本人為籌備婚事有點積蓄,堅持下去,等待奇跡的發生。
轉眼到了清明節,祖母準備了很多冥品,讓小爺去祖父的墳上燒紙,并叮囑了一些細節,包括冥品焚燒的順序和禱告的內容。祖母是耶穌教徒,從來不信鬼神之說。為了挽救兒子的生命,她只能把個人的信仰暫時擱置一下。
祖父的墳在老猴嘴山頭的半山腰上。從新浦出發到圓墳、燒紙、禱告、磕頭等一整套程序下來,約莫兩個多小時。上午十點來鐘,一夜沒合眼的我,趴在父親的病床邊上進入淺睡眠狀態,恍惚間,我感覺到床微微地動了幾下。驚醒后,眼前的一切讓我不敢相信,父親坐起來了,伸著懶腰,嘴里不停地念叨“累死我了”。在場的所有人都被這突如其來的一幕驚呆了。母親得知這一消息,固執地拔下針頭,從隔壁的女病房跑了過來,抱著父親號啕大哭。面對這一切,父親一臉茫然。在他看來,猶如昨夜睡覺今早醒來。對于其在鬼門關徘徊了三十八個日日夜夜一無所知。父親是在小爺祈求和禱告聲中蘇醒過來的。迷信也好,巧合也罷,父親的重生是不爭的事實。
父親的身體稍有恢復,壞習慣不改,整天鬧著要喝酒抽煙。父親的這次劫難,使年輕氣盛的我對生與命有了新的領悟,對父親特別孝順,一切由他性子來。
出院后,父親獨自一個人住在小東屋,這是他執意的選擇。
西山頭的小東屋
我家的新居是三間堂屋,兩間西屋。大概是延續老宅子的居住習慣,父親在院子里栽了四棵槐樹,鋪了一條一米多寬的碎石板路,從西屋門口一直到龍尾河邊,貫穿整個院落。石板路兩邊分別種上深紅的月季和粉色玫瑰,彌漫著芳香,頗具幾分都市田園的韻味。
在西屋與堂屋之間有個不寬的巷子,父親在這兒搭建了一個鴨圈。每天清晨七八只鴨子會順著碎石板路去到河里,撲騰一會兒然后鉆進蘆葦叢中覓食,傍晚時分,父親在河邊敲幾下鴨食盆,鴨子很理解主人的意圖,便原路返回。第二早上,天還沒有大亮,鴨圈里一陣喧囂后,地上留下四五只鴨蛋,有白皮有綠皮的。父親喜歡綠皮的鴨蛋,說是營養價值高。龍尾河邊的鴨子有得天獨厚的優勢,河里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魚蝦,為它們提供源源不斷的食物。作為回報,鴨子賣力地下蛋,以博得主人的開心。這是我家除了計劃供應之外的唯一營養補給。
小東屋在我家主屋的西山頭,原來是一條巷子,是前后鄰居來往的通道。西屋雖然不大,不過十來平方米,由于是相對獨立的空間,不受別打擾,上師范之前,由我居住。男孩子總希望有自己的自由空間,但我生來膽小,半夜時分,經常被莫名的動靜吵醒,或被恐怖的噩夢驚醒,一個人開著燈,提心吊膽地等待著天明。我從來沒有把這可怕的經歷與任何人提及過。有一天,我的師范同學蔣義好住在我家,半夜時,他死命地哭喊,當我把他叫醒時,他說他做了一個噩夢,一架日本轟炸機在半空中盤旋,日本鬼子帶著風鏡猙獰地向他狂笑,然后投下一枚炸彈,將他炸得粉身碎骨。我打了個寒戰,因為同樣的場景在我的夢中也多次出現過。所以當父親病愈后要住在小東屋時我是堅決反對的,他很固執,我又不敢說出理由,只好由他去了。據說,人一年要做三百至一千個夢,有清晰的有模糊的。夢中的情境大多與日常生活相關聯,有的夢是感受到的,有的夢境是的確存在而人卻感受不到的。有一天早晨,我剛起床,看到父親站在院子里,單手叉腰,仰望著我夢中飛機扔炸彈的天空,臉泛著莫名其妙的神情,莫非他也做到了同樣的夢?
夢是現實生活潛藏在意識深處,并以虛擬的形式反映現實生活。不同的人在同一個地方做著同一個夢,這種怪誕的現象確實不可思議。
事隔三年,父親舊病復發。這一次沒有奇跡發生,父親悄悄地走了,就在西山頭的小東屋里。那一年他五十四歲。
母親追隨父親而去
兒女在出生之前在母親的肚子里待了十個月,所以兒女與母親之間,語言、眼神、肢體的交流都顯多余,血緣的感應是無形的溝通。
1984 年8 月10 日,我應邀陪同時任市文聯副主席、市書協主席陳鳳桐先生赴安徽阜陽參加兩地書法聯展開幕式。對于第一次參加如此規模活動的我而言,其激動和興奮是無法言表的。看著東來的列車,吐著濃濃的白煙緩緩地駛進站臺,一種離奇的感覺從心底冒了出來:我好像不是出差,不是旅行,而是漂泊,甚至有點兒像是逃荒。當列車即將啟動時,我抓起簡單的行李,毫不猶豫地從火車上跳了下來。一切都那么突然,那么莫名其妙。陳鳳桐主席將頭伸出車窗外不停地與我打招呼,可是我一句也沒有聽見。空蕩蕩的站臺就我一個人孤零零站在那兒。我不知道要上哪去也不知道事發的原因,冥冥之中聽到有一個沙啞的聲音在呼喚著我,看到有一雙手在空中無力地揮動著。我不由自主地下了鐵路橋,沿著龍尾河邊憂心忡忡來到了家門口。大門緊鎖著,從門縫里看到院子里滿地散落著發黃的樹葉,一只木桶的鐵箍已經脫落。我不由收緊了頭皮,不祥之感襲上心來。回到自己的小家,坐臥不安。半夜時分,有人在敲門,我第一感覺是一定與母親有關。敲門的人告訴我,母親走了,下午六點多鐘,吃過晚飯以后,在第一人民醫院的病床上走的。彌留之際,她環顧四周,沒有一張熟悉的面孔,于是,無可奈何地合上了雙眼。
母親先天心臟不好,按醫生的建議,像她這樣的身體狀況是不能生孩子的,可她一連生了六個孩子,(前兩個孩子夭折),這對于她而言是身體與精神的雙重打擊,無異于雪上加霜。母親曾就職于地毯廠、麻紡廠、化纖廠等單位,每次工作的變動,大概均由身體的原因造成的。父親心地很善但脾氣很差,尤其是酒后常常惹母親生氣,母親無力反抗,只能生悶氣。好在祖母對她好,處處護著她,加上我們幾個孩子也很懂事,這對她是很大的安慰。我參加工作,二弟當兵,讓她看到走出困境的希望。當我把工作第一個月的工資交到她手里時,她看到了二十年來含辛茹苦的回報,身體和精神較前些年有很大的改觀。母親突然離世,作為長子我有預感,但沒想到如此突然,以至無法接受這一殘酷的現實。
這對恩恩怨怨幾十年的夫妻,一年之內雙雙離去。父親卒于1983 年10 月22 日,陰歷九月十七,享年五十四歲;母親卒于1984年8 月10 日,陰歷七月十四,享年四十九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