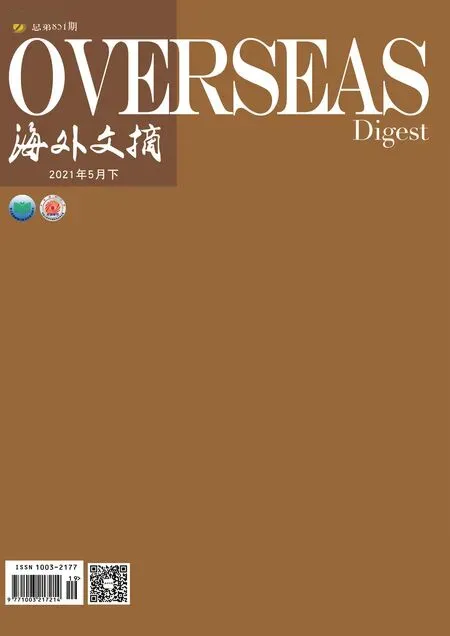創傷視角下《飛越瘋人院》中印第安敘事者的創傷根源
周婧
(天津師范大學,天津 300387)
0 引言
肯·凱西是美國垮掉派作家,是反文化運動的先驅,嬉皮士的代表人物。肯·凱西本人對20世紀六十年代的美國工業化社會有著敏銳的洞察力。肯·凱西在經歷一次迷幻藥物研究的實驗后,深陷迷幻藥物作用,并依據此經歷創作出《飛越瘋人院》。小說以精神病院為社會微觀縮影,刻畫了一群在工業化機制影響下,受到不同程度創傷并患有精神疾病的人。并使讀者通過一名印第安酋長的視角感受個體遭受創傷后的生存困境與自我認同的過程。
酋長的慘痛經歷是北美印第安部落群體創傷的個體體現。細讀文本后,不難感知,只有根植于創傷的具象化體現,剖析創傷根源才能尋求一條創傷復原之路。
1 創傷理論與文學
在20世紀90年代,美國心理學家朱迪斯·赫爾曼著作《創傷與康復》為創傷理論概念發展做出貢獻。該書從社會背景角度分析個體創傷經歷,打破傳統治療創傷的方式,開創創傷復原新視角。
目前,在傳統研究方法受到多樣化新方法的挑戰下,創傷理論研究逐漸多元化。在文學領域,創傷研究傾向形成一種涵蓋文學體裁多樣性,作者經驗多樣化的脫離單一研究形式的多元創傷觀。這表明,創傷理論在文學研究中的潛質與發展可能。
2 創傷表征:困頓與分割
勃魯姆頓以敘事者的身份,講述了麥克默菲在精神病院中的一系列反叛行為及其最后悲劇性的結局。讀者通過肯·凱西所構建的受創者的精神世界,感知主體在遭遇創傷后的心理運作機制。對慘痛的創傷經歷的回避,會使創傷主體會產生敘事障礙,無法將過往沉重的創傷經歷完整表述,甚至在飽受回憶的痛苦和自我壓抑之下,失去了個體完整性,困頓于創傷領域,而產生了個人世界的異化,如同生活在兩個世界,“一是創傷領域,另一個是現在的、通常生活的領域。兩個世界很難溝通”。在《飛越瘋人院》中,勃魯姆頓的敘事中,時常穿插著閃回,尤其當他在現實世界中,感受到危險事發生之時,如此反復跳脫,致使勃魯姆頓受困于往事,而使自身世界分化最終產生割裂。
勃魯姆頓的創傷不僅表征于其自身世界的分割,同時體現在其與外部世界的割裂。勃魯姆頓親眼目睹了父親,這位印第安老酋長在失去家園造成的精神痛苦的侵蝕下,終日惶惶,酗酒,最終身亡的悲劇。而后勃魯姆頓孤身一人,背井離鄉地生活在瘋人院中,遭受瘋人院中以大護士為代表的“康拜因”大機器的管控。在瘋人院的生活時期,勃魯姆頓一直裝聾作啞,不與他人交流,這一行為成為其與外部世界交流的最大障礙。美國語言學家伊萊娜·斯卡里認為痛苦有著不可分享性的特征。創傷主體的痛苦無法用語言完整表述,而其語言功能受到了痛苦的破壞。創傷痛苦埋藏在勃魯姆頓的心中,這位印第安酋長用沉默將自身置于一個異化的空間,一個與現實世界斷聯的空間。
在《飛越瘋人院》中,博魯姆頓受創后的整體創傷表征,從其內心困頓到自我世界異化的過程,展現了個體在遭受創傷后的心理運作機制。
3 創傷根源:壓抑與沖突
肯·凱西投身于反文化運動中,用一種喧囂與張揚的方式抨擊著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資本主義工業化社會制度中的弊端,深刻擔憂人類在工業化文明的強烈沖擊之下的生存境況。
3.1 工業化制度的壓抑
肯凱西用精神病院展現工業化社會對機構的操控,并通過勃魯姆頓,這一因工業發展進程而被迫失去家園的北美印第安人,來譴責工業化制度無情的一面。酋長經歷父親死亡的重創后,生出了對工業化社會的恐懼,把這個吞噬其家園,充斥著各種機器新制度看成了“聯合機制”。酋長對“聯合機制“始終保持著清醒的認知,內心深刻感知它的力量與其操控人的方式。在精神病院中,病人們都受大護士拉切特的管控,內心恐懼其各種殘忍的管理手段,但酋長十分清楚,拉切特也只是“聯合機制”下的一員,甚至處于一個邊緣位置。
在精神病院中,大護士的管制方式就是工業化制度對人操控的微縮代表。大護士讓病人按照精確的時間表作息,如同機器的流水線作業,將病人們物化成為單向度的工業化產品,甚至不惜用安眠藥來達到目的。這種強制性生活,并不能真正的治愈病人的傷痛,而是用手段營造出病人們正處在趨于恢復的假象。這是工業化制度體系對個體個性的壓抑,標準化的管理過程削弱了一切個性化的存在,人類逐漸陷入一種生存困境,在個體本性多樣化與工業化制度單一化中掙扎求生。生存于這種困境中,如勃魯姆頓一般的人就成為了犧牲品,以邊緣者的身份觀察著制度下的各種病態人生。
3.2 異質文明的沖突
此外,異質文化相互交融時所表露出的沖突,致使酋長對本民族文化的認同感逐漸缺失。身為印第安人,酋長一直接受著貼近自然的農耕化文明,根植于土地之上,遠離機械化的喧囂。在工業化文明不可阻擋的發展拓張的大時代背景中,酋長游離在文化沖擊的間隙中,失去自我民族身份認同感,難以接受異質文明的管治體系。進而成長為異質文明沖擊之下的邊緣個體,失去在社會中與他人的聯結感,無法建立相互信任的親密關系。
勃魯姆頓渴望獲得一種認同感,可資本主義工業化社會的侵蝕,催使勃魯姆頓生出迷茫感與疏離感。自然是印第安文明中的重要存在,印第安文明崇尚自然和諧的生存方式,但工業化文明在最初拓張時,展現出的侵略性是與印第安文明和諧性的對立工業化文明以野蠻的手段侵略了美洲大陸,占據主流話語地位,美化其侵略性的本質,將一切異質文明異邊緣化。老酋長在拒絕簽署賣地協約后,慘遭毒打與指責,這是對其威脅的警示,其背后是強大的工業制度的權力體現,表露出其背后的同化性實質。這種同化性對印第安文明的侵蝕,使酋長陷入創傷的痛苦。創傷在勃魯姆頓的心里幻化成了“迷霧”,使其失去感知能力,游離于一切之外。這是工業化文明侵蝕之下,現代人心理特質的表征,也是受創個體在歷經抵抗與逃脫后,自身陷入的混亂無序。
4 創傷復原:重建與解脫
赫爾曼認為無助感和孤立感是精神創傷的核心經歷,“重獲自主權和再建聯系感則是復原的核心經歷”。
麥克墨菲崇尚自由,反抗被束縛的精神成為酋長迷茫生活中的一道光。勃魯姆頓在其影響下,開始正視過去的創傷。達涅利強調,發掘患者早期歷史的重要性,在于對患者的生活“改造其流動進程”,并恢復患者當下與過去的連貫感。酋長審視著過去創傷事件,意識到時間的流動性,對當下生活有了新的闡釋,不再認為自身的話語權應當沉寂,對自身身份產生了新的定義。由此,酋長主觀爭取曾經失去的自主權,在最后一次電擊治療時,只用了一天就從中恢復過來。
此外,重新建立與外部的聯系感對創傷復原有重要意義。在酋長創傷復原的過程中,麥克默菲引導其主動修復曾經破碎的信念,麥克默菲清楚地告訴酋長,“我發誓你是我見過最高大的印第安人”。而在此之后,麥克默菲的訓練讓酋長重新獲得了力量,變得強大。酋長開始積極參與這個世界,與其他病人交流,而那些困擾著酋長許久的迷茫感與疏離感為力量與信念所代替。最終,酋長沖破了恐懼與傷痛的禁錮,奮起反抗,奔向原野。
肯·凱西由此也為遭遇創傷的印第安民族恢復自身主導權,創造了希望。正視過去遭遇沖擊的歷史,審視自身地位的象征,找尋身份認同感,重建民族力量與信念,正是印第安民族需要經歷的過程。
5 總結
肯·凱西的《飛越瘋人院》表現出反文化運動的鮮明立場。印第安敘事者勃魯姆頓個人創傷經歷是北美印第安民族整體的微縮代表,酋長的創傷根源表露出肯·凱西對工業化進程中侵略性,野蠻性的批判。印第安文明與工業化文明碰撞,承載著印第安民族的命運。肯·凱西重提這段歷史,探究其創傷根源,為民族走出創傷陰影提供途徑。勃魯姆頓掙脫枷鎖,重獲自主權的過程,表明了創傷復原要創傷個體內部打破自我異化的世界,主觀建立與外部世界的聯系,才能獲取力量抵抗創傷痛苦,重塑自身。肯·凱西的《飛越瘋人院》為創傷個體尋求復原的途徑具有重要啟發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