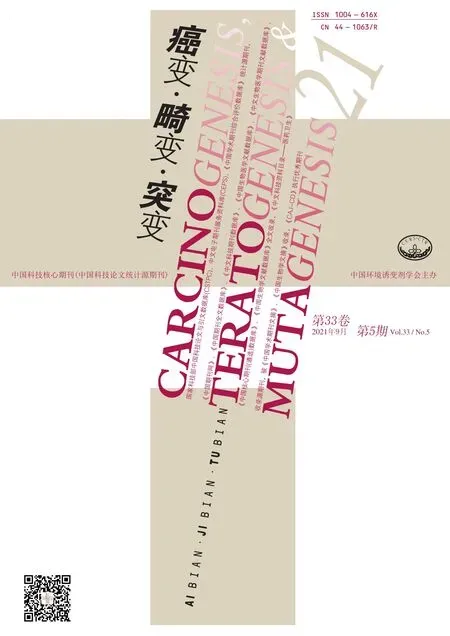抗氧化悖論真的成立嗎?
于衛華,孔德欽,龍子,劉瑞,李文麗,海春旭
(空軍軍醫大學軍事預防醫學院軍事毒理學與防化醫學教研室,陜西省自由基生物學與醫學重點實驗室,特殊作業環境危害評估與防治教育部重點實驗室,陜西西安710032)
抗氧化劑(antioxidants)是指可以清除自由基,從而減輕或防止體內氧化損傷的一類化學物質。抗氧化劑種類繁多,功效也存在差異。按其溶解性抗氧化劑可分為水溶性、脂溶性和兼容性3種;就化學結構而言,抗氧化劑可分為巰基類、酮胺類和多酚類;按來源可劃分為外源性和內源性兩種;按合成途徑可分為天然抗氧化劑和人工合成抗氧化劑;按作用方式差異則劃分為酶類和非酶類抗氧化劑。關于抗氧化劑健康效應的研究可以分為兩個階段。自20世紀60年代至90年代,是抗氧化研究的一個“黃金時期”,以國際自由基學會創始人TF-Slater教授為主的一批研究者先后揭示了氧化損傷在多種疾病發生中的關鍵作用,并研究使用抗氧化劑防治疾病。而真正將抗氧化劑推向神壇的當屬美國著名化學家萊納斯·鮑林,他一生中曾兩次獲得諾貝爾獎。鮑林提倡大劑量服用維生素C(vitamin C,VC),達到促進健康的目的。1977年,他指出每日攝入20~30 g(營養推薦用量60 mg)的VC,可將肺癌死亡率降低70%。同時,他還認為如果美國人堅持長期服用抗氧化劑,人群預期壽命會提高至100~110歲。在鮑林的影響下國際抗氧化研究和相關保健品市場也進入火熱時期,1996年《紐約時報》報道稱,約5 000萬美國人長期服用維生素,其中20%的人群每天用量超過1 g,這些保健品為美國每年貢獻約230億美金的GDP。然而,90年代以后,大量的人群前瞻性和回顧性調查研究顯示,服用維生素、硒和胡蘿卜素等抗氧化劑,不僅無法降低疾病風險,反而會增加某些疾病的死亡率。例如,美國和芬蘭的流行病學研究顯示,抗氧化劑對腫瘤治療無效。克利夫蘭醫學中心研究認為,服用VE(約400 IU/d)會使男性患前列腺癌的風險增加17%。2000年新加坡國立大學Barry Halliwell提出抗氧化悖論(antioxidant paradox)假說,即氧化損傷可導致諸多疾病,但在人群中給予抗氧化劑卻無明顯治療效果。自此,不少研究者對抗氧化劑的臨床應用價值持懷疑或否定態度,有關抗氧化劑的研究和產業開始進入了“寒冬期”。那么,抗氧化悖論假說真的成立嗎?抗氧化劑又是否具有實際臨床應用價值呢?本文就抗氧化悖論問題進行了深入探討,以期促進人們對抗氧化劑的正確認識和合理使用。
1 抗氧化悖論假說并不成立
大量基礎和臨床研究證實,氧化應激是導致機體損傷和多種疾病的“罪魁禍首”。活性氧(reactive oxygen species,ROS)可攻擊蛋白質、脂肪酸和DNA,并可通過調控多種基因的轉錄影響組織細胞功能,進而參與多數疾病的發生發展,且細胞和動物研究證實抗氧化劑干預可有效預防或逆轉多種疾病的發生和發展。事實上,許多基礎和臨床研究都涉及氧化損傷和抗氧化效應,但相關指標過于簡單,缺乏系統性和科學性。此外,目前國內外關于抗氧化劑鑒定篩選、用藥劑量、個體化用藥和聯合用藥等問題研究較少,且不夠科學合理。因此,本文基于長期的研究基礎,剖析了支持“抗氧化劑無效或有害”相關研究中存在的缺陷,提出抗氧化悖論假說可能并不成立,其原因總結如下。
1.1 抗氧化劑存在相對靶向性,單一抗氧化劑效果有限
機體內的ROS呈現多態性,包括超氧陰離子自由基(O)、過氧化氫(HO)、一氧化氮(NO)和羥自由基(OH)等,且不同自由基可相互轉化,形成鏈式反應。同時,抗氧化劑化學結構和性質迥異,在清除ROS時具有相對靶向性,如超氧化物歧化酶SOD和SOD可催化O轉變為低毒的HO,過氧化氫酶和谷胱甘肽過氧化物酶可有效分解HO;而非酶性抗氧化劑在清除ROS時也存在特異性,單一抗氧化劑往往無法清除所有類型自由基。海春旭教授在20世紀90年代提出“抗氧化復合鏈”理論,其基本觀點是體內的自由基和氧化產物具有多態性和相互轉化特點,而抗氧化劑(酶)的溶解性、作用部位和活性強度各不相同,但抗氧化劑間存在相互替代補充作用,共同構成抗氧化防御體系。基于微粒體模型和抗氧化研究平臺,海春旭教授帶領課題組對上百種藥物單體的抗氧化能力進行篩選和評價,成功研制了新藥“安體欣”,并在美國FDA成功上市。以往臨床和流行病學研究中常單獨使用維生素(A、C或E)、β-胡蘿卜素和硒等,這些物質自身抗氧化能力有限,只能針對某一類ROS,無法全面清除自由基,因此并未表現出明顯的疾病防治效果。然而,水果、蔬菜和中藥富含維生素、β-胡蘿卜素和硒,以及抗氧化單體如白藜蘆醇、紅景天苷、槲皮素、姜黃素和二苯乙烯苷等,經常使用這類物質可減輕機體氧化損傷,能有效預防心肌缺血、腦損傷和衰老。此外,VA和VC在Fe存在環境下會通過Fenton反應,生成活性更強的OH。許多研究者在選擇抗氧化劑時忽略了其靶向性,妄圖以一種或一類抗氧化劑清除所有ROS,結局自然是失敗的。基于這種理論得出的抗氧化劑人群治療無效結論也是站不住腳的。因此,臨床上應選取復方抗氧化劑,才能有效清除ROS,達到防治疾病的效果。
1.2 臨床上抗氧化劑用藥劑量是否恰當難以衡量
ROS具有廣泛的生物學效應,可調控細胞的增殖、分化、凋亡、壞死、衰老和惡性轉化等過程,而ROS劑量是決定其生物學效應的關鍵。研究表明低劑量ROS可通過Akt、Erk和P38等信號分子調控肝細胞靜息和增殖轉換,在肝臟發育和再生過程中發揮關鍵作用。過表達線粒體過氧化氫酶,可降低細胞內HO含量,并阻斷細胞由G向G期的轉變,證明ROS在調控細胞分裂中具有重要意義。隨著ROS劑量升高,可誘導細胞發生凋亡和壞死。因此,機體內ROS量并非越低越好,抗氧化劑用量也非越高越好,且部分抗氧化劑在高劑量時會產生細胞毒性。β-胡蘿卜素是維生素A(vitamin A,VA)的重要前提物質,也被認為是一種天然抗氧化劑。日本8萬名人群流行病學研究結果表明,男性吸煙人群每日攝入20 mg(推薦劑量2~7 mg)β-胡蘿卜素,罹患肺癌(特別是小細胞肺癌)的風險顯著增加。同樣,在果蠅食物中加入適量維生素E(約20 μg/mL),可有效延長其壽命,但如果VE加入過量(200 μg/mL)則會縮短果蠅壽命。二苯乙烯苷是從何首烏中提取的重要活性單體,低劑量時可清除ROS,在炎癥、衰老和神經損傷等疾病模型中具有顯著保護效果,但大量服用則會導致嚴重肝損傷。Wang等的研究也證實硒元素在低劑量時具有抗氧化作用,而高水平硒可加重氧化損傷,并導致嚴重細胞毒性。在腫瘤發生發展過程中ROS的作用更為復雜,低劑量ROS長期反復刺激,可促進正常細胞的惡性轉化以及腫瘤細胞的增殖;而高劑量的ROS則會殺傷腫瘤細胞。此外,動物和細胞實驗中ROS生成和抗氧化劑用量能夠很好控制,但人群研究中ROS生成水平難以掌控,用藥劑量也無法判斷。同時,服用抗氧化劑會被全身組織細胞吸收利用,真正在氧化損傷部位發揮作用的劑量更是無法估算。因此,臨床上抗氧化劑不當使用,可能會適得其反,加重氧化損傷和疾病程度。
1.3 部分氧化損傷及所致病癥具有不可逆性
氧化還原是細胞內最基本的生化反應,對于維持細胞正常結構和功能具有重要意義。研究表明,衰老、腫瘤和神經損傷等疾病模型及患者體內的氧化產物水平均顯著升高。例如,隨著年齡增長體內ROS可促進生物大分子與葡萄糖發生共價結合,形成穩定的糖基化終末產物AGEs,而AGEs的堆積可加速衰老,引起多種慢性疾病。而在致癌因素刺激下,ROS可修飾DNA形成8-OHdG和4-HNE等氧化產物,并進一步引起堿基突變和細胞惡性轉化,誘導腫瘤發生。在腦缺血再灌注和神經退行性疾病中,神經細胞受到自由基攻擊發生大量損傷和死亡,而機體內神經細胞不可再生,這也是臨床上神經損傷疾病救治困難的重要原因。由此可見,并非所有的氧化損傷都是可逆的,一些穩定的氧化修飾或損傷一旦形成,便不可恢復。但是,早期補充抗氧化劑可阻止氧化損傷,進而起到延緩或預防疾病的作用。這也解釋了為什么抗氧化可降低致癌因素導致的實驗動物腫瘤發生,但關于抗氧化劑治療成瘤動物和患者成功的案例卻鮮有報道。此外,百草枯暴露可引起機體細胞死亡,金屬蛋白會釋放Fe等過渡金屬,使用VC預處理可阻斷百草枯誘導的機體損傷,但是在中毒后再給予VC干預,則會誘發Fenton反應而加重損傷。因而,對某些不可逆性損傷或疾病來說,抗氧化劑可發揮預防作用,但治療效果卻欠佳。
1.4 臨床疾病機制復雜,氧化損傷并非唯一機制
氧化損傷與目前已知的多數臨床疾病息息相關。機體在病理、衰老和精神等因素刺激下,氧化產物生成增多,抗氧化防御削弱,導致ROS大量蓄積,最終引起組織器官的結構功能障礙。然而,氧化損傷并非臨床疾病的唯一調控機制,相關致病假說層出不窮。以腫瘤為例,雖然多數研究認可DNA氧化損傷是腫瘤的核心事件,但遺傳、免疫逃逸、促癌基因和端粒酶激活等也與腫瘤發生發展密不可分。同時,ROS對腫瘤的調控機制也較為復雜,可影響腫瘤細胞的形成、生存和轉移等一系列過程,在腫瘤的不同階段ROS的生物學作用存在差異。研究發現,早期合理補充抗氧化劑可有效降低DNA氧化損傷和基因突變,預防腫瘤發生;而在放化療時給予抗氧化劑可增強腫瘤細胞逃避免疫系統和放化療殺傷的能力,進而增加治療后腫瘤復發的風險。動脈粥樣硬化致病機制也眾說紛紜,除脂蛋白氧化修飾損傷假說外,還包括突變學說、受體缺失學說、細胞因子學說以及病毒學說。在衰老動物模型中,可使用抗氧化劑延長其壽命,但卻無法從根本上解決衰老和死亡問題,其原因在于衰老是一個多機制的復雜生命現象,目前提出的理論有十數種,包括端粒學說、密碼子限制學說和免疫退化學說等。因此,氧化損傷是機體的關鍵致病機制,但并非唯一,單純應用抗氧化劑可能無法解決衰老和腫瘤等復雜性臨床疾病。
1.5 炎癥與氧化應激相互依賴,單純補充抗氧化劑不能根除問題
炎癥是臨床上多種急慢性疾病的重要病理基礎,大量研究證實氧化應激與炎癥反應密不可分。一方面,炎癥過程可生成大量的ROS和RNS,是機體清除細菌感染和惡性轉化細胞的重要機制;另一方面,ROS可通過多種信號影響炎癥細胞激活和炎癥因子釋放。例如,2011年Nature報道證實線粒體ROS與巨噬細胞NLRP3炎癥小體活化密切相關。因此,炎癥反應和氧化應激彼此依賴,二者相互作用并形成惡性循環,是導致炎癥遷延不愈的原因。但炎癥反應和氧化應激具有相對獨立的調控系統,通過各自體系控制機體ROS和炎癥信號表達。炎癥過程中ROS生成途徑主要有3種:NADPH氧化酶、線粒體電子漏出和一氧化氮合酶(iNOS),ROS清除能力則受以Nrf2為核心的抗氧化酶系統;而炎癥因子轉錄調控則受NF-κB、COX、iNOS和NLRP3等信號途徑調控。因此,單純給予抗氧化劑雖然可清除炎癥過程中生成的ROS,但無法完全消除炎癥,最終仍會通過級聯反應生成ROS和炎癥因子。新加坡的一項臨床隨機對照實驗表明,服用抗氧化劑(維生素E,400 IU;維生素C,500 mg;硒,50 μg)可顯著改善肥胖兒童和青年人群的氧化損傷和肝功能紊亂,但對整體的炎癥反應并沒有顯著抑制效應。因而,氧化應激和炎癥反應既相互依賴又相對獨立的特性,是導致臨床上炎癥相關疾病使用抗氧化劑治療無效的重要原因。
2 抗氧化劑臨床用藥存在的問題
以往研究認為,ROS是細胞代謝的“垃圾”、引起衰老的“動因”、中毒發生的“扳機”、基因突變的“毒素”和疾病發作的“元兇”。近年來人們逐漸認識到ROS具有多種生物學有益功能,包括調控細胞增殖、分化、殺滅病原菌和調控心血管功能等。抗氧化和氧化應激相輔相成,氧化還原平衡是維持機體健康的關鍵。幾十年來,學術界對于抗氧化劑的功效褒貶不一,抗氧化劑曾一度被認為可治百病,攝入劑量越高越好。然而,自Barry Halliwell提出抗氧化悖論,許多學者持相反態度,提出抗氧化劑完全無效,甚至有害。在本文看來,這兩種說法都不夠客觀和科學,沒有正確認識抗氧化劑的價值。一方面,抗氧化劑并非萬能靈藥,部分藥物大量服用還可能有害;另一方面,大量基礎研究證實了氧化損傷的致病機制以及抗氧化劑對疾病防治的有效性,抗氧化治療疾病的思路存在必然的合理性。此外,由于利益驅使,許多保健和飲食行業商家宣稱其產品具有顯著抗氧化效果,可預防人類罹患疾病,甚至可治愈許多疾病,廣大消費者對于這些不確切的廣告信息也半信半疑。因此,目前關于抗氧化劑的相關研究和臨床應用比較混亂,臨床用藥中也存在一系列問題尚未解決,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一是抗氧化劑的鑒定與篩選問題。近年來研究報道的抗氧化劑種類繁多,效果存在差異,國際上也缺少統一的抗氧化劑評估鑒定方法。很多藥物可能并非真正的抗氧化劑,只是通過損傷修復等間接因素降低機體氧化損傷。二是抗氧化劑的個體化用藥問題。不同人群、不同個體、不同部位以及不同時期,機體氧化還原水平都有很大差異,盲目補充抗氧化劑是不科學的。三是抗氧化劑用藥方法問題。抗氧化劑的使用劑量可影響其效果,使用不當可能適得其反。由于氧化應激和炎癥反應的相互放大效應,針對炎癥疾病單純使用抗氧化劑難以根除問題。上述問題嚴重制約抗氧化藥物的研發和使用,只有攻克上述技術難題,并規范醫藥市場秩序,才能從根本上解決抗氧化劑臨床用藥的混亂。
3 抗氧化劑合理用藥的前景展望
目前,抗氧化劑的合理用藥是實現人類疾病防治和延緩衰老的潛在武器,也是困擾全球醫學界的重要學術難題。本科室在海春旭教授帶領下,在抗氧化研究領域取得重大突破,在國際上首次提出了“抗氧化復合鏈理論”,構建了抗氧化劑篩選平臺;基于微粒體模型、細胞模型和動物模型綜合評估藥物抗氧化特性,分析藥物對不同類型自由基(如O、HO、NO和OH等)的清除效果,并對其總抗氧化能力進行分級,成功研制了抗氧化新藥安體欣。此外,與中國科學院陳暢教授觀點一致,本文認為抗氧化劑的使用不能一概而論,要遵循精準抗氧化的“5R”原則,即在用藥時要考慮ROS的存在種類(right species)、生成劑量(right level)、時間分布(right time)、空間分布(right places)和作用靶點(right targets)的差異。以往研究中,抗氧化劑對疾病治療效果不理想,可能多數是由于忽視了精準抗氧化的重要性。值得注意的是,食物和中藥中存在多種抗氧化單體,在多種疾病模型中顯示出良好的防治效果,盡管目前對其功效認識和研究還不夠完善,但相關產品開發應用的前景十分廣闊。未來抗氧化藥物的研發離不開氧化還原的精準檢測,準確評估生理和病理條件下機體氧化還原狀態,并在此基礎上遵循5R原則開發高效抗氧化劑。基于多年研究成果,本文主張在臨床疾病治療中按照精準化和個體化用藥原則,采用復方抗氧化劑,并聯合使用抗炎藥物和其他特效靶點藥物,才能實現根除炎癥、防治病變和延緩衰老的目的。綜上所述,抗氧化劑應用前景廣闊,但合理用藥問題任重而道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