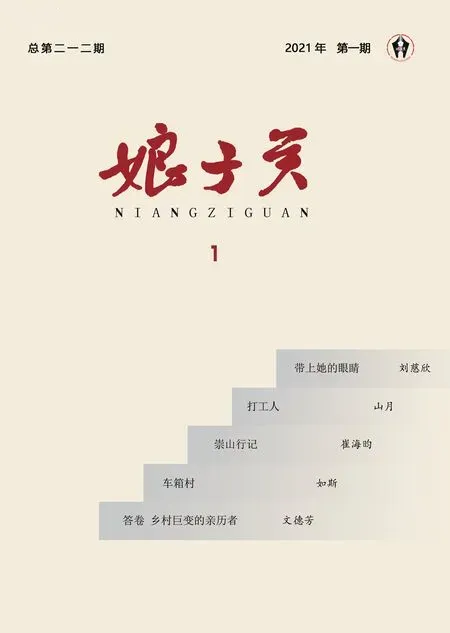崇山行記
崔海昀(臨汾)
天光映亮麻紙窗的時候,村子便在雞鳴風唳中醒來。東邊逶迤的山峰,形成三面合圍的態勢,把起伏的丘陵、廣袤的田野攬入懷中。《山海經》記載,山的名字叫“崇山”,“崇”者山之宗也,形義高大巍峨,至高無上。晉南大大小小的村莊靜落在山的環抱中,綠樹成蔭、炊煙裊裊,成為褐色土地上生動的點綴。居住在村莊的人們,一出門,便能看到火紅的大太陽從東面主山峰的塔頂升起來。晨光里的崇山先祖總會扯起嗓子高喊一聲:“下地干活了!”他們含哺鼓腹,擊壤而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多少年多少代,崇山人在日升月落、季節變換中,使自然、種族瓜瓞延綿,星火不息。
節氣
春種一粒粟,秋收萬顆籽。
一粒種子的輪回里,記錄著日月運行,時序更替。春播秋收,夏耘冬藏,這樣一個簡單的季節時令,不知經過多少次駐足田間,遍訪黎民,苦苦求索。
種子落地,吐露綠芽,一派豐收在望。奈何一夜北風,冰封大地。撒入泥土的種子,顆粒無收。先賢體恤民之疾苦,憂民之憂,褐衣疏食,探索著自然與生命的奧秘。《尚書·堯典》記載,“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羲和櫛風沐雨,經歷了怎樣艱辛的觀察、探索,在時日的循環里,密切關注著季節里的點滴變化,測定日月星辰的運行規律,為天下蒼生尋求、制定計算時間的歷法。
春雨驚春清谷天,
夏滿芒夏暑相連,
秋處露秋寒霜降,
冬雪雪冬小大寒。
暮雨晨風里,這回蕩在東山腳下的二十四節氣童謠,蘊藏著人與天地宇宙對話的密碼。季節的輪回里,裹挾著風雨、耕耘、播種、收獲、繁衍、愛戀,演繹著倉廩實而知禮儀,衣食足而知榮辱——
那位宵衣旰食的先賢,看到子民們順應自然萬物之規律,尊時勞作,五谷蕃熟,穰穰滿家,該有多么歡欣鼓舞。
我田既臧,農夫之慶。
在東山的月光下,在豐收的谷囤旁,一場天地狂歡盛大啟幕。鼉鼓逢逢,蒙瞍奏公。鼉鼓、石磬、土鼓奏出大地深處渾厚、古樸的樂章,崇山深處也一定傳來悠長回響。“樂者,天地之和也;禮者,天地之序也。”禮序人倫,樂移風俗。在歡慶的人群里,先賢一定載歌載舞,與民同樂。
“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云。富而不驕,貴而不舒——”他的身旁,可有一位翩翩起舞的妙齡女子,向他投去欽羨的目光?月光融融,遍地清輝。月光下,可曾演繹一段地動山搖的傾世之戀?他們,一定被這山里的清風明月滋潤過,滿山的草木,因此有了生命的靈性,在無涯的時空里搖曳生姿、脈脈含情。
清夜無塵,月色如銀。崇山的黃土在歲月里漫過,滄海桑田,積沙成丘。生于斯長于斯的吾鄉吾民,尊時而作,從容不迫,并不知道腳下這片土地浸含著多少關于文明與愛的密碼。
吃著崇山里的五谷,在每個節氣里汲取著大山里的草木氣息。立春了,吾鄉人叫“打春”,有趕著耕牛下地干活的漢子,揮起皮鞭當空一甩,清脆悅耳的聲音便在空里繚繞。鞭打耕牛,開啟了春播秋收的又一個輪回。山綠了,雨水多起來,田里一片水汪汪的禾苗,蛙鳴聲此起彼伏。
“清明前后,種瓜點豆”,隨著農事活動來臨的,還有一個重大節日——上墳祭祖。清明和其他的節氣不同,按照二十四節氣的平氣計算結果,是唯一按照陽歷定日子的節氣。
清明前五天,是吾鄉上墳的日子。經冬的麥田里,麥苗返青挺立,老家的說法,叫麥子“起身”。一想起這個詞就偷著樂,吾鄉有多么沾著地氣的語言啊!“起身”一詞,形象地說出麥子拔節生長的節點。
上墳那天,一個家族大大小小幾十口人,從天南海北趕回來,在青青的麥田里,站成肅穆的風景。
每到這個時節,回鄉祭奠時看到沿途這樣的情景,都生發出莫名的感動——枯榮之間,生命自有輪回,春風又綠,生生不息。
清晨的崇山腳下,初日照高林。大清早,本家祖先的墳前,擺滿了菜肴、花饃、酒、水果、糕點、紙錢、元寶、旌幡等供品,菜肴以紅、黃、綠、白顏色為主,講求色彩對比鮮艷;以雞蛋、菠菜、藕、五花肉為主要原料。
菜肴皆不放鹽,貴在色形而不在味。白生生的藕產自水中,中空多眼,意喻后代多出有心眼之聰明伶俐者。煮熟的雞蛋、菠菜、五花肉皆為陸產,雞蛋拿細棉線割開,便露出里面黃燦燦的蛋黃,意喻后代飛黃騰達;翠綠的菠菜意喻后代多出博學多才之人;五花肉帶著肉膘子,意喻后代彪悍、強壯,有一副健康的體格。
清明時節,院子里的桃花、杏花開得正烈,榆錢也在枝頭一嘟嚕一嘟嚕鮮嫩著,飄著淡淡的清甜氣息。祖母在蒸汽氤氳的灶間準備上墳的菜肴,做好了,放在竹籃子里,用家織的粗布手巾蓋好,牽著我的手,隨家族人向墳地里走去。在蒲公英、薺菜吐露花香的鄉間土路上,這種祭奠的形式,被吾鄉川流的人群一代一代傳承著。
最吸引孩童的,是上墳用的“蛇饅頭”“刺魚”等面食祭品。揉得光光堂堂的饅頭上盤著一條面塑小蛇,稱為“蛇饅頭”,小蛇的嘴里還吐著信子,獻祭完畢后供男性食用。魚形面塑者稱為“刺魚”,上供完畢供女性食用。身上長滿面刺、憨態可掬的刺猬者稱為“駒娃兒”,祭祖先用。另一種稱為“甜瓜”的花饃供走親戚上供用。
當沉寂數千年的漠漠黃土,層層疊疊,掀開遠古時期的絢爛文明,陶寺龍盤驚艷了世界。龍盤上,嘴里銜著麥穗的“龍”造型,是否就是早期王族的祖先神像抑或圖騰族徽?“蛇饅頭”和“刺魚”是否襄汾一帶現在民俗從陶寺龍盤圖案的傳承與演化呢?
住在胡同那頭的玩伴梨兒有五個姑姑,清明時節,每個姑姑給她蒸一個“刺魚”,“刺魚”的大小,根據這一年的收成及姑姑家的貧富而定。這一年的收成好,姑姑們的“刺魚”又白又暄,惹人眼熱。有個姑姑日子拮據,無論怎樣心疼侄女,蒸出的“刺魚”也會遜色許多。
梨兒美炫了!加上奶奶、姥姥蒸的,每年收到的“刺魚”有六七個,一時吃不了掛在墻上,風干了能吃好長時間。玩耍時,時不時掰下一塊來,分給同伴們,嚼得“嘎巴”響。經年的奔波后,那淡淡的麥香味,依然會帶著節氣的氣息和暖暖的親情,從長長的胡同里、從一群玩伴中間飄來。
四時行焉,百物生焉。
人誤地一時,地誤人一年。對自然的敬畏、對節氣的把握、對土地的熱愛、對五谷的珍惜,在吾鄉久遠的時空里源遠流長。
同鄉好友婷兒與我同在一個城市工作,閑暇時多有往來。結伴回鄉,與家鄉師友談談古老的民俗、悠久的人文,是我們最為傾心的事情。午后,街上風輕云淡,一杯香茗,幾位摯友,閑話家常,也是難得的愜意。
十多年前,在陶寺鄉東坡溝青翠無際的麥田里,中國考古人員有了一個驚人的發現——在陶寺遺址復原中,古觀象臺石破天驚、橫空出世。它由13 根夯土柱組成,呈半圓形。從觀測點通過土柱狹縫望去,崇山蒼茫,云遮霧罩。先賢們就從這些縫隙觀測日出方位,確定季節、節氣,安排農耕。
能想到考古隊當時的激動心情。在原址復制模型進行模擬實測,從第二個狹縫看到日出為冬至日,第12個狹縫看到日出為夏至日,第7個狹縫看到日出為春、秋分。“兩分兩至”,劃分了四季,指導了農耕。
古觀象臺就發現于婷兒家的麥田里。這個距今約4700年,陶寺遺址考古中重大的發現,證實了《尚書·堯典》上所說的“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的真實歷史背景與社會現實。我們驚訝婷兒家的麥田里竟能發現上古時期國寶級的建筑,進一步奠定了陶寺作為“帝堯古都”的地位,比世界上公認的英國巨石陣觀測臺還要早近500年。
第一次和婷兒去觀象臺,是個美麗的秋天。觀象臺邊的柿子樹上,一樹火紅的柿子。婷兒說,她們是吃著這棵樹上的柿子長大的,當時哪里會知道,自家地里,竟蘊藏著古老的秘密與驚天的文明。秋風從崇山的梯田里一層一層漫下來,碧空如濯,萬里湛藍。我們沐在一片清爽中。
婷兒跑過去摘發軟的柿子給我吃,蜜一樣流淌的汁液,直抵心扉。
節氣不饒人。這是吾鄉老輩人總結出的生活經驗。尊時而做,什么節氣安排什么農事,是吾鄉人的生活智慧。坐在村口大榆樹下的老爺爺,總愛念叨“頭伏蘿卜末伏菜”“秋分早,霜降遲,寒露種麥正當時”等農諺。從小到大,來來回回地聽,和節氣的親密聯系,漸漸熟記于心。
節氣里蘊含太多的秘密、太多的過往,已融入吾鄉的血脈基因當中。芒種時節的酷暑驕陽下拾過麥穗,秋風流云中摘過棉花,大雪時節的熱炕頭上喝過濃稠的熱粥,除夕夜“一夜連雙歲,五更分二年”的守望中迎接過新春的太陽。在季節的運行里,體會二十四節氣的美麗與多彩、耕耘與收獲。
從崇山下走出求學、打工的同鄉們,天南海北,散居各地。無論他們從事什么職業,無論身居何方,都懷著一份對四季的熱愛和對故鄉的眷戀。在自己的人生里辛勤耕耘,不負年華。回望故鄉,崇山腳下有一份永遠的情懷與底氣。
歲月忽已晚。
少年、青年一路走過,一腳踏進中年里,算是感受到人生濃濃的霜意。前路漫漫,生活無語,唯有順應天時,在二十四節氣的每一輪變幻中,感受天地浩渺,滄海一粟。
靜心安然,默默耕耘。
居舍
晨光熹微,鳥雀出巢。
吾鄉陶寺,也在這個當兒蘇醒過來。村前屋后,鳥語草香。阡陌小路上,下地干活、上學、趕集的鄉鄰們匆匆忙忙,去做手頭的事情。
下地歸來,抑或趕集串親,遇上了總會在路邊寒暄,聊聊節氣、收成、當下日子,以及尚未婚嫁的子女,末了,總會加一句:“閑了來居舍坐坐啊!”然后道別,各趕各的路。
居舍,就是居住的屋舍,家的意思。是啊,若沒有居舍這個安家的地方,哪有家的依附。
邀請來“居舍”坐坐,是鄉鄰間最飽滿、最見真情的邀約,“居舍”之間來來往往,鄉鄰之情一下子春水般漾起來。
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吾鄉居舍,大多是土坯房。村外一塊平地上,常見貴叔在打土坯。貴叔家里窮,一家人擠在一間破草屋里,因為沒有像樣的居舍,快三十了還沒娶媳婦。貴叔一刻也不停歇,很有節奏地搭模具、培土、打壓、摞放。一上午的時間,便打了兩大溜,長方形的土坯一塊塊摞起來,遠遠望去,整齊劃一,像當時的一種方型餅干。
土坯打好了,然后準備翻蓋新居舍的材料。一根一根的椽、檁條,從山間、河畔運回來,一片片瓦,從磚瓦窯滾燙的爐膛運出來,懷著期待,一樣一樣地歸置到位。這些料備齊整了,有時候需要幾年、幾十年,甚至漫漫一生的時間。心中有個念想,就一天天、一年年奔它而去。
舍,在人類漫長的進化過程中,大致經過了三個階段:深山穴居,依山舍居,尊山安居。構木為舍,標志著先民們狩獵采野向農耕生存方式的轉變,磚瓦房,承載著一種美好的生活理想。記得貴叔到底住進了新居舍,只不過幾年后了。雖茅檐低小,但麻紙窗里,飯菜馨香,炕頭傳來孩童的呢喃和一家人的歡笑。
歲月蒼茫,千年不居。世世代代吃著東山腳下的玉米、紅薯長大的鄉親,血脈里流淌著一份永遠的家園情懷。炊煙裊裊的古樸村莊,秋日小院的豐收情景,粗瓷大碗的家常飯菜,家人團坐的親切可觸,是心底里對家園的最初認同。先賢最初構造的生活理想,不就是這樣一幅住有所居,安居樂業的生活圖景嗎?
“居舍”是許許多多東山女子一輩子的活動場地,在這里生,在這里死,在這里傾其一生,又星辰寥落,歸于沉寂。
冬夜的燈光下,捧讀喬忠延先生的《晉南土話》。“‘居舍’就是居住的屋舍,也有把‘居舍’喚作居廈的。女娃長大,要嫁人。咱村里人說要改了。改了的女人居舍成了兩面:婆舍、娘舍。婆舍,是男人家里,頂頭上司是婆婆。娘舍,是原來的自家,那里有最疼愛自家的親娘,不管是婆舍、還是娘舍,都是居舍。”每每看到喬先生書中這段文字,帶著鄉土暖意的氣息撲面而來。從小聽大、熟悉親切的鄉土語言,在心里激起層層漣漪。
是啊,東山女子,嫁到婆舍,哪里會有自己的姓名,娘家是哪個村兒的,就叫她哪兒的。奶奶一輩子在居舍忙碌,居舍,就是她全部的人生舞臺。一家人的四季三餐、冬棉夏單,占據了奶奶一生的日月。奶奶娘家是東侯村的,同輩奶奶就叫她“東侯的”,直至終老,我們才在填寫神龕時,知道她的名字叫“芳惠”。透過字面,想奶奶當年也是沾著露水、帶著花香的青春女子,她生命的全部年華,都奉獻在居舍里。
居舍里,隱藏著絲絲縷縷、欲說還休的本土氣場、地域烙印。離家日久,一句鄉音,便可勾起遙遠的鄉愁;一聲老鄉,便可拉近彼此的心靈。
君家何處住,妾住在橫塘。
停船暫借問,或恐是同鄉。
唐代崔顥的《長干行·君家何處住》,傳遞出一種暖暖的同鄉情懷。水波浩渺的江面,一葉小舟,在風波里出沒。天際間又駛來另一條小船,遠遠看著,兩船相遇時停下來問一聲:“不知你家住在哪里?我家是橫塘的,或許我們是同鄉呢?”看似簡單俏皮的問話,卻蘊含著一種大情懷,有著田園、山水、居舍的大底色。蒼茫人生里,失意、孤獨常常占據我們的內心,同鄉是一種召喚,居舍是一種純樸的回歸,讓我們于滾滾紅塵中,忽然心底溫熱,想起生命最初的來處,想起家園的溫暖,培植人生的底氣。
山腳下一處處普通的居舍里,多少崇山兒女從這里走出,無論為文、為商、為官,都沾染著泥土和五谷的氣息,帶著崇山賦予的黃土般厚重、樸實的生命基因,處江湖之遠、居廟堂之高,都有一方水土培育出的居舍情結。
有的少小離家,千里之外,崇山的一草一木卻魂牽夢縈。及至歸來,一腳踏上山下這片土地,抬頭望見山頂的寶塔,才覺得回到了家園。“不見塔兒山,雙眼淚不干;見了塔兒山,始知到家園”,久違的歸屬感便會在鄉土鄉音的彌漫中漸漸深濃。
孩子曾遠渡重洋,出國留學。在獨自求學的日子里,微信上發來一句話:“離家這么遠,才更好地理解了家的含義。”一下觸到痛處。是啊,在居舍時,有熟悉的風物,親人的關愛,及至離開了,一下隔開了遙遠的距離,生活中所有的一切,都要靠自己去打理,這時候才想想原來家里的溫暖,卻已是山長水迢,遙不可及。就在這樣的離別與感悟中,一代代孩子成長著,走出居舍,走出家園,卻走不出父母濃濃的牽掛。
多年奔波,無非在城市一隅購一處“居舍”,讓漂泊的心靈有一個安放的地方。而忙碌的現代人,卻又向往在鄉下有一處房子,種花種菜,貼近自然。有了“居舍”,便有了一處安身之所,可以縱一葦之所如,凌萬頃之茫然。
深秋時節,幾位好友約回鄉一敘。吾鄉陶寺,作為蒼黃上古的帝王之都,崇山高聳、汾水映帶,萬壑含嵐,呈現出一派煌煌氣象。經歷了春的萌發、夏的熱烈,才蓄積了這滿目的山明水秀,秋色無邊。
在陶寺博物館里,出土文物板瓦的出現,不由讓人眼前一亮。心頭閃出的一束光里,浮現出遠古歲月里居舍儼然、男耕女織、芳草鮮美的生活圖景——先賢古人,在遠古時期就已經制造出了“目前中國最早的屋頂裝飾材料”板瓦,并用它建造家園。一片小小的板瓦,讓中國人用瓦的歷史提前了一千多年,并在這千年的歲月里,為吾鄉吾民遮風避雨,居家安舍。
“居舍”間穿行,如穿行在歷史的時空里。站在山上望去,山腳下一座座村莊、一處處居舍,在秋光下明凈恬淡、素樸自然,如千年歲月的一個個音符,彈奏出古老、遼遠的回響。
土陶
秋陽疏朗地照著。
山腳下土墻壘的農家院里,窗臺上大多放著幾個灰頭土臉的家伙什——陶罐。罐子里盛放著五谷雜糧,也盛放著腌菜、草藥等莊戶人家瑣碎而平常的日月。陶罐,盛著崇山人家一日三餐的溫馨記憶,留有一個家庭、一個民族一路走來的漫長印跡。
吾鄉陶寺,上古便是制陶的地方。回鄉時,村頭繁茂的大槐樹下,常圍坐一群人,聽村里的老先生講古:陶寺的陶,當然與制陶有關,寺,漢代以前,是官署之稱。站在一邊入神聽著,老先生的口中,吾鄉陶寺,上古時期就是管理制陶的官署。
風從田野掠過樹下,吹進巷子里,又從巷子里帶著柴火草棍吹出來,彌漫著神秘而迷人的氣息。講古老人早已化為崇山腳下一捧蒿草,聽故事的人也已風流云散,各處謀生。遙望巍巍崇山,歷經千萬年時光的洗禮,依然散發出圣潔的光彩。
漫漫歲月里,陶和崇山的先民們息息相關,成為代代相傳的生活物件和精神圖騰。
冬天的風冷冷地刮過村巷,清淡的陽光里,駕著兩頭大牲口的老農從東山里下來,車上,拉的全是陶。裝糧食的“老甕”、裝面的“面甕”、裝水的“水甕”,米罐、鹽罐,居家過日子的家伙什兒一應俱全。車進了村巷,甫一停穩,“呼啦”就圍了一圈人,挑挑揀揀,尋東問西。有的尋個腌咸菜的小甕,有的尋個細致一些的,裝面。車一頭兒,還有兩摞砂鍋,也引來大伙兒關注。鄉里人家,熬藥、燉菜,全憑這個土頭土臉的物件。不一會兒,一車陶器搶售一空。
寒風呼呼地在村巷里刮過,裹挾著漫漫沙塵。胡同里小爺家的院子里,炭火爐子上砂鍋“咕嘟咕嘟”冒著熱氣,飄著奇異的清香。掀開沙鍋蓋,自家腌的酸菜翻滾著,燉著鹵水點制的豆腐。豆腐白嫩、瓷實,吸足了菜里的酸香味,以及砂鍋里的泥土氣息,滋味綿長。下地或趕集回來,揺一碗出來,就著剛蒸的二面饃,稀里呼嚕下肚,渾身都冒熱汗。那滋味,真是爽啊!
陶是樸素的、粗糲的,放在居舍的某個角落,灰頭土臉,其貌不揚。用最樸實的黏土,摶成盛物的器皿,經烈火焚燒,便涅槃般脫胎換骨,堅固為盛東西的陶器。一口缸,盛水,便是水缸;盛米,便是米缸;盛菜,便是菜缸。
求學的日子里,母親把芥菜炒成辣鼻子的細絲,配上煮好的黃豆,裝在陶罐里,放在不生火的冷房里存著。回家時搛上一碟,便是佐餐的開胃小菜。離家時裝上一罐,整個冬天,都有這樣的辣菜絲陪著。身體偶感風寒,一碟辣菜絲下肚,五臟六腑都騰騰地冒熱氣,感冒也好了一大半。
陶來自吾鄉陶寺厚實的泥土,保留了山川河流的基因,和四周氤氳的地氣一脈貫通。米、面、豆子放在里面,仿佛還躺在大地母親的懷抱里,吐納之間,接收著源源不斷的地氣滋養。
老屋的八仙桌下,擺放著大大小小的陶罐,存放著農家散發著土地馨香的五谷雜糧。稱奇的是,這些陶罐里存放的物品,經年不壞。有一個陶罐其貌不揚,多年前的秋日,艷艷秋陽下,放上了從田里采摘、晾干的綠豆。農事忙碌,春播秋收。歲月的推移中,這罐綠豆從此淡忘在角落里,經年的風雨里,靜默一隅。及至多年后,忽然想起這罐綠豆,打開來看,色澤碧綠,飽滿如初,掬一把出來,甚至還能嗅出當年陽光的味道。
春天,崇山的暖陽溫煦地照在草木之間,桃李綻放,滿山含翠。走在村巷里的我,忽然怔怔呆立那里——井臺上,一個身著白衣藍褲的少年,正搖著轆轤往上打水,抬頭的那刻,眼里滿是暖暖的笑意。牛羊緩緩從身邊走過,風輕拂披肩的長發,一時醒悟,原來于時間的無涯中,沒有早一步也沒有晚一步,就在這一刻,我們相遇。
此后的人生,被這土陶一樣的愛滋潤著,溫暖、厚重,像巍巍崇山一樣,即使相顧無語,也滿含如海深情。
四季的輪回里,陶吸納著光陰,保護著光陰,也儲存著光陰。上古的陽光下,制陶業如火如荼。崇山的先民們摶土造型,烈火焚燒,制作成了樂器、陶盤等各色物件,這些物件承載著上古年月的印記,穿越千年時光,于晨鐘暮鼓里逶迤而來。
麥收時節,與祖父在田里撿麥穗,驕陽似火,干渴難忍。想要水喝,卻咽一下嗓子不敢張口。挨到地頭,終于撿了滿滿一布兜麥穗。此時夕陽西下,背著麥穗,與祖父在夕陽余暉里踏上回家的路。習習晚風中,感到了勞動的艱辛與喜悅。那時不知道,祖祖輩輩辛勤勞作的田野之下,埋藏著四千多年前瑰麗的文明遺骸——宮城、觀象臺、貴族居住區、倉儲區、手工業作坊區、天文建筑區、祭祀區等等,那是上古文明之火在漫漫歲月的起源,是一個民族的光華與榮耀。古城墻遺址的碳素年代,恰在堯舜時期,堯有唐陶氏之稱,那么吾鄉陶寺,亦即成了陶唐氏的管理城邑。
綿綿秋雨中,與外地友人回鄉參觀。沿著搭建起來的棧道,撐起傘徐徐而行。博物館的朋友引領著一路講解。陶寺曠野里規模空前的城址、與之相匹配的王墓等,使這里呈現著上古帝國的輝煌氣象。一件陶制扁壺上面的兩個朱文字——堯、文,將中國文字祖根又向上追溯了千年以上,成為比甲骨文還要早的文字。
每每此時,心里總會漾起十足的自豪感——九曲黃河,蜿蜒而過。吾鄉肥沃的土地上,華夏族先民創造了以龍山文化陶寺類型遺址,可追溯為華夏文明源頭之一。
被陶罐里的日月養育的我們,心中裝有崇山草木、更浸潤著鄉音鄉情。
秋風漸起,背陰的南墻根兒下,鄰家嬸子埋下幾個陶罐。把剛刨出的胡蘿卜、蘿卜,切去根部,碼放一邊;新摘的紅果、蘋果、梨子,一樣一樣、小心翼翼放進陶罐里,上面蓋上厚厚的石葉,再培上一層厚厚的黃土。經冬的雪霜里,陶罐保護著他們吐納自如,酣然入睡。
夏日繁茂,綠樹成蔭。回老家時,嬸子總會刨出這些果蔬,給我們帶一些回城。窗外艷陽高照,擺放在餐桌上的果蔬是怎樣的鮮嫩啊!冬天的風霜雪劍,沒有在它們身上留下任何痕跡,它們依然水靈潤澤、本色天然,保留著對這個世界最初的模樣。品嘗著這些果蔬,常常想,在歷經了人生的種種之后,還能持有一份對生活的初心嗎?還能有那份少年時期的熱情、鮮活與感動嗎?
“惆悵東欄一株雪,人生看得幾清明。”曾經土陶般原汁原味的生活,終究是一去不復返了;曾經深愛的人,也已隨著時光漸行漸遠。一路走來,看慣了春花秋月,潮起潮落,終于學會了自在隨緣,風輕云淡。
在亙古的時光面前,陶皿器具里,以最原始純樸的狀態,留存著璀璨的文明、流逝的光陰、人世的溫馨。夜闌人靜的時刻,遙望浩瀚的夜空,深感蒼茫而遼遠。人世間所有的歡樂與苦痛,能否收納于一罐陶器之中,吐納之間,化為耳旁的一縷清風,抑或崇山之上一輪朗朗的明月?
那些飽含陽光、風雨、憧憬,以及人世冷暖的日子,在年年月月的輪回里儲存、發酵,會釀成陶罐里時光的老酒嗎?
味道
霜降后,風落霜緊,萬物蕭條。
該是儲存冬蔥、紅薯、白菜和蘿卜的季節了。
走在山間灑滿落葉的小道上,能看到田野里翠綠的白菜地,以及霜打后耷拉著腦袋的紅薯蔓。各種菜蔬,由于品類特性的不同,在田野里呈現不同的狀態。它們被運回村子里,晾曬、下窖,成為漫漫寒冬和來年春天餐桌上的當家菜。家家戶戶的庭院里,主婦帶著孩子們忙碌著,頭上飄零的樹葉落在他們的衣服上、頭發間,四周充斥著藤蔓與菜葉的味道。
整個冬天,這本土菜蔬便氤氳在崇山人家的灶頭,散發出特有的氣息。以至于多年后,我以為最本色、最接地氣的飯菜,就是這新鮮的、含著泥土氣息的菜品味道。
日子平淡,便想調出些滋味。最原始的味道,便是酸。酸來自崇山里土生土長的五谷雜糧,是生活自然生發的味道。
有一種“水飯”,便是把大麥泡在水里讓其發酵,然后旺火熱油,放蔥姜蒜,隨著“滋啦”的響聲,把發酵的水倒入熗鍋,調和湯粥,飯菜里便有了一種特殊的酸香味。春夏時節食欲不好,不用吃藥,喝一碗這樣的湯飯,便會渾身冒汗,身子通透,胃口也隨之大開。“水飯”,是漫長、枯燥日月里的一種調劑,能品出生活里特有的滋味。只是經過歲月演變,這種“水飯”現在已絕跡了,偶爾從老一輩婦女的口中聽到一些,也是很久以前的山村小吃了。倒是一種和“水飯”很相似的“油粉飯”,在家鄉很火——把綠豆磨成漿讓其發酵,然后下海帶、白蘿卜等菜蔬,煮上剛搟好的面條,配上米醋調的涼菜,便散發出一種誘人的、獨具特色的風味。下班后,常與同事好友開車去吃,興沖沖來回奔波幾十里,就為這一口酸爽。
酸味派生出的,是一種叫“醋豆”的零食。自家釀的高粱醋,分“頭瀝”“二瀝”“三瀝”,“頭瀝”醋是第一次瀝出的醋,待貴客時,才會拿出來當調味品。“搟薄切寬,陳醋調酸”,說的就是這種醋調出的面條,很誘惑人的腸胃。“二瀝”醋逢年過節拿出來享用,也具一定的儀式感。平時吃飯調菜用的,便是“三瀝”醋了,味道有些寡淡,口味倒也純正。“三瀝”之后的醋,便沒了什么味道,家人們倒掉可惜,便把黃豆泡在里面,加些花椒、辣椒、食鹽,煮上幾滾,成為佐餐小菜。物資匱乏的年代,這些“醋豆”略微晾干放在口袋里,也是孩子們難得的零食。
初中時的一群同學,多年后在同一個城市謀生。閑暇時刻,多有相聚。說起小時候的吃食,大家不約而同想起了醋豆。那是貧瘠的年少歲月里難得的點綴,是共同的家鄉記憶。就是這些看似不起眼的味道,聯起了同學間的情誼,也喚起了漫長歲月里的縷縷鄉情。
所謂鄉情、所謂鄉愁,其實便是味道的記憶罷。
崇山人好客,有客人來,留飯是基本的禮節,還常常“設酒殺雞作食”。那年表姐生了孩子,跟著母親前去探望。坐在人家的廳屋里,聽主人在灶間忙活。剛在后窯里割的豆腐,彌漫著豆香氣,火爐上藍色的火苗正旺。燒好一鍋水,把剛殺好的雞褪毛,然后在鐵鍋里燉煮,滿院子都飄滿了香味。
多年后的深秋,和同事到表姐的村里采訪,說起當年吃的那鍋雞,還口齒生香。表姐見到我們,忙到旁邊的田里采摘,回來一通洗涮,生起柴火爐做飯。那真是難忘的美好時光。她在園子里拔回長著青翠葉子的罐兒蘿卜,這種蘿卜水氣大,鮮脆爽口。一刀切下去,兩面兒都是水津津的,簡單涼拌,便是一道鄉村至味。灶上鍋里煮著鮮嫩的玉米,蒸著剛從田里挖出的紅薯,滿院子飄起了久違的草木煙火氣息。揭開籠蓋那一刻,熱騰騰的蒸汽裹著香甜的氣息彌漫。多年后,還能嗅到歲月里一路飄來的柴火味道。
這些味道縈繞在記憶里,匯成了豐盈的生命之河。上中學時,學校組織去山里植樹。春三月,崇山上已是春意萌動,桃紅杏白。植完樹下山,已是日高人渴,此時多想喝一碗水解解乏啊。同學說,前面村子里,有她一家親戚,可以去歇歇腳、喝口水。走進親戚家大門,一個年輕的媳婦正抱著嬰孩,在院子里曬太陽。看到我們進門,忙把孩子放在炕上,麻利地招呼我們進屋,洗手和面。當時的農村,糧食金貴,也沒有什么菜。為不給人家添麻煩,我們喝完水便執意要走,年輕媳婦卻攔住不讓,說哪有親戚進門不吃飯的道理。只聽見灶間一陣叮當響,不一會兒,兩碗雞蛋蔥炒面就做好了。
人生中能記得住的飯菜,可能就那么幾頓吧。想起來,飽含著親切溫潤。和世界的某種聯系,就這樣被打通了。吾鄉吾民,用粗瓷大碗,把食物的本色本味奉獻給你,也呈現出樸實溫暖的情懷。以至于在心里汪出了一泓秋水,漾著鄉風鄉情,也映著草木古塔、長天白云。
陶寺出土的蒸食器皿——甗,可以追溯到漫漫4300 多年前。也就是說,上古時期,吾鄉就最早使用了蒸食器皿。蒸者,氣之上達也,食者,日之所需也,我們與先祖的心靈,透過這升騰的蒸汽,達成了千年的傳承。
四時更替中,山下勞作、生活的人們,一抬頭,便會看到崇山之上的千年古塔。相傳隋代有一千尺大蛇臥于山頂之上,便在此地建造了臥龍祠。歲月的風云變幻中,世代鄉民在這里祭祀神靈,祈求風調雨順、五谷豐登。穿越千年的炊煙,縈繞在家家戶戶的餐桌,寄托著他們居有所、衣食足的生活理想。
2019 年清明前夕,和婷兒趕個大早,回鄉參加國家考古隊和陶寺管委會組織的緬懷先祖活動。在古觀象臺前,等待太陽穿破晨霧,在第8號縫閃起一道亮光,升起在塔兒山巔。古老的儀式感和神圣感,在我們心中升起。
襄汾作協幾位朋友已在那里等候,活動結束便邀我們去縣城一家早餐店共進早餐,吃老豆腐、蔥花烙餅。
春林初盛。路邊青青的榆樹上,長出青青的榆錢,松軟濕潤的土地,各種野菜正在吐露芳翠,一片青潤。多年前云邱山筆會,和幾位文友歷經千難萬險,卻被一處懸崖攔住了去路。是作協的朋友,歷盡艱險,把我們拉上了懸崖。此后經年,很少聯系,卻有一份親人般的親切與信賴。人與人之間,最可貴的便是這份真摯無言的感情。
群山環抱,炊煙繚繞,屋舍儼然。許多個早晨,一直以為所有的黎明都是從東山開始的。所有的日出,都升起在崇山之巔。每次走在散發著泥土芳香的鄉間小道上,總有一種特殊的味道,從遠古、從居舍氤氳而來。
熹微的晨光照在街巷里,三三兩兩的孩童揉著將醒未醒的眼睛,前后呼應著走出家門,挎個籃子走下坡田拔豬草,或者提個水罐,撲撲踏踏跟在趕著耕牛、推著犁鏵的父親后面,往村外更遠處的田里走去,間或傳來一聲響亮的鞭哨,在村旁樹影婆娑的空里久久回響。村子便在各種聲音中活泛開來、水墨畫一般舒展開來,小路、屋舍、牛羊、青草罩在一片和暖的紅光中。
這是少年時期的崇山腳下。
人至中年,經歷了人生的霜落風緊,走在這一程山水里,更覺出了一份薄涼。品嘗著人生的千般滋味,唯有自渡心靈,方能達到彼岸。
猶喜柳宗元的《漁翁》:“煙銷日出不見人,欸乃一聲山水綠。”一聲“欸乃”,把人心中的一池水攪活了。吾鄉的山水,卻是什么喚醒呢?
仔細想想,是清晨下地的一聲鞭哨?抑或是豐收季節的陣陣鼓聲?每年秋分,瓜熟蒂落,五谷豐登,品類之盛,目不暇接。被譽為“豐收節”,去年這天,曾和同事下鄉采訪,在豐收的谷堆旁,在無邊的稻田里,感受豐收的喜悅。
那些古樸的、悠然的生活場景,以及天然、本色的味道,長久地珍存于記憶一隅,以至于在思想深處濡出一片鮮美濕地,生長四季莊稼,也喧響長河落日、鳥雀歸林。在某個夜闌人靜的時刻,能聽到汩汩的流水聲,以及彌漫的青草氣息。
這便是人之初生命的印記啊!是吾鄉水土滋養出的基因密碼。也許生命,便是崇山上穿越千年的一棵小草,歷經風雨輪回,依然眷戀故土。在崇山之巔迎日出,送夕陽,扎根腳下泥土,兀自生長搖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