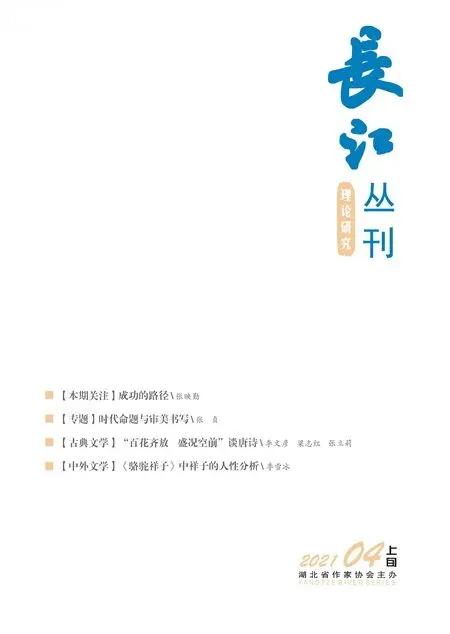病態心理的文學表現及其文本困境
——評高惠芬長篇小說《銀手鐲》
■桑大鵬 于紅新
高惠芬長篇小說《銀手鐲》描寫了一批心理疾患者的沉淪與拯救的故事。出版社在小說扉頁上標上“中國版《羅威的森林》”的推薦語。客觀的說,小說顯然遠沒有達到村上春樹《羅威的森林》的藝術高度,當然,其構思理念與敘事行進路徑確乎與《羅威的森林》有可比之處。
一、病態心理學視野下的性格塑造
《銀手鐲》敘述具有正常人格的林碧萱所關聯著的各色人類,他們分屬不同的階層,由于生活經歷的曲折與差異,他們或多或少都有不同程度的精神創傷、心理疾病,在病態心理學視野下探究人物的性格形成與人格類型,就成了小說的主要致思理路。大體而言,作者往往在平緩的敘事進程中突然安排情節斗折蛇行,讓人物心理在深層震蕩中得到本質性的凸顯,展現其創傷深重的內心及其與眾不同的價值取向,使人物性格在急遽的情節推動中加速形成,以此完成小說“塑造性格”的核心使命。此種性格表現方式有利有弊,具體分析如下:
林碧萱:林碧萱大體屬于缺乏雙親之愛、內心保守、用情專一、直覺發達、謹守人倫、不畏懼挑戰的知識女性,她是全書的中心人物,關聯著眾多線索,林的性格在種種線索的展示中逐步顯現,由于有關林的敘述節奏大體平緩,因此林的性格形成有清晰的脈絡,上述種種性格特征的形成有跡可循,既有情節的線索又有情節的實證。小說寫林的心理游走于病態心理的危險邊緣,通過尋找母親和愛人,拯救別人而達到自救,在愛的施與中獲得愛的回歸,最后復歸人格的正常,其性格形成頗具辯證否定意味。
鄧書來:出于建筑設計專業的鄧書來理性、冷靜而寬容,忠誠于愛情,雖被眾多少女矚目但絕不受誘惑。他被寧素珍囚禁在自己設計的樓房中,雖備受折磨,但被解救后還是寬容了自己的對手,正是這種寬容使自己免受病態心理的干擾,由于鄧書來心中無恨,因而他能逃出仇恨的折磨,小說為寫出鄧書來性格而設計的眾多情節隱然體現了無處不在的因果律。
舅媽(母親):林碧萱舅媽(母親)是徘徊在理性與情感之間蹉跎一生的矛盾女性。小說寫舅媽與裁縫師傅寧開濟的婚外情貫穿其兩次正式婚姻,生死孽戀的情節設計表明不倫之情主導了其全部心智,追求真情不得而導致一地雞毛,理性回歸之后又陷入對女兒深重的負罪感而出走,此種出走其實是一種逃避,逃避罪孽,逃避倫理的譴責。她通過劉婆婆將傳家寶銀手鐲留給女兒,意味著她要將她所珍視的人倫傳統假手于人傳承給自己女兒,而自己顯然沒有資格。這是一種自我認定,是理性的判斷。小說就在理性與情感的來回波動之間設計情節,使舅媽的性格獲得豐富的層次感。舅媽之病與其說是心理之病,不如說是不倫之情沖蕩婚姻倫理而被反噬的倫理之病。爾后舅媽不斷退守于道德的自我譴責之中,成為一個退縮于“道德與心理盔甲”之中的人。她是全書性格塑造最成功的人物。
寧素珍:仇恨是寧素珍的性格基調。小說寫舅媽破壞寧開濟家庭而被寧素珍仇恨,寫林碧萱無意間搶走女兒情人鄧書來而被寧素珍仇恨,寫她瘋狂報復鄧書來而流露仇恨。小說為了寫出寧素珍的仇恨主調,設計了系列情節:最初到林碧萱的服裝店打探;之后盤下隔壁董老板的服裝店作勢要與林碧萱競爭;知曉林碧萱的一切,二人發生沖突,林碧萱把寧素珍推到在地;女兒藍月的情人被林碧萱無意間搶走,寧素珍仇恨更深;出于報復她將鄧書來囚禁在樓中折磨,等等。一系列的情節設計將寧素珍以仇恨為主調的病態心理鋪敘到十分充分。
何幻香:雖然記者是這一知識女性的事業成功的標簽,但情執是何幻香的性格主流。她執著于與朱念真虛幻的所謂“愛情”,無視朱念真的根本背叛,反倒為這種背叛尋找理由,缺乏基本的理性,寬容而自欺欺人,這是一切陷入情執的女性的根本心理特征,最后從高樓一躍而下,用生命為情執買單。何幻香雖事業成功,但她走不出情執,其實是走不出自己。小說將何幻香的矛盾與病態心理表現到相當的深度。
如上人物的成功塑造,表明作者有清醒的使命意識:小說的核心使命就是塑造人物性格。至于文本的價值之思、情懷擔當、詩意想象、文化探索、哲學領悟等,都是在“性格”這一核心的精神凝注中才得以發生。小說正是在成功的性格塑造中才有系列的價值指向。
二、銀手鐲的表意價值
銀手鐲作為林碧萱母親的傳家寶,是小說的線索和焦點。小說共出現四個銀手鐲,劉婆婆手中的三個和失足女黃雨佳的一個。由于銀手鐲分屬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出場方式,這使銀手鐲作為表意符號領有了不同的功能價值。
(一)文本結構價值。作為小說的線索,銀手鐲是故事行進的路徑,在故事行進中,小說將劉婆婆、舅媽、林碧萱祖孫三代作為一個整體表現并關聯起形形色色的其他人與事,形成一個整合的結構。作為焦點,銀手鐲是小說灼照所有心理疾病的最后光源,各種類型的精神動蕩在銀手鐲所代表的深度安寧中被放大。
(二)倫理隱喻價值。銀手鐲代代傳承,它代表著古老的文化和傳統,在我們的文化傳統中,女性是被“塑造”的,是被文化的倫理價值觀念強力規范而生成的,其中尤其是貞操觀,是傳統女性人格生成的強大能量場。但舅媽的三個銀手鐲被劉婆婆保管著,這一筆意味深長,意味著舅媽自覺自己因為未婚先孕,沒有守住女性婚前應該保有的貞操而沒有資格把銀手鐲親手傳承給自己女兒,只能由自己姨媽代為保管和傳承,舅媽的自責本質是一種倫理的自責。
(三)心理灼照價值。舅媽的情執、自責、懺悔以及試圖以逃世的方式達到自救的矛盾糾結心理,在銀手鐲純樸、透明、安寧中被深度灼照,人物心理性格因此多層次凸顯,這是銀手鐲心理灼照價值的直接顯現;以仇恨為性格主調的寧素珍其仇恨心理也因銀手鐲的安寧平靜而被放大。
(四)精神救贖價值。因為銀手鐲的存在并被代代傳承,一種行將崩潰的倫理傳統在人的自責與反思中得以最終彌合。在銀手鐲的安撫中,舅媽從寺廟中自省歸來;林碧萱與鄧書來破鏡重圓;黃雨佳在寺廟中通過做義工修復破碎的靈魂。銀手鐲已超越了其物質性,以其承載的文化力量實現了精神救贖的功能。
三、作為小說文本的若干可疑之處
全書31萬余字,出版社標以“中國版的《羅威的森林》”,實話說,小說除了關注心理疾病這一共同主題有可比之處外,其藝術價值與《羅威的森林》存在相當大的距離。今從如下若干可疑之處討論。
(一)敘述。全書31萬字,鋪敘過長,語言泡沫過多,不夠精煉,31萬字的故事至多可在8萬字的大中篇內解決。全書圍繞林碧萱展開多線故事,有部分富余人物可以舍棄,譬如白風、黃雨佳等。白風沒有下文,有始無終,小說里不應有可有可無的廢人;黃雨佳突然出現,又突然消失,她的作用是用來引導林碧萱找到寺廟里的舅媽,但這種作用完全可用林的別的熟人引起,如果要通過黃雨佳寫出靈魂拯救的意義,則應詳敘,不應突然出現和消失。而且由黃雨佳帶出第四個銀手鐲,她的這一銀手鐲與舅媽的三個銀手鐲是什么關系?有何內在聯系?有何補充價值?這一系列問題小說里都沒有交代,這么看來有關黃雨佳的故事及其手中的銀手鐲就是小說的贅瘤了。
(二)故事結構。小說以林碧萱為中心關聯各種人物,構成放射狀人物關系結構,而不是圍繞林碧萱建立起來的多層環狀結構,這是其中某些單線人物的故事可以取消的原因。譬如前述林碧萱與白風、林碧萱與黃雨佳的關系故事,因有始無終,都可直接取消而使文本結構趨于凝練。小說固然也設計了白風與其男友、白風與鐘教授、白風與何幻香的關系,但他們的關系毫無情節展開,更無性格生成,沒有在他們關系中透視某種心理疾病的發生,又因白風的消失而戛然而止,小說最終還是回到單一的放射狀結構。
(三)社會背景。小說社會背景過于單薄。使得促成心理疾病發生的社會因素與生活節奏不夠充分有力,經濟的快速發展導致精神危機加深的社會背景沒有充分敘述。沒有寫出生活方式、傳統人倫與價值觀變異導致精神疾病發生的合理邏輯。人物關系和故事大多在舅媽的后院里展開,這是戲劇的場景設計,但《銀手鐲》作為小說卻無法容納更多更豐富的社會與文化資源用之于心理疾病的表現。
(四)對話。小說對話一般有兩種功能:1、凸顯人物性格;2、深化或引導情節轉向。以此兩種功能對標《銀手鐲》發現,文本對話多屬于廢話連篇,既不能凸顯性格,又不是深化或引導情節轉向,寡淡無味,無法引動讀者的性格之思或價值領悟。
(五)情節進程。小說無數次在描寫情節進程的關鍵環節突然旁敘,蕩開一筆,打斷情節進程。按小說的一般套路,蕩開一筆之后接續的情節應是情節的轉向,或情節新的開始,但小說的接續之處不過是過往情節的延續,那么蕩開一筆有何必要?
(六)性格。1、情節非性格內生。一般而言,小說作者固然可以設計人物的性格基調,但人物性格一旦形成,就有了自主性,性格自主運演,此謂之“性格邏輯”。換言之,情節與性格有其行進理路:當性格形成之前,還可由作家設計情節,指向某種預想的性格,但人物性格一旦形成就有其內在邏輯,性格決定情節走向,情節都是性格“內生”的。魯迅就在有關《阿Q正傳》的創作談中談到了自己的“不得已”——不得不將阿Q寫向死路,這表明魯迅是遵循性格邏輯的高手,故有阿Q這一經典形象的誕生。《銀手鐲》的情節對于性格而言卻多是“外設”,即多由作者設計情節,以此引導性格生成。譬如林碧萱與其閨蜜白風探訪燕臨河,白風突然將林碧萱拋在懸崖邊不管不顧,這一情節因何而來?有白風的性格內因嗎?是白風性格使然嗎?即使是出于閨蜜之間的仇恨,這一仇恨有來由嗎?如果是出于惡作劇,惡作劇有解釋嗎?小說一概付之闕如,使讀者頗涉疑思。2、鐘教授為何走向圣人?林碧萱答應了鐘教授的求婚,已開始拍婚紗照了,突然知曉了鄧書來的消息,于是不顧一切去尋找鄧書來,此時的鐘教授不僅心中無恨,沒有半點焦躁和惱怒,反倒協助林碧萱尋找鄧書來,他是傻子嗎?或是圣人嗎?既然是教授,多少總有點智商,可見傻子的判斷不成立,那就是圣人了!小說能不能寫圣人?當然能寫!金庸小說《射雕英雄傳》就寫了中神通王重陽,《倚天屠龍記》就寫了張三豐等圣人,但圣人自有圣人之跡,有小說情節鋪就的邏輯軌跡,讀者搜尋情節的蛛絲馬跡,自會覺得他們成為圣人合情合理。鐘教授從出場到向林碧萱求婚,始終是凡夫之姿,突然就有圣人人格了,這個轉折是如何發生的?有情節軌跡可尋嗎?小說并無情節鋪墊,讀者再次迷茫。
(七)銀手鐲最終功能不張。小說《銀手鐲》有一個目的:通過銀手鐲負載的人倫價值最終實現其精神創傷的彌合功能。此種功能確乎一定程度上實現了,林碧萱、舅媽、黃雨佳等人都在銀手鐲的敘事中得到人倫與精神安寧的回歸,此種功能在林碧萱的尋找與精神重建中層層凸顯,但既然銀手鐲有此精神彌合功能,并在舅媽、黃雨佳身上完美實現,那么與林碧萱關聯著的何幻香何以跳樓?寧素珍何以因仇恨失志?她們處于銀手鐲的價值傳統之外嗎?小說提供此種“之外”的資源沒有?通觀文本,并沒有提供此種“之外”的情節或思想資源。銀手鐲的表意價值至此萎縮。
(八)硬傷。1、兩次燕臨探訪的時間安排有誤。小說先寫林碧萱與白風陽春三月探訪燕臨河,僅僅四天之后,林碧萱又與鄧書來一起探訪同一條河,“按節氣來說今天剛好是寒露,‘九月節,露氣寒冷,將凝結也。’”——陰歷九月至少是陽歷十月了,如此,四天過了七個月!2、找到舅媽之后的春節時間計算有誤。小說寫林碧萱與鄧書來一起臘月三十通過黃雨佳在南方某小鎮寺廟找到舅媽后,當天開始周轉兩天回到中部小鎮的家,其間因過于疲累又睡了一天,按理應是新年初三了,但兩人醒來聽到四周鞭炮聲爆響,知道人們開始過春節了——“人們”與兩人一同誤認新年初三為初一了!
綜上,由于文本存在多處缺漏,顯得稚嫩。與村上春樹《羅威的森林》之藝術價值不具有可比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