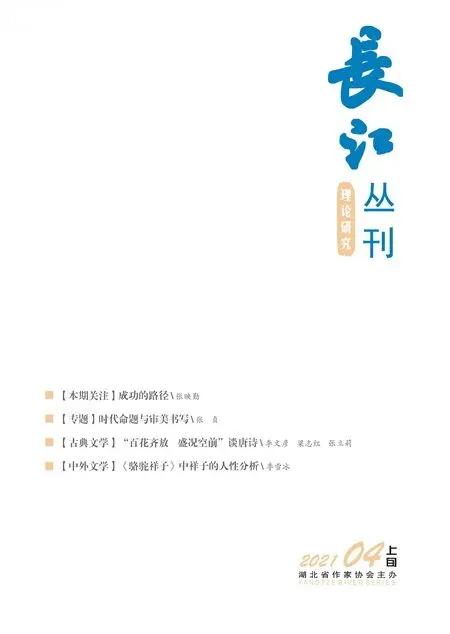掙扎在冬日
——讀《飄雪的冬天》
■江妍逸
雷默的《飄雪的冬天》圍繞著南田父親——一個大半截身子已埋進黃土的身患絕癥的老人的生死故事展開。小說開篇便是“這冬天怎么熬過去”的發問,定下沉郁的基調。老人終究在寒冬臘月里燃盡了生命的燭光,南田一家“循規蹈矩”地完成了他的身后事。
判斷小說好壞的標準在于其“容量”以及所帶來的思考想象空間的大小。《飄雪的冬天》是一篇極具生活況味的小說,作者將人性放在“生死”這個嚴肅的話題面前進行暢快淋漓的解剖,使一萬五千字左右的篇幅擁有了沉甸甸的巨大容量。小說主線清晰簡單,但作者的重點并不僅在情節構筑上,由主線所抽生出的枝枝蔓蔓,構成了一個宏大的為人性充斥的世界,這才是小說的重點、精髓所在。
小說主要有三部分場景,第一部分是父親去世前的一段生活,第二部分是父親去世后,親戚朋友們料理其后事的經過,最后部分則是所有事情告一段落后,家人圍坐小敘之事。在這些場景中,工作與家庭,婚姻與家族,親情與利益,生死與宿命等被作者悄悄攤開,輪番研討。
日益復雜化的社會生活使得主人公南田的生活重心呈現出多樣化。南田明知父親“命不久矣”,理應陪伴老人走完最后一程,卻仍然選擇奔赴工作崗位,回到妻、子身邊。面對母親提出的“打聲招呼”再走的建議,他也以父親難得安睡為由拒絕了。現實無法令人停下奔波的步伐,子女與父母間的情誼在逐漸復雜的生活內容里慢慢喪失地位。當父親的一生即將劃上句點,究竟是喚醒父親,與他做一個周全的告別,還是以不打攪其“安好”的借口逃避訣別,這是一個無解命題,而人世的艱難也常在一剎那之間。
男性在情感方面向來比女性來的內斂,父子之間流淌的往往是一種堅毅卻克制的情誼,而女性便常在這種關系中扮演涓涓細流。經歷數天的陰霾籠罩后,南田需要來自小家庭,尤其是來自妻子的慰藉。而南田與其妻秀萍,卻正在經歷婚姻的冷淡期。秀萍并沒有給他建構風雨后的溫馨港灣,無論是南田看望父親回家后,還是得知父親去世后,秀萍似乎僅處于一個旁觀者、邊緣化的位置,參與度、熱情度甚至不及丟失兒子的那對夫婦。文章末尾部分寫到丈夫兩兄弟與母親討論“人情簿”被秀萍撞見一事,秀萍的反應是“慌張”的——由此,兒媳與丈夫家庭的隔閡與疏遠,此種互為推阻的婚姻關系借助父親病逝的契機被置于臺面之上緩緩展現。
回歸到父親之死。在本應肅穆的葬禮之事上,道士班子的挑選問題令二叔和堂哥大起間隙;入殮時的形式化和粗魯草率的動作,仿佛“在合伙欺負已經不會掙扎的父親”;做道場這場儀式,在南田舅舅眼里只剩“這道場賣力的,很熱鬧,錢花得值”;火葬場的老人用火鉗搗碎頭骨和肋骨……微帶調侃的筆鋒,描繪出了刺痛卻真實的生活事實。除卻至親之人的沉痛哀悼,其余大部分參與者只將葬禮當做陪伴死者走完最后一程的儀式,或者一場利益糾葛、人情往來的機械化的形式。作者將親戚間的糾紛安排在葬禮這個背景下,又多了一層疏離的意味,與“無甚關系”的“那對夫婦”的態度形成鮮明對比。
死是令人沉痛的。老人逝世,家里年少的孩子卻不知傷悲,仍舊追逐嬉鬧,令人反添哀愁。父親臨走的晚上曾說“我這兩個兒子都送不到我的”,父輩養育子女一世,臨終時終究是孤身而去。南田的哥哥南華在父親火化時回憶起“十多年前,奶奶火化也是這個爐子”,此類簡單的敘述,卻都隱藏某種宿命般的不可訴說的神秘感。入殮時被錯拿的皮手套,那對夫婦中的妻子高喊的“別進火葬場,看到爐子趕緊跑出來,不要留在里面”,母親說的“你們爸爸死了還在為你們考慮”,聽完丈夫火化之后的腿骨跟老虎骨頭一樣粗壯后很是受用等諸多細節,又使“生”與“死”通過活人的寄托與緬懷有了一層說不清道不明的關系。
喪禮終于完畢,母子三人拿出人情簿,梳理完一系列人情關系后,母親哭了。身體陡然放松下來后,對丈夫的懷念,對人情交往的擔憂,對未來獨居生活的恐懼,使得母親的內心轟然倒塌。所幸這個飄雪的冬天里,還有熱心鄉人老鄭的雪中送炭,鄰居夫婦從始至終、盡心竭力的幫助,這些都使千里冰封的大地開出一樹樹梅花來。
小說文辭細膩,平靜克制,雖無大喜大悲之詞,卻常讓人在看似波瀾無風之處潸然淚下。通過冷靜甚至微帶戲謔的口吻,作者為我們緩緩鋪展開生活畫面,道出了人性的復雜和對生死的體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