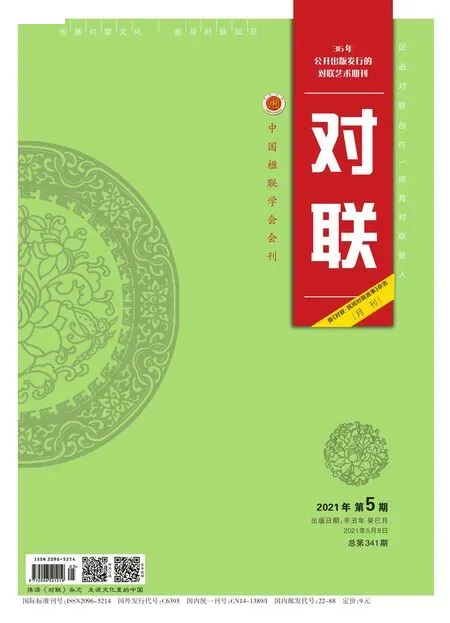淺析王安憶的創(chuàng)作觀及其創(chuàng)作實踐
文 || 吳鴻雁
王安憶的創(chuàng)作具有風(fēng)格多樣、敘述方式多變、題材廣泛的特點,她的作品一直是學(xué)界研究的熱點。本文從女性觀、愛情觀和生活觀三個方面入手,分析王安憶的創(chuàng)作觀,并結(jié)合其創(chuàng)作實踐來把握創(chuàng)作主體思想特征,以期對王安憶的創(chuàng)作觀和創(chuàng)作實踐進行較為深刻的理解和認識。
國內(nèi)對王安憶的創(chuàng)作研究,習(xí)慣從女性主義角度展開。20世紀80年代后,從女性主義角度分析王安憶的作品蔚然成風(fēng)。與女性觀一樣貫穿于王安憶作品的是她的愛情觀,解讀王安憶的作品,會發(fā)現(xiàn)其愛情觀與女性觀的聯(lián)結(jié)。作品《長恨歌》發(fā)表之后,王安憶的生活觀開始被研究者關(guān)注,他們普遍認為王安憶的作品書寫了不一樣的生活。
一、王安憶創(chuàng)作的女性觀及其創(chuàng)作實踐
20世紀80年代以來,國內(nèi)學(xué)者對王安憶女性觀的研究熱度始終居高不下,女性主義成為研究王安憶創(chuàng)作觀和創(chuàng)作實踐的重要視角之一。
(一)超然的女性觀,不拘泥于女性
王安憶在《從現(xiàn)實人生的體驗到敘述策略的轉(zhuǎn)型——關(guān)于王安憶十年小說創(chuàng)作的訪談錄》中表示,她反對單獨從女性的角度看待世界,在她對自己作品的解讀如《我是女性主義者么?》中也可以發(fā)現(xiàn),王安憶實際上表達出了一種超然的女性觀,她以更加開闊的視野觀察世界和人生,而不拘泥于女性。王安憶在訪談中提到:“我在面對女性題材時,往往思考的是如何擺脫純粹的女性目光。我希望在我的作品中獲得一種第三性視角,如此才能更加精確的把握女性生存狀況。”王安憶的《小城之戀》《雨,沙沙沙》《69屆初中生》等作品,都體現(xiàn)了其超然的女性觀。王安憶在訪談中談到:“《69屆初中生》里的雯雯就像是一個半蠶半蛹的東西,前半段與我的經(jīng)驗有關(guān)聯(lián),后半段我讓她脫離個人,脫離女性,表現(xiàn)的是大多數(shù)人的命運。”由此可見,王安憶有著超然的女性觀。
(二)反對男權(quán)中心,尊重女性應(yīng)有權(quán)利
王安憶的作品反對男權(quán)中心,尊重女性。男權(quán)指的是男人具有絕對性和權(quán)威性,男權(quán)主義把女性當作被動者。反對男權(quán)主義一直是女性創(chuàng)作的基調(diào),王安憶的創(chuàng)作同樣如此。王安憶作品中的女性雖然多是底層人物,但是她們的“人”的意識很強,堅守做人的底線,《長恨歌》中的王琦瑤便是突出代表。20世紀40年代,身為“上海小姐”的王琦瑤還未來得及享受上層生活,便被拋到了社會底層。1949年后,她辛勤勞動,無怨無艾,自給自足。有一次嚴家?guī)熌笇λf:“女人的生活就是為了男人。”王琦瑤回答道:“我偏要為自己!”改革開放后,王琦瑤雖然上了歲數(shù),但她燙頭發(fā)、逛舞會,打扮得比她的女兒還時髦。可見王琦瑤對活出女性風(fēng)采的執(zhí)著。
(三)反對西方女權(quán)中心,理解男性
西方的女權(quán)主義運動發(fā)展到后期產(chǎn)生了扭曲,由原本的追求男女平等逐漸演變成男女對立,女權(quán)中心漸漸成為部分女性主義者的綱領(lǐng)。王安憶對此問題在訪談中提到:“我們對女性主義的觀點是從西方傳過來的,我們實際的女性問題比他們殘酷得多。”她堅決反對西方的女權(quán)中心思想,堅決反對男女關(guān)系對立。“天是偌大的一個天,地是偌大的一個地,不管是男人還是女人,在這宇宙中都是渺小的,又何苦自相貶抑呢?”作品《長恨歌》中,王琦瑤有了康明遜的孩子,可康明遜迫于家庭的壓力無法認親,王琦瑤并沒有怨恨康明遜,只要求康明遜明白她的心。王安憶超越了女性的狹隘視角,既尊重女性,也理解男性。
二、王安憶創(chuàng)作的愛情觀及其創(chuàng)作實踐
愛情是文學(xué)的母題之一,王安憶的作品將愛情敘述作為創(chuàng)作基調(diào)。王安憶的作品中描繪了許多形式的愛情,有的愛情沉溺于人類自然性欲中,有的愛情充滿浪漫的幻想色彩,還有的愛情來自生活磨礪。
(一)自然本能的性愛
人們向往美好的愛情,很多文學(xué)作品中都有著熠熠生輝的愛情故事。不過,大部分的愛情作品對于愛情的描述都是精神層面的,而描寫性愛情節(jié)的作品反而被許多人認為是低級的色情文學(xué)。之所以會出現(xiàn)這種現(xiàn)象,是因為大部分人對愛情的解讀都是非性欲的、高層次的精神交流。然而,真正的愛情難以完全脫離性愛。王安憶表示:“如果寫人不寫性,是不能全面地表現(xiàn)人的,也無法寫到人的核心。”作品《小城之戀》中,一對文工團中的小青年在結(jié)為情侶后,因為沒有接受過性教育,面對性沖動時不知所措。一開始,他們互相咒罵、斥責(zé),在宣泄之后,他們反而更加激烈地糾纏,最終他們在性欲中越陷越深。“他們愛得過于拼命,過于盡情,有些疲倦,他們則更加狂熱地愛。”
(二)純粹精神交流的“柏拉圖”式愛情
王安憶作品中也有著“柏拉圖”式的愛情,即追求純粹的精神的戀愛。作品《神圣祭壇》中,項五一對戰(zhàn)卡佳的肉體沒有一絲欲念,他與戰(zhàn)卡佳進行精神交流后,欣喜地發(fā)現(xiàn)戰(zhàn)卡佳或許能將他從精神困境中解放出來。于是在一個風(fēng)雪交加的夜晚,戰(zhàn)卡佳抵達了項五一的精神深處,“他們腦袋里嗡嗡作響,臉頰發(fā)燙,激動又疲倦”。然而,在此之后,他們再也沒有相遇。綜觀王安憶作品,其中關(guān)于“柏拉圖”式的愛情雖然燦爛,但都是短暫的。可見,王安憶不認為這種愛情可以長久。王安憶在訪談中表示:“追求精神交流的愛情如同煙花,燦爛卻短暫。”
(三)恩義一般的愛情
王安憶的作品中還有一種愛情,即“恩義一般的愛情”。例如,作品《香港的情與愛》中,在香港打拼數(shù)年仍處于社會底層的逢佳,想要移民美國,因此她與美國商人老魏進行了錢色交易——與老魏同居。在交往過程中,二人之間雖然并沒有產(chǎn)生兩情相悅的愛情,但是卻充滿了一種恩義一般的愛情,這種愛情基于的是人的情義。二人分別時,老魏涕泗橫流,逢佳也難以自禁,熱淚盈眶。
三、王安憶創(chuàng)作的生活觀及其創(chuàng)作實踐
王安憶筆下的生活是瑣碎的,但又是審美的。再平常不過的生活小事,在王安憶的筆下都變得生機勃勃。以王安憶自己的話來說,她想表現(xiàn)出生活“恒長”的一面,歷史巨變和人生趣味也可以用吃飯穿衣來體現(xiàn)。因此,讀者在她的作品中可以欣賞到富有詩意的日常生活。
(一)習(xí)慣描述日常生活
王安憶一直對描述日常生活有著十足的興趣。作品《庸常之輩》中,王安憶對何芬日復(fù)一日上下班、波瀾不驚的每一天都進行了書寫;作品《流逝》中,歐陽端麗如何盤算家中收支、如何操辦一家人的吃穿等都被王安憶詳細地描寫了出來。雖然王安憶作品中的日常生活描述非常多,但是這并不妨礙她作品語言理性思考的發(fā)散。王安憶將對社會的理性思考和探索轉(zhuǎn)化成為了小說作品中的生活化語言,她沒有大張旗鼓地進行口頭控訴,更沒有歇斯底里的反抗,而是將堅決維護祥和生活的精神蘊藏在了日常生活描述中。
(二)將詩意帶入日常生活
王安憶描述日常生活時,尤其突出生活小事背后的人文情懷,吃飯穿衣、婆媳斗嘴、姐妹妒忌等,都充滿了人的生活情調(diào)。“家長里短是我們最熟悉的部分,當這部分進入審美領(lǐng)域,就有些生,但又似曾相識。”王安憶將生活小事寫得富有詩意,有學(xué)者評價其達到了“俗、瑣出韻”的境界。王安憶從生活中的男女之情、鄰里關(guān)系、日常生活等小事出發(fā),感受其中的詩意,從實際的城市生活中感受并且提升審美意蘊,在生活小事中發(fā)掘?qū)Ξ斚率澜绲娜滤伎迹@實際上便是王安憶創(chuàng)作中一種新的審美經(jīng)驗和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