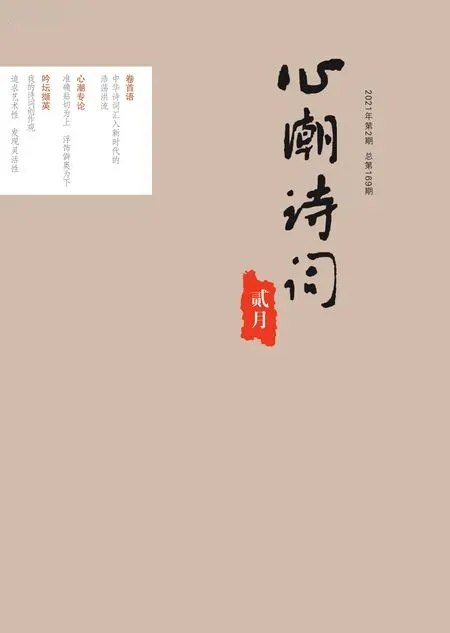我的詩詞創作觀
褚寶增
余自1985年于南京大學從許永璋教授學詩至今,逾三十五年矣。在學習、創作、教學、授徒過程中,對自己詩詞的創作觀,逐漸調整、修正,應該說已然穩定。茲稍做提煉,分四類八點,所余下者非不顧及,實恐葉茂而妨花也。具體為:總體上重立意且必從新,法度上求工穩也要渾融,風格上崇厚重偶炫機巧,內容上緣時事復尊科學。
詩詞創作最主要的一點,必須是以意或曰以思想取勝,先求“慧中”,再求“秀外”,古人于此論述頗多。唐杜甫《奉和嚴中丞西城晚眺十韻》:“政簡移風速,詩清立意新。”宋魏慶之《詩人玉屑》:“作詩必先命意,意正則思生,然后擇韻而用,如驅奴隸,此乃以韻承意,故首尾有序。”明王文祿《詩的》:“杜詩意在前,詩在后,故能感動人。今人詩在前,意在后,不能感動人。”清冒春榮《葚原詩說》:“不能命意者,沾沾于字句,方以避熟趁生為工。若知命意,迥不猶人,則神骨自超,風度自異。僅在字句求新者,猶村夫著新衣,徒增丑態而已。”作詩必須先立意,圍繞所立之意,調動詞句及施展一切藝術手段。
從新,既要要求精神從新,又要要求聲韻從新。精神從新,因人而異,難以概括,茲就聲韻從新重點闡明。《詩經》用周代當時的上古音系統,一千余年后的唐詩順應時代潮流改用當時的中古音系統,再一千余年后的今天我們也應順應時代潮流改用近現代音系統,今天近現代音系統的代表就是普通話。時間不可逆,潮流不可逆,詩是給今人和后人讀的,不是給死人和古人讀的。本人在1985年跟隨許永璋教授學詩時,以《平水韻》入手,后來逐漸留意古今聲韻的區別,2000年前后,暗中開始用既符合《平水韻》又符合新韻的新舊皆合的方式創作,難度自然增加,內心極度矛盾。終于在2002年下定決心,將用了十七年創作三千余首的平水韻斷然拋棄,用自定的《今聲韻》創作、授徒、教學。到2019年又十七年創作三千余首,因為2019年國家頒布了《中華通韻》,我開始用《中華通韻》創作(雖然本人反對“三鵝”的分部)。善于矯情者會說:“如果放棄《平水韻》,我們如何教孩子讀唐詩。”我的回答很簡單:“你去問問唐朝人,如何教他們的孩子讀《詩經》就可以了。”
格律詩顧名思義,就是講格律,“律”乃“法”也,“執法必嚴,違法必究”同樣適用于詩詞創作,合律者乃稱工穩。結構上起承轉合不易評判,聲韻上拗病與出韻極易檢測,可明言、可評判、可講究處當是律詩中之對仗。對句中上下兩句除結構、節奏、詞性必須相同或相近外,其意思、品類、時間、空間、隱顯、大小這六個維度,太近曰合掌,太遠曰隔斷。若以這六個維度計算數學中的相關系數,等于1者是徹底合掌,等于0者是徹底隔斷,在0.4與0.6之間為佳,如此既可張出空間又可保持張力。再有就是對仗時必須遵從“事對基于言對”的原則,如“此日六軍同駐馬,當時七夕笑牽牛”(唐李商隱《馬嵬》)、”窗迎西渭封侯竹,地接東陵隱士瓜”(宋石延年《金鄉張氏園亭》)、“聆聽論述黃山谷,覺似吞服紫雪丹”(褚寶增《吊念蔡厚示先生》)等。
渾融者,融會不顯露也。詩要渾然一體,非壘摞、湊泊、捆綁可得。欲渾融,氣脈通暢,雕琢無痕,“藝術的成功在于沒有人工雕琢的痕跡”(古羅馬奧維德),“到老全無刀斧痕”(宋釋了惠《木翁》),“巨斧無痕因匠力”(褚寶增《論詩絕句》)等,皆為此理。賈島善于推敲,可惜留有推敲的痕跡;李白何嘗不善于推敲,但沒有推敲的痕跡。能做到“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唐李白《經亂離后天恩流夜郎憶舊游書懷贈江夏韋太守良宰》)的效果,便可產生“捶字堅而難移,結響凝而不滯”(南朝梁劉勰《文心雕龍》)的風骨。
詩之厚重,非詩之文辭可生,非詩之技法可成,需作者真氣所注。詩之厚重必須仰仗詩外之工,岳飛的《滿江紅》之所以厚重,是因為岳飛以人格做擔保、以生命做抵押、以行為做渲染在支撐著。辛棄疾的詞多數厚重,其厚重之原因,其門人范開在《稼軒詞甲乙集·序》中說得十分明了,范開說:“公一世之豪,以氣節自負,以功業自許,果何意于歌詞?故其詞之為體,如張樂洞庭之野,無首無尾,不主故常,又如春云浮空卷舒起滅,隨所變態,無非可觀,無他,意不在于作詞,而其氣之所充意之所發,詞自不能不爾也。”家國、蒼生納于胸中,“文以載道”負于肩上,何愁詩詞不厚重乎?
小題目、小內容、小心情,不妨賣弄下機巧,機巧可生趣興,但不可常為之,如同小聰明。機巧分兩類,一曰詩意,二曰詩藝。“風自窗前學雨聲,雨聲翻轉又學風。何能夢里時常客,許我時常入夢中”(褚寶增《黃昏》),意機巧也。“同聽一夜雨,雨讓心生草。草長媚如花,花令心難老。夢總不及真,愿夢飛成鳥。又怕月光出,照見增煩惱”(褚寶增《生查子》),藝機巧也。
漢樂府講究“感于哀樂,緣事而發”,此原則從未過時。世界上根本不存在超然世外的詩人,入世者在世中,避世者同樣離不開世,否則無參照系何能避之,何況所謂避世者多是先入世后的無奈。不關心時事,不可能成為大詩人。少陵之所以被尊為“詩圣”,大半原因是其詩可為史,如同民族的才是世界的,現實的才是歷史的。有一種謬論,說詩是寫給自己的,與自慰何異。所以我的詩,從不回避現實,也從不掩蓋我的政治主張。
詩學不等于科學,可詩學不能違背科學,其實詩學還可借鑒科學。當詩學與科學產生矛盾,詩人一定會成為笑柄。“人間四月芳菲盡,山寺桃花始盛開”(唐白居易《大林寺桃花》),尊重科學,包含地理學與氣象學。“好山萬皺無人見,都被斜陽拈出來”(宋楊萬里《舟過謝潭三首其一》)利用科學,是物理學中的光學,與“陰陽割分曉”(唐杜甫《望岳》)原理相同。“葉垂千口劍,干聳萬條槍”(宋王祈《詠竹》),都上升不到數學的高度,根本就不會算術。我這首《浣溪沙·說月》,自覺是比較成功的嘗試,詞曰:“月在長空從未缺。缺因光線被攔截。情癡借此鬧糾結。 露面即該別掛念,含羞也算不失約。人應理性再多些。”隨同也產生了翻案詩的效果。
四類八點,只是梗概,若想既簡潔又全面,可道出我心中最大的偶像,就是杜甫。杜甫是我于詩學中最仰慕者,其魂靈在我的額頭,揮之不去,也不愿揮之。杜甫的成績與能力,就是我終生追求的最大目標。其目標是“上薄風騷,下該沈宋,言奪蘇李,氣吞曹劉,掩顏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久古今之體勢,而兼昔人之所獨專矣。……茍以為能所不能,無可無不可”(唐元稹《唐故工部員外郎杜君墓系銘》)。有差距,才有提升的空間,才有前進的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