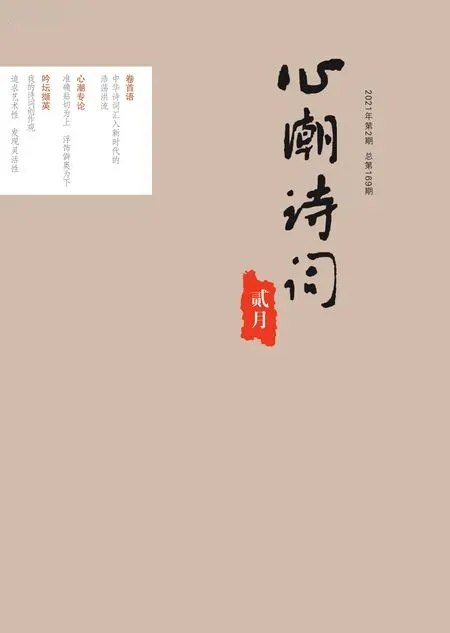淺談當代詩詞發展
喬 喬
詩詞創作從古至今都是文人墨客的一大標志性特點。不一定是學者,文學愛好者也寫;不一定能寫好,合轍押韻的就成;不一定有意義,表情達意了便是。這并非是否定,而是一種客觀事實。但寫詩詞者眾,真正叫得上姓名留得下經典的卻不多,大部分都沉默在了時間這無涯的荒野之中。大抵有的詩是千古絕唱,便成就了詩人;有的人為帝王將相,便留下了詩文。
在近幾年的當代詩詞研究中,已有學者提出了詩詞中應有現代性,而后又出現了關于“既要有現代性,也不能犧牲其古典性”的討論。在當代進行詩詞創作已經不再只是一種傳承,更是一種挑戰。而作為一種藝術形式,有三點是一定要去關注的,那就是其作者、作品和受眾。
一、“詩人”和“學者”
當代詩詞創作者較之古時,數量更多,兩極分化也更為明顯。而在詩詞的研究和創作過程中,首先要區別“詩人”和“學者”。并非是鑒別詩詞作品的好壞,也無褒貶之意,而是對其作者身份進行區分。
“詩人”和“學者”從字面上就有著明顯的分別。“詩人”是寫詩的人,而“學者”意為做研究的人,這里僅指做詩詞研究的人。在古代,能夠識文斷字的人非常有限,讀書是一件十分奢侈的事,年代越久遠,越奢侈。但也正因為這樣反而將詩人詞人的范圍控制在了真正有學識的人當中。同時也產生了“詩人”即“學者”的情況。當然,這里不排除依然有大部分的詩人由于不那么出眾,其詩文并未能流傳至后世。而當代社會在九年義務教育政策的實施下,大部分人都有一定的文化基礎。這對于詩詞本身的推廣自然是有益的,讀者的鑒賞水平理論上也應有所提高。對于詩詞創作來說,卻是降低了門檻。人人都知道律詩、絕句,人人都懂得詞牌名和押韻。因此“詩人”和“學者”之別就顯現出來了。
“詩人”以詩詞創作為主。當代“詩人”早已不只是某一個特定的群體。每一個人,只要愿意寫,都可以被稱為詩人。有人偶爾靈感乍現寫出了好句子,有人始終寫得隨意,連平仄也不循。龔剛教授在對當代新性靈主義書寫進行釋義時表示:詩是先有被閃電抓住的瞬間,然后再于沉靜中回味而得(華茲華斯《我好似一朵云獨自漫游》)。這一觀點同樣適用于古體詩詞的創作。當代詩人寫詩詞有著不可避免的問題,比如沒有靈感卻有指標時如何寫?沒有感悟卻有任務時怎么辦?又或者只有情緒沒有經歷的人寫什么?浮于表面的詩寫多了,也會有慣性。太多不可抗力擺在當代詩人的面前時,一首好詩就尤為難得了。何況好的表達、好的意象就那么多,前人早就寫爛了,想要寫出足以流傳的詩句就更難。
“學者”以詩詞研究為主。這一群體就更為特殊。有的學者只做研究,而有的學者同時也進行詩詞創作。做詩詞研究的人會在研究過程中學習到更多的理論知識,并對理論進行深挖。誠然,理論會使創作的進步更加迅速,卻也會為靈感戴上枷鎖。知道越多顧慮越多,學者在創作詩詞時更容易瞻前顧后。盡管早在清代的《隨園詩話》中就已有:“不過一時興到語,不可以詞害意。”而《紅樓夢》里在香菱學詩一段中,也出現了“不以詞害意”的說法。但知易行難,這也是各行各業“學院派”和“野路子”之間最大的差別。也有人說,這都是初學者犯的毛病,一個成熟的學者會知道如何用好理論,寫出好詩。
即使有了不拘于外物的詩人和成熟的學者,也并不意味著當代詩詞就能有更好的發展。作者固然重要,讀者卻也必不可少。
二、“讀者”和“作者”
與古代詩詞相比,當代詩詞還有一個問題,就是讀者少而作者多。前一章提到了當代詩人較之古代詩人應是一個更加龐大的群體。盡管質量參差不齊,但數量甚多。若是寫詩的便叫詩人,那除了各地詩詞學會成員外,還有多少不被大家所知道的小圈子、小范圍的詩人存在?
可讀者不是。古代由于娛樂活動少,書籍紙張貴,因而詩詞成了成本最低的娛樂活動。官方的詩詞有專人編纂成冊,民間詩詞也有機會在坊間傳唱。反觀當代,各樣的娛樂活動充斥著人們的生活。如果不是圈內人,能接觸到古典詩詞的機會實在不多,又何來傳唱。而詩人自己,捫心自問有多少當代詩人會去研讀當代詩人的古典詩詞?即使有研讀,卻也甚少,更多的時間也是放在了那些經歷過時間的洗刷所留下的精品上。因而當代詩詞真正的讀者群體,幾乎就只有各期刊的編輯,或做當代詩詞研究的學者。
這并不是人的問題,而是時代的問題。鑒賞詩歌對于讀者的要求是高過小說、歌詞等更加通俗的藝術形式的,而讀古體詩詞對于讀者的要求又要大過于現代詩。從鑒賞能力和閱讀時間上就攔住了大部分當代人。但這大部分當代人,卻正是當代社會最大的讀者群體。
一個人關在屋子里寫詩是閉門造車,一群人也是。現在有一個詞很有趣,叫“火出圈”,指的是某句話、某件事、某個梗的熱度已經從自己的固定圈子傳播出去,成了圈外路人也熟知的事。詩詞創作也一樣,只有群里人知道這首詩,只有朋友圈的人點了贊,過幾個月再沒有人記得。那詩詞創作的意義有多大?盡管大部分詩詞的宿命注定是淹沒在時間里,但至少,應該想辦法使它們留下。
近幾年越來越多的古代詩詞、現代詩歌被譜出曲、唱成歌,卻鮮有當代古體詩詞能“獲此殊榮”。其一,眾口難調,每個人的欣賞角度和評判標準不同。其二,與古人相比,部分當代詩人的詩詞韻味確實不足。古代文人自小所習便是文言,而當代人并不人人熟通白話,何況文言。其三,在資本占領市場的大環境中,另辟蹊徑并非明智之舉,風險甚大。這就涉及當代古體詩詞的傳播要不要造星,該不該造星的問題,這里不做深入探討。
被唱成歌的當代詩詞并不是沒有。《大宋提刑官》的主題曲《滿江紅》其歌詞就改編自當代詩人王凱娟的詞《滿江紅·狂風沙》。其改編也僅僅是在副歌部分將詞的上下闋相結合重新唱了一遍,并無太大改動。盡管學界對這首詞的評價褒貶不一,但它依然是一首火出圈的當代詞。自2008年《滿江紅》之后,并無新的當代古體詩詞以這樣的方式進入大眾的視線之中。但2007年前后卻涌現出一批古風原創歌手,有團隊也有個人。他們也均是以古代詩詞或當代古風詩入歌,并未進行古體詩詞的創作。
但無論是“詩人”“學者”之別還是“作者”“讀者”之量,都是限制當代詩詞進一步發展的客觀因素。最重要的還是當代詩詞應該有屬于自己的風格,學習前人固然重要,但一味的模仿,卻也會失掉了當代的特色。
三、“古代詩詞”和“當代詩詞”
詩,志也,從言寺聲。意為表達內心之志向,抒發心中之情感。詞,意內而言外,從司從言。本意是對于內在意義的外在表達,而詞作為詩歌的一種表現形式,與詩一樣,有著表情達意之意。詩詞最初的意義,便是用來表達心之所想、心之所感、心之所愿。歷經千年,詩詞早已成為獨立的文體,而不是時代的附屬品。
時代在發展,人們的生活也產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中華詩詞發展報告2018》中提到當年的討論焦點之一便是“現代性”。古體詩是否、怎樣具有“現代性”以及如何讓當代詩詞接地氣。誠然,古人今人都是人,有著相同的七情六欲,但表現形式定然有所不同。而這不同也使得詩人們在進行詩詞創作時有著不同的特點。
從創作角度上來說,差別最大的是邊塞詩。古代的邊塞詩偏重“我見”,而當代的邊塞詩偏重“我聞”。古代的邊塞詩人一般分為兩類:為建功或心之所向行至邊塞的文人,因戰事或戍守邊關后有感而發的武將。但這兩類詩人都是自己來到了邊塞經歷了戰爭,或在前線或在后方,但都親身經歷過、親眼見過、親自指揮過戰爭。因此他們對于戰爭的理解與感悟應是更為直觀也更為透徹的。而當代詩人,擅寫邊塞的就已不多。在當代中國數十年來相對和平的大背景下,戰爭離生活在城市中的每個人都十分遙遠。因此創作出的邊塞詩只得以塞外風光為主。塞外風光是什么?對今人而言它是沉淀的文化,是厚重的歷史,是掩埋的鮮血,是原始的風貌,它并不以單純的皮相之美而美,更多的是因其背后所承載的一切。但這只能被記得,無法被看見。能寫出“我見”的,永遠只有那些已經被塵封在歷史洪流中的人們。如今再寫,也只得用“憶當年”“憶往昔”“遙想”“遙記”等諸如此類的詞來回溯歷史。那些“金戈鐵馬”“烽煙四起”“血染山河”于今早已不復存在,“黃沙百戰穿金甲,不破樓蘭終不還”(王昌齡《從軍行七首·其四》)、“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飲琵琶馬上催”(王翰《涼州詞二首·其一》)也不再是如今詩人們所能體會的了。
從意象使用上來說,變化最明顯的也是生活氣息最濃厚的,就是閨怨詩。閨怨詩是女性視角下的產物,在傳統男主外女主內的背景下,應是最能反映古時日常生活起居的詩文。而日常生活起居也正是古代與當代差別最大的地方。“云中誰寄錦書來,雁字回時,月滿西樓”(李清照《一剪梅·紅藕香殘玉簟秋》)其中提到的“錦書”為書信,一般指夫妻間互傳的書信。在古詩詞中非常常見,但若是放在如今就顯得奇怪。有哪個夫妻會將一條微信一個電話能解決的事,非得寫信呢?哪怕是有這個生活情趣也并非常態,更不會因為等不到信而著急致使分隔兩地的二人思念倍增。可若是將“微信”“電話”等詞放進詩詞之中,卻又破壞了詩詞的古雅和含蓄。同樣被日常生活所淘汰的意象除了書信還有蠟燭。“何當共剪西窗燭,卻話巴山夜雨時”(李商隱《夜雨寄北》)中雖是以剪燭形容深夜秉燭長談,其意并不在燭,但放在今日卻也不再合適。幸而“燈”之一字倒還古今通用不顯得過分違和。
和“古代詩詞”相比,“當代詩詞”應該有更多當代的氣息。如今的讀者可以從詩詞中了解和學習歷史與文化,看見曾經的人文風貌。畢竟詩本身就是用來記錄民風民俗表達思想觀念的。可當21世紀成為“古代”的那一天,后人是否還能從詩詞中了解今時今日的一切?還是說只能通過其它的材料,如影視作品、小說、散文去了解?可喜的是已經有學者開始實踐并在大學的課堂上將此種嘗試延續了下去。
結語
詩、詞作為文學體裁,自古以來就不是少數人的娛樂,而是屬于整個中華民族的珍寶。為了推動其發展和傳承,今天的詩人們要做的,不只是寫好詩,還需要以開放的態度去接納更多元的融合。文化沒有圈,人人都可寫詩詞,都應該被鼓勵。讀者沒有界,人人都該讀詩詞,詩人更要閱讀。詩詞沒有代,代代都得有特色,融合古典現在。